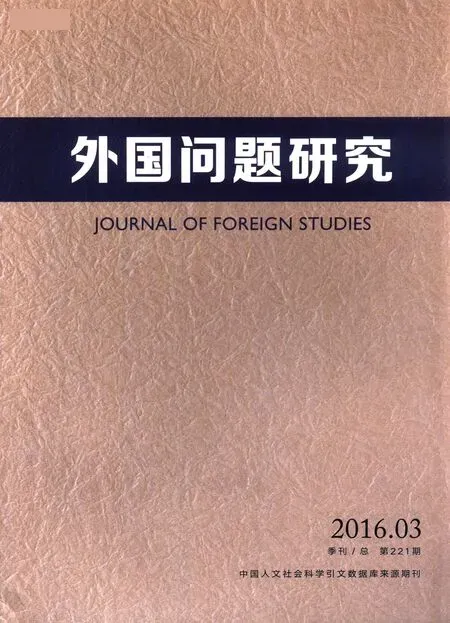立憲君主制時期埃及宗教政治認同復興的原因探析
謝 志 恒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450001)
?
立憲君主制時期埃及宗教政治認同復興的原因探析
謝 志 恒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450001)
立憲君主制時期,埃及經歷了官方自由民族主義認同的衰落和伊斯蘭政治認同的復興,二者呈現出內在的邏輯承繼關系。體現自由民族主義理念的立憲政府無視或有意模糊世俗與宗教的沖突,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認同定位危機。同時,自由民族主義政黨無力維持憲政的有效平穩運作,曾經熱情追隨自由民族主義的知識青年在困頓的現實面前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認同。這些自由民族主義衰落的跡象揭示了這樣一個社會現實:埃及仍然是一個傳統思想觀念占主導的社會,自由民族主義并沒有成為共同體普遍的政治認同,自由民族主義者的合法性在于他追求民族獨立的目標,由于他自身的階級局限,他不能實現國家獨立的最終目標,也不能解決社會所面臨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而這也是伊斯蘭認同復興的原因。穆斯林兄弟會在本質上是一個用改革了的伊斯蘭思想為指導,暴力反抗各種失敗意識形態和自由民族主義政權統治失敗的民眾政治組織,它的成功是憲政體制失敗的結果。
埃及;立憲君主制;自由民族主義;宗教政治認同
1923年至1952年的立憲君主制時期是埃及世俗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在政治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也是宗教政治認同重新興起的關鍵時期。自由民族主義在埃及經過整個19世紀的緩慢孕育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幾年里達到了發展的頂峰,但在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十年的高漲期后就走向了危機和衰敗,它的衰敗過程與宗教政治認同的復興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回顧世俗民族主義的興衰有助于厘清伊斯蘭政治復興的原因。
一、自由民族主義的盛極而衰
自由民族主義*傳統意義上西方所宣揚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是對政府角色的限制和對個人主義及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視。此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在當時的埃及并不存在,這里使用的“自由”主要是指埃及用世俗的國家觀念和理性人道價值重塑社會的嘗試。的興起是埃及傳統社會秩序衰落、面對西方侵略控制的背景下埃及本土統治者試圖借用西化改革實現自強自立的結果。18世紀中期以來,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歐洲漸成世界主宰,固守傳統的奧斯曼帝國日益衰落,地方勢力坐大,中央的統治名存實亡。1798至1801年法國對埃及的短暫征服結束后,埃及確立了以穆罕默德·阿里為首的家族統治。為應對西方的擴張,阿里及其后繼者進行了一系列學習西方的富國強兵改革,以期抵御外來入侵,擺脫中央控制,實現永久自立。他們模仿西方的政治體制,發展面向市場的現代經濟,引入西方教育,建立新式軍隊,由此引發了埃及政治體制、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形態的深層次變動,開啟了埃及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但阿里的后繼者企圖依靠舉借西方資本實現歐化改革,鞏固家族統治,其結果是埃及政治、經濟和司法自主權的喪失,并最終在反抗失敗后于1883年被英國直接軍事占領,淪為半殖民地。
19世紀前的埃及無疑是一個傳統的伊斯蘭社會,人們普遍相信真主安拉是世界萬物的創造者,是社會秩序的制定者,安拉降給先知的啟示《古蘭經》是真理的來源,是穆斯林一切行為的指南。阿里家族的現代變革將西方的科學、技術、經濟、組織方式甚至是文化觀念引入了埃及,帶來埃及物質生活和社會體制的根本轉變,侵蝕了附著其上的傳統政治認同——伊斯蘭思想體系。同時,殖民地的命運打擊了阿里家族統治的權威,動搖了社會各階層順從其統治的社會基礎,促成了對現有伊斯蘭社會秩序的反思。伊斯蘭現代主義和自由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潮與運動正是這種環境中產生的。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伊斯蘭改革思想家賈邁勒丁·阿富汗尼及其學生穆罕默德·阿卜杜。阿富汗尼呼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宣稱宗教不應違背科學事實,伊斯蘭教應拋棄摒棄鄙視自然科學的陳腐觀念。*M. A. Zaki Badawi, The Reformers of Egypt,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78, p.21.他要求重新評估伊斯蘭教教義,重開創制大門,重返最初真正的伊斯蘭教精神。*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 Analysi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of Egypt, 1804—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4.阿卜杜同樣認為科學和伊斯蘭教并不沖突,主張穆斯林有權根據變化了的條件重新解釋伊斯蘭教法的規則。*哈全安:《中東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9頁。他在堅持維護埃及社會伊斯蘭教的本質特征的同時,允許接受世俗倫理中的有益成分指導社會和政治行為。*P.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2nd 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colson, 1980, p.195.總體上,阿富汗尼和阿卜杜的思想都是在堅持忠于伊斯蘭教啟示和教義基本原則的同時,倡導對伊斯蘭教進行理性的和科學的改革。但通過理性解釋《古蘭經》不僅本身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而且也招致了傳統宗教勢力的激烈反對,而他們希望改革伊斯蘭教使之重新占據社會中心地位的思想和主張也沒有得到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政治領袖的熱烈回應。隨著英國占領統治的確立及其世俗化改革舉措的深入,以反對英國統治為目標的自由民族主義開始興起。
自由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是穆斯塔法·卡邁勒和艾哈邁德·魯特菲·賽義德。作為自由民族主義的先驅,卡邁勒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定位自己認同的政治社會實體,他的全部興趣旨在培育和宣揚民族主義,傾向于從愛國主義的角度對待民族主義,但不認為它與伊斯蘭教相沖突。*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87.在此基礎上,他倡導埃及人超越宗教的廣泛政治聯合,反對英國的占領,建立獨立的國家。*哈全安:《中東史》,第521頁。同樣出于民族主義的需要,他提出了制定憲法以防止自由與正義受到人為損害的主張。*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89.魯特菲·賽義德作為埃及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將民族主義從伊斯蘭現代主義中剝離出來,并賦予其堅實的內涵。他借助亞里士多德、盧梭、洛克、邊沁和斯賓塞所闡發的自由社會政治思想來建立一套民族主義思想體系。魯特菲十分崇尚歐洲的兩個觀念,即理性能改變社會和人類向往自由。這使得他認為能夠建立一種用理性統治的政治體制,并將實現個人自由作為追求高尚民族生活的愿望。他不認為獨立本身是一個目標,而只是實現高尚民族生活和責任公民意識的手段。獨立民族存在的主要品質是個人自由、有限政府和憲政權力。*P.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p.242.
在卡邁勒和魯特菲宣揚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十年后,埃及爆發了1919年大革命,社會各階層團結在民族主義組織華夫脫黨的周圍同英國英勇抗爭,迫使后者于1922年宣布埃及獨立。隨后頒布的1923年憲法,開啟了埃及立憲君主制時期,也標志著自由民族主義的思想達到了發展的頂點,它的原則集中體現在1923年的憲法條文中。該憲法宣布埃及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主權國家,其主權不可分割、不能轉讓,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取代了傳統的烏瑪主張。憲法還宣稱埃及人不分種族、語言、宗教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廢除了伊斯蘭教法中將社會成員區分為穆斯林、迪米和異教徒的原則。憲法規定,所有權力源于人民,議會擁有完全的立法權,不受現行伊斯蘭教法的任何限制,規定公民享有人身、言論、集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些都表明了主權在民的現代政治原則和迫切脫離伊斯蘭教傳統信條的傾向。*1923年憲法英譯本全文見“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Egypt,” Current History, vol. 25:4 (Jan.1927), p.532. 關于憲法的概要介紹請參看Norman Bentwich, “The Constitution of Egyp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3rd Series, vol. 6:1,1924, pp.41-49.
然而,立憲君主制時期,自由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既沒有成為全體民眾的共同政治認同,甚至也沒有得到掌握權力的國王和民族主義政黨的遵循。隨著埃及社會發展態勢的演變,無論是思想界精英、自由派政治領袖或者知識青年都不再將理性和個人道德、社會責任作為思想的來源和行為的準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及其載體君主立憲政體成為人民憎惡的對象。自由民族主義的危機和衰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府自身思想認同的危機。1923年憲法雖然規定議會權力至上,但并沒有明確界定政府與宗教的關系。1924年首屆議會政府成立后,受土耳其凱末爾激烈世俗化改革的影響,埃及議員們也曾就傳統沙里亞法所規范的人身地位問題提議推行世俗法律,廢除家庭宗教基金和取消大穆夫提職位等,但這些提案從未在議會獲得通過。議會也確實就個人身份的一些問題進行了一些立法改革,第一個法律條例是1929年第25號法令,條例的內容是糾正沙里亞法在婚姻問題上的不當規定。*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113.然而從這部法律的條文中,人們無法找到政府對待沙里亞法的基本立場。政府僅僅模糊地表明自己具有“伊智提哈德”(根據伊斯蘭的基本原則創建符合現實需要的新律令)的權力,它雖然希望擁有自由行動的權利,但又不想明確承擔伊智提哈德的義務。因此接受了伊智提哈德的批判精神,而拒絕按照公認的解釋原則建立新的法律架構。一方面,政府仍將自己限制在修改過的宗教司法框架里行事,暗示宗教法律中的一些原則和積極條款仍然有用;另一方面盡力避免民眾受這些條款約束的印象。*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p.115-118.事實上,政府甚至借用古蘭經和沙里亞法法官判決的權威來確立新法律條文的合法性。政府自身對于自由民族主義原則缺乏堅持并刻意模糊宗教與世俗的沖突,其結果是削弱和混淆而非增強了世俗民族主義的觀念。而且由于這種模糊態度,政府沒有對憲法規定的原則給予應有的支持并推動這些原則深入人心,相反卻給了傳統思想的捍衛者堅持讓政府服從伊斯蘭教法的希望。
第二,除了自身思想的不堅定,自由民族主義者也不能維持憲政秩序的有效穩定運行。華夫脫黨等民族主義激進派領導的反英運動雖然促成了埃及的獨立,但并沒有參與1923年憲法的制定,而是被動接受了這部賦予國王過多權力的憲法。華夫脫黨領袖扎格盧勒在憲法公布后曾抨擊說,盡管憲法規定一切權利源于人民,但這一原則在憲法本身的起草過程中就沒有得以實施,因而在未來也不可能得到貫徹。憲法賦予了國王真正的權力,這將會被用來損害埃及人民的權利。*Marius Deeb, Party Politics in Egypt: The Wafd & its Rivals 1919—1939, Oxford: Ithaca Press for the Middle East Centre, St Antony’s College, 1979, p.60.國王借助特權破壞或中止憲法,解散政府和議會,頻繁的操縱和脅迫選舉。在福阿德國王統治時期,憲法三次中止實行,在1923年至1930年間埃及更像是處于無憲法時期。1930年,國王廢除了1923年憲法,并頒行了一部旨在加強自己權力的新憲法。盡管華夫脫黨是憲政時代30年里最受選民歡迎的政黨,但它真正執政的時間不超過8年,它的政府先后四次被解散。*Ali E.H. Dessouki, The Party as a M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Egypt 1952—1967, Montreal: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McGill University, Apr. 1968, p.40.這一時期,沒有一屆議會能履行完自己的任期,沒有一屆政府的倒臺是源自議會的不信任投票,所有政府的平均執政時間都不足一年半。
第三,善于接受新思想、曾經沐浴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政治認同的轉變。自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以來,受過西式教育的青年人一直是自由民族主義的倡導者和追隨者,更是1919年革命的主力軍。然而,曾經竭力擺脫傳統束縛、崇尚西方價值觀念、被議會民族主義政黨競相爭取的青年人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卻轉向與政府對抗、尋求其他指導思想的道路,這其中表現最突出的就是青年埃及協會。該協會建立于1933年,是立憲君主制時期埃及首個青年人自己的政治性組織,1937年成立青年埃及政黨,1940年至1941年改稱伊斯蘭民族黨,二戰時期短暫蟄伏,1944年重新改回青年埃及黨,1949年改組為埃及社會黨直至1953年被革命政府所取締。從該組織的名字變更中就可以看出它的指導思想有時是伊斯蘭的,有時又受社會主義影響。事實上,該組織的創建人之一艾哈邁德·侯賽因曾經是自由民族主義的忠實追隨者,他中學時就加入了議會政黨自由立憲黨的青年組織,并協助組織了“自由青年支持締約協會”為埃及1929年與英國的條約協商爭取民眾的支持。*James P.Jankowski, Egypt’s Young Rebels: “Young Egypt” 1933—1952,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5, p.9.然而,面臨著30年代前期國王對憲政的破壞和經濟危機的后果以及英埃協商毫無進展的局面,青年埃及協會決心摒棄墨守傳統路線的守舊政黨,開創屬于青年新一代的民族主義運動道路。青年埃及協會提出的口號是“安拉—祖國—國王”,宣稱自己的目標是將埃及建成一個涵蓋蘇丹和埃及、聯合阿拉伯國家、領導伊斯蘭教的偉大強盛國家。*James P.Jankowski, Egypt’s Young Rebels: “Young Egypt” 1933—1952, p.13.從其口號中就可以看出,它的指導思想糅合了伊斯蘭的、民族主義的和法老主義的傳統。青年埃及協會甚至還有意模仿納粹的一些做法建立了帶有法西斯色彩的準軍事組織“綠衫軍”,*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1.成為采取激烈手段反對議會政治體制的主要青年力量。
最后,打著恢復伊斯蘭秩序旗號的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這一點將在第二部分內容中詳述。總體上看,憲政體制運行不彰以及同時期歐洲國家內部法西斯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沖突讓埃及民眾特別是只是青年對整個自由民主體系產生質疑。更重要的是,30年代前期的經濟危機和二戰后進一步惡化經濟局勢,動搖了整個社會政治體系,最終導致了自由民族主義的徹底崩塌。
二、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
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是埃及1936年至1952年革命前實力最強也最重要的民眾政治反對派組織,它也是許多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組織的母體。
穆兄會由小學教師哈桑·班納1928年在伊斯梅利亞創建。從成立到1936年這段時間是穆兄會組織創建和力量積蓄的時期;1936年到1948年是穆兄會擴張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它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宗教性政治組織;從1948年12月穆兄會遭鎮壓以及數月后班納遭暗殺到1952年7月革命,穆兄會在經歷一段時期的地下活動后又回歸合法身份在新領袖胡代比的領導下進行了重組,并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社會影響力,但在1952年至1954年間與軍人革命政府的權力斗爭失敗后,穆兄會最終被取締。
在組織創建階段,穆斯林兄弟會更多的是一個反對西方世俗主義腐化埃及社會、捍衛伊斯蘭教核心價值的溫和的宗教道德組織,其主要活動是提升自身素質、完善組織體系,建造清真寺和學習傳播啟示。成立之初,穆兄會還開展了教育培訓和社會服務活動,它為孩子們建立中小學,為工人建立技校,開設古蘭經講解課程和基本技能培訓班。同時,它還開辦城鎮企業,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工作機會,在幫助窮人的同時也增強了穆兄會的經濟實力。但班納并不否認穆斯林兄弟懷有政治目標,他宣稱兄弟會所倡導的回歸伊斯蘭的主張無論對于現世世界還是其他世界都是必須的,這是伊斯蘭教的核心。1936年穆兄會在寫給埃及國王信中要求進行普遍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簡要地表達了兄弟會的主張,呼吁“廢除政黨政治”,“引導全國的所有政治力量形成一個統一指揮的集團”。*Marius Deeb, Party Politics in Egypt: the Wafd & its Rivals 1919—1939, p.379.
穆兄會真正引起公眾的注意是1937年埃及議會政黨對待巴勒斯坦起義態度曖昧之際,它開始從事組織力量支援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活動。而事實上,早在1936年當華夫脫黨為首的跨黨派談判小組與英國簽署英埃同盟條約從而放棄民族事業的領導權時,穆兄會就已經接過爭取完全獨立以及埃及、蘇丹統一的大旗。此時穆兄會的主張早已超出了宗教和道德問題。為了確保人們按照伊斯蘭的觀念生活,它主張整個社會應該建立基于古蘭經的伊斯蘭政治秩序體制。隨著民生問題越來越突出,穆兄會提出了基于烏瑪團結和成員共享福利的社會綱領,并將此視作是從異教徒統治下解放伊斯蘭家園的步驟之一。*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199.
二戰和二戰后的社會環境及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為穆兄會的壯大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穆兄會抓住了這次機會。面對戰爭帶來的嚴重社會和經濟后果,戰后數屆政府的應對措施輕率短視、三心二意,讓倍感煎熬的人們深惡痛絕,而穆兄會趁機給出了解決問題的答案——推翻整個體制。戰時盟軍建立的軍工廠和因進口萎縮而有所發展的本土企業吸引了大量農村貧困人口進城,導致大城市貧民群體規模更加龐大。戰爭結束后,軍工廠被拆除,外來廉價商品的涌入導致許多新建工廠關閉,許多新進移民不愿返回鄉村,失業問題進一步加劇。由失業造成的貧困、工資下降以及通貨膨脹帶來的生活水平下降等嚴峻壓力導致了各地罷工浪潮的出現,參加罷工的人包括工人、政府雇員甚至警察。許多罷工雖遭鎮壓,但痛苦和對政府的仇恨卻深藏人們心中。同時,生活資料的短缺給廣大貧困人口的健康帶來了巨大威脅。1943年至1944年,上埃及發生了奪走20萬人生命的瘧疾傳染病災難,統治階級上層不是團結救災,卻相互勾心斗角,推諉責任,讓民眾雪上加霜,對政府和立憲體制絕望透頂。于是,人們開始將社會危機中不公和腐敗的根源指向現行的體制,認為埃及所有政黨都只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那就是大地主階級。這個階級把控議會,剝奪其他所有階層組建工會自我管理和自我保護的權力。*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201.隨著局勢的持續惡化,這種抨擊越來越激烈且蔓延至各種媒體、作品和各個階層當中。
面對苦難民眾的不滿、怨恨、絕望和當權者的逃避、腐化、墮落,穆兄會通過直接反對現體制而展現出自己是唯一能夠為未來提供希望和機會的組織。虔誠的穆斯林和夢想幻滅的自由派分子在看到整個社會道德淪喪且冷漠無情之時,被穆兄會宗教和道德上的虔誠守禮所打動,大量貧民窟的流浪者和城市新移民從穆兄會的支部會議和集體祈禱中找到了精神慰藉,而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民族主義知識青年則將穆兄會看作是民族主義事業的繼承人,就連政治機會主義者也希望借助加入或者支持穆兄會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此外,還有一些人是受到穆兄會舉辦的一些活動的吸引而加入該組織,包括創建體育俱樂部、童子軍組織、準軍事組織、秘密恐怖組織、雜志報紙、診所、福利院、學校、合作社、工會等。所有這些因素導致穆兄會成員在二戰和二戰后急劇增加,人數在50萬至100萬之間,1944年地方支部數量達到1070個,*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201; 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p.121; Christina W. Michelmore, Student Politics in Egypt 1922—1952, Ph.D.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3, p.204.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民眾政治組織。穆兄會的支持者主要是知識青年和城市中產階層,但由于傳統色彩濃厚和主張簡明易懂,兄弟會在農村的支持力量要比當時其他的政治組織大得多。關于穆斯林兄弟會成員的社會和地理分布的資料十分有限,有學者從涉及兄弟會法律案件中分析了兄弟會成員的社會組成。在1948年因隱匿爆炸物而被審判的32名兄弟會成員中,8人為公務員、5人為教師、7人為私企白領、7人為小企業主、2名學生,其余三人分別是農民、醫生和牧師;在首相努克拉什遇刺案被審判的15人中,6人為學生,5人為公務員,1名工程師和3名小商人。*Richard P.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328-329.這些數據表明,兄弟會成員中城市職業的人員要遠多于農村從業者,城市中產階級在會員中占主導地位。
二戰后,在把社會各領域的不滿分子招募到自己組織之中后,穆兄會領導人開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爭取民族獨立的訴求上,成為一個致力于暴力驅逐英國和推翻現政權的激進組織。兄弟會認為伊斯蘭教受到了基督教帝國主義者及其西化支持者的致命威脅,鏟除他們、建立神權國家、保護腹背受敵的伊斯蘭教是一項宗教義務。*Christina W. Michelmore, Student Politics in Egypt 1922—1952, p.202.任何反對穆斯林兄弟會思想和主張的埃及政治家以及表現出親英傾向的埃及人或外國人成為兄弟會襲擊的目標。*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p.122.從二戰結束到1948年,埃及局勢陷入持續動蕩之中,兄弟會發起無數次示威、游行和抗議,勢力達至鼎盛。1947年,穆斯林兄弟會加入由15個民族主義和伊斯蘭組織組成的全國陣線組織,要求英國軍隊完全撤出埃及,開展經濟和社會改革。*Christina P.Harri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Egypt: The Rol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p.184.面對巨大的民意壓力,政府只能在與英國的協商中采取決不妥協的立場,最終造成協商破裂,政府頻繁辭職。
1948年巴勒斯坦戰爭爆發,暫時緩解了埃及國內的緊張局勢,埃及政府也借機號召人們出錢出力支援巴勒斯坦。穆兄會發表大量報紙文章號召保衛阿拉伯巴勒斯坦免遭歐洲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占領,并募集資金和武器,訓練和派出志愿軍與阿拉伯人并肩作戰。然而戰爭局勢卻并未朝著阿拉伯人希望看到的方向轉變,埃及政府派出的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但政府卻不敢承認失敗結束戰爭。穆兄會因為派出志愿軍而名聲大振,并利用安全控制的松動搜集武器和訓練隊員。戰爭結束時,埃及努克拉什政府試圖借助戒嚴令消除穆兄會對政府的威脅,于1948年12月宣布解散兄弟會,并對其成員進行了嚴厲鎮壓,理由是后者陰謀發動革命和針對個人進行殘忍的恐怖襲擊。*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p.123.作為報復,時任首相努克拉什遭到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暗殺。幾個月后,兄弟會首領哈桑·班納遭到親政府分子槍殺,兄弟會勢力因此大為削弱,被迫轉入地下。
巴勒斯坦戰爭結束后,埃及獨立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而此時伴隨著戰爭失敗的災難、尖銳的社會危機、穆兄會持續不斷的地下活動以及戰爭期間軍隊供應物資丑聞的曝光,整個國家處于火山噴發的臨界點,政府的領導職位成了燙手山芋。在這種情況下,國王不得不宣布大選。隨之,華夫脫黨贏得選舉重新執政,為鞏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同時獨立問題上毫無退路的華夫脫黨政府冒險掀起反英宣傳,并單邊撕毀1936年條約,把埃及民族主義的情緒推向了頂點。為了贏得支持,它還恢復了穆兄會的合法身份。單方面宣布廢除1936年條約使得英埃關系陷入危機,埃及國內秩序也幾近崩潰,穆斯林兄弟會得以不受約束地和共產黨、社會黨、左派華夫脫黨組成聯盟對英國展開游擊戰爭。1952年1月,游擊隊突襲英國運河區軍需庫,遭英國報復,造成大量埃及警察人傷亡,致使大規模反英示威活動的爆發,憤怒的人群將開羅充滿歐式風格的富人和外國人聚集區付之一炬,制造了著名的“黑色星期六”事件。*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06-307.雖然50年代穆兄會從影響到隊伍力量都沒能再恢復至哈桑·班納時代那樣的輝煌地位,但憑借著巴勒斯坦戰爭期間與自由軍官關系的加強和戰后學生支持群體的上升,穆兄會得以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與推翻法魯克國王專制統治的基礎上與自由軍官組織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直到1954年被取締。
伴隨著穆兄會在二戰后崛起,帶有明顯傳統思想色彩的伊斯蘭政治認同再次成為聚集在穆兄會組織中的社會各階層反對自由民族主義憲政體制的最強大精神武器。由于哈桑·班納是這一時期穆兄會長期的無可匹敵的領導人,他的政治主張也成為了穆兄會組織的政治綱領,而這些主張無疑又源于班納對伊斯蘭教的感知。在班納看來,伊斯蘭教不只是進行祈禱的個人事務或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個方面,而是一個覆蓋所有公私領域、為伊斯蘭國家和社會奠定根基的包羅萬象的思想體系。伊斯蘭教的教義和圣訓完全能夠規范社會各種年齡段、每個人一生中面臨的所有事情。伊斯蘭教是全知全能的和永恒不滅的,因而是應該予以全面遵守的。*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p.121.與此同時,班納繼承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和拉希德·里達倡導的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想,反對盲從和守舊,強調創制的信仰原則,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演變》,《西亞非洲》 2011年第4期。也就是說,班納所主張的返璞歸真,不是簡單的回歸過去,而是要改革發展的道路與埃及的宗教和社會實際相結合。具體來看,在政治方面,穆斯林兄弟會的目標是將伊斯蘭教法制定為國家的最高法律;在民眾中樹立伊斯蘭烏瑪是效忠的主體,而非烏瑪中任何特定的民族;重新設立伊斯蘭哈里發,并將埃及和所有穆斯林民族從異教徒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在社會和個人方面,穆斯林兄弟會聲稱要提升古蘭經中的精神和道德,將宗教從束縛它的儀式和迷信中解脫出來。兄弟會要求廢除政黨和派閥,認為派系是虛弱和碎裂的表現。為避免導致分歧和分裂,兄弟會反對不同伊斯蘭派別之間進行激烈的爭論,無論是理論上的、邏輯上的、哲學上的或是政治上的。解決分歧的辦法是接受古蘭經的權威,避免可能造成人們分歧的詭辯式解釋。*T. Barghouti, The Case of Egypt: A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a Colonially Created Government, Ph.D.Dissertation, Boston:Boston University, 2004, pp.261-262.對于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班納的答案是捍衛和服從伊斯蘭教,武力斗爭以實現埃及擺脫占領。穆斯林兄弟會宣稱:“安拉是我們的目標,古蘭經是我們的憲法,使者是我們的領袖,圣戰是我們的道路,為主而戰是我們最崇高的愿望”。*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演變》,《西亞非洲》 2011年第4期。這使得穆斯林兄弟會的主張十分簡明,因而比任何其他伊斯蘭組織對普通民眾都更有吸引力。
作為20世紀30至50年代在埃及號召人們借助伊斯蘭教來尋找解決獨立和現實社會經濟問題答案的主要代表,穆兄會展示了民眾要求變革的強烈愿望,沉重地打擊了以國王和大地主為代表阻礙社會經濟變革的舊勢力,加速了自由民族主義舊秩序的瓦解和崩潰。
三、伊斯蘭政治認同復興的深層次原因
1919年大革命期間,社會眾多階層都匯集在以華夫脫黨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的周圍,為爭取國家的獨立而斗爭。1922年獨立聲明發布后,憲政民主的聲望曾如日中天,即便是當時的宗教界領袖、保守派分子也竭力從伊斯蘭傳統信條中尋找證據為立憲政府辯護。但這種聲望的興隆是不是就是因為人們相信并認同自由民族主義的思想原則呢?埃及社會各群體多大程度上相信,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支持自由民族主義者,這關系著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及其體制的命運,也揭示著伊斯蘭政治認同復興的原因。
第一,自由民族主義的思想原則并沒有取代伊斯蘭信仰成為全民的政治認同,埃及的伊斯蘭政治理念從來沒有離開過,存在著天然對抗西化世俗主義的龐大社會基礎。自由憲政并非是一種可以在任何社會都能發揮作用的純粹政治機制,它需要一定的文化條件,包括指信仰某些與人類本質和社會有關的理念、價值和準則。憲政在西方是一種漸進發展的產物,經歷世俗與宗教數百年的沖突調和,才最終建立了一套符合現實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并得到全民認可的政治體制,這一制度的背后蘊含著整個西歐的歷史和人們對一些價值和準則如理性主義、個人自由、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代議制、精神和思想自由、政治參與等的相信與堅守。而埃及傳統的伊斯蘭政治信仰則靠神啟的古蘭經和沙里亞法來實現社會統治,與來自西方的依靠人的理性進行社會治理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在一個大部分人的觀念和生活依然處于傳統束縛的社會里,突兀的來自異質文化環境的自由民族主義及其憲政體制并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因而也很難回應埃及伊斯蘭社會的張力和壓力,因為新的觀念、體制和物質現實與埃及過去傳統觀念體系和生活方式存在著沖突、斷裂。為了解決埃及社會推行西方體制所面臨的思想障礙,伊斯蘭現代主義者穆罕默德·阿卜杜嘗試通過縮小啟示的適用范圍從而減少神啟和理性之間可能的沖突來調和兩種信仰體系,但未能解決存在的問題。許多穆斯林學者包括阿卜杜都拒絕接受世俗的民族主義,他們認為民族主義主張是西方在文化和政治上控制穆斯林世界的間接手段。穆斯林兄弟會的思想體系保留了這一基本看法,哈桑·班納聲稱伊斯蘭是穆斯林唯一的民族屬性和祖國,是最高的效忠對象。*Ali E.H. Dessouki, The Party as a M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Egypt 1952—1967, p.36.最終,在普通大眾看來,這些提倡憲政和世俗化的少數人遠離大多數民眾,他們的主張既非原創也非土生土長,對下層民眾最為關心的生計問題不管不問,因而顯得另類且無用。
立憲君主政體確立后,國家在思想領域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用自由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取代已經遭到削弱且與現實發展不符的傳統伊斯蘭思想體系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基礎。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將憲法規定的自由民族主義的紙上條文轉變成公眾自身普遍認同的世界觀。然而,實際情況是1923年憲法雖然規定宗教信仰絕對自由,但規定伊斯蘭教是國教,同時又宣稱政府保護所有符合埃及既有慣例的宗教活動和信條。憲法條文以及前面提及的政府在宗教問題上對傳統思想體系模糊并有意接納的立場造成以后自由民族主義的立憲政府與伊斯蘭勢力之間持續不斷的沖突。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哈里發存廢問題。1924年3月,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宣布廢哈里發制度,這個和埃及主權沒有關系的問題卻迅速激起了埃及各群體對該舉動的有效性以及該舉動對埃及的影響展開熱烈討論。爭論產生了兩種觀點,一是呼吁繼續承認土耳其阿布德·馬吉德的哈里發身份,并讓其定居埃及。另一觀點認為馬吉德的哈里發身份已經失效,穆斯林對他的效忠也隨之被解除,需要召開穆斯林大會討論哈里發問題并按照穆斯林的宗教規則選出新的候選人。*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112.爭論的結果是,1926年各國非官方代表團齊聚開羅召開討論哈里發的存廢問題,但與會代表甚至連哈里發應具備的基本條件都沒有達成一致,問題最終不了了之。針對該問題的提出,時任立憲政府首相的華夫脫黨領袖扎格盧勒雖然質疑效忠外國君主違背了憲法中國家主權獨立的原則,但他還是宣布埃及在此問題上保持中立。扎格盧勒私下解釋說他反對哈里發制度,并非基于世俗主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但他并不想公開表達這種看法,因為公眾對該問題過于敏感。*Nadav Safran,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p.112.這一事件表明面對強大的傳統思想體系,憲政的原則十分脆弱,連受過西方教育的領袖扎格盧勒對哈里發制度所代表的含義的理解也是幼稚。由是觀之,自由民族主義者在1919年各種的勝利,并不意味著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勝利,因為它沒有得到人們普遍的信奉和遵守。人們支持自由民族主義者是相信他們倡導的原則能像它在歐洲一樣帶來國家的獨立和強大。
第二,不存在一個維持自由民族主義憲政體制的強大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卡邁勒和魯特菲所宣揚的自由民族主義在埃及確實得到了富有的中產階級的持續支持,其成員主要來自專業人士、公務員和知識分子。這個階級之所以積極回應自由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全新的階層,與傳統社會沒有牽絆,更容易接受新思想。為更好的勝任諸如律師、法官、政府雇員等新工作,他們都受到了西方教育的熏陶,熟知并按照西方的法律術語和管理制度思考和解決問題。因而,他們不是傳統社會體系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獨立專業團體,然而這個群體的規模和實力太過微弱,無法獨立發揮作用。埃及社會仍然是一個由地主和農民兩大主要群體構成的前工業社會。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十分貧窮落后、食不果腹,缺乏教育和組織性,不具備參與現代政治生活經濟實力和文化素質。小商業和工業階層主要由外國人和少數族群構成,如敘利亞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他們很難發揮西方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作用。工人階級只是社會中很小的一個城市群體,在1942年之前甚至不被允許建立獨立的組織。
而地主雖然人數少,卻是社會中一股最強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他們獨享了憲政的果實。1923年成立的30人制憲委員會其成員均來自地主階層,其制定的憲法賦予了國王這個全國最大的地主以廣泛的立法權,并確保富有的地主把控著議會上院。*Ali E.H. Dessouki, The Party as a M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Egypt 1952—1967, p.39.盡管華夫脫黨是議會政治時期最強大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民族主義政黨,其主導力量也是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早在議會政治開啟前,華夫脫黨領導機構最高指揮部共有27名成員,其中11名屬于大地主階級,其余16名成員為中等地主或城市中產階級,大地主的比例超過了40%,他們不少人是19世紀中葉以來不斷集聚土地的村長烏木達和部落酋長謝赫,部分人則是新近購買大量土地的城市富人。*Marius Deeb, Party Politics in Egypt: The Wafd & its Rivals 1919—1939, pp.68-70.華夫脫黨領導層的社會身份遠不能代表其追隨者和支持者的多樣性,工業界和商界等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很少,而無論在最高領導層,還是在議會下院,都沒有城市工人和農村農民的代表。這反映了埃及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即地主階層在埃及經濟占據絕對優勢,工商業界十分虛弱,工人和農民工人和農民還沒有發展成為自覺的階級。大地主通過控制憲政機構來推行最大程度上反映他們利益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從1914年4月侯賽因·魯什迪政府到1952年7月24日的阿里·馬希爾政府,埃及共經歷的15屆內閣,大地主在政府閣員中所占比例平均58.4%。包括華夫脫黨在內的政府其大多數閣員職位也主要是被地主階層所占有。例如,在1942年2月4日成立的穆斯塔法·納哈斯政府中,大地主閣員占有63.8%,在1942年5月的新一屆政府中,大地主比例為64.2%。*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p.79.處于社會轉型和半殖民地經濟體系的大地主和新貴族雖然生產經營方式逐步融入到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雖然開始具有自身獨特的經濟利益并希望獲取更大的政治權力從而具有擺脫殖民控制的進步的一面,但他們仍然與舊體制、舊思想和帝國主義者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他們在與國王專制和殖民控制的斗爭中具有軟弱性,但又不愿發動團結下層民眾進行徹底的獨立斗爭。相反,他們千方百計阻礙損害自身利益的改革舉措在自己把控的議會里通過,這必然使得憲政民主體制在民眾心中名譽掃地。對于普通埃及人來說,代議制意味著國王和帕夏,推翻它才能實現自身的解放。
第三,自由民族主義憲政體制不能解決國家和社會面臨的歷史問題。既然自由民族主義者引入立憲政府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取得和在同一思想原則指導下的歐洲國家那樣的成功,那么根據1923年憲法所成立的政府,它的命運主要取決于它解決埃及人所面臨重大問題的成效。對于全體埃及人來說,實現國家完全獨立正是這樣的問題。對于下層民眾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解決民生問題,特別是在危機時刻。然而,立憲政府在爭取國家完全獨立和推動社會經濟公平正義方面的任務都沒有完成。
1922年英國單方面發表的聲明雖然承認埃及為獨立主權國家,但卻設定了“四點保留條款”,將英國在埃交通安全、防御埃及、保護外國人利益以及蘇丹回歸埃及等一系列核心問題在兩國協商達成一致協定之前置于英國的決定之下,也就是說,英國依然保留著保護所有在埃及需要它保護的權力,埃及所謂的獨立只是表面上。立憲政府成立后,自由民族主義政黨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通過與英國的協商實現埃及完全獨立。但完全獨立必然意味著英國特權的喪失,而英國絕不會主動放棄特權,因此,四項保留條款成為了兩國關系不斷發生摩擦的根源。從1924年首屆議會政府成立到1936年雙方最終達成同盟條約為止,英埃之間共進行了五次、斷續14年的協商,其中前四次均因雙方在英國駐軍和蘇丹問題上沒有共識而流產。在協商中一旦埃及民族主義政黨采取強硬不妥協立場,英國就會通過施壓國王解散政府甚至直接武力炫耀迫使立憲政府就范。1924年的英埃協商因為華夫脫黨政府在所有議題上強硬不妥協的姿態而迅速失敗,事后英國駐埃及代表就向埃及國王表達不希望華夫脫黨繼續執政的想法。*Marius Deeb, Party Politics in Egypt: The Wafd & its Rivals 1919—1939, p.132.11月英籍埃及軍隊總司令兼蘇丹總督李·斯塔克在開羅遭埃及民族主義者槍殺,英國駐埃及代表隨即對華夫脫黨政府進行了羞辱性的報復,提出了道歉、懲兇、賠款、鎮壓反英示威、埃及軍隊撤出蘇丹完全交英國管理等一系列過分要求,*John Marlowe,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3, pp.268-269.華夫脫黨政府不愿接受,只得下臺。1926年大選結束后,華夫脫黨再次贏得議會多數,但英國為阻止強硬的華夫脫黨組閣,公然派戰艦進駐埃及亞歷山大港,用赤裸裸的炮艦政策打消了華夫脫黨執政的念頭。*C. W. R. Long, British Pro-Consuls in Egypt 1914—1929: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5, p.148.盡管兩國在1936年達成了同盟條約,但在交通安全防護和蘇丹問題上埃及依然沒有實現自己的訴求,條約規定英國依然有權在和平時期駐軍蘇伊士運河,并在戰時使用埃及全部領土領空及交通設施;在蘇丹問題上只是恢復到了李·斯塔克事件前的英埃共管的局面,遠非埃及一貫希望的將蘇丹收歸己的主張。*“The Anglo-Egyptian Treaty of 1936,” Current History, vol.22:128 (Apr.1952) pp.231-239.面對這樣一個條約,曾經竭力爭取徹底獨立的華夫脫黨領導人竟然向議會宣稱該條約的執行“將給埃及帶來真正的獨立”。*Janice J. Terry, Cornerstone of Egyptian Political Power: The Wafd 1919—1952, London: Third World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Pub., 1982, p.234.這說明華夫脫黨等議會民族主義勢力已經不再是埃及民族主義運動的旗手,也自然激發了青年埃及黨和穆兄會的嚴厲抨擊,它們發動示威抗議條約的簽署。
除了彰顯議會政治合法性的民族獨立目標沒有實現外,立憲政府對于民眾關切的土地、貧困、失業和兩極分化等經濟社會問題也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立憲君主制時期的埃及,傳統經濟仍占據主導地位。農業產出占國民收入的絕大部分,三分之二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而農業又嚴重依賴單一作物棉花。同時,地主土地所有制長期存在,租佃制廣泛流行。*哈全安:《中東史:610-2000》,第515頁。1947年,埃及人口據估計有1900萬左右,其中只有大約575萬人居住在城市。*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p.73.一戰后,埃及農業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實現快速發展時期的結束,從1912年到1952年,埃及耕地僅從528萬費丹增長至584.5萬費丹。*Charles Issawi, Egypt in Revolu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5.而同期埃及人口卻從1897年的970萬增加至1947年的1900萬,增長了一倍還多。*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2, p.313.耕地和產量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意味著兩次大戰之間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實際上出現了顯著下降。與此同時,埃及土地分配又嚴重不均。從20世紀伊始到1952年土地改革,埃及大約2000個擁有巨額地產的土地精英和占地50費丹以上的12000個中等農業貴族家庭,總共控制著全國大約40%的耕地。同期,占地等于或小于5費丹的小農人數從76萬人增加至264萬人,人均土地面積從1.46費丹降至0.8費丹,無地農民的數量急劇增加。截止到1939年,90%的農村家庭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3費丹,而3費丹是支撐一個四口之家生計的最低要求。*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2, p.322.土地分配的嚴重不均,導致社會結構的兩極分化,大多數農民生活在極端的貧窮、疾病、骯臟和愚昧之中。貧困帶來的生存壓力導致無地農民大量向城市遷徙。開羅和亞歷山大的總人口1917年時為124萬,1947年時已經超過了300萬,增速是當時全國人口增長速度的3倍多,而只有很小一部分城市居民能夠在制造業中找到工作,*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2, p.313.緩慢的工業化進程未能緩解城市的人口壓力和讓農民擺脫貧困狀態。直到1937年,在10人及以上規模制造企業工作的人數也只有15.5萬人,到二戰爆發時,埃及制造業、采掘業、天然氣、自來水和電力企業產值在GNP中的比重仍然只有大約8%。*Charles Issawi, Egypt in Revolu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p.44.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此小規模的非農經濟,基本上還是由生活在埃及的少數族群和外國人所控制。少數族群占埃及人口的不到10%,歐洲人和埃及少數族群占有埃及全國所有投資資本的91%。30年代埃及工業化啟動后,外國商人在埃及新建企業中的投資比重不斷下降,但直到1948年時,外國人在全部埃及企業中的投資占比依然高達61%。*Selma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1952, pp.81-82, 84.因此,總體上,立憲君主制時期埃及的經濟發展表現為農業陷入停滯和危機、工業發展緩慢曲折、金融和商貿為外部勢力及少數族群所主導,社會大眾貧困化、兩極化十分明顯。
二戰期間這樣的經濟局面進一步惡化。二戰爆發后,埃及化肥進口渠道中斷,糧食產量下降,隨著盟軍對民用物資的征用,埃及出現了食物短缺、物價上升、通貨膨脹和民眾貧困加劇的嚴重后果。加上戰時英國對埃及軍事控制的強化,戰爭后期和結束后,政府應對危機無效,埃及爆發連綿不絕的反英反政府浪潮也就不足為奇。
第四、公共教育的失敗。理論上,教育可以宣揚政府倡導的觀念通過對人的塑造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事實上,面對新舊觀念沖突帶來的迷茫和壓力,政府和知識界精英也都認為教育是扭轉傳統觀念體系適應新的社會現實、鞏固西化體制和實現獨立自主的最重要手段。1925年,埃及政府通過一項旨在實行義務基礎教育、掃除文盲的法令,公立教育系統中學生人數增長迅速。在校生人數從1913年的32.4萬增長至1933年的94.2萬和1951年160萬。*Ali E.H. Dessouki, The Party as a M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Egypt 1952—1967, p.206.從教育層次的發展比例上看,高等教育在數量的發展上要高于總體水平。1925到1950年間,大學入學人數增加了10倍,從3273人增加至30169人,其增長速度幾乎是初等教育的2倍。1950年,當超過80%的人口還是文盲之時,大學的支出卻已占預算的13%。在1952年革命前,將近一半的學齡兒童無法得到任何形式的教育,而上大學的人卻超過了整個人口的1%。*Christina W. Michelmore, Student Politics in Egypt 1922—1952, p.138.受教育人數的龐大,特別是中學與大學生人數規模的龐大意味著政治意識的覺醒和政治參與要求的增加。
面對大幅增長的學生人數,國家卻不能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其結果是許多知識青年失業。從1928到1933年的五年里,高等學校的畢業人數以平均每年21%的速度增加,而政府并未為此做好準備。*Afaf Lutfi al-Sayyid-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1922—193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201.統計表明,1933年54%有學歷證書的人失業,其中大多數人可能都是初級文憑持有者。但到了1937年,大約1萬到1.1萬中級和高級學校學歷持有者同樣處于失業狀態。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屬于持有中學或職業技術文憑,其余為大學學歷。僅在1936年8到11月這4個月里,就有4512名失業青年申請救助,其中63%的人持有高等學校學歷。*Christina W. Michelmore, Student Politics in Egypt 1922—1952, pp.143-144.同時,由于學生大量增加,埃及所有學校教室都塞滿了學生,教育設施嚴重緊張,教育質量大幅下滑,由此造成學生就業問題進一步加劇,引起了學生的普遍不滿。
除了失業問題,學生面臨的另一重大問題是精神上的困惑。他們在課堂上學到了大量從西方照搬過來的民主政治理念,而現實中他們看到的卻是英國干涉、憲政失序、選舉操縱和政黨傾軋,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加上自身失業的不幸遭遇,一些青年學生必然對政府所倡導的自由民族主義產生質疑,迷茫。正由于學校教育的失敗,人們頭腦中的道德價值困境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進一步加深了。教育不僅沒有起到保護民主制度的作用,相反制造了大量處于失業狀態知識青年,他們對一事無成的現有體制怨恨最深,也成為反抗現體制最激烈的群體。
結語
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的埃及近代社會在西方殖民入侵的嚴峻挑戰下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劇烈變遷過程,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商社會之間新舊生產關系的轉換既造就現代民族國家所需的制度、文化和階層,也導致了經濟上依附、政治軍事上被西方控制的嚴重后果,伴隨著新興階層的壯大,他們爭取民族獨立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時代命題。然而,具有西方現代觀念的自由民族主義者仍然是埃及強大傳統社會的一小部分,他們倡導的新觀念體系并沒有得到全社會的認同,各階層能夠一度團結他們周圍爭取獨立是因為大家有著相似的目標,而不是相同的價值觀,這就決定了自由民族主義者維護的憲政體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民族獨立任務的實現上。在沒有共同的政治認同的前提下,立憲政府既不能實現國家獨立,又不能夠解決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訴求,那些曾經是自由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就很快地導向了穆兄會那里。西方娛樂和生活方式帶來了冷漠放縱、腐化墮落,穆兄會就強調伊斯蘭的虔誠互助、節制修身;議會政治帶來了爭吵分裂、自私傾軋,穆兄會就強調團結服從、集體奉獻;議會政黨漠視百姓疾苦,穆兄會就辦校設廠,扶危濟困;整個社會大部分人仍是文盲和傳統宗教徒,穆兄會就用人們熟悉的意識形態重塑共同體的認同,強調正本清源、返璞歸真;人們痛恨它們的議會政黨拋棄民族事業而通敵叛國,穆兄會就接過爭取完全獨立的大旗,號召武力推翻已經腐朽的現制度。因此,穆兄會通過自己的組織、行動和綱領向所有社會不滿階層提供了他們想要表達的訴求與愿景,自然也獲得了社會空前的支持。但和自由民族主義者一樣,穆兄會的勝利并不都是人們認同它所倡導的思想體系的結果,它能吸引下層民眾廣泛參與并訴諸暴力實現自己的目標,一定程度上是自由民族主義政府社會政策失敗的結果,是自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沒有深入人心的結果,是自由派政治領導人背棄民族獨立事業的結果,是立憲政治體制運行失敗的結果。穆兄會在本質上是一個用伊斯蘭思想暴力反抗各種失敗意識形態和自由民族主義政權統治失敗的宗教性政治組織。穆兄會倡導的伊斯蘭思想并非對傳統的簡單重復,而是融入了許多現代西方的政治理念,是19世紀宗教改革思潮的延續,它和自由民族主義政黨的理念并非一個守舊一個進步,一個傳統一個現代的對應關系,它們都是爭取國家獨立和解決社會危機的一種道路選擇。然而,穆兄會雖然非常清楚自己要反對什么,但對在古蘭經的基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烏瑪社會才能應對現實社會紛繁復雜的矛盾沖突,以及如何建立一個這樣的社會卻并不清楚。因此,穆兄會在立憲君主制時期的歷史作用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摧毀瓦解不合理舊體制的功能。
(責任編輯:郭丹彤)
2016-08-30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現代埃及世俗政治與宗教政治互動關系的歷史考察”(編號:13CSS021)。
謝志恒(1979-),男,河南舞陽人,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A
1674-6201(2016)03-00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