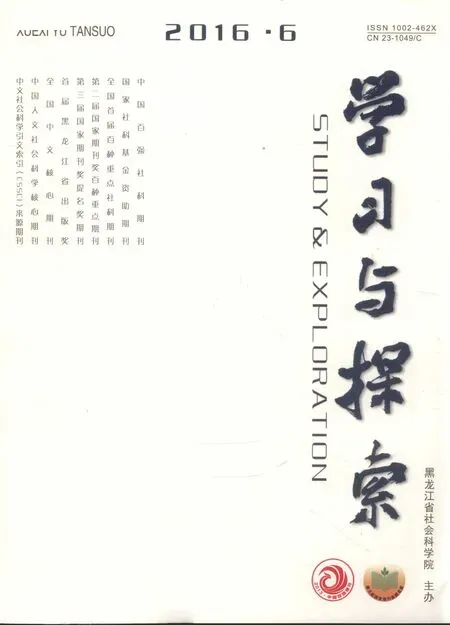貨幣異化:人的自我異化與相互異化
——重估《論猶太人問題》在馬克思思想歷程中的地位
李 彬 彬
(中共中央黨校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91)
?
貨幣異化:人的自我異化與相互異化
——重估《論猶太人問題》在馬克思思想歷程中的地位
李彬彬
(中共中央黨校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91)
摘要: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轉變了鮑威爾理解猶太人問題的視角,把“猶太人問題”從神學問題轉變為社會歷史問題,從考察“安息日的猶太人”轉向考察“日常的猶太人”,發現了現代市民社會中的貨幣異化,并從“人的自我異化”和“人的相互異化”兩個維度探討了貨幣異化的內涵和表現。馬克思對于“人的相互異化”的討論一方面表明了他與鮑威爾的思想距離,另一方面也預示了他在“巴黎手稿”和“穆勒評注”中的研究。
關鍵詞:《論猶太人問題》;貨幣異化;人的自我異化;人的相互異化;馬克思
在馬克思的思想歷程中,《論猶太人問題》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這并不是簡單地因為馬克思在這篇論文中公開向自己曾經的導師布魯諾·鮑威爾宣戰,更重要的是因為馬克思在其中提出了“貨幣異化”的議題。這一議題的重要價值在于,馬克思從以下兩個維度展開了對它的討論:第一,就貨幣作為人創造的對象而言,“貨幣異化”探討的是人的自我異化的問題;第二,就貨幣作為人與人相交往的中介而言,“貨幣異化”探討的是人的相互異化的問題。在前一個維度上,馬克思的分析工具還是“類本質”,他的思想依舊處在以布魯諾·鮑威爾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批判”的平臺上;在后一個維度上,馬克思面對的則是表現為數目龐大的現象堆積的整個市民社會,他必須要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來解剖市民社會。后一思路直接通向“巴黎筆記”尤其是“穆勒評注”的相關研究。
一、“貨幣異化”的發現和提出
馬克思撰寫《論猶太人問題》的目的在于批判鮑威爾的《猶太人問題》和《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馬克思和鮑威爾的論戰是當時整個社會上關于“猶太人問題”大論戰的一部分,這場論戰是由新登基的國王弗里德里希·威爾海姆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提議恢復中世紀的猶太人同業公會而引起的,這一保守的、復辟的行動引發了整個社會極大的反響。鮑威爾在《猶太人問題》中提出,自從中世紀以來,歐洲人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唯獨“猶太人問題”一直沒能得到解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所有的人在思考“猶太人問題”時都沒有正確地提出問題。因此,當務之急是首先正確地提出問題。鮑威爾認為,“猶太人問題”既不能單獨歸咎于基督徒,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猶太人,只要猶太人和基督徒都還保留自己的信仰,那么“猶太人問題”就永遠無法得到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根源在于,宗教信仰壓制了自由的人性。鮑威爾指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前提是消滅宗教: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不再信仰宗教,而以人的立場對待彼此,這樣就不會存在特權和壓迫[1]。在《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一文中,鮑威爾探討了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所面臨的困難,并分析了他們誰距離自由更近。由于基督教是猶太教的發展結果,它把猶太教的偽善、罪惡觀念、排他性發展的都更加徹底,相對于猶太人,基督徒的宗教異化更加徹底。正因為如此,基督徒消滅基督教帶來的異化為人類帶來的貢獻是自由的人性,而猶太人消滅自己的宗教異化只能達到基督徒現有的教養水平。猶太人需要在此基礎上再完成基督徒的事情才能達到自由的人性[2]。
在馬克思看來,鮑威爾的方法把猶太人解放的事業變成了“哲學兼神學的行動”,鮑威爾的觀點并沒有真正回答猶太人如何才能獲得自由和解放。為了讓猶太人的解放成為現實的行動,他調整了鮑威爾的視角:把猶太人問題從神學問題變成社會歷史問題,從關注“安息日的猶太人”到關注“日常的猶太人”。在考察“日常的猶太人”的生活時,馬克思發現了“貨幣異化”的問題。
第一,重新提出問題,把“猶太人問題”從“神學問題”變成一個社會歷史問題。馬克思指出,鮑威爾雖然試圖重新提出“猶太人問題”,但是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和提出的問題本身都出現了偏差。在1840年代的德國,“猶太人問題”是一個具有鮮明社會和政治意義的問題,鮑威爾卻把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神學問題”。只有鮑威爾這樣的神學家才會撇開猶太人和基督徒生活的社會歷史背景,單單從自我意識的教養的角度討論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因此,馬克思指出,必須重新提出問題:“我們現在試著突破對問題的神學提法。在我們看來,猶太人獲得解放的能力問題,變成了必須克服什么樣的特殊社會要素才能廢除猶太教的問題。因為現代猶太人獲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猶太教和現代世界解放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由于猶太教在現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產生的。”[3]49
鮑威爾基于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戒律、宗教信念分析他們和普遍的自由的人性有多大的差距,提出基督徒只要“跨過一個臺階”就可以獲得自由,而猶太人則要跨過兩個臺階。馬克思指出,像鮑威爾這樣在神學的論域內討論“猶太人問題”是不切實際的、片面的。之所以說這種做法不切實際,是因為它并沒有告訴猶太人和基督徒到底怎么做才能擺脫宗教獲得自由。在擺明了猶太人所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和困難之后,又輕巧地安慰他們“在人面前一切皆有可能”,不過鮑威爾始終沒有告訴我們到底怎么做才能把“可能”變成“現實”。之所以說鮑威爾的做法片面,是因為不論基督徒還是猶太人,宗教都不是他們的一切。但是,在鮑威爾的視野中,宗教就是一個信徒的一切,他把猶太教看作猶太人的“全部本質”。猶太人不僅是一個宗教徒,他還是某一個家庭中的一員,有自己的職業,生活在不同的國家等等,這些關系綜合在一起構成了猶太人的“全部本質”,但是鮑威爾卻以偏概全。
第二,從考察“安息日的猶太人”到考察“日常的猶太人”。馬克思把“猶太人問題”從鮑威爾的“神學問題”變成一個社會問題來處理,這意味著馬克思主張不能只是關注猶太人的宗教屬性,而是要全面地關注猶太人的整個社會屬性。正是為了全面地考察猶太人的社會屬性,馬克思從考察“安息日的猶太人”轉向考察“日常的猶太人”。在指出鮑威爾把“猶太人問題”變成“純粹的神學問題”所面臨的困難時,馬克思指出:不能只是單純地說猶太人和基督徒擺脫宗教之后就能獲得自由,而是要實實在在地回答猶太人和基督徒到底如何做才能擺脫宗教。隨著政治解放的完成,猶太教和基督教不再具有政治屬性,它們變成了純粹的私人事務,變成了市民社會中的特殊性要素。為了找到消滅宗教的道路,就要從市民社會本身入手。在馬克思看來,理解市民社會的切入點應該是“日常的猶太人”,而不是“安息日的猶太人”[4]247。“現在我們來觀察一下現實的世俗猶太人,但不是像鮑威爾那樣,觀察安息日的猶太人,而是觀察日常的猶太人。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他的宗教的秘密。”[3]49
“安息日的猶太人”與“日常的猶太人”之間的區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馬克思本人也一再提醒我們注意這一區分。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用加粗的黑體字表示這一區分的重要地位。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還說過,《德法年鑒》“剝掉了猶太教的宗教外殼,使它只剩下經驗的、世俗的、實際的內核”[3]307。正如奧爾格爾所指出的,“對于馬克思而言,‘現實的’猶太人是脫去宗教外衣之后的分析的產物。但是,在消除了神秘的外殼之后,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接下來的分析所針對的并非猶太人而是市民社會的利己的人。”[4]247必須在嚴格的理論意義上來理解馬克思在“安息日的猶太人”與“日常的猶太人”之間所做的區分。“安息日的猶太人”與“日常的猶太人”之間的區分是理解馬克思走向市民社會批判的關鍵。
“安息日的猶太人”是鮑威爾所關注的那種把宗教信仰視為自己的最高本質的人,與此相對,“日常的猶太人”只不過是市民社會眾多成員中的一分子。馬克思借助于觀察“日常的猶太人”,他所考察的和批判的事實上則是整個市民社會的成員。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的下述論斷,即“市民社會從自己內部不斷產生猶太人”[3]52。馬克思所說的從市民社會內部不斷產生出來的“猶太人”并不是宗教信仰意義上的猶太人,也不是人種學、民族志意義上的猶太人,而是以“實際需要和利己主義”這一“市民社會的原則”為宗教信仰之基礎的“猶太人”。
第三,從“宗教異化”到“貨幣異化”。鮑威爾是在“宗教異化”的整體框架之下理解“猶太人問題”的。他認為,“猶太人問題”就是“宗教異化”的一個表現,由于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把自己的上帝作為最崇高的本質,沒有把“普遍的自我意識”作為自己的本質,所以猶太人和基督徒才為了各自的上帝而相互隔絕。猶太教由于自己的宗教而與其他民族隔絕,不愿意與基督徒融合在一起;基督徒和基督教國家也由于自身的宗教本質而拒絕給予猶太人平等的市民權利。因此,要想解決猶太人問題,必須消滅宗教,恢復人的真正的普遍的自我意識。
馬克思則在社會歷史問題的大背景下發現了“貨幣異化”。馬克思指出,德國的猶太人所要求的是平等的政治權利,這是一項“政治解放”。在保留宗教的同時,法國和美國已經實現了猶太人和基督徒的政治平等。這一現實的社會歷史經驗已經表明,猶太人并不需要放棄宗教就能獲得平等的市民權利。但是,“政治解放”完成以后,人的生活依舊是有局限的,因為他還需要宗教的慰藉。宗教的局限性只是人的現實生活的局限性的一種表達。馬克思借助于對“日常的猶太人”的觀察,得出了如下重要的結論:“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禮拜是什么呢?經商牟利。他們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錢。”[3]49與鮑威爾不同,馬克思把宗教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要素。相對于市民社會的其他要素而言,宗教并不是其他要素的原因,而只是人的世俗生活的局限性的一種表現。因此,馬克思提出,“從經商牟利和金錢中解放出來”就是“現代的自我解放”,換句話說,“貨幣異化”成了“人的解放”必須揚棄的障礙。
二、“貨幣異化”的兩個維度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對貨幣的概念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界定,即“金錢是人的勞動(Arbeit)和人的存在(Dasein)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質(Wesen)”[5]。在這里,馬克思首先把貨幣界定為“同人相異化的本質”;其次,他把這種異化出去的本質更進一步規定為“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貨幣是“同人相異化的本質”,這一界定是有特殊的社會歷史語境的,即現代的市民社會。貨幣是“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的本質(Wesen)”,這一界定表明了貨幣的普遍性特征。不論在什么樣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貨幣都是人通過勞動創造出來,是人的存在的凝結。馬克思通過這一界定表明了,金錢本是人在勞動中創造出來的產物,它是人的存在的凝結,但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卻成了一種控制著人的異化力量。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是因為現代的市民社會不斷地從自身中產生出“猶太人”(即“日常的猶太人”),他們是以經商牟利和發財致富為最高目標的人。貨幣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的生產活動,成了一種統治人的力量,變得“同人相異化”了。這一界定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概念界定,更不是一個嚴格的經濟學表達,但是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為沿著這一界定,馬克思一方面把費爾巴哈和鮑威爾的宗教批判應用到社會批判當中;另一方面,馬克思對社會的批判并沒有局限于費爾巴哈的“類本質的異化”和鮑威爾的“自我意識的異化”等“自我異化”的范疇內談論貨幣異化,而是在“自我異化”之外同時還拓展出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異化,即社會關系異化的內涵。
“貨幣異化”的第一個維度是,它是“人的自我異化”。按照馬克思對貨幣的界定,“貨幣是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的本質”。因為貨幣既是人的勞動的本質,又是人的存在的本質,因此貨幣具有超越于個人的具體勞動之上的普遍價值,它能夠交換到一切具體的勞動和一切具體的個人所創造的產品。作為自然人,每一個人都有著多樣化的需要體系,但是每一個人由于自身先天素質和后天能力的差異,只能從事有限種類的勞動,創造有限的產品。為了滿足自身多樣化的需要,每個人都需要一種普遍的勞動產品,他擁有的這種勞動產品越多,他就能滿足自身越多樣的需要,而且只有當他的勞動產品能夠交換到普遍的勞動產品時,他才能用普遍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具體勞動的產品,他的勞動才是有價值的。貨幣作為人的具體勞動的產物卻具有凌駕于一切具體勞動之上的價值,人在勞動中創造了貨幣,同時也創造了自己世俗的上帝。在現代的市民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猶太人”,即以經商牟利和發財致富為最高目標的人,貨幣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的生產活動,成了一種統治人的力量,變得“同人相異化”了。因此,馬克思把“貨幣異化”稱為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異化的最高表現”[3]49。“實際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錢。金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錢蔑視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變成商品。金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獨立的價值。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價值。金錢是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質;這種異己的本質統治了人,而人則向它頂禮膜拜。”[3]52
貨幣是人的自我異化的表現。其內涵是,人創造了貨幣,貨幣卻反過來統治了人。馬克思對貨幣異化的這一內涵的批判與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批判有著同樣的理論邏輯。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批判是對人的自我異化的批判,即宗教是人所創造的,例如宗教是“類本質”、“自我意識”的表達,但是卻變成了控制人、統治人、壓制人的存在。馬克思在這里采用的是同樣的論證邏輯,即貨幣是人的勞動創造,但是貨幣最終卻成了壓迫人、控制人的力量。
“貨幣異化”的第二個維度是,它是人的相互異化。在這個維度上,馬克思把“貨幣異化”稱為“現代的反社會的要素”[3]49發展的頂點,即“貨幣異化”造成了現代市民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如同狼對狼一樣的關系。馬克思所稱謂的“現代”是與“舊社會”相對的,舊社會“用一個詞來表達”就是“封建主義”[3]44。馬克思指出,“舊的市民社會直接具有政治性質”,“市民生活的要素”通過特定的形式“上升為國家生活的要素”[3]44,即政治的領域和市民社會的領域還沒有完全分離。隨著封建主義瓦解,人類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紀元,政治領域與市民生活的領域分離,政治國家從市民社會中獨立出來。“政治國家的建立和市民社會分解為獨立的個體……是通過同一種行為實現的。”[3]45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標志著人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形成兩個獨立的領域。“猶太精神隨著市民社會的完成而達到自己的頂點;但是市民社會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倫理的、理論的關系變成對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統治下,市民社會才完全從國家生活中分離出來,扯斷人的一切類聯系,代之以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3]54
“猶太精神”是發財致富的精神,表現為無限度地追求金錢和貨幣。由于貨幣是“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的本質”,因而現代市民社會中的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必須借助于貨幣的力量才能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隨著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彼此獨立,人在政治生活中完成自己的類生活,在市民生活完成的是私人生活。“實際需要、利己主義是市民社會的原則;只要市民社會完全從自身中產生出政治國家,這個原則就赤裸裸地顯現出來。實際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錢。”[3]52與政治生活關心普遍利益不同,市民社會中的個人以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而金錢作為“人的勞動和人的存在的本質”成為決定一個人的需要和利益能否得到滿足的最為重要的手段,同時也成為衡量一個人的個人價值的最高標尺,一個人掌握的金錢的數量直接決定著他的生活狀態和個人地位。在私人利益的驅動之下,每一個人為了掙錢而互相把對方視為自己發財手段,人與人陷入相互敵對的關系之中。可見,人的相互異化是市民生活中人與人社會關系的異化,而人的自我異化則是人與自己類本質的異化。
三、“貨幣異化”的揚棄
馬克思對于如何才能揚棄“貨幣異化”的思考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單單從《論猶太人問題》必須回答如何實現“人的解放”來談揚棄“貨幣異化”的重要性,這種做法遠遠不夠。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揚棄“貨幣異化”并沒有把《論猶太人問題》放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脈絡中來考察。事實上,我們之所以關注“貨幣異化”的揚棄,是因為這里涉及他對于“貨幣異化”的兩個維度之間的關系的思考。在回答如何揚棄“貨幣異化”時,馬克思涉及了“人的自我異化”與“人的相互異化”何者更為根本的問題。盡管這個問題存在著邏輯上的“循環論證”,但是馬克思思考的側重點表明了他理解問題的獨特思路以及他進一步探究這個問題的努力方向。
馬克思在觀察“日常的猶太人”的生活時,發現了“經商牟利”和“金錢”對人的控制。因此,他提出,“從經商牟利和金錢中解放出來——因而從實際的、實在的猶太教中解放出來——就會是現代的自我解放了。”[3]49“如果有一種社會組織消除了經商牟利的前提,從而消除經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這種社會組織也就會使猶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識就會像淡淡的煙霧一樣,在社會的現實的、生命所需的空氣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如果猶太人承認自己這個實際的本質毫無價值,并為消除它而工作,那么他就會從自己以前的發展中解脫出來,直接為人的解放工作,并轉而反對人的自我異化的最高實際表現。”[3]49
馬克思在這里談到了兩個方面的解放,即人的社會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人的社會解放是說,社會從金錢和貨幣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人與人在社會生活中不再是相互敵對的個體。人的自我解放說的是,人消滅金錢對自己的控制,不再把貨幣視為最高的價值。正如馬克思所言,“人的自我解放”是“人的社會解放”的“另一方面”,它們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樣,很難說出哪一方面是原因,哪一方面是結果,哪一方面更根本,哪一方面較次要。但是,馬克思本人的思考是有傾向的,或者說是有側重的,他實現“人的解放”的最后的落腳點是,“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3]55這表明馬克思認為人的社會解放更為根本。這種看法源自于馬克思把人的相互異化視為自我異化的根源。
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自我異化”是“人的相互異化”的結果。馬克思說,“在利己的需要的統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產品和自己的活動處于異己本質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異己本質——金錢——的作用,才能實際進行活動,才能實際生產出產品。”[3]54正是因為市民社會的每一個人都被“利己的需要”控制著,人與人像狼對狼一樣,每一個人離開金錢都將寸步難行,所以每一個人都必須使自己的具體勞動獲得金錢的價值,金錢被人視為自己的最高本質,只有這樣人才能進行“實際的活動”。馬克思還提到,“抽象地存在于猶太人的宗教中的那種對理論、藝術、歷史的蔑視和對于作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視,是財迷的現實的、自覺的看法和品行。”[3]53蔑視理論、藝術、歷史和蔑視作為自我目的的人,是“人的自我異化”的表現;財迷則是相互異化的人。前者是后者在行為中的表現,表明了后者更為根本。由于馬克思認為“人的相互異化”是“人的自我異化”的根據,所以他才提出只有實現社會解放,才能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
四、小結
馬克思對于“貨幣異化”的思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史課題。他對其兩個維度之間關系的思考首先將他與布魯諾·鮑威爾區別開來。“人的自我異化”與“人的相互異化”在邏輯關系上存在著解釋學上“循環論證”的可能。首先,“人的自我異化”可以被解釋為“人的相互異化”的原因:由于人把貨幣視為自己最高的本質,把掙錢視為最高的職業,為了掙錢,每一個人對待其他人都像狼對狼一樣。其次,“人的相互異化”也可以被解釋為“人的自我異化”的原因:由于市民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像狼對狼的關系一樣,每個人只有靠著貨幣的力量才能保證自己的生存,因此人把貨幣視為最高的本質。在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時候,鮑威爾采納的是第一種解釋邏輯:由于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把宗教視為各自的最高本質,因此他們在社會關系中相互敵對,造成了現代的“猶太人問題”,解決猶太人問題必須對宗教進行批判,即批判人的自我異化。馬克思采納的則是后一種邏輯,他注意到了貨幣對于現代人的生活的控制,提出必須消滅貨幣造成的異化,在對“貨幣異化”的分析中,馬克思提出“相互異化”是“自我異化”的根源,必須對異化的社會關系進行批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猶太人問題”。
馬克思對于“貨幣異化”,尤其是其“相互異化”維度的思考,預示著馬克思更進一步的探究方向。對于“貨幣異化”中人的“相互異化”的考察,必然要求對現代市民社會中的社會關系做徹底的研究,這是馬克思寫作“巴黎筆記”和“巴黎手稿”的主要目的。另外,“自我異化”和“相互異化”還為馬克思的“穆勒評注”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對于“貨幣異化”提出了許多重要認識。他提出,在貨幣中,“表現出異化的物對人的全面統治。過去表現為個人對個人的統治的東西, 現在則是物對個人、產品對生產者的普遍統治。”并且提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使得“自我異化不僅以自我異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異化的形式表現出來”[6]。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在“穆勒評注”中還從“相互異化”引申到了“交往異化”,并在這一議題下更進一步深化了對“相互異化”的研究。
參考文獻:
[1]BAUER.Die Judenfrage[M].Braunschweig: Druck und Verlag von Friedrich Otto, 1843:62.
[2]鮑威爾.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J].現代哲學,2013,(6).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ORGEL.Julius Carlebach, 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J].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1980,(21).
[5]Marx Engels Werke: Band 1[M].Berlin: Dietz Verlag, 1983:37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0.
[責任編輯:高云涌]
收稿日期:2015-11-1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神圣家族》及其當代價值研究”(15CKS001)
作者簡介:李彬彬(1983—),男,講師,哲學博士,從事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中圖分類號:B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462X(2016)06-0010-05
·當代哲學問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