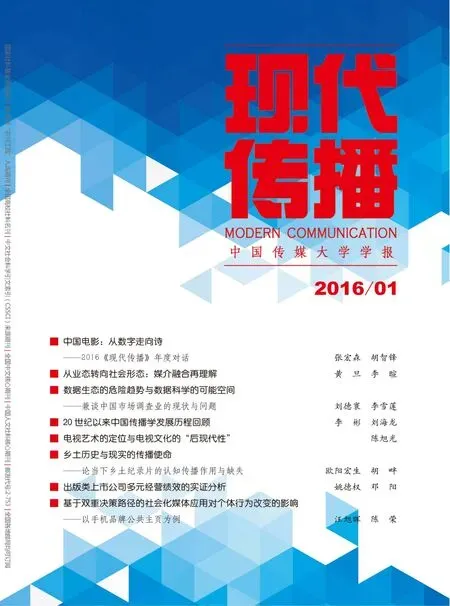互聯網與中國新聞業的重構*——以結構、生產、公共性為維度的研究
■ 張志安 吳 濤
?
互聯網與中國新聞業的重構*——以結構、生產、公共性為維度的研究
■ 張志安吳濤
【內容摘要】 伴隨著互聯網用戶的激增和互聯網產業的蓬勃發展,中國新聞業的深層結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互聯網改變了中國新聞業的產業結構、受眾結構、股權結構和權力結構,同時,也深刻影響著中國新聞生產實踐的變革,呈現出生產主體從專業化到社會化、生產機構從封閉性到透明性、生產周期從周期性到循環性等變化趨勢以及軟性新聞主導的特點,使得在中國本就碎片化、局部呈現的新聞專業主義又面臨新的重構挑戰。而在新的重構過程中消解與促進、挑戰與機遇因素并存,新聞業的公共性面臨新的隱憂。
【關鍵詞】互聯網;中國新聞業;新聞生產;公共性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當代中國新聞業:變革與演進(1992—2012)”(項目編號:1209087)的研究成果。
過去10余年,互聯網正在深刻改變乃至重塑著中國新聞業。以新浪、騰訊等為代表的商業門戶網站,以東方網、南方網等為代表的重點新聞網站,和以人民網、新華網為代表的媒體新聞網站,已經成為主流媒體版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傳統報業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生存危機,網絡新聞業無論是用戶規模還是媒體市值都相當可觀。以整體的用戶規模而言,根據CNNIC第36次報告,截至2015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6.68億,中國網民的人均每周上網時長達25.6小時,網絡新聞的用戶規模達到5.54億人,也就是有5.54億人通過互聯網獲取新聞;從媒體市值來看,截至2015年6月15日,騰訊的市值已高達11480億人民幣,網易也高達1184.9億人民幣。
伴隨互聯網用戶規模的擴大和互聯網產業的蓬勃發展,從產業結構、管理制度到生產方式,互聯網正在改變著中國新聞業的深層結構和整體生態。本文試圖從新聞業的結構(structure)、行動者(agency)的生產實踐、傳媒的公共性(publicity)三個維度來總結和探討互聯網對中國新聞業的影響。
一、中國新聞業市場和權力結構的雙重變化
新聞業的結構,包括用戶結構、產業結構、產權結構和管制結構等不同維度,主要體現在市場和權力兩個層次。互聯網的日益應用和普及,使中國新聞業在結構層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一)互聯網用戶增長改變受眾結構
受眾結構的變化直接表現在傳統媒體受眾的減少、網絡用戶規模的增長,尤其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于“不看報紙、少看電視”的使用習慣,更加依賴通過手機、Pad等終端來隨時隨地的上網,移動網民規模日益擴大。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36次(CNNIC)報告顯示,手機網民規模達5.94億,較2014年12月增加3679萬人,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年底的85.8%提升至88.9%。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日趨完善、手機終端的大屏化以及手機應用體驗的不斷提升,手機作為網民主要上網終端的趨勢進一步明顯。
為滿足新型受眾的移動化閱讀需求,各大媒體紛紛發力移動互聯網,推出大量新聞App。根據人民網研究院2013年1月對國內1486份報紙的統計顯示,推出新聞App的有170家,占報紙總數的11.4%(1)。2015年,在澎湃新聞的引領下,傳統新聞媒體更是掀起新一輪建設新聞客戶端的高潮,并讀、無界、上游、封面、猛犸、九派、南方+等紛紛亮相,據清華大學沈陽發布的《未來媒體趨勢報告》統計,110家官方媒體中60%已擁有自己的客戶端。
(二)互聯網產業收入改造產業結構
從傳媒產業的市場結構看,互聯網已經遠超報業,成為第一大傳媒產業。2014年,互聯網業務(包括網絡加移動增值)規模達到傳媒產業總體市場的47.2%,幾乎占據了傳媒產業的半壁江山,而傳統報業的市場份額已經下降到5.1%。(2)
自2012—2013年傳統報業出現“拐點”以來,在互聯網行業的猛烈沖擊下,傳統報業持續衰退,2014年更是呈現“斷崖式”下滑局面。據清華大學發布的《2015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大趨勢》顯示(3),2014年全國報紙印刷用紙量約為270萬噸,比2013年減少了近1/4,報紙發行量事實上下降了25%。作為傳統報業收入主要來源的廣告市場,也連續4年負增長,2014年的下降幅度達到15%,2015年報業廣告則普遍下降20%以上,個別報紙甚至降幅高達30%。與傳統報業廣告市場的慘淡相比,2014年網絡廣告的收入規模則超過了1500億,增長了40%。
(三)互聯網產權突破改變股權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媒體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運作”的雙軌制,產權結構比較單一,始終堅持國家控股。進入2000年以后,政府加快了傳統新聞業融資政策、產權結構的改革步伐,允許報業集團上市進入股票市場,比如2004年12月《北京青年報》在香港上市,但仍規定非國有股權不得超過49%,以保持國家的控股地位。(4)此后,盡管陸續有粵傳媒(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新華傳媒(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等在國內上市,但報業集團的產權結構始終是國家主導。
但是,以騰訊、網易、新浪、搜狐為代表的IT企業,其創業資本主要來源是海外基金,加上在美國納斯達克等海外資本市場整體上市,這些商業新聞網站的產權結構實質上已經突破了中國新聞業必須“國有”的傳統。以騰訊為例,南非的兩家外資集團MIH 和ABSA分別占有34.27%和6.32%的股權,以馬化騰為首的創業團隊占有剩余股權。考慮到商業新聞網站在當下中國新聞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影響,某種程度上看,中國新聞業的“事業單位”的性質已被徹底改變,形成了傳統媒體堅持國有、網絡媒體國有與私有并存的全新格局。
(四)互聯網管制體系改變權力結構
過去,報刊和廣電的準入門檻和行政管理歸口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廣電總局,而互聯網業務的牌照多年來主要由國務院新聞辦來管理,而整體的輿論導向皆由宣傳部門主導。如今,互聯網新聞業務的歸口管理已經從國務院新聞辦轉至2011年成立的“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辦公室”。而且,隨著網絡成為輿論調控和管理的“重中之重”,2013年國信辦與國新辦正式分家,成為互聯網的主要監管機構。加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廣電總局已合并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總體上看,網絡新聞業的監管呈現出集中化、升級化特征。
再具體到新聞審查的機制看,互聯網新聞業跟傳統新聞業最主要的不同有三點:第一,監管主體的“聯動性”更強。由“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辦公室”來主導,公安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參與協同治理,過去網絡新聞業“多龍治水”的局面得以根本性改觀。第二,管理權限更加集中。過去“互聯網的管理規則雖然出自于北京,但是每個省都有自己的管制規定,甚至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性自治條例,結果在不同的地方,存在著很大的政策、法規、服務和價格的變異”。(5)現在,由于主流的商業網站和媒體網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尤其在北京特別集中,由此導致網絡新聞的監管呈現“屬地化”特征,其監管效率更高。第三,“事先審查”和“自我審查”的強化。過去,傳統媒體采取的是審看制、追錯制,而網絡媒體采取的則是過濾制、糾錯制,主要體現在:建立防火墻,將臉書、推特等一些國外網站內容屏蔽過濾于國內網絡媒體之外;采用關鍵詞過濾技術,將一些涉及敏感話題的關鍵詞和諧掉,使受眾無法搜索到與該關鍵詞相關的內容(6);及時有效地糾錯,將出現問題的違法或敏感內容盡快刪除乃至全部從網絡上清除干凈。據稱,我國的互聯網管制在5—30分鐘內可以將接近30%的“違規內容”刪除,接近90%的“違規內容”在發表后的24小時內會被刪除(7)。總體上看,過濾制提高了新聞發布事先審查的效率,糾錯制一方面能快速消除網絡上負面、敏感信息的不良影響,另一方面也給新聞網站在敏感議題上“打擦邊球”提供了一定的機會。
二、傳統新聞業生產變革與網絡新聞業實踐特點
Mitchelstein和Boczkowski(2009)指出(8):以往對網絡新聞的研究中缺乏歷史性視角,對于網絡新聞業的研究需要超越新聞編輯室和新聞業的層面引入新的研究視角以便更好地理解“誰開始生產了網絡新聞,生產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怎樣的故事在這樣的動力機制下被生產出來”。下面,我們試圖引入一定的歷史性視角,對傳統新聞業與網絡新聞業的生產方式進行簡要對比,總結傳統新聞業的生產變革和網絡新聞業的實踐特點。
(一)傳統新聞業的生產變革
在互聯網的沖擊和影響下,傳統媒體利用門戶網站、論壇、博客、微博等互聯網技術平臺對其已經形成的新聞實踐“慣習”進行再造,通過流程重構、機制調整和形態融合等方式進行了顯著的生產變革,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生產主體:從專業化到社會化
從行動者的角度來說,由于采集新聞信息的高成本,傳統的新聞生產的行動者是由新聞組織機構雇傭的職業的新聞從業者(記者、編輯)進行,是一種專業化組織化的生產行為。而在“人人皆是記者”的互聯網時代,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介入新聞生產領域,通過個人微博、微信等發布自己目擊甚至調查的新聞。當下,“公民新聞”主要有三種形態:一是目擊新聞,即重大事件目擊者快速發布現場照片和滾動播報所見所聞;二是網絡爆料,以知名爆料人周筱為代表,主要接受匿名消息源對公權力機構或官員進行網絡輿論監督;三是社會動員,即普通公眾為了激發網絡情感、形成網絡輿論而進行的“網絡抗爭”,其主要目的在于發起環保、維權等社會運動。再加上傳統媒體對用戶生產內容(UGC)的吸納和整合,越來越多的公眾有機會參與到原先的專業化新聞生產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新聞業從專業化組織化到社會化生產的轉變。新聞生產不再僅僅是一個專業組織的封閉生產形態或者機制過程,而是共同參與、協同生產的活動,新聞業的把關人逐漸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合作、廣泛參與的方式進行新聞生產活動。
2.生產機構:從封閉性到透明性
傳統的新聞生產過程是相對不透明的,新聞生產被置于后臺,很少有機會為公眾所見。但在互聯網語境下,新聞線索的發現、與信源的聯系、階段性報道的發布,使得新聞把關的控制過程更加開放、直接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在這種新聞生產“可視化”的新生態中,受眾既可以了解新聞生產的過程,還可以頻繁地參與互動(9)。由此帶來傳統媒體組織透明性的強化,主要體現在“向公眾說明”和“邀公眾參與”兩個層面,“透明意味著在新聞報道中植入一種新的意識,說明新聞是如何獲得的以及為什么要用這種方式表達”。(10)比如:新聞行業的爭議性話題,會在微博等網絡平臺上激烈討論,強化了公眾對新聞倫理和規范的認知;調查記者利用微博等進行采訪突破,尤其當遭遇地方政府和官員阻撓時進行的滾動直播和在線動員,拉近了職業新聞人跟受眾之間的距離;大量媒體人開設實名微博,利用微博等新媒體手段來服務于新聞生產、轉載和發表報道……這些都大大增強了新聞機構的透明性。
3.生產頻率:從周期型到循環型
互聯網語境下,傳統的截稿時間不復存在,24小時滾動循環成為常態。比如傳統媒體在報道地震等突發性事件時,利用微博等24小時不斷滾動發布地震救災進展,并對已經刊發的紙質報道內容進行補充修訂,突破了截稿時間的限制。為了保證24小時滾動循環生產的運行,媒體機構也必須在組織制度上做出相應調整,采用新的生產流程和考評機制。以人民日報的微博運營為例(11),報社將微博作為“獨立的媒體”來運作,微博的發起、籌備、運營統一交由《人民日報》編輯采訪的總樞紐——新聞協調部負責,打破部門限制,人民日報社的全體編輯、記者包括評論員都要參與到微博內容生產當中。生產頻率從周期型到循環型的轉變,使得針對重大事件的“直播”成為一種常態,而與之相對應,新聞從業者的工作強度與工作壓力也會顯著提升。
4.生產資源:信息源結構的多元
傳統的新聞生產,在信息源的篩選過程中,新聞記者主要靠日積月累的人際關系網從信息源那里獲取新聞線索,而且對不同類型新聞線索的依賴和習慣背后是新聞作為社會建構的“框架”,是社會權力結構的“再現”。正如塔奇曼所言(12),“新聞從業者更傾向于選擇體制內的信息源,而不是普通人提供的信息”,造成了政府部門官員、專家、精英人士更多地成為記者的信息源,出現在新聞報道中。遇到特殊情況,新聞記者則依賴于深喉等線人的報料,如水門事件。而互聯網的興起,至少從兩個層面在改變傳統的消息源權力結構。一是,機構消息源具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和設置議題的能力,比如大量的政務微博(薄熙來案中濟南中院的直播)、企業微博(農夫山泉和《京華時報》事件中的企業微博);二是普通草根的聲音更多在網絡新聞中占據明顯位置,以及更多地被傳統媒體的報道所吸納。
5.生產壓力:網絡民意的影響擴大
過去,控制新聞的力量主要來自政府權力、商業利益和專業主義,受眾的興趣和需要主要通過市場化的商業驅動來發揮作用。如今,由于公眾輿論在傳統媒體的話語空間中很難生成,因此,互聯網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輿論場的核心平臺,甚至中國的網絡輿論已經呈現“微博化生存”的態勢。
由此導致網絡民意對新聞生產的影響力大大增強:一方面,傳統媒體的調查報道借助互聯網迅猛傳播,快速激發的網絡民意和社會影響對公權力機關會造成監督壓力,從而形成網絡輿論監督和傳統媒體批評報道的合力,有利于推動國家和社會治理;另一方面,職業新聞人邊進行報道,邊進行微博直播、實時掌握網絡民意。而整體上,相對民粹化、非理性、群體極化的網絡民意對記者的價值判斷和報道立場會產生負面影響。總結來看,網絡民意對新聞生產的影響是利弊共存的。
(二)網絡新聞業的實踐特點
互聯網時代新聞生產方式的變革不僅表現在傳統媒體利用門戶網站、論壇、博客、微博等互聯網技術平臺產生新的特點,還表現在以新浪、騰訊為代表的商業網站自身新聞生產所呈現的新特點。
1.從記者主導轉向編輯主導
傳統新聞生產的主體行動者是記者,主要負責現場采訪和快速寫稿,稿件編輯雖然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審核、編輯和排版,但稿件的關鍵部分卻受制于記者的供稿。但是在互聯網時代,根據《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的相關條例,新浪、騰訊等商業網站只有新聞編輯和刊載權,而沒有原創新聞采訪權,因而其生產主體主要是編輯。目前,網絡新聞多數是非原創的,供稿來源主要還是傳統媒體,編輯為吸引網民點擊或擴大稿件影響,往往需要對標題做深加工。由此,傳統新聞報道中記者主導的高成本原創被“復制/改編+聚合(草根新聞)+少數原創”的編輯主導所取代,記者在場的offline research(線下觀察)被編輯不在場的online research(在線觀察)所取代。網絡編輯對新聞的選擇、整合和挖掘決定了新聞產品的質量,以及能否吸引更多的受眾,編輯的素質高低越來越多地決定了網絡新聞的傳播效果。
2.從作為產品到作為過程的新聞
傳統的新聞生產機制是由記者主導,嚴格遵循截稿和發稿周期,在規定時間內集中采集、合成和分發。新聞報道是社會化的產品,由編輯部主導,以中心化的機制一天一次刊發,實現一對多的單向傳播。同時,新聞作為產品,衡量其優劣的標準主要是專業品質。網絡新聞則不同,依托海量、開放的發稿平臺和聚合空間,商業網站的傳稿和發稿不再有嚴格的截稿時間,可以實現每周7天、每天24小時的滾動發布和即時更新,制作和發布的新聞專題也可以根據新聞事件的動態進展而不斷更新和補充,作為過程的新聞可以只有開始、永不結束。此外,基于相對平等和開放的公眾參與性,網絡新聞具有內在的“去中心化”的偏向,其傳播和擴散由鏈接促發,是一個不斷整合、加工和添加的動態過程。
3.新聞生產的偏向從硬變軟
傳統新聞生產的新聞內容以整體、深度、一次性、文本性的方式呈現,在新聞形態上強調事實至上,在新聞價值上崇尚由快至深,不斷逼近真相的努力和公眾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使其對“硬新聞”的社會意義更加看重。對于網絡新聞生產來說,其對用戶需求的滿足、對技術表達的注重、對點擊量的追求,使其在新聞形態上更加重視視覺至上而非事實至上。由于娛樂化、碎片化、視覺化的文本,最適合通過移動互聯網的載體和工具進行發布和傳播,也最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爆炸式、病毒式的傳播效果,所以商業網站的新聞內容逐漸趨向速度而非深度、強調體驗而非質量。
總體上看,伴隨著網絡新聞的日益規模化和主流化,軟性新聞業(soft journalism)開始興起,具體體現在從傳統的提供公眾需要的(needed)轉向提供公眾想要的(wanted),從硬/軟兼顧的公共利益偏向轉向逐漸偏軟的用戶興趣偏向,從讀者口碑驅動的質量至上評估轉向用戶點擊率驅動的影響至上標準,其背后是商業主義的強化和專業主義的弱化。
三、社會控制的新趨勢與傳媒公共性的隱憂
我們探討互聯網對中國新聞業的整體影響,歸根結底要回到兩個關于新聞業的核心問題:自主性和公共性。前者強調的是新聞生產的獨立性,即互聯網能否為中國新聞業“賦權”,創造更大的報道空間和傳播自由;后者追求的是,在轉型社會的中國,新聞業能否在更大程度上承擔其公共責任,以更好的公共性來服務和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總體上,從社會控制的新趨勢和互聯網新聞業的公共性角度看,值得關注的變化和趨勢主要有三點:
(一)過度的商業控制導致專業倫理的失范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傳媒市場化,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中國媒體的“自主性”發揮著“解放性”的積極作用,有利于將媒體在拉向市場的過程中更加注重為受眾服務,并通過調查報道和深度時評等實踐輿論監督、進行公民啟蒙和推動社會進步。但過去10余年,市場化的負面效應正在都市報、電視娛樂節目等方面體現出利益至上、過度煽情等商業主義的問題,市場化所扮演的“壓制性”的消極作用,正在逐步體現出來,同時越來越集中地體現在網絡新聞實踐中。因此,對過度市場化的反思正成為審視網絡新聞業的重要命題。如有學者指出:“媒體的市場化進程培育了一種新型的媒介—受眾關系,使得媒體更傾向于對受眾的市場需求做出回應。媒體的改革使得中國的新聞業從意識形態到專業主義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從毛時代的政黨—媒體模式轉變到改革時代的市場—受眾模式……互聯網更是加速了這一模式轉變的進程。”(13)
從新聞生產的自主性看,互聯網行業對傳統媒體的沖擊,促使傳統媒體在轉型和自救過程中,越來越多地采取“事業部制”、實施整合營銷等理念和做法,從而導致編輯部門和經營部門之間的“防火墻”崩塌,由此,對新聞生產的專業原則和獨立性產生極大損害。而以商業網站為代表的網絡新聞編輯部,盡管在吸納用戶生產內容(UGC)和探索原創新聞報道上有一些專業主義的努力,但整體上,受制于“市場導向新聞業”的公司文化驅動,其新聞生產的專業性和自主性整體上均比較弱。而且,這些商業公司運營新聞網站的目的,歸根結底在于直接盈利或服務于公司的品牌和利益,而非通過披露真相來滿足公眾利益,因此資本力量主導下的商業控制會對編輯部產生更加嚴苛的約束機制,甚至導致新聞網站實際上扮演著商業公司的“公關部”的角色。
此外,新聞尋租、有償不聞等倫理缺失也是網絡新聞業讓人痛心疾首的現象。據媒體報道披露,不少商業網站的財經頻道通過對準備IPO的企業進行報道,抓住和放大企業存在的問題,通過敲詐勒索來獲取高額廣告或“封口費”;一些商業新聞網站內部存在“大客戶保護名單”,只要大企業每年給網站投放一定額度的廣告,網站就可以協助這些大企業屏蔽負面新聞,這種“有償不聞”的做法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極大傷害;一些侵犯公民隱私權、名譽權的新聞或“爆料”,在網絡上被輕易地廣泛傳播,而相關的把關機制卻形同虛設……這些專業倫理缺失的現象,在當下和未來的網絡新聞業可能會愈演愈烈。
(二)政治控制的內化導致自我審查的強化
一方面,傳統的行政管理和權力控制,無論對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媒體的影響都在不斷加大。伴隨著互聯網監管力度的強化和管制結構的調整,對網絡新聞的監管和輿論治理正在走向“行政化”和“法制化”合力的趨勢。另一方面,外部政治控制的強化,再輔之以關鍵詞過濾和審查技術的不斷升級,導致網絡新聞生產過程中的“自我審查”現象也越來越嚴重。
筆者關于網絡新聞從業者的一項調查顯示(14),對“新聞網站編輯記者應當主動淡化不利于政府的信息”的態度上,受訪者的得分均值為3.07分,傾向于較為肯定。可見,網絡新聞從業者面對行政控制的壓力感知比較強烈,外部政治控制容易內化,致使其在新聞生產過程中主動規避風險。另外一項研究也表明(15),即便是比較善于突破的調查記者群體,在強有力的權力管控和組織規范之下,調查性報道生產過程中自我審查普遍化,調查記者主要通過使用微博等互聯網技術提升新聞生產效率,進行新聞突破、社會動員乃至職業抗爭只是非常規情境下的極少數偶發事件而已。
(三)網絡輿論的極化導致公共空間的弱化
傳統媒體時代,受眾對媒體的直接影響相對較弱,由民意造成的社會壓力往往只有在極端事件中才能引發,常規新聞生產中記者和編輯部受到民意的影響并不大也不直接。而進入互聯網時代,以論壇、博客、微博為主的平臺給網民提供了活躍的表達空間,由此也容易針對熱點事件形成洶涌的網絡輿論。不過,當下的網絡輿論場卻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缺陷,比如:由于敏感言論的有效管制,導致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無法充分表達,致使網絡輿論對真實民意的體現有所不足;由于公民社會的不成熟和狹隘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局部失控,導致網絡輿論的情緒化和非理性傾向明顯;由于微博等技術平臺碎片化、爆炸式傳播的特點和效能,導致事實和觀點的割裂、難以在網絡上形成真正持久的深入對話,因而也難以形成理性的社會共識;由于“結構性怨恨”和“普遍不信任”的社會心理機制,網絡輿論很容易走向“群體極化”甚至“對抗性”文化的方向。
盡管財新網等少數專業性的網絡平臺,嘗試在每條新聞下方將本站跟帖、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等不同渠道的評論“抓取”在一起,試圖建立一種基于事實基礎上觀點表達的互動機制和表現形態,但這種在提供準確真實事實、匯聚不同渠道的言論方面試圖推動理性網絡空間形塑的努力,總體上仍然非常稀缺,其作用也相對較小。基于網絡輿論的分化、輿論的割裂、輿論的極化等上述特點,很難真正從理性、積極的方向持續推動中國新聞業的進步和發展,相反,可能會導致作為傳媒的互聯網變成更加弱化的公共空間。
四、結語
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從未像西方新聞業一樣“已經形成了闡述這些專業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話語,并且有相對獨立于商業和政治利益的專業規范機制”(16),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是未完成的進行時。當下,在互聯網重塑中國新聞業的整體語境中,本已局部化、碎片化呈現的專業主義又面臨新的重構可能,其中既包含著有利于新聞專業主義建構的因素,也包含著不利于新聞專業主義建構的因素。從行動者如何影響結構的角度看,無論是傳統媒體利用互聯網平臺進行新聞生產實踐,還是商業網站自身的新聞生產,以記者編輯為代表的職業新聞人和以草根新聞為代表的普通公眾,他們之間的合作、博弈直接影響著新聞專業主義建構。
首先,新聞專業主義要求的準確、客觀、公正原則,主要是針對職業新聞人而言的。網絡新聞生產實踐中,職業新聞人面臨兩方面的挑戰。一是“職業新聞人已經不再滿足于傳統的把關人角色,而是利用博客、微博等互聯網技術工具試圖超越它”(17),在傳統媒體利用互聯網進行的新聞生產實踐中,職業新聞人“參與者”角色在不斷強化。在大量公共事件中,記者利用微博進行的在線報道和網絡動員,增強了其直接參與事件的幾率和風險,由此對其“記錄者”的專業角色造成偏差。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參與者”的角色使得職業新聞人自身的情感和情緒很容易被表達出來。這種將自我置于新聞的中心舞臺,將情緒裹挾在新聞報道中的傾向,容易產生如石扉客所概括的“社運型”記者現象(18);二是在商業新聞網站新聞生產中,作為職業新聞人的網站編輯,過度迎合公眾對視覺、娛樂、煽情新聞的偏好,生產和推送過度碎片化、娛樂化的軟新聞,造成網絡新聞“標題黨”現象盛行,使得商業主義驅動的生產機制完全主導,而新聞專業主義則更加缺失。
其次,普通公眾在網絡新聞業的專業主義建構中扮演的角色是雙重的,他們既是職業新聞人建構新聞專業主義的有效助力,也以一種去“專業化”話語挑戰著職業新聞人對傳統專業主義規范的堅守和對自我作為職業權威的捍衛。一方面,普通公眾已經更加廣泛地參與到新聞生產實踐中。他們的參與擴大了新聞報道的空間,豐富了新聞報道的內容,也改變著傳統的消息源權力結構,有助于職業新聞人擺脫對于體制內信息源的依賴。另一方面,新聞作為“一種詮釋現實的權力實踐”,在傳統媒體時代,原有的新聞場域是由組織內的新聞專業人士主導確立的,而在互聯網語境下,這種詮釋現實的權力實踐和話語權威正面臨普通公眾發起的嚴峻挑戰,比如:技術賦權使得新聞生產工具資料社會化、全民化,專業人士面臨場域內新入者、即普通公眾的激烈競爭;過去,新聞從業者依靠專門訓練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以及與大眾絕緣的方式獲得專業資本,如今在改編、復制和聚合為主的網絡生產模式之下,傳統新聞專業的核心能力被邊緣化(19);大眾不僅能夠通過市場對新聞加諸間接影響,而且可以通過公共輿論參與干涉新聞生產,職業新聞從業者在新聞場域內的專業資本在縮小;此外,網絡民意匯聚形成的“去專業化”話語要求新聞業體現與普通公眾的聯系,既要代表公眾、反映底層人民的疾苦,又要參與社會行動、幫助底層人民解決實際問題(20)。于是,大量的網絡傳播實踐都采取了情感宣泄、反諷戲謔、悲情化、標簽化等話語方式,這種易走向極端化的、去專業化話語,不僅與新聞專業主義所要求的“客觀性”格格不入,而且在專業話語和去專業話語之間也很難形成理性對話的空間。
回到社會控制新趨勢和傳媒公共性的關系,我們大體可以這樣總結互聯網對中國新聞業的結構性影響:其一,政治權力的強勢介入和有效監管,未能為互聯網新聞業帶來比傳統媒體更大的報道空間和獨立性;其二,市場驅動的利益短視和逐利傾向,導致互聯網新聞業很難在商業網站建立專業主義的價值規范和品質追求,整體上的煽情主義、商業主義影響了網絡新聞的品質和水準;其三,互聯網技術的傳播賦權和信息突破,給少數公民和機構帶來了提升知情權和表達權的機會,但非理性的網絡輿論又可能會對新聞生產的自主性造成負面影響,“去專業化”的話語也會導致職業新聞人的自我認同感趨于弱化。
綜上所述,在互聯網的影響下,中國新聞業面臨著“雙重尷尬”:一方面,在傳統媒體時代,專業主義的啟蒙和共識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碎片和局部的新聞專業主義又面臨新的重構,而在新的重構過程中消解與促進、挑戰與機遇因素并存。未來中國新聞業的走向,需要媒體管理者在宏觀政策上有更積極的改革、機構所有者在組織制度架構中有更合理的設計,以及新聞從業者在生產實踐中有更專業的追求和更理性的自覺。
(本文為廣州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資助項目的成果之一。)
注釋:
(1) 唐緒軍:《中國新媒體年度報告(2013)》,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2) 參見《2015年中國傳媒產業報告誰才是贏家》,來源:http://www.yejibang.com/news-details-10779.html,2015年7月2日。
(3) 中國社會科學網:《清華大學研究報告:2015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大趨勢》,來源:http://www.cssn.cn/dybg/dyba_wh/201506/t20150615_2035014_9.shtml,2015年6月15日。
(4) Stockmann D.Race to the Bottom:Media Marketization and Increasing Negativit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11,28(3),pp.270.
(5) Yang G.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Preliminary Assessmen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3,12(36),p.457.
(6) King G,Pan J,Roberts M.E.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3,107(02),pp.326-343.
(7) Tao Zhu、David Phipps、Adam Pridgen:The Velocity of Censorship:High-Fidelity Detection of Post Deletions,//22nd USENIX Security Symposium.2013:11.
(8) Steensen S.:Online Journalism and the Promises of New Technology:A Critical Review and Look Ahead.Journalism Studies,2011,12(3),p.321.
(9) 周葆華:《從“后臺”到“前臺”:新媒體技術環境下新聞業的“可視化”》,香港《傳播與社會學刊》,2013年總第25期。
(10) [美]比爾·科瓦奇:《新聞業的十大原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頁。
(11) 涂光晉、陳敏:《媒體微博的內容特色與生產機制研究——以三家報紙的官方微博為例》,《現代傳播》,2013年第3期。
(12) [美]蓋伊·塔奇曼:《做新聞》,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
(13) Tai Z,Sun T.Media Dependencie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the Case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in China.New Media&Society,2007,9(6),pp.991-992.
(14) 張志安、陶建杰:《網絡新聞從業者的自我審查研究》,《新聞大學》,2011年第3期。
(15) 吳濤、張志安:《調查記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職業影響研究》,《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16) 陸曄、潘忠黨:《成名的想象》,臺灣《新聞學研究》,第71期。
(17) Yu H..Beyond Gatekeeping:J-blogging in China Journalism,2011,12(4),pp.379-393.
(18) 石扉客:《“社運型”記者的特征和行事邊界》,《南方傳媒研究》第30期,http://www.southcn.com/nfdaily/media/cmyj/30/04/content/2011-07/01/content_26239520.htm,2011年7月1日。
(19) 李艷紅:《重塑專業還是遠離專業——從倫理和評價維度解析網絡新聞業的職業模式》,《新聞記者》,2013年第2期。
(20) 謝靜:《民粹主義:中國新聞場域的一種話語策略》,《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3期。
(作者張志安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吳濤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公共傳媒管理方向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張毓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