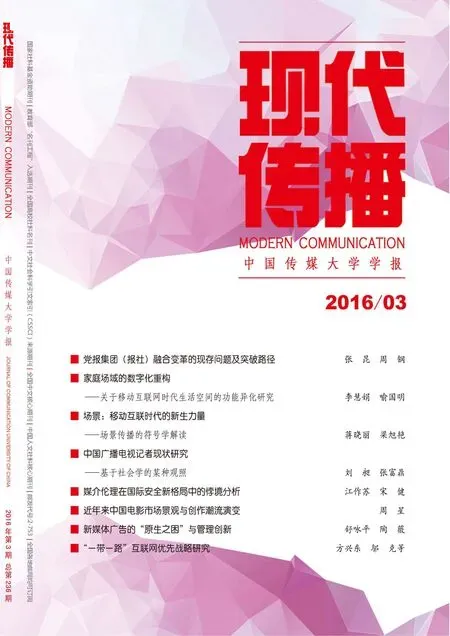全媒體時代政府傳播的新變局
■ 李淑芳
?
全媒體時代政府傳播的新變局
■ 李淑芳
在全媒體時代,政府傳播主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帶有系統性的傳播危機和傳媒變局,表現在傳統的管理運作方式已經難以應付瞬息萬變的傳播現實。全媒體時代政府傳播主體面臨著以下重要變局。
一、傳播模式發生轉向:由點對面的支配型到點對點的平衡型
政府對公眾進行的傳播通常經由大眾傳播媒介來實現。由于傳播地位及信息資源配置的因素,政府傳播大多呈現自上而下、由傳到受的傳播形態。在傳播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方面,“點對面支配型”傳播模式占主要地位。政府傳播主體居于絕對主導地位,面向大眾貫徹傳播目標、控制傳播行為、主導傳受關系。整個傳播過程有賴于政府傳播主體的積極推進。這種傳播模式更重視傳播主體對傳播過程的掌控以及傳播目標的達成,在傳播實踐中與目標受眾存在一定的關系距離。
在全媒體時代,網絡與現實密切聯動,網絡輿情與現實輿情交相呼應。傳受之間的主客體關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傳播權力悄悄地在發生著某種偏移。“支配型”傳播模式日漸被動,“平衡型”的傳播模式悄然興起。在這種“平衡型”的傳播模式中,傳播主體與客體彼此之間聯系方便快捷,互動頻繁。如政府傳播主體的法人賬號直接開在了微博微信上,開在每個點擊它的網友的電腦或手機顯示屏上,彼此直面以對,實現了零距離的實時對接。政府傳播主體可以隨時捕捉輿論變化,主動適時發布信息或應對網友提問,爭取彼此之間的良好互動,尋求在認識和反應的基礎上與其受眾發生聯系。這一模式意味著傳播者愿意對受眾的需求、興趣和反響做出反應,愿意將更可能存在于非大眾傳播情形中的那種人際傳播關系引進大眾傳播。政府傳播主體更具有人性化色彩。應該說,這種“點對點平衡型”的傳播模式是一種更加符合現代社會理念的理想的傳播形態。從傳統大眾傳播到全媒體時代,由“點對面支配型”到“點對點平衡型”,政府傳播的模式在不知不覺之中出現了重大轉向。這種轉向來自于全媒體帶來的深刻變革以及由技術革命帶來的內部的嶄新的社會動員機制。
二、傳播生態發生逆轉:由政府一言九鼎到網絡眾聲喧嘩
傳播生態是指“處于情景之中的傳播活動或過程”,①是傳播系統內部的組織、構成、沖突及其與個體、人群、社會大環境之間的互動與演化。傳播生態是由傳播主體、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及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是充滿著符號意義的互動環境。
從傳播生態學角度來看,政府傳播主體通常處于傳播生態鏈的上端,掌控話語權,從而使得主體意識形態得以言說與伸張。受眾通常作為被動分散的客體,位于傳播生態中的目標或靶心。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各種雜音逐漸沉淀,使得政府一言九鼎,“一個聲音”得以響徹云端。然而,全媒體時代的傳播技術革命使得社會關系、社會行為和社會進程都發生了改變。個體聲音經由互聯網得以放大,個體傳播行為和意愿被空前激發。網絡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傳播生態因而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政府傳播主體想要使自己的聲音超越一片嘈雜變得比以往艱難。“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激活了以個人為其基本單位的社會傳播構造,重新分配了社會話語權,并因此改造了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在大眾獲得前所未有的話語權后,精英階層對真相和真理的壟斷被打破。”②微傳播的分散化、裂變式、移動性的傳播技術賦予作為個人的基本社會單位以極大的權利,使其在傳播的過程當中真切感受到了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無論是馬航飛機失事還是天津爆炸事件,無論是民工討薪還是地震泥石流,普通人通過新媒體可以時刻保持對社會熱點事件的關注,具有一種參與者及關心者的悲憫情懷,并在這種關注中實現了自我對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體現自我存在的意義。“在數字化生存的情況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子集。”③受眾顯示出強烈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形成網絡上的公共話語空間,從而“眾聲喧嘩”。而政府主體則往往淪為輿論靶心,被互聯網裹挾著陷入傳播被動局面。對于世界而言,其實這已成為社會常態。縱觀全局,整個傳播生態的改變源自互聯網革命,我們對此應該端正認識,不必過于驚慌,經風雨見世面,學習在逆境中成長。
三、傳播機制出現變換:由行政縱向層級式到網絡橫向分散式
傳播機制是指傳播行為發生作用的過程以及所產生的傳播關系。我國政府傳播主體踐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組織原則和宣傳機制,以組織傳播為主要形態,突出各級政府行政部門的縱向垂直關系。在具體分工和執行上強調各層組織的具體任務和職責。這種“層級結構”在“功能實現上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強烈的意識形態管控的工具性;一個是社會政治生活意義的引導性”。④通過這種傳播機制,可以確保傳播信息輸送、傳播過程運作以及傳播目標達成等一系列傳播主體行為的實現。
在全媒體時代,網絡傳播更多體現出橫向的主體間性關系。政府傳播機制也由行政縱向層級式逐漸轉向網絡橫向分散式。信息生產與傳播幾乎瞬間同時發生,甚至很多時候政府的信息生產滯后于網絡信息傳播速度,形成輿論倒逼;傳播的方式是分散式或裂變式;傳播態勢迅猛,呈現全方位、多角度、碎片化的即時傳播形態,激烈撞擊縱向層級傳播機制,使之沒有足夠回旋的時間和空間以協調應對,原有傳播機制遇到了新技術的有力挑戰。這種網絡橫向分散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政府傳播主客體關系地位變化帶來的傳播力度的改變,政府傳播主體也只是作為一個網絡節點而存在,必須俯下身來爭取更多關注度及正面傳播效應,以博得更大的網絡影響力。傳受雙方之間關系的力量對比更趨于對等與互動。二是媒介大融合打破了原有媒介傳播機制,新媒體的信息來源分散與傳播擴散無序通常造成政府傳播控制能力下降、傳播不確定性增強,容易陷入傳播失序的復雜狀態。例如天津爆炸事件中,政府傳播主體無法繼續使用以往熟悉的套路。各部門之間既缺乏溝通協調的時間,也沒有足夠回旋的余地,鮮有靈活得體的處置應對過程。同時,在行政縱向管理責任下又不敢擅自做主,所以顯得十分被動尷尬,回應常常是“我不知道”“我不掌握”“下去問一下”,政府傳播力度明顯減弱,在全媒體時代這無異于“掩耳盜鈴”,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從天津爆炸事件,我們真切感受到了傳統的政府傳播機制在應對全媒體時代的危機傳播中的困窘與無奈。在這種網絡橫向分散的傳播機制下,一旦政府傳播主體責任不能及時補位,傳播被動就在所難免。誠如李克強總理所言,“權威發布一旦跟不上,謠言就會滿天飛”。
四、傳播效果大幅縮減:由宣傳魔彈到效果協商
傳播效果這里指的是政府傳播主體對于自身既定的政治傳播目標和政府形象在受眾的認知、情感以及行為上實現的程度。通常表現在政府的公信力方面以及對目標受眾的說服效果上。
從認知到態度再到行動,有一個效果的累積、深化和擴大的過程。傳統上由于信息資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大眾媒介手里,政府因而擁有強大的傳播力量和傳播效能,一般能夠通過宣傳方式順利達到目標,獲得預期的傳播效果,猶如“魔彈”一般毫無阻攔、所向披靡,有力地影響和引導著人們的行為。然而,全媒體時代使得對信息傳播控制變得日益艱難,傳播不確定性增強,政府傳播主體對受眾的說服效果減弱,事情的最終解決往往需要各方對話協商,甚至需要一定的溝通藝術才能最后達成共識。例如在天津爆炸事件中我們就明顯感受到了這種變化。從一錘定音到協商對話,政府傳播主體要學會適時變通、順勢而為,放下姿態與互聯網居民一起合力共建網絡利益共同體的精神家園。這是傳播技術革命帶來的世界傳播格局的大趨勢。對此我們還需要一個不斷學習和適應的過程。迎接未來,就從改變我們自己開始。
注釋:
① 李淑芳、張開榮:《從傳播生態學角度審視新聞輿論監督》,《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4期。
② 喻國明等:《“個人被激活”的時代:互聯網邏輯下的傳播生態重構》,《現代傳播》,2015年第5期。
③ [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頁。
④ 荊學民、施惠玲:《政治與傳播的視界融合:政治傳播研究五個基本理論問題辨析》,《現代傳播》,2009年第4期。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張毓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