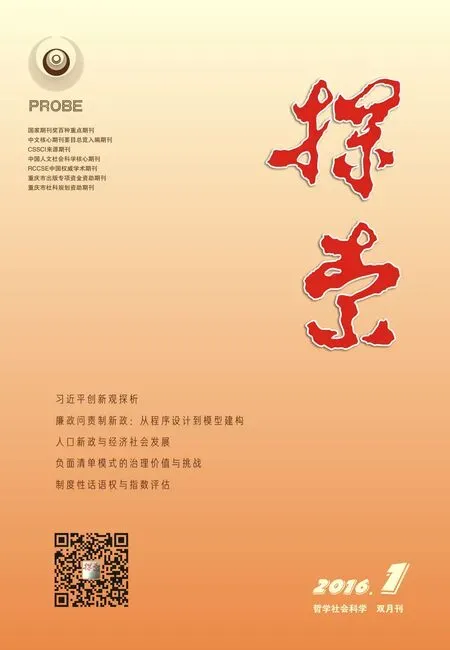“空心化”背景下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建設研究
周忠麗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江蘇南京210013)
工業化、城市化是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過程,伴隨著社會急劇轉型,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特別是青壯年和社會精英進城務工經商,使得本就缺乏組織資源的農村社區結構呈現疏松趨勢,導致農村人才空心化,不僅如此,包括土地、資金等其他資源也向城市單向流動,出現農村經濟空心化,同時由此引發的農村價值空心化也日趨凸顯,這為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出了諸多方面的挑戰。
1 問題的提出
“空心化”現象及其對于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建設,黨在農村基層的執政基礎及農村基層治理的影響,成為最近10年學界持續關注的熱點。研究發現,農村“空心化”并沒有因為人口壓力下降而減少對基層黨組織的挑戰,反而因利益和價值多元等諸種因素的影響,弱化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同時農村地區民眾的權利意識增強也使農民更愿意表達自己的訴求和不滿。
據中組部黨建所課題組開展的“當前群眾對黨的各級組織的滿意度調查”發現,在問到“當前,基層群眾特別是農村群眾對黨的各級組織的信任情況”這一問題時,回答“對黨中央信任,對地方(基層)黨組織不信任”占53.67%[1]。
肖唐鏢、王欣歷時10年(1999—2008年),在江西、江蘇、山西、重慶和上海5省市60個村莊的4次調查數據也提出了“農民認為中央比地方值得信任”的觀點。數據顯示,“從黨中央開始,每下降一個層級,農民的政治信任度下降10%左右,直到鄉鎮和村組織,僅有三成多”[2]。由此可見,不同層級黨組織對于農村基層群眾的公信力和凝聚力是自上而下逐級遞減的。
還有一些專門針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調查研究,也顯示出農村基層黨組織影響力和凝聚力令人擔憂的現狀。吳梅芳在安徽、江蘇和河南等省開展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有30%的村民對農村基層黨組織“不滿意”或“很不滿意”;有6%的村民認為,當前農村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威信很低[3]等。王文強、張黎在湖南五個縣、市、區開展的入戶調查顯示,當問及“您是否認為村里的黨員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時”,回答“發揮了作用”“大多數發揮了作用”“只要少數發揮了作用”“都未能發揮作用”的比例分別占2%、30% 、46% 和 22%[4]。
2 農村“空心化”背景下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弱化的表現及成因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覆蓋農村基層社會民眾組織網絡體系的節點,是黨在農村的政治領導核心和全部工作的基礎,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農村基層的有效貫徹,關乎黨在農村基層的執政基礎、執政合法性及基層政治穩定。但是,在市場經濟和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大部分農村人口向城鎮大量轉移,出現了農村“空心化”現象,導致農村社會的政治生態和治理結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與此同時,由于基層黨組織自身的轉型滯后于農村社會的轉型,一定程度影響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功能的正常發揮,其影響力和凝聚力出現弱化現象。
2.1 利益代表功能弱化
利益是政治行為的邏輯起點,利益的實現和滿足程度以及實現過程中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政黨凝聚力的強弱,因此,利益代表成為政黨的首要功能。計劃經濟時期,黨在農村地區通過建立人民公社體制擁有農民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渠道,農民利益的實現完全依賴于黨政系統。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深入發展,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出現萎縮,削弱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和運行的物質基礎,從而無經濟資源可以再分配,也無力為農村居民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與凝聚力。同時,上世紀90年代前后,過重的農民負擔也加劇了農村的黨群、干群矛盾。另一方面,人口流動增加了黨組織聯系民眾的難度,部分農民對基層黨組織的依賴性日益降低。
2.2 基層黨組織政治領導功能弱化
《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規定,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農村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討論決定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領導和支持集體經濟組織,管理集體資產,協調利益關系。就當前農村基層工作實際而言,黨組織最主要的工作是動員和組織農民參與到新農村建設中來,解決與農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產品供給等問題。但不少農村地區出現“空心化”現象,導致基層黨組織處于“無人、財、物可動員”的尷尬境地,無法有效地將村民動員、組織起來達成一致的集體行動,以致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出現“基層組織越主動,農民群眾越被動”的局面。同樣,在政治權利方面,對于群眾一些新的政治訴求和社會需要,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也難以滿足,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對基層黨組織的疏離感。
在“兩委”關系上,盡管法律和相關規章制度規定了兩者的職權,即黨組織是享有領導權的農村領導核心,村委會是享有自治權的農村自治組織,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管理本村屬于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但在日常的具體實踐操作中,領導權和自治權的職權規定存在重疊之處,權力邊界不清晰,造成了“兩委”關系緊張。加之部分基層黨組織仍沿襲計劃經濟時期的觀念和做法,習慣大包大攬,陷入農村基層各種具體瑣碎的事務之中,不僅容易招致村委會的不滿,更因忽視黨組織自身的能力建設,弱化了在村級事務的領導權,進而影響利益整合功能。
在利益和價值日趨多元的農村地區,如何對群眾進行有效整合,不僅關系黨自身的執政基礎,也關系整個農村社會的穩定。相應地,農村基層黨組織需要不斷強化自身的利益整合功能。從現有的實踐來看,由于一些基層干部決策水平不高,或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致使群眾對黨的政策和基層組織的決策產生疑問,對組織的權威和干群關系均產生不良影響。
2.3 基層黨組織政治錄用功能弱化
政治錄用是政黨的一項重要功能,具體到農村基層黨組織而言,政治錄用就是將農村社會中的“能人”吸納到黨的隊伍中來,進而把黨員中的優秀分子培養成后備干部,并通過法定程序使之在鄉鎮政府、人大和村委會中擔任領導工作,把黨的主張和意圖落實到各項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增強黨在農村基層的執政基礎。
青壯年勞動力作為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各方面能力較強的群體,不僅是農村發展的生力軍,也是黨組織的重點發展對象。但是,由于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的雙重作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多外出務工或經商,農村普遍出現人才“空心化”現象,農村基層黨組織難以有效吸納能力強、素質高的青年人才入黨,造成農村黨員年齡結構老化,后繼乏力。不少地區農村黨組織為完成發展新黨員的工作指標,降低入黨門檻,吸納一些不具備黨員資格和條件的人進入黨內,直接導致農村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整體素質下降。此外,一些農村地區還出現基層黨組織家族化現象,形成封閉的“圈子”,這些都直接削弱了基層黨組織的公信力。
2.4 基層黨組織政治社會化的功能弱化
權力是維系政治統治的關鍵,但“即使是最強者也絕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5]9,因此,政治權力會“大力發揮意識形態對統治地位合法化的辯護功能,證明自己政權存在的合理性”[6],這同時也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政治社會化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是直接發揮政治宣傳功能,為政治統治提供合法性論證;二是通過價值評判和規范來引導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即“以表現、解釋和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的行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為模式或方式”[7]345。當前,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的價值認同基礎面臨農民價值認同理性化和基層意識形態宣傳有效性不足的雙重困境。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交通、通信、傳媒等現代技術的發展,農民傳統的宗族、家族及鄉土意識受到沖擊,交織著多重文化的沖擊,價值觀日趨多元化、復雜化,傳統農村地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傳統人文情懷逐漸淡漠。與此同時,農民作為利益主體的自主性日益增強,利益意識被喚醒,農民的價值認同趨于理性化。利益成為個體行動的重要邏輯,為獲取個體自身利益最大化,部分農民嘗試挖掘一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組織載體與社會資源,基層黨組織如果帶領農民致富不力,就會被農民所疏遠。農民流動性的增加與職業、收入分化的加劇,使得原本較為均質的農村社區出現異質化傾向,村民的集體意識及村莊社區認同逐漸被市場經濟所淡化。
“空心化”不僅體現在經濟和人力資源領域,還表現為農村價值空心化方面,農村的留守人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精神苦悶甚至心理健康問題,加之外來文化和觀念裹挾著市場經濟和信息化迅猛而來,部分農民呈現出種種矛盾、困惑、迷茫、焦慮和浮躁的文化心態,對黨所倡導的價值理念持懷疑態度。部分農民無所寄托的精神狀態,為一些不良勢力甚至是邪教的蔓延提供了機會。同時,傳統陋俗的滋長也有變本加厲之勢,賭博現象等也日漸泛濫,由此導致部分黨組織在農村思想價值和意識形態領域出現邊緣化傾向。
3 “空心化”背景下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建設的路徑分析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村“空心化”現象將會加劇,基層黨組織只有更好地嵌入社會,實現功能調整和機制創新,才能在不斷強化自身權威的同時,增強凝聚力,積極引導農村社會的發展方向。
3.1 基層黨組織要有效嵌入農村社會,實現對社會的有機整合
“嵌入”這一概念最早由波蘭尼(Karl Polanyi)提出,指兩種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和融合性[8]。就農村基層黨建而言,“嵌入”就是黨組織有效深入社會,構建以黨組織為核心、包括各類外圍組織在內的組織體系,針對不同社會群體的特性,通過不同的途徑與方式與之建立聯系,并建立穩定的關聯性,提高相互間的融合度,實現組織嵌入與價值嵌入的統一,這是解決當前基層黨組織與農村社會之間利益關聯弱化問題的關鍵。
社會轉型對農村基層黨組織提出了全新挑戰,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社會獲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黨的社會基礎。因此,將黨的組織網絡延伸至社會自主空間,并將原子化的個體納入黨的組織體系,成為當前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建設的內在邏輯。為此,黨組織要對社會實現“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全覆蓋,但這一舉措還只是基層黨組織轉型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要實現基層黨組織對農村社會的有機整合。“沒有組織的參與就會墮落為群眾運動,而缺乏群眾參與的組織就墮落為個人宗派,強大的政黨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眾支持。”[9]336在“空心化”背景下,基層黨組織需要介入農村社會結構轉型的整個過程,引導和帶動農村社會各種聯系紐帶和鏈接的重構,推進黨組織與農村社會形成一種新型合作與互動關系。同時,積極推進農村“兩新”組織黨建工作,實現在新興社會領域的“政黨擴張”和“政黨增殖”[10]。此外,建立有關平臺支持各類社會組織的發育和發展,不斷發揮與激活各種基層黨組織外圍組織的功能,并以此關系網絡為間接載體,實現對農村社會組織的整合。
同時,要求黨組織將主流價值觀嵌入農村社會現有的價值體系之中,尋求雙方的共同點,建立彼此間的關聯性,實現對黨的權威及所倡導的價值體系的認同。但是,隨著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基層黨組織對農村社會進行價值嵌入的難度較大。應對這一挑戰,一方面,基層黨組織的宣傳教育功能工作需要立足于農村社會價值體系的特點,打造適應農民生活需要的價值話語體系,并通過搭建有效的嵌入載體,實現價值嵌入的柔性化、生活化、平民化和多樣化,不斷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農村社會的滲透力和說服力。另一方面,各類宗教組織甚至邪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蔓延,在意識形態方面“客觀上造成了與政黨的潛在競爭,削弱了政黨作為這種工具的優勢地位乃至壟斷地位”[11]310。因此,基層黨組織的價值嵌入還涉及培養民眾的行為理性,以引導農村思想意識的健康發展。
3.2 功能定位實現由行政向服務的轉變
農村基層黨組織立足社會,同時也直接受制于社會。因此,農村基層黨建不能脫離農村社會搞“自我循環”,必須緊密聯系農村社會轉型及發展的大趨勢,來確定自身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有效路徑。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對基層黨組織都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如農民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等服務以何種方式獲得,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安全等如何保障等。基于此,黨的十八大提出,基層黨組織要“充分發揮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作用”,這就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新形勢下實現功能轉型,即從以組織或動員革命與生產為軸心的功能結構,轉變為以社會關懷和利益協調為軸心的功能結構[12]。
3.2.1 培育“新農民”,帶領群眾致富,維護農村社會穩定
首先,創新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有效推進土地流轉,確保耕地經營權流向技術水平高、經營能力強的“新農民”手里。其次,引進和造就各種專門人才,吸引返鄉農民工就業創業,培育有能力、有意愿立足農村經濟發展的下一代成為“新農民”,并提供政策、資金、技術和信息扶持。最后,最大限度地壓縮黑惡勢力滋生的空間,維護農村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保護農民的安全與權益。
3.2.2 從農村人口結構出發,為農村“三留守”人員提供定向服務
“三留守”人員在成長、生產和生活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加強對這個群體的關愛服務是基層黨組織的重要工作。一是健全農村“三留守”人員關愛服務體系,重點提供學前教育和養老服務,同時做好各類惠農政策及申請辦理流程的宣傳工作,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二是建立農村社區“三留守”人員的動態信息庫,做到精準幫扶。三是多方籌集資金,借助社會志愿以及鄰里互助等方式,建立面向農村老人、婦女和兒童服務的社會工作者隊伍或服務站點,提供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心理輔導等服務。
3.2.3 以美麗鄉村建設為抓手,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一是培育優良家風,圍繞勤勞致富、崇德向善、誠實守信、遵紀守法等內容開展評比活動,引導農民群眾向上向善。二是培育文明鄉風,充分運用鄉風教化資源,使優秀的傳統鮮活起來,潛移默化地影響農民群眾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三是培育鄉賢文化。從現實情況看,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和身邊好人,在當地有著較高的威望和影響,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要發揮這些人的示范引領作用。同時,要以鄉情為紐帶,吸引和凝聚成功人士回鄉支持農村建設,建設美麗鄉村。
3.3 創新農村基層黨建工作機制
3.3.1 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工作和運行方式
基層黨組織活動要影響和帶動群眾,不能搞“自娛自樂”和“自我循環”,要實現從“縱向垂直指令式”“封閉集中型”向網絡式、扁平化的方向轉變,重視對社會關系網絡的掌握,形成吸納社會力量的機制:一是吸納社會一般民眾的力量,通過推進農村社會自治工作,使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民主和基層治理中扮演主角,從而獲得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動權;二是在堅持黨員標準的前提下,將農村“能人”吸納到黨內。同時,對那些有較強社會責任感且能真正代表民眾利益的精英,建立例行化、制度化的聯絡方式,使之與黨組織良性互動,成為基層黨組織服務和整合社會的力量;三是通過引領、組織和借力各類社會組織,使普通黨員及民眾在互動過程中積累社會資本,從而降低農村基層治理的成本,同時也為基層黨組織集聚政治資源、價值權威和凝聚力奠定基礎。
3.3.2 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頭人的選任、培養和監督機制
一是以“選”為立足點,跳出“就地取材”“本村人當本村官”的模式,運用“黨找人才”的科學辦法,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選任機制,建設“雙強”型領導班子。二是以“育”為關鍵點,加強對群眾工作方法和政策法律法規的培訓,同時強化業務培訓、實用技術技能培訓,不斷拓寬基層黨組織帶頭人視野,提高專業知識水平。三是以“管”為落腳點,建立健全村務黨務監督機制。
3.3.3 創新農村流動黨員的管理機制
一是摸清底數,規范管理。利用春節前后流動黨員集中返鄉的時機,采取入戶調查、電話訪問的方式展開“地毯式”登記工作,對返鄉及在外流動黨員進行信息登記與更新,建立流動黨員數據庫。二是創新管理方式,長效管理。根據收集到的流動黨員信息,組建流動黨員QQ群或微信群,在群里定期上傳中央、地方文件精神,及時傳達地方政策、招工等信息,確保流動黨員流動不流失。
參考文獻:
[1] 中組部黨建所課題組.新時期黨群關系調研報告[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1):4-25.
[2] 肖唐鏢,王欣.中國農民政治信任的變遷:對五省份60個村的跟蹤研究(1999—2008)[J].管理世界2010(9):88-94.
[3] 吳梅芳.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用發揮狀況的調查與思考[J].理論探索,2013(3):48-51.
[4] 王文強,張黎.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號召力調查研究[J].中國鄉村發現,2012(5):21-24.
[5] 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6] 楊雪冬.論意識形態與經濟增長[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2):12-18.
[7] 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8] 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M].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9] 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薩托利.政黨與政黨體制[M].王明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1]王長江.政黨現代化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12]林尚立.基層組織:執政能力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戰略資源[J].理論前沿,2006(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