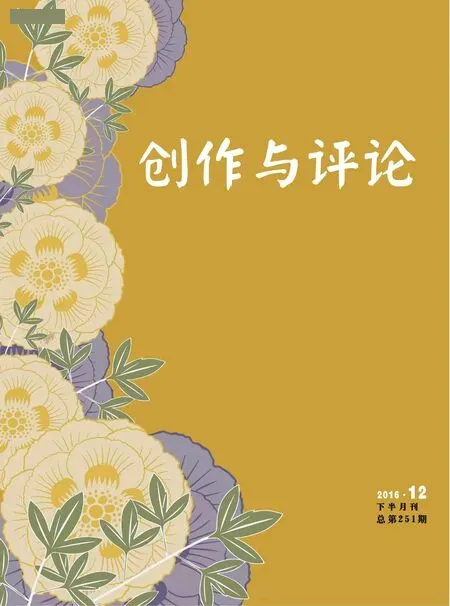公共藝術與城市的文化邏輯
——以舊上海公共藝術為例
○喬遷
公共藝術與城市的文化邏輯
——以舊上海公共藝術為例
○喬遷
主持人語:
從現實層面來看,公共藝術在當代中國呈現出的繁榮景象與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關。與其他的藝術形式最大的不同,公共藝術要求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公眾的存在。它接受公眾的檢閱,也改變公眾的視覺與觀念。它是最有可能對民眾進行藝術啟蒙并最終改變國民素質的一種藝術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共藝術創作者身上所肩負的重任,超過了以往的其他藝術家。隨著更多的公共藝術在當代中國的各大城市乃至鄉村落地生根,我們的文化觀念和審美態度也會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面貌;而對公共藝術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則顯得尤為必要而且緊迫。本期這組關于“公共藝術”的文章涵蓋面非常廣泛,既有對公共藝術精神、審美價值等問題的深入探討,也有藝術家的創作經驗之談,而王強關于鄉村公共藝術的思考,則開了此類題材研究的先河。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公共藝術是隨城市發展而來的共生物。城市是公共藝術的依托,一個城市公共藝術的發展是城市文化邏輯的一環。中國缺少傳統的公共藝術,因為中國的城市發展起步較遲。按照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的說法,中國歷史上沒有城市,他認為城市是由商業行為聚集的自然秩序,這個秩序弄夠制約和規范人的行為,并不依靠行政的力量達到這樣的目的。近代以來,中國沿海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出現,其一莫過于上海。
上海是一個短期爆發式發展起來的城市,還沒有形成長久的文化積淀,她呈現各種文化巨大差異的混合。“世界性和地方性并存,摩登性與傳統性并存,貧富懸殊,高度分層,這使得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呈現駁雜奇異的色彩,有中有西,有土有樣。中西混雜,現代與傳統交叉,都市里有鄉村的內容和基因。多元、混雜,這就是近代上海民眾的文化特點。”①
上海是適合回望歷史的地方,開埠一百多年,集中了中國最豐富、復雜精彩的故事。歷史往往有無法預測的走向,一百多年前在槍炮聲中誕生的上海,于20世紀中期,在又一陣更密集的槍炮聲中急轉至另一條發展的軌道。從此,舊上海生活曾經的活色生香就沉寂在云煙般的想象中了。上海、舊上海漸漸模糊,留下的只是依然被稱呼為“上海”的軀殼。
其實舊上海一直存留在國人心底,“上海”二字在新中國很長時間里是“摩登”的注解。所謂“摩登”,是普通大眾對于現代文明的直覺。近三十年,開放的氛圍使我們向外頻繁與國際當代文化接觸的同時,也向內挖掘曾經的現代文明樣本。文化界流行追憶,上海自然成為最容易被追憶的地方,曾經的時代風潮、細枝末節重新被提起,追憶中帶著驚羨、驕傲、惋惜。
上海的形骸還在,外灘還在,石庫門還在,留下追憶中敘事的痕跡,追憶的根基顯得尤為真切。
每位追憶者都可以選擇自己的角度尋找線索。文學家找到了張愛玲,一本《半生緣》告訴讀者中國的文學不只是刀光劍影的斗爭,也曾經塑造過深刻的普世人性;舊上海的電影在那個時代曾經是世界電影的翹楚,《孤兒救母》《火燒紅蓮寺》《漁光曲》《風云兒女》《夜半歌聲》《一江春水向東流》 《麗人行》等等,哪一部都是中國電影的驕傲,是第五代導演拿幾只金獅、金熊獎也難以望其項背的;一曲《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突顯國際都市的自信情懷、雍容大度,與之后幾十年裝腔作勢的對口號注解式的音樂,顯然是兩個層次;張嘯林、黃金榮、杜月笙,曾經橫行霸道的黑幫老大也頻頻成為史海鉤沉的主角。
而我希望借一些舊影,想象舊上海市民曾經徜徉在怎樣的公共空間。勾畫一幅市民社會樣板的空間狀態。在物態的舊上海的構建中,紀念碑和城市雕塑記錄著城市的故事、命運,并關乎城市的精神。當然,我追憶的憑借難以在這些遺存中尋找,更多需要我憑舊影和文本展開想象。
上海的開埠與攝影的時代差不多同時到來,盡管缺失實物,我卻可以通過舊影中的資料,組合出以舊上海紀念碑和雕塑為主的公共藝術的布局和系統。
在百年的老上海發展史里,紀念碑和城市雕塑有百件左右的數量,只是在二戰期間和20世紀上半葉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基本被摧毀殆盡,沒有留下多少遺跡。
上海的紀念碑和雕塑是隨上海開埠而逐漸興建的。中國也有立碑的傳統,形式主要為墓碑和記功碑,或建于陵前,或立于廟堂前側,多屬祭奠場所。而立于公共生活空間的,成為公共建筑一部分的,基本采用建造石牌坊的方法來紀念某事件或表彰某人。自開埠以后,西方文化開始進入上海,西方的紀念碑和雕塑的形式進行記事與表功也隨之被采用。
上海西式紀念碑最早出現在1861年。當時,上海租界最早的開辟者英國,首先在外灘33號駐滬英國領事公署前的草坪上樹立“紅石紀念碑”,正式的名稱叫做“英領署地上十字紀念碑”。“紅石紀念碑”建于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作為戰爭的勝利者,在中國的英國僑民特地從英國定制了花崗石十字架,以紀念那些與侵略中國的巴夏禮一同被中國官兵殺死的人。現在還殘存著兩塊棗紅色大理石基座。
卜羅德銅像,則是上海西式雕像建設的肇始。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法國海軍上將卜 羅 德 (Admiral Auguste Lèopold Protet,1808~1862),指揮法軍聯合英軍、華爾洋槍隊等在上海附近與太平軍作戰,后來在進攻奉賢南橋鎮時,被太平軍擊斃。1865年1月,法國人在法租界公董局內建立卜羅德銅,。銅像為典型的西方古典造型。
此后,英、美、法、德、日等國的紀念碑和紀念雕塑隨著上海租界市政建設的發展而發展,相繼在以外灘為中心的租界區域矗立起來(圖1)。較為著名的有1890年11月8日英國人在南京路外灘竣工巴夏禮銅像(圖2);1896年底,德國僑民和德商怡和洋行為紀念在山東海面遇風暴沉沒的德軍炮艦伊爾底斯號的70余名死難者,在外灘公園旁建立伊爾底斯碑,并將半截船桅樹立碑上(圖3)。1911年,法租界公董局在顧家宅公園內建立環龍碑,以紀念在上海上空作飛翔表演時失事的法國飛行員環龍,碑上置有環龍的青銅頭像;民國2年,中英官商合力在外灘江海北關署對面馬路的江邊綠地建立起曾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達48年之久的英國人赫德銅像(圖4);民國26年(1937年)2月10日,蘇俄僑民在祁齊路、畢勛路口建立普希金紀念碑,優雅的碑座頂端置一尊青銅的普希金胸像,碑身正面用俄文刻有“俄國詩人亞利山大·普希金先生逝世百年紀念碑”(圖5)。受西方紀念建筑造像之風的影響,辛亥革命前后,中國人也開始建立西洋式的紀念碑和塑像。李氏族人首先在徐家匯海格路李公祠內立李鴻章胸像;民國18年10月10日,雕塑家江小鶼創作的孫中山銅像,在江灣五角場北首的市政府大樓前落成,像高3米,加上基座總高10余米(圖6)。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出現過的紀念建筑、塑像應該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而確切數字則無從統計。

圖1 常勝碑

圖2 巴夏禮銅像

圖3 伊爾底斯紀念碑
舊上海紀念碑和城市雕塑的影響力莫過于歐戰勝利紀念碑,那高高底座上舒展雙翼的和平女神雕塑像早已成為老上海經典的場景(圖7)。在電影《間諜佐爾格》中,就是通過這尊雕塑反映20世紀30年代上海外灘全景的一個俯瞰的鏡頭;1941年,旅居上海的奧地利人費穆編劇,猶太人J·佛蘭克導演的電影《世界兒女》中,這尊雕塑出現在電影的首尾段落,是故事發生的重要場地。如今周圍老建筑依舊,雕塑早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中了。
這座成為老上海經典記憶的紀念碑存世的時間并不長,但她記錄了舊上海一段最輝煌和最滄桑的交替時代,已經成為舊上海血液的一部分。紀念碑的建設緣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勝利。戰爭結束后,有著古希臘羅馬紀念碑藝術傳統的英、美、法等國家,在各地修建了各種大小不同、造型各異的紀念碑和雕塑,以紀念在戰爭中陣亡的將士。在“一戰”中,上海也有許多外僑遠赴歐洲戰場,加入各自國家的隊伍,其中有一些人戰死疆場,于是上海租界當局也在戰后建立了歐戰勝利紀念碑。
1917年,大戰還在繼續。公共租界的英國商會就開始向工部局提議,希望能建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上海英、法、俄、意等國僑民赴歐從戎的陣亡者,并建議這一紀念碑的位置設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江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接壤處。工部局同意了這個提議,并由英國商會通過法國商會,向代表法國利益的公董局征求意見。公董局也贊同了這個建議。大戰結束后,上海租界專門成立了一個戰事紀念委員會。至1920年,委員會始正式決定在以前所議位置建碑,并成立了紀念碑委員會,開始實際操作。由英商馬海洋行(Messrs.Spence,Robinson&Partners)的J.E.March負責設計。關于紀念碑的形式,曾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建成實用性的建筑物,如里面可以辟作商品陳列室,另一種是建成單純的形象輝煌的紀念碑。主張后者的占了多數,委員會采用了后者建議。紀念碑的設計圖案由委員會公開有獎征集。獎金最高達750兩銀子。最后通過的方案是:下為豎直的高大石碑,上綴黑色和平女神銅像,以求“永久之和平”(圖8)。另外,地基和周圍環境改造也花費頗多。其中一部分經費由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承擔,大部分來自向社會公眾的勸募。1923年,紀念碑的地坪、碑身及周圍的環境建好,向國外訂制的和平女神的青銅像在1924年初始運抵上海。經安裝后,兩租界當局于2月16日舉行揭幕典禮(圖9)。

圖4 赫德銅像

圖5 普希金像

圖6 孫中山銅像

圖7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外灘
紀念碑呈長方形盒狀,整個碑底座由鋼筋混凝土砌成,中間為空心,墻面貼有花崗巖石料。紀念碑的碑身面上,鐫刻著紀念文字和在一戰中死難的上海僑民的姓名,兩旁裝飾著銅雕的盔、胄、盾、甲等古代兵器。碑座背面,“功炳歐西,名留華夏”八個大字,赫然而書。碑頂的上方,就是巍然而立的和平女神像了。女神像雙翼高展,腳下兩孺子分居兩側,怡然牽裙。
1941年底,隨著美英向日本宣戰,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公共租界的中心區,歐戰紀念碑作為敵對國標志性的建筑物被拆下。兩邊銅雕的盔、胄、盾、甲等古代兵器被毀掉,碑面的文字則被全部磨去。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日本投降后,將拆下后尚保留著的女神像歸還給英國領事館。此時,上海外國租界已經被國民政府收回,西方人在上海的獨立統治已結束,歐戰紀念碑無法恢復。

圖8 上海歐戰紀念碑
從和平女神雕塑的建立到被拆除,雖只經歷了17個年頭,但已經被譽為遠東第一紀念碑,成為舊上海文明的永恒象征。成為舊上海的象征絕非偶然,上海的時代發展階段、文明樣式、社會形態、市民的精神訴求共同為這尊紀念碑價值產生提供了邏輯條件。
舊上海是舊中國的一部分,卻不是舊中國的縮影,上海之外是另外一種舊中國,上海是異樣的存在,有自在的文明邏輯。上海的文明性質是多歧的、互滲的,是沖突中的平衡。西方原汁原味的文明在這里有自己的完整體系,附生在這個系統的社會在物質和精神上和倫敦、巴黎、紐約近在咫尺,而與一河之隔的浦東卻恍若天涯。在上海孕育出一個西方城市社會形態的同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從北京轉移到上海。在其后的幾十年里,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康有為、梁啟超、魯迅等等,上海囊括了那個時代中國大半的文化精英。在同一個時空之間,還有一個延續型的中國社會,屬于整個中國文明系統中的一環,但是,二者的交叉并不充分,基本處于相互的封閉狀態。租界是西方人的世界。西方人將歐美的物質文明、市政管理、議會制度、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都帶到這里,使租界變成東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塊西方文化“飛地”。迄今為止,中國還未出現像舊上海一樣的市民社會。這就是西式紀念碑和雕塑被認可,以及歐戰紀念碑成為城市標志的時代和社會邏輯。
舊上海是中國的城市,但更像是坐落在中國的西方城市。舊上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文明特征幾乎是西方的翻版。傳統中國以經驗為主的營造法式,在現代規劃理念主導下的上海城市建設中,顯然力不從心,只有建立在數理科學基礎上的西方建筑體系才能夠發揮作用。舊上海的建筑是亞洲地區最完整的最具規模的西方建筑群,20世紀20年代建設的錦江飯店,是那個時代世界著名的現代建筑之一。在物態上,舊上海比較接近于西方,各國租界內又有各自國家的特點,法國的、英國的、德國的、日本的,包括西方現代主義的,舊上海的建筑素有萬國建筑博覽會之稱。即使今天的上海外灘,也比以西方移民為主的紐約更像歐洲的街景。老上海的紀念碑和城市雕塑具有在這樣的建筑系統中產生發展的形式邏輯。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的第四卷第一章《論公意是不可摧毀的》中說,“只要有一些人聯合在一起,并人為他們是一個整體,那么他們就有了唯一的意志,這個意志指向他們共同的生存和公共福利。”舊上海是舊中國社會形態中現代文明制度在中國土地上的唯一實踐,唯一具有市民社會的城市。租界內的社會系統和西方是接軌的,也對周圍的中國市政當局產生直接的影響。舊上海,尤其生存于租界內的市民,包括總數曾達到15萬人的外僑和更多的中國人,他們身上所體現的現代文明首先是西方化的。所受的教育、價值觀是西方式的,或受到西方影響的。那么,體現市民社會主體價值的公共藝術必然為傳統的西方藝術風格。
這些雕塑包含了舊上海的城市文化傳統和文化性格,從而象征了舊上海的城市靈魂。
城市的文化是流變的,有時甚至是天翻地覆的革命。那么,特定時代的代表性雕塑或紀念碑在一個時代是文化的象征,在另一個時代,則可能沒有與城市文化上的邏輯關聯。一個城市乃至一種文明的象征物往往遭受與此文明同樣的命運。美國世貿雙塔在911中的轟然倒塌;阿富汗巴米揚大佛安靜地站立一千多年,卻在塔利班的炮火中化為齏粉,這恰恰反映象征物脫離不了產生的文明基礎和文化邏輯。
注釋:
①熊月之著,姜進編:《都市文化中的現代中國》,《鄉村里的都市與都市里的鄉村——論近代上海民眾文化的特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頁。
②[法]盧梭著,戴光年譯:《社會契約論》,武漢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頁。
(作者單位:北方工業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圖9 歐戰紀念碑落成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