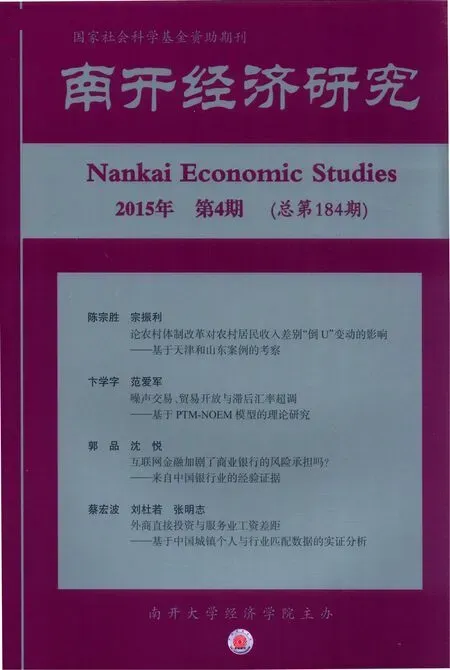論農村體制改革對農村居民收入差別“倒U”變動的影響——基于天津和山東案例的考察
陳宗勝 宗振利
關于我國農村經濟增長、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居民收入差別同時逐步擴大這一典型現象①在收入增長過程中收入差別持續拉大,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從1978 年的0.3023 上升到2013 年的0.473,上升了56.47%,年均上升1.3%。1978 年數據來自《關于公有經濟收入差別倒U理論的討論和驗證》,高玉偉: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2),第102 頁。2013 年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401/t20140120_502414.html,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論證。本文作者積極探索從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兩個大的方面開展研究,并做出了一些努力(陳宗勝,1991;陳宗勝、周云波,2002;陳宗勝,2005;陳宗勝、鐘茂初、周云波,2008)。總體上看,多數研究都是從這兩個方面對其展開探究的,但具體到某個問題或在一篇文章中則側重點有所不同,有的側重經濟發展因素,如強調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陳宗勝、武潔,1990;張平,1992)、農戶非農收入(主要是工資性收入)的快速不均等增長(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1999)、非農就業機會的不平等(林毅夫等,1998)以及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影響等等(Knight,J.and Song,L.,1993;Howes and Hussain,1994;Rozelle,1996;張平,1998;Wan and Zhou,2005);而另外一些則側重于體制改革和經濟政策因素,如強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周云波等,2008)、農副產品價格改革(林毅夫,1998)以及農村稅收和信貸政策等影響(唐平,1995)。
本文根據所掌握的天津市農村社會經濟調查數據資料,并輔之以山東省農村的相關資料,從農村體制改革這一角度,對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分析。比較而言,這些資料的一個特點是屬于較長時期的時序數據(1994—2008 年),據此所進行的分析和得出的結論可能具有更好的穩健性和代表性。從農村體制改革的角度研究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主要是通過對農民家戶收入來源的構成及其變動的影響來反映的,或者說是通過農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變革來體現的。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農村居民從不同收入來源即集體經營、家庭經營以及勞動工資或資本經營中得到的收入的規模和變化,來考察其對收入差別的影響。這是體現我國農村體制改革對農村經濟及農村收入分配影響的一個很好角度,因為正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打破了傳統人民公社集體工分體制下農村居民的單一集體收入來源,也正是家庭承包責任制強化了農村家庭經營,發展了鄉鎮企業以及農民外出打工,使農民有了工資收入,積累了家庭及個人財產等,才使農民收入的來源多樣化,從而導致了居民收入分配差別的變化。另外稅收、補貼等政策因素的影響,也可歸為收入來源的變化。
一、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由1978 年的133.6 元上升到2013 年的8,896 元,年均增長12.74%,,,去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幅也達到7.22%,①1978 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3 年數據來自《2013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天津市同全國一樣,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表現出更加快速的增長趨勢,地區生產總值從1978 年的82.65 億元迅猛增長到2012 年的12,893.88 億元,年均增速高達16.01%,,,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增速也達到11.39%,,。相應地,天津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在不斷攀升,天津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 年的178.4 元/人上升到2012 年的14,025.54 元/人,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3.69%,,,在全國范圍內屬于發展較快的地區。
在農村經濟快速增長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提高的同時,天津市農村居民的收入差別也發生深刻變化。由圖1 可以看出②2007 年天津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出現了異動,躍升至0.4108。仔細分析樣本資料,發現至少有10%的樣本沒有生產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同時,還有15 戶家庭未提供收入的相關數據,這導致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過低,正是這一因素使得該年的基尼系數奇高。故此本文對其進行了修正,具體方法是將人均純收入最低的15%刪除,這樣做不會大幅減少樣本量,而修正后的基尼系數0.3132 與前后兩年的數據相比相差不大,具有合理性。,天津農村內部收入差別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1984—2003 年,收入差別不斷擴大,基尼系數從0.147,6 上升到0.403,6,年均上升5.44%,,,這與全國的變動趨勢基本一致;2003—2008 年,農村內部收入差別不斷拉大的趨勢發生逆轉,步入我們提出并力圖證明的“公有經濟倒U 曲線”的下降區間①“公有經濟收入差別倒U 理論”由陳宗勝提出并不斷證明(可參見陳宗勝,1991;陳宗勝、周云波,2002;陳宗勝,2005;陳宗勝、鐘茂初、周云波,2008)。,基尼系數從0.403,6 下降到0.315,5,年均降低4.8%,,,這與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別持續上升的趨勢發生了偏離。我們認為這一現象值得深入研究(后文將對此進行詳細論述)。直觀地看來,相較于全國,天津的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 衡量較高,天津農村人均純收入也較高,2003 年即達到4,566.01 元,目前全國農村也達到甚至超越這一水平②《2013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數據顯示,2013 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896 元/人,以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平減到2003 年為6330.42 元/人。,因此天津農村內部收入差別的變動可能預示著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的變動方向。這意味著,至少從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的角度來看,“公有經濟收入差別倒U 理論”得到了驗證(山東農村居民的情況與天津大致一致,只是其考察期時序較短)。

圖1 全國及天津農村內部收入差別(基尼系數)和人均年純收入的變動軌跡
為了對收入差別基尼系數有一個更直觀、清晰了解,我們分析2001—2009 年按農戶五等分組的收入份額和每組平均收入的變動情況(見表1)。由表1 可知,(1)無論是從全國來看還是天津和山東的個案,最高收入組的收入份額都達到了40%,,左右,而最低收入組20%,,的家戶僅占有不足8%,,的收入份額,這是較高的收入差別程度;(2)全國范圍內最高收入組和次高收入組的收入份額基本保持穩定甚至有所上升,而最低收入組和次低收入組的收入份額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收入向高收入家庭集中,這意味入水平的持續上升,從2003年開始,天津最高收入組的收入份額出現了下降的趨勢,而最低收入組和次低收入組的收入份額上升幅度明顯,收入向低收入家庭轉移,這表明著低收入群體的相對收入比重減少;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考察期內隨著人均收天津低收入群體的相對貧困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3)全國范圍內的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家庭的平均收入比①此處的收入比,專指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家庭的平均收入之比。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而天津的收入比在2003年之前是上升的,之后呈逐步明顯下降態勢,這與基尼系數表現出來的收入差別變動趨勢相一致。再以圖示形象考察一下,以天津最高收入組的收入份額的演變看,基本反映了基尼系數的變化狀況,見圖2。二者隨時間的變化態勢是一致的,基本上呈現出先增大后減少的趨勢,在2003 年達到最大值之后轉而下降(山東的變化趨勢與之類似)。

表1 按農戶收入水平五等分組的收入份額(×100)和每組的平均收入

圖2 最高收入組的收入份額(%)與基尼系數
二、農村體制改革對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
上文已經說明,從體制改革的角度研究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主要是通過對農民家戶收入來源的構成及其變動的影響來體現的,即主要分析農村體制改革中居民從集體經營、家庭經營或是工資勞動或資本經營中得到的收入的規模和變化,從中考察其對收入差別的影響。研究方法采用學界通常使用的基尼系數分解法。
(一)基尼系數按收入來源分解方法簡介② 從收入構成上分解收入差別是收入分配研究領域中一種常用的方法,最早是由饒(Rao,1969)提出的,Fei etc.(1978),后來Shorrocks(1982)對此方法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通常泰爾指數、基尼系數均可進行分解分析,本文采用的收入差別指標是基尼系數(陳宗勝、周云波,2002;周云波,2008)。
為了后文說明的方便,這里簡單回顧一下分解方法。假設Y 代表個人或家庭的總收入,Y1,Y2,…,Yk,…,YK代表其K 種不同來源的收入,則有:

假設有N 個家庭或個人,G 代表這N 個家庭總收入的基尼系數,G1,G2,…,Gk,…,GK代表各分項收入 Y1,Y2,…,Yk,…,YK的擬基尼系數。μ 代表總收入的平均收入,μ1,μ2,…,μk,…,μK代表各分項收入的平均收入,θ1,θ2,…,θk,…,θK為各分項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則有:

則基尼系數按要素分解的公式可以寫成:

假設 Φk為第k 項收入對總體收入差別的貢獻率,則:

(二)體制改革對收入來源格局的影響
為了能較好地表現農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變革,首先給出農村居民收入來源結構及其變動情況(如表2)。從表2 中可直觀地看出,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各項不同來源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發生的變化:(1)家庭經營收入從改革初期逐步上升到20 世紀90 年代的58%,,左右之后,又緩緩下降到2008 年的38.47%,,,下降幅度明顯,這反映了在改革之初由集體經營收入為主轉變為家庭經營收入為主,然后又逐步轉為以脫離家庭的企業經營為主的演變過程。(2)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總體上呈上升態勢,說明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村居民增收的重要來源,其中比重較大的企業工資上升幅度明顯,由1996 年的27.28%,,上升到2008 年48.18%,,,增長了將近20 個百分點,表明農村改革使得各種形式的企業(如集體企業、個體企業、三資企業、鄉鎮企業等)在迅速發展壯大,無論從規模、數量還是經濟效益等方面都吸引并容納了越來越多的農業勞動力,使他們擺脫傳統的集體農業勞動或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轉而以工資或勞動報酬的形式作為獲取收入主要來源。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及相應的城鎮化、工業化的推進,這一趨勢仍將持續。其中略有差異的現象是,比重較小的非企業工資收入在波動中有所下降,由1994 年的11.73%,,下降到2008 年的5.08%,,,下降了6 個百分點,這可能與獲得這部分收入的行政事業單位、民辦教師等的工資增長速度減慢有關。這里,把工資性收入整體趨勢與前面的經營性收入變動作比較,我們發現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現象是:從2003 年開始工資性收入的比重持續大于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比重①與前后兩年相比,2002 年的數據出現了異動,故未將其納入分析之內。,并且越來越大,由于通常工資收入的差別小于家庭經營收入的差別,故這可能是從收入來源考察導致天津農村收入差別在2003 年轉而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3)作為農村居民新形式收入來源的財產性收入比重有所上升,從1995 年的1.4%,,上升到2008 年的3.24%,,,上升了將近2 個百分點,雖然所占比重仍然很小,但其增長速度引人注目。這說明隨著財產制度的改革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將越來越多地通過儲蓄、投資等活動獲取利息、股息等財產性收入,隨著制度改革及投資渠道的拓寬,這一收入比例會逐步升高。(4)轉移性收入比重上升是近幾年來特別突出的一個現象,呈現出較快的增長勢頭,由1995 年的1.85%,,上升到2008 年的5.03%,,,上升了3 個百分點,反映了政府對農民的支持和補助力度不斷加強,特別是2004 年以來,支農惠農政策的不斷出臺后上升更加明顯。這可能是從收入來源看導致天津農村居民收入差別下降的原因之一,因為通常轉移收入基本是補貼給低收入階層的。從收入格局上表現出來的特征看,山東作為農村經濟比重較大的省份與天津略有區別(見表2 下方數字),目前階段山東農村居民各收入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仍居于第一位,而天津是工資性收入比重占第一位②這反映了大城市小農村經濟特點,天津市農村地區農民獲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較多,特別是塘沽、漢沽、大港、東麗、西青等幾個區非農產業發達,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等數量多且規模大。,但二者趨勢是一致的,即工資收入比重逐步上升,而家庭經營收入比重逐步下降。這反映了全國的一般情況①附表中的數據映證了我們的論斷。該附表在本刊官網附錄中,有需要者可掃描本文二維碼查閱。。

表2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收入來源格局(%)
(三)農村居民各種來源收入在擁有該種收入的家戶中的分配
先看各種收入來源在能夠獲得該種收入的家戶中的分配情況,即測算各種收入“在有該種收入的家戶中的分配基尼系數”②不是在全部家戶中的分配情況,有些收入比如財產性收入在一些家庭中是沒有的,由于這是排除了那些不占有該項收入的家戶后的差別,所以一定意義上這是真正的“有收入差別”。(見表3)。表3 中數據表明,(1)各種收入差別都比較大,基尼系數多在0.5 以上,其中最低的工資性收入差別在0.40 左右,是因為其中企業工資的收入差別較小些,這是通常的規律性現象。(2)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在有該種收入家戶中的分配差別,都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變動過程,巧合的是拐點恰都出現在2003 年,此兩者收入差別的縮小效應的疊加,可能共同促使天津農村居民的收入差別在2003 年轉而下降。(3)財產性收入差別近年來呈現上升的態勢,這是符合發達國家經驗的,說明我國農村中財產積累效應已經開始顯現。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4)山東省轉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數是下降的,這符合預期,而天津市轉移性收入差別總體是擴大的,可能是由于離退休金在高收入戶中比較集中所致。

表3 在體制改革影響下各種來源收入在有該種收入的家戶中分配的基尼系數
(四)農村居民擁有各種來源收入戶數占被調查戶數的比重及變動
從各種收入來源的家戶比重的變動趨勢看,如果只作考察期兩端的比較,則除了財產性收入外,其他各種收入的家戶比重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其中獲得非企業工資、家庭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家戶比重下降幅度都超過了10%,,以上,其他諸項則不足10%,,。如果這種變動不是暫時的,而是持續性的,則可能是一種很重要的變動趨勢,可能表示各種收入都在向專業化、集中化方向發展,或者說在向更少數家庭、更少數人集中;而獲得轉移性收入家戶比重的減少,則說明需要補貼的貧困家庭越來越少了,說明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涓滴效應”。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家戶比重經歷一個先降后升的變動過程,支持了我們之前做出的關于“財產性收入戶數比重的下降可能是一種短期現象”的論斷(陳宗勝、周云波,2002)。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有財產積累收益的家庭應當是越來越多并最終占大多數。山東省有財產性收入家戶占被調查戶總數的比重由40.33%,,上升到52.05%,,,幾年間上升了近12 個百分點,也印證了上述變動趨勢。

表4 農村在體制改革影響下有該收入的戶數占被調查總戶數的比重(%)
(五)農村居民各種來源收入在全部被調查家戶中的分配
考察各種來源收入在全部家戶中的差別程度及變化(見表5),實際上是綜合了前述幾種角度的考察(表3 和表4 中有兩種考察),并包含了不占有某種收入和占有這種收入的家戶之間的差別。所以從收入差別絕對數值看,這里的收入差別基尼系數(見表5)一定普遍都高于前面的(表3 中的數值)。
聯系前文分析并與之比較來看,天津農村居民的各種來源收入差別存在著下面幾種情況:(1)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收入差別變動趨勢與表3 基本一致,同樣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拐點也都出現在2003 年。2003 年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使兩種來源收入在家戶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向著集中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但其在擁有該種收入家戶中的收入差別下降幅度更為明顯,最終導致兩者在全部調查家戶中的收入差別下降,這是總差別發生轉折的重要原因;(2)財產性收入集中在更少家戶,其全部家戶基尼系數在各收入來源中最高,但是隨著農村土地體制改革,越來越多的家庭能夠獲得財產性收入,致其差別有微降趨勢;(3)轉移性收入雖內部差別略有上升,但獲得轉移性收入的家戶比重下降了,結果致其全部家戶基尼系數變化不大;(4)非企業工資的收入差別下降較大,抵消了企業工資收入差別的擴大,結果致工資性收入差別變化不大。與天津的情況相比,山東情況的最大不同就是工資性收入基尼系數上升,這可能是因為山東是農業大省,農村居民獲得工資性收入的家戶比重較天津低近5 個百分點,即有相當部分家戶未能獲得工資性收入。

表5 在體制改革后各種來源收入在全部調查家戶中的分配基尼系數
(六)農村居民各種來源收入的分配差別與總收入差別的關系
上述分析均是基于每種來源收入自身所進行的研究,下面通過構成總體基尼系數組成部分的擬基尼系數,進一步考察各項收入分配差別與總收入差別的關系及變化(見表6)。從各年份的具體情況看,在天津(及山東)農村居民各項收入中,各項收入差別與總收入差別的關系是:家庭經營收入差別的擬基尼系數大于總收入差別基尼系數,因而是擴大總差別的重要因素,因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特色的中國農村改革,雖然以基本生產資料土地按人口或按勞動力大致平均分配為起點,但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體制很快導致越來越明顯的差異。第一,使得農民家庭通過承包、租賃等方式經營家庭農場、牧場、林場、果園、養殖場等成為可能,還有的農民將產銷結合發展成為一條龍服務的企業;第二,家庭經營逐漸擺脫了小農經濟影響,逐漸向規模化、機械化的方向發展;第三,土地等重要生產資料也不同程度發生集中,從而引致家庭積累率不同,勞動力數量、文化素質、經營產業等都會發生更大的差異。可以說,承包責任制初期的小農家庭經營方式,實際上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發展成為個體或私營性質的家庭式企業,相當部分戶主成為企業主。由此可以看出,家庭經營所帶來的收入通常不同于其它來源收入,其差別較大是正常的,大于總收入差別也具有必然性①材料分析表明,農民從傳統家庭經營中,分化出帶有個體、私營性質的家庭經營,這類似于城市中第一批致富的“個體戶”, 他們購置更多更先進的固定資產,通過承包、租賃等方式經營具有一定規模的農場、果園、魚塘,或種植特種農作物、養殖珍稀水產等,或從事非農業經營,例如搞運輸、搞商業、經營餐廳、旅館等服務業等。這類家庭經營收入通常較高,且從事此類家庭經營的農戶也少。。但從其自身軌跡看,2003 年后也呈不變或略下降的傾向,這可能也一定程度上帶動了總差別的下降。

表6 農村體制改革后居民收入總差別與不同來源各項收入的擬基尼系數
財產性收入的擬基尼系數也遠高出總收入的基尼系數,成為引起農村收入差別擴大的因素,其原因在前文中已經涉及。就是說,在我國目前條件下財產性收入只能集中在少數較高收入者手中,貧困階層根本沒有能力獲取。這也反映了財富積累的“馬太效應”:先富起來的家庭,積累了財富,成為企業主和投資者,他們的財產性收入在其總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上升,而致富人越來越富。
非企業工資收入的擬基尼系數與總收入差別的關系是變化的,在2003 年之前小于總收入的基尼系數,在這之后則大于總收入的基尼系數。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非企業收入的受眾面較小,且越來越小。表4 數據表明,從1994 年到2008 年擁有該項收入的戶數占比下降了34.53%,,,在各項中下降比重最大。這勢必造成非企業工資收入擬基尼系數在某個年份后由小于變為大于總收入基尼系數。另一方面,小于總收入差別的各項收入差別有:企業工資性收入有一個最小的集中率且總是小于總收入差別,這值得深入研究。文獻考察表明,在研究中國農村收入差別的文章中得出的通常結論是,企業工資性收入是擴大農村收入差別的重要因素①例如趙人偉等測算出中國農村1988 年和1995 年的工資收入擬基尼系數分別為0.710 和0.738,得出“中國農村收入不平等最為重要的來源是工資收入。它對農村收入分配總體不平等的作用為40%,工資收入高度集中在高收入組”(1999)。。為什么天津農村居民的工資收入卻成為縮小總差別的因素?我們把分析的視野擴展一下,研究2008 年全國各地區農村居民不同來源人均純收入,發現工資性收入水平在全國各地區農村之間的差異極大。人均工資性收入最高的5 個地區為上海(8,108.32 元)、北京(6,389.31 元)、浙江(4,587.44 元)、天津(4,064.95 元)以及江蘇(3,895.5 元),最低的5 個地區為新疆(422.82 元)、云南(617.47 元)、西藏(759.72 元)、內蒙古(806.48 元)以及海南(808.63元)。可見,工資性收入獲得者多分布在那些較為富裕、周邊城市發達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較快的地域,中西部農村居民獲得較少。這勢必造成工資性收入較高的集中率,即較高的擬基尼系數。本文作為案例研究的天津(及山東②山東省2008 年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2263.46 元,占總收入的比重為40.12%。)農村在全國屬于城市化、非農化程度較高、企業工資性收入比重較大且水平較高的地區,近80%的家庭都有企業工資收入(見表4),平均比重占總收入的50%上下,并且各個區縣差異不是特別大,因而集中率必較全國情況偏低,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縮小總差別的力量。不僅如此,如果前后比較一下,其較小差別在2003 年后也沒有多少變化,因而實際上也就抵消了非企業工資收入在2003 年后的擴大,從而使總工資收入差別整體上小于總差別,成為致使總差別縮小的因素。這可能代表了中國農村下一步發展的趨勢。
天津農村居民轉移收入的擬基尼系數較低,且小于總基尼系數,不過有一定波動性。總體來看,獲得此項收入的家庭比重為60%以上,并且集中于較低收入家庭,表明主要由財政支付的轉移收入的分配是傾向于較貧困家庭,這符合財政補貼政策的預期結果(山東農村案例略有不同,但年份過少似不足以說明問題)。
(七)農村居民各種來源收入對總收入差別的影響程度(貢獻率%)
利用公式(4)可求得不同來源的各種收入對總收入差別的貢獻率,具體見表7。在各項來源收入中,家庭經營收入是農村居民總體收入差別的最大貢獻者,貢獻率平均保持在60%左右;處于第二位的是工資性收入,對總體差別的貢獻率大約在30%左右①這一結果得到了魏后凱等(1997)及萬廣華(1998)研究結論的支持。,其中企業工資收入的貢獻占大部分,平均為23 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貢獻率都較小,不到5%。從變動趨勢來看,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及轉移性收入的貢獻率均呈上升趨勢,原因是這三項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及擬基尼系數分別都是上升的;不過由于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故其對總收入差別的貢獻率雖然上升但比重不大;家庭經營收入的貢獻率呈下降態勢,主要由于其收入比重下降幅度更大,所以雖然其擬基尼系數是上升的,但總體上還是造成家庭經營收入的貢獻率呈下降趨勢②這一變化趨勢得到了張平(1998、2006)的映證。。

表7 農村體制改革中各種來源收入對總收入差別的貢獻率(%)
總之,通過以上從各種收入來源的收入比重、獲取各收入的家戶比重、各收入差別與總收入差別的關系等側面比較全面的討論,可以歸納出如下一些觀察:在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各種收入來源中,對農村居民收入總差別影響最大的是家庭經營收入。這項收入的比重大、差別大,涉及絕大多數家庭,且其差別大于總差別,故其對總收入差別的貢獻最大,是目前階段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的主要變量,但其趨勢是下降的。
影響力處于第二位的是工資性收入。工資收入的比重較大,差別相對不大,家戶分布較廣泛,但其差別低于總收入差別,所以其較大的貢獻率主要是其收入比重較大所致。從本身來看,現階段工資性收入的差別程度較低(其擬基尼系數小于總收入的基尼系數),是縮小收入差別的重要力量。隨著農村體制改革的深化和農村城鎮化發展,工資收入的比重特別是其中的企業工資收入比重會持續上升,這可能會導致居民間收入差別減小。
貢獻率居第三位的是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家戶分布較窄,其差別大于總收入差別,如2008 年財產性收入擬基尼系數高達0.803,9,是相對于總收入來說分配最為不均等的一項收入,表明農村的財產積累效應已經開始明顯化。只因其比重很小,故對總收入差別的影響不大,但從發展看其趨勢是逐漸增大的。
居第四位的是轉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轉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所占的比重較小,內部差別程度不大,對總收入差別是縮小的影響,或者說對其擴大是一種抑制性影響。
結合前文的細致分析,在這里我們系統回答開篇提出的問題,即為什么天津農村居民的收入差別從2003 年開始轉而下降?原因可能有兩方面:(1)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下,工資性收入的比重持續上升而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從2003年開始工資性收入的比重穩定大于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比重,且兩者此消彼長的差額越來越大;由于此變化是在工資性收入的分配差別遠小于家庭經營性收入差別的前提下,所以工資性收入持續增大必促使總收入差別下降;(2)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自身的分配差別,都表現出先升后平甚或后降的變動特征,而拐點大致都出現在2003 年左右。由此可見,正是在這兩個大的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天津農村居民的收入差別在改革過程中呈現出符合預期的倒U 型變化。這也為解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別過大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繼續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收入來源的結構性調整,向非農化發展,同時縮小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分配差別。
(八)從整體考察各項收入差別變動和比重變動對總收入差別變動的影響
從收入來源的角度看,總收入差別的變化是各項收入的擬基尼系數與其比重共同變化的結果,也就是說是各項收入差別變動與其收入結構變動共同作用所致。但是如果從整體上看,那么各分項差別變動的加總與各分項比重變動的加總,二者比較到底哪個因素對總差別變動起作用更大更重要呢?

這里,以天津1994 年和2008 年為例進行分析,用1994 年各種收入的比重乘以2008 年各種收入的擬基尼系數的和,同以1994 年各種收入的擬基尼系數乘以2008 年的各種收入的比重的和加以比較。計算過程如下:

農村居民各項來源收入交叉相乘的虛擬結果見表8。從計算的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到:如果以2008 年各種來源收入的比重取代1994 年的比重,而其分配差別仍然保持1994 年的狀態,則計算的結果(0.275,7)與2008 年的實際基尼系數 G2008(0.311,3)相差較大(0.035,6),而與1994 年的實際基尼系數 G1994(0.287,8)相差較小(0.012,1)。這說明兩個比較年份的收入差別的變動,主要不是由收入比重變動引起的。
如果以2008 年各種來源收入的擬基尼系數取代1994 年的擬基尼系數,而收入比重則仍然保持1994 年的不變,則計算的結果(0.347,2)與2008 年的實際基尼系數相差較小(0.035,9),而與1994 年的基尼系數相差較大(0.059,4)。這說明兩個比較年份的收入差別變動,主要是由收入差別變動引起的。

表8 1994—2008年天津市農村居民各種來源收入交叉相乘的虛擬結果
這幾點觀察合起來的啟示:1994 到2008 年農村居民總的收入分配差別的變化,主要是由各種來源收入內部的分配差別的變化引致的,而不是各種來源收入構成的比重變化所致。如果將虛擬相乘的計算結果和跟1994 年的實際基尼系數0.287,8 相比較,可以發現小于它,而大于它,可以證明各種來源收入的內部差別對總收入差別的影響,較其比重對總收入差別的影響要大。進一步可推測,從總體上看,這期間各種來源收入的內部差別使總收入差別擴大,而收入比重變動可能使總收入差別縮小。
其次,這些虛擬分析結論可在下面實際數據的分解分析中可得到進一步驗證。式(3)兩邊對t 分別求導,則:


表9 農村居民收入差別擴大部分中各種收入的分配效應與結構效應分解
表9 中的天津(及山東)的實際數據分析。從總體上看,在考察期內,分配效應是導致總收入差別擴大的主要因素,對收入差別擴大的貢獻率達 125.39%(山東為144.34%),即各收入來源內部收入差別的變動,是引起農村內部收入差別變動的主要原因①這再次證實并支持了我們以前的分析結論,見陳宗勝、周云波(2002)。;結構效應是負的,即各收入來源比重的變化是導致收入差別縮小的原因。進一步細致考察,在分配效應中,工資性收入內部差別是導致總收入差別擴大的最主要的因素,貢獻率為82.44%(山東為77.95%);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效應次之,為34.66%(山東為72.07%);轉移性及財產性收入的分配效應很小,均僅為幾個百分點(山東為負,但絕對值較小)。在結構效應中,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收入差別縮小效應是最大的,貢獻率達-57.29%(山東為-95.87%),彌補了其余收入項的差別擴大效應,且導致總的結構效應為負,其對收入差別產生縮小的作用。
將分配效應與結構效應綜合起來看,工資性收入是導致總收入差別擴大的最主要因素,其貢獻率達到了93.32%(山東為117.37%);轉移性收入的影響次之,其貢獻率為15.76%(山東為31.20%),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府在轉移性收入的分配上存在一定的問題;財產性收入的差別擴大效應最小,為13.55%(山東為 6.43%),與我們以前研究發現財產性收入的效應為負的結論不一致(陳宗勝、周云波(2002)),由此不難看到,財產性收入在農村居民收入差別中發揮的作用由縮小效應轉化為擴大效應,并且隨著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的加快,其收入差別擴大效應將會越來越明顯,應引起我們格外關注。家庭經營性收入則是導致收入差別縮小的因素,其貢獻率為-22.63%(山東為-23.80%),意味著家庭經營性收入起著均衡化收入、縮小收入差別的作用②這一結果與張平(2006)的研究結論一致。。因此,提高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水平,將有助于縮小農村內部的收入差別。
前文已經對天津農村居民收入差別從2003 年開始轉而下降的原因,進行了定性的解釋,而具體影響的程度未予說明,在這里我們利用分解公式(5)對其定量分析。由于影響因素的作用具有持續性,收入差別發生逆轉并非一時之力,為了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我們把分解分析的范圍選定為2003—2008 年③這些年份中天津農村居民的收入差別是持續下降的。。具體的分解結果見表10。

表10 天津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縮小中各種收入的分配效應與結構效應分解(2003—2008年)
表10 中的數據表明,從總體上看,分配效應和結構效應都是天津農村居民收入差別轉而下降的影響因素,這與前文的定性解釋相一致。兩者中比較分配效應的作用更大些,貢獻率達到83.54%,其中家庭經營性收入的貢獻居于第一位,為73.28%;工資性收入次之,為17.24%;轉移性收入的作用較小,僅為2.55%;而財產性收入則有拉大收入差別的效應。結構效應的貢獻率不足17%,其中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差別縮小作用最大,部分抵消了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以及轉移性收入的負效應,以致結構效應最終對收入差別產生平抑作用。
將兩個效應綜合起來分析,家庭經營性收入是導致收入差別轉而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其貢獻率達到114.51%;工資性收入的正向作用次之,其貢獻率為4.82%;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則具有負向影響即擴大收入差別的效應,其貢獻率分別為-14.92%、-4.41%,這也與前文的分析相吻合。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別不斷拉大,雖然近年來上升的總趨勢有所緩解,但仍居于較高的程度。本文利用天津(和山東)農村社會經濟調查數據資料,發現了與全國總的趨勢不同的新現象,即天津市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由上升轉而下降的趨勢。我們選取農村體制改革的若干變量進一步研究發現:農村改革導致的分配效應和結構效應都是天津農村居民收入差別從2003 年開始轉而下降的重要原因,兩者比較而言,分配效應的作用更大些。從各收入來源看,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分配效應和結構效應都是最大的,兩者疊加最終表現為家庭經營性收入是導致收入差別轉而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工資性收入的差別縮小效應次之。這些研究結論都具有明顯的政策指導意義,為針對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差別提出政策建議提供了依據。
(1) 天津市農村內部收入差別由上升轉而下降,為解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別過大的問題提供了借鑒:繼續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縮小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內部的分配差別,同時促進收入來源的結構性調整,向非農化發展。具體的改革措施有:逐步取消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大力推進城鎮化,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順利轉移;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創新農業經營方式,發展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經營;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渠道。
(2) 家庭經營收入差別是農村居民收入差別形成的主要來源,近年來其在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著縮小收入差別的效應。因此,應當通過土地的流轉、農業經營方式的創新及向規模化、專業化和集中化發展,擴大家庭經營收入水平,激發其縮小收入差別的效應,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差別逐步下降。應充分認識到這一發展趨勢,因勢利導,在堅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引導農民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推動家庭經營性收入差別適度減低。
(3) 大力推進城鎮化,擴大農村居民就業。工資性收入在全國是導致農村居民收入差別擴大的最主要因素,這可能與獲得該收入家戶的比重較少有關;而在天津最近幾年則有抑制收入差別擴大的作用,這是符合規律的,應當順勢而為,增強工資性收入的差別縮小效應。具體的措施為:持續推進城鎮化,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和技能培訓,積極擴大農村居民就業。
(4) 重視和預防財產性收入擴大收入差別的效應。目前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所占的比重不高,在農戶之間的差異很大,對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的擴大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可預見的是,隨著農地確權流轉,特別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將穩步增長,財產的集中程度也會隨之加劇,促使財產性收入差別成為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差別擴大的重要因素。目前的選擇應是,一方面認識到財產性收入差別上升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創造條件讓越來越多的農村家庭擁有財產性收入,從而減緩上升的速度。
(5) 改進和完善轉移性收入的分配機制。轉移性收入存在明顯的收入差別擴大效應,與其應具備的補貼低收入階層的功能相悖,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府在轉移性收入的分配上存在一定的問題,如轉移性收入中的離退休金集中于高收入家戶,政府發放的救濟撫恤金并不是完全傾向于低收入戶等等。因此,對其分配的機制還需進一步的改進和完善,以達到真正補貼農村貧困家庭的目的。

附表:全國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格局(%)
[1] 陳宗勝. 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M].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1991.
[2] 陳宗勝,周云波. 再論改革與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國發生兩極分化了嗎[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3] 陳宗勝. 雙重過渡經濟學[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4] 陳宗勝,鐘茂初,周云波.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和發展[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
[5] 馬九杰.農業、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民收入差別變化[J].改革,2001(6):92-101.
[6] 唐 平.農村居民收入差別的變動及影響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6(5):69-75.
[7] 萬廣華.中國農村區域間居民收入差異及其變化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1998(5):37-42.
[8] 魏后凱.中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異及其分解[J].經濟研究,1996(11):66-73.
[9] 張 平.中國農村居民區域間收入差別與非農就業[J].經濟研究,1998(8):59-66.
[10] Howes,S and A. Hussain. Regional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M].London:The Suntory-Toyot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1994.
[11] Rozelle,S. Stagnation without Equity:Patterns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China's Rural Economy[J].The China Journal,1996,35:63-92.
[12] Wan,G. and Z. Zhou.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Using Household Data[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9(1):107-20.
[13] Knight,J. and Song,L. The Spatial Contribution to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7(2):195- 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