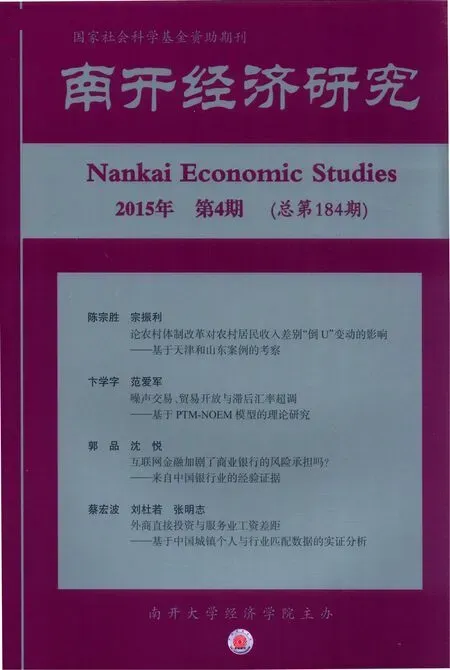外商直接投資與服務業工資差距——基于中國城鎮個人與行業匹配數據的實證分析
蔡宏波 劉杜若 張明志
眾所周知,服務業在一國經濟中的地位是衡量這個國家內部經濟結構是否合理、國際競爭能力孰強孰弱、經濟社會發展協調與否的重要標志。一般而言,這種重要地位被量化為服務業產出和就業比重。對于前者,過去數十年來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2013 年服務業產值首次超過制造業(祝寶良,2014)已經提供了很好佐證;對于后者,伴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結構調整,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大、就業容納能力強的獨特優勢會進一步得到發揮(胡曉義,2013)。其實,服務業不僅在就業數量方面表現搶眼,與制造業相比,其在就業結構和工資等方面的表現也有許多鮮明的特征。例如,服務業員工平均工資自2003 年開始超過制造業(2011,1.09 倍),而同一地區的金融、通信等行業與餐飲、零售等部門之間以及同一部門在東部、沿海與中部、西部之間差距明顯。那么,如何解釋十余年來中國服務業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及其當前特征的形成?顯然,這段時期正值中國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在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 的背景下,中國服務業開放和服務貿易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12 年中國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538.4 億美元,占FDI 總額的48.2%,,,超過制造業4.5 個百分點;2012 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增長12.3%,,,達到4,715 億美元,比貨物貿易增速高出近一倍。由此,能否把外資進入為特征的服務業開放視為對上述問題的一種解釋呢?能否建立起服務業領域對外開放與勞動力市場的聯系呢?
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命題之一,對外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歷來備受關注卻難有定論。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斯托爾伯-薩繆爾森定理提供了分析這一問題的理論框架,此后圍繞展開的實證研究大量涌現。目前來看,有關服務業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尚缺乏針對性研究,這與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快速上升形成了不小反差。況且,我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和服務業工資都表現出明顯的地區差異和部門差異,這恰好為實證研究提供了天然的樣本。因此,本文將服務業細分行業的外資數據匹配至中國城鄉移民調查數據中的城鎮個人,建立包含性別、技能、所在地區、所在企業和所在行業等豐富信息的微觀個人樣本,實證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服務業工資差距的影響。這不僅將對外開放收入分配效應的規范研究拓展到了服務業領域,也為中國啟動新一輪對外開放之時如何引導外資流向和縮小收入差距及其相應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工資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領域,針對服務業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還不多見。其中,通過宏觀變量的匹配構造出微觀數據樣本,用以檢驗對外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
1. 外商投資對東道國工資差距的影響
大量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擴大了東道國的工資差距,在控制了行業和企業因素后,FDI 仍然對工資差距有顯著拉大作用(Haddad 和Harrison,1993,摩洛哥;Girma et al.,2001,英國)。Lipsey 和Sj˙˙o holm(2001)利用印度尼西亞1996 年14000 個制造業企業數據,分析指出外資企業對藍領工人的工資支付比內資企業高12%,,,對白領工人的工資支付高22%,,。所以,FDI 拉大了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的工資差距。Driffeld 等(2010)采用1980—1995 年英國企業調查數據,運用IV-GMM 方法分析發現具有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效應的FDI 會提高高技術勞動力的相對工資水平。包群和邵敏(2008)研究指出外資企業提高了工業行業科技人員的相對報酬,FDI 的收入外溢效應與行業特征密切相關。許和連等(2009)利用1998—2001 年12180 家中國制造業企業數據,從行業和地區視角分析發現外資企業自身較高的技術水平和資本密集度等特征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內外資企業的工資差距。朱彤等(2012)將用2002 年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CHIP)分為技能組、所有制組、性別組,分別檢驗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工資水平的影響,發現FDI 擴大了工資差距。
很明顯,國內外有關FDI 影響工資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服務業樣本還不多見。戴楓和趙曙東(2009)驗證了上海市生產性服務業FDI 對技能工資差距的擴大作用。鐘曉君和劉德學(2013)認為廣東省服務業FDI 對工資水平有微弱的提升作用,但其中降低了消費性服務業的工資水平。此外,也有學者在服務業FDI 影響就業的研究中間接提到FDI 可能對工資水平具有的提升作用(薛敬孝和韓燕,2006)。
2. 基于宏觀和個人匹配數據的研究
勞動經濟學中最具影響力的研究之一是明瑟工資方程(Mincer,1974),它明確了工資與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等個人特征的關系,此后性別、種族、職業、行業和區域等因素對工資的影響也相繼得到關注(Bratsberg 和Terrel,1998;Altonji 和Williams,1992;Kain,1968)。隨著中國家庭住戶調查數據可獲得性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經過宏觀變量匹配的個人數據來檢驗工資水平受到的影響。Hering 和Poncet(HP,2010)利用“CHIP1995”分析發現,較好的市場準入條件促進了工資的增加,其中高技能工人更能從較好的市場準入條件中受益,民營企業相對國有企業更為敏感。Kamal、Lovely 和Ouyang(2012)利用“CHIP1995”和“CHIP2002”更為詳實地證明了HP 的結論。以HP 為基礎,李磊和劉斌(2011)利用“CHIP2002”就城市貿易影響個人工資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貿易對工資水平有提升作用,拉大了不同技能組、不同性別組的工資差距。Han、Liu 和Zhang(2012)利用中國城市家庭調查數據(UHS),在工資方程中引入高貿易開放度地區、南巡講話、加入WTO 三個虛擬變量,結論顯示加入WTO 導致工資不平等加劇。
綜上所述,以往研究大多采用制造業中行業和地區層面的宏觀數據,無法考慮個人特征差異、企業異質性等問題,比如在區分技能與非技能時,部分研究甚至直接以整個行業的員工技能水平作為替代。而且,就以往基于微觀數據樣本的研究而言,主要是將個人所在的地區與該地區的對外開放指標進行匹配,但顯然個人所在企業或行業的對外開放對工資水平的影響更為直接。本文將由此入手,在解決FDI 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的同時,控制個人、企業等因素,檢驗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服務業整體工資水平,以及不同的技能組、性別組、行業要素密集度組工資水平的影響。
二、計量模型、變量設計與數據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1 計量模型和變量設計
基于國外以往研究和微觀數據樣本的特點,本文以明瑟工資方程(Mincer,1974)為基礎構造用以檢驗個人工資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

其中,i 表示個人,j 表示個人所在的服務業細分行業。wageij表示個人i 在j 行業的小時工資。我們將個人月工資和周工作小時數相結合求得小時工資,主要是考慮到“同工不同時”這一現實情況。FDIj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表示服務業細分行業j的外商直接投資,即j 行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與匯率的乘積。在中國城鄉移民調查數據中個人所在的服務業被細分為以下14 個行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本文據此整理行業FDI 數據,將其與行業中的個人進行匹配。考慮到服務業發展水平和服務業就業人數可能會對服務業工資水平產生影響,本文引入服務業產值VADj和服務業年底就業人數EMPj來分別衡量這兩方面的作用。另外,Xij表示行業j 中個人i 的特征變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工作經驗、性別、婚姻狀態和職業類型等以及個人所在企業的特征,比如所有制、規模和所在地區等。其中,工作經驗的數據來自調查問卷中“您是從哪一年開始從事這份工作的?”,可以用被調查的2007 年減去該項數值得到。職業類型被劃分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農、林、牧、漁、水利生產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軍人、不便分類的其他從事人員等。國有企業的壟斷性質可能會影響其內部工資的制定,在此引入國有企業虛擬變量。企業規模被劃分為小(少于100 人)、中(100~999 人)、大(多于1,000 人)三種類型。在將數據中的省市區域代碼進行歸類后,省份和直轄市包括廣東、河南、湖北、上海、江蘇、浙江、重慶和四川。國外通常以是否取得高等教育文憑來劃分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不過,中國城鄉移民調查數據沒有提供最高教育程度的個人數據,我們采用調查問卷中“排除跳級、休學后的受正規教育年限”大于(等于)15 年和小于15 年來分別表示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之所以選取這一指標,是因為15 年對應了在中國取得大專及以上文憑所需的年限。
對于解釋變量FDIj需要說明的是,外資一般具有較高的中間品投入、先進的管理水平、較強的盈利能力以及高資本密集度和較高的技術水平等特點,所以外資進入服務業將會增加對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高他們的工資水平(Feenstra 和Hanson,1997)。長期來看,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會整體上提高行業生產率,這會進一步增加對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促進其工資水平的提高。對非技能勞動力而言,外資進入服務業可能產生兩方面的影響:第一,如果外資進入的動機是利用優惠政策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則會增加對非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高他們的工資;如果外資進入了房地產等投機性強或金融、保險等資本密集型行業,則會影響對非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薛敬孝和韓燕,2006),可能降低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第二,由于外資進入服務業加劇了產品市場上的競爭,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可能會降低工資水平(亓朋等,2008)。綜上,外資進入服務業對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影響無法確定。此外,服務業發展水平、服務業就業同樣會對個人的工資造成影響。從服務業發展水平來看,一方面行業發展水平可能對該行業工資的增加起到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勞動力的自選擇效應導致發展水平越高的行業勞動力市場競爭越激烈,從而降低了個人的工資水平。從服務業就業來看,一方面就業人數的增加可能導致人力競爭加劇,個人的工資水平下降;另一方面行業內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可能會提高在工資談判中的話語權,進而對工資水平有正向促進作用(鐘曉君和劉德學,2013)。由此可見,服務業發展水平和服務業就業對個人工資的影響也不明確。
2. 數據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本文中服務業行業層面的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并利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為以2007 年為基期的實際值。中國城鄉移民調查數據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發起調查,德國勞動經濟研究所(IZA)提供技術支持,我們使用2007 年數據中城市家庭調查、農村家庭調查和移民家庭調查中的城市家庭調查,該部分覆蓋了9 個省份(直轄市)、18 個城市、5,003 個家庭、14,683 個城鎮個人,涉及被調查者的年齡、教育、工作和家庭等方面的信息。本文將數據樣本限定為:從事工資性工作的服務業勞動力,合同類型為固定合同、長期合同和短期合同,男性年齡為16 歲到60 歲,女性年齡為16 歲到55 歲,剔除務農和自我雇傭勞動力。為了避免戶籍限制這一制度因素造成的偏誤,剔除農村戶籍的樣本,只保留城鎮戶籍。表1 列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及其討論
由于個人工資對行業變量的影響極為微小,將宏觀變量引入微觀工資方程的優點之一便是能夠減輕方程的內生性(Hering 和Poncet,2010)。考慮到服務業行業變量對個人工資影響的時滯性,且服務業行業變量和個人工資可能受到同時期的外部沖擊,本文采用Ebenstein 等(2009)的做法,將滯后一期的行業變量引入工資方程,以便解決外資開放可能存在的內生性,這使得本文設定的工資方程更加貼近現實。為了考察引入滯后期行業變量對內生性問題的解決能力,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檢驗行業FDI 的外生性。本文借鑒王志鵬和李子奈(2004)的思路,選取滯后三期的服務業FDI 作為服務業FDI 的工具變量。在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別對全體組、不同技能組、不同性別組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度組進行回歸后,DWH 結果顯示不拒絕服務業FDI 為外生變量的原假設(見表5)。當變量不存在內生性問題時,OLS 比2,SLS 更有效,表2 至表4 報告了回歸結果。

表2 全體組和不同技能組的回歸結果

表3 不同性別組回歸結果
如表2 所示,行業FDI 對工資有顯著提升作用,但對不同技能水平工資的影響顯著不同。FDI 顯著提高了服務業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對非技能勞動力工資的影響卻不顯著。這意味著,外資進入中國服務業擴大了對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升了他們的工資。以往部分學者指出,為利用相對充裕的非技能勞動力而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可能促進非技能勞動力工資的增加,這一結論顯然不被支持。行業產值和就業人數也對工資存在顯著的影響。對于全體組,行業產值提升反而降低了工資水平,而且行業產值對工資的負向作用主要來自非技能組。也就是說,行業產值越高的服務業細分行業,對非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越低,進而降低了這部分勞動力的工資水平。行業產值對技能勞動力工資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就業人數對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也有顯著影響,這說明在非技能群體中,“抱團”現象可能更加明顯,就業人數上升有利于其與雇主工資談判能力的提升,進而提高了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受教育年限對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但對技能勞動力的影響則不顯著。工作經驗對工資的影響呈現倒U 型作用,即工作年限的增加開始會提高工資,但工齡的進一步增加可能對于雇主而言意味著員工接受新知識的能力在下降,進而對工資有負面影響。此外,已婚、更大的企業規模對工資有正向影響,女性勞動力面臨“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

表4 不同要素密集型行業組的回歸結果
如表3 所示,FDI 對不同性別勞動力工資的影響均是顯著的。進一步的,對女性工資的提升作用較男性更強,即FDI 有助于縮小性別工資差距。其實,相比制造業,女性由于自身能力特質而更適合于服務業,許多服務業細分行業的女性就業比例顯著高于男性。值得一提的是,婚姻狀況對不同性別勞動力工資的影響具有顯著差異,結婚對男性工資具有明顯的正向拉動作用,對女性的影響則不顯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男性在婚后更多地承擔了“養家糊口”的責任,使其更加努力的工作甚至犧牲閑暇時間,而女性則更多從事家務活動、生育子女等無酬勞動(劉斌和李磊,2012);另一方面,男性的工資差距會對女性的婚嫁行為產生影響,通常工資水平較高的男性更容易得到女性的青睞,且在婚姻選擇上也更具競爭力,所以結婚率相對較高(Ginther 和Zavodny,2001)。
接下來我們將服務業細分行業按不同要素密集度類型進行重新劃分,參照蔡宏波(2013)的方法,將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房地產業,租賃商業服務業劃分為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將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劃分為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將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如表4 所示,FDI 對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工資水平有顯著提升作用,對技術密集型服務業有提升作用但不顯著,對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影響為負但不顯著。造成這些結果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近年來FDI 較多進入資本密集型行業,對這些行業勞動力的需求有所擴大,也提高了相應的工資水平。對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行業工資的影響不顯著但方向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前述技能組的回歸結果,說明FDI 不會提升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工資,也不會降低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資,而只對不同技能水平的個人存在顯著影響。這也再次說明使用個人微觀數據而不是使用行業層面的加總數據來研究這一問題的必要性。

表5 2,SLS與OLS系數及DWH檢驗結果
四、結 論
本文將中國城鄉移民調查數據的城鎮個人與其所在服務業細分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相匹配,利用OLS 和工具變量實證分析了外資進入對中國服務業工資的影響。研究發現:外資對服務業勞動力的整體工資水平有顯著的提升作用。針對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性別、不同要素密集型行業的分組檢驗表明:第一,FDI 顯著提高了服務業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對非技能勞動力的影響卻不顯著。第二,FDI 對服務業女性工資的提升作用大于男性,有助于縮小服務業中的性別工資差距并降低性別工資歧視。第三,FDI 對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工資水平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對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的影響不顯著,對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影響為負也不顯著。第四,行業產值對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的工資水平存在顯著的提升作用,對服務業中男性和非技能勞動力工資的影響顯著為負。行業就業人數的增加提高了服務業非技能勞動力的工資,且對男女工資水平均有提升,但擴大了性別工資差距。此外,行業就業人數的增加還降低了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工資水平。第五,以往研究的部分結論在本文中得到了證實: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工資水平;工作經驗對工資的影響呈現出倒U 型;已婚、更大的企業規模對工資存在正向影響。
正值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大幕拉起,在已然成為世界頭號引資國和全球服務業外資迅速興起的新形勢下,本文將外資進入為特征的對外開放與國內服務業工資差距建立起了聯系,根據研究結果我們提出如下建議:我國應繼續積極、穩妥、有序地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引導外資更多地進入服務業部門。當然,與此同時應更注重引資的質量和結構,加強引進具有較高資本、技術和知識含量的投資項目,充分發揮服務業外資通過直接的勞動力需求和長期技術外溢在提升我國技能勞動力工資水平及縮小性別工資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面對本文研究過程中揭示出的問題,我們認為,首先應該進一步加大對非技能勞動力的教育培訓力度,鼓勵對非技能群體及其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加速完成從非技能向技能的轉變。其次,為打破“同工不同酬”這一既損害經濟效率又顯失公平的扭曲性制度,應盡快取消國內勞動力市場上的頑固壁壘并摒棄各種歧視性規章,最大程度上消除勞動力市場分割,這對于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狀況意義重大。
[1] 蔡宏波. 國際服務貿易(第2 版)[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2] 包 群,邵 敏. 外商投資與東道國工資差異:基于我國工業行業的經驗研究[J]. 管理世界,2008(5):46-55.
[3] 戴 楓,趙曙東. 生產者服務業FDI 與東道國工資差距:理論與實證[J]. 世界經濟研究,2009(4):57-66.
[4] 鄧曲恒. 城鎮居民與流動人口的收入差異——基于Oaxaca Blinder 和Quantile 方法的分解[J]. 中國人口科學,2007(2):8-18.
[5] 葛玉好,曾湘泉. 市場歧視對城鎮地區性別工資差距的影響[J]. 經濟研究,2011(6):45-58.
[6] 李 磊,劉 斌,胡 博,謝 璐. 貿易開放對城鎮居民收入及分配的影響[J]. 經濟學(季刊),2011(10):309-327.
[7] 李 實,王亞柯. 中國東西部地區企業職工收入差距的實證分析[J]. 管理世界,2005(6):16-27.
[8] 李 實,楊修娜. 農民工工資的性別差異及其影響因素[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5):82-90.
[9] 劉 斌,李 磊. 貿易開放與性別工資差距[J]. 經濟學(季刊),2012(2):429-462.
[10] 亓 朋,許和連.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溢出效應: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2008(4):58-69.
[11] 王志鵬,李子奈. 外商直接投資、外溢效應與內生經濟增長[J]. 世界經濟文匯,2004(3):23-34.
[12] 許和連,亓 朋,李海崢. 外商直接投資、勞動力市場與工資溢出效應[J]. 管理世界,2009(9):53-69.
[13] 薛敬孝,韓 燕. 服務業FDI 對我國就業的影響[J]. 南開學報,2006(2):125-134.
[14] 薛欣欣. 不同所有制部門工資差異的行業分布特征分析[J]. 產業經濟評論,2010(1):52-66.
[15] 姚先國,俞 玲. 農民工職業分層與人力資本約束[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5):16-23.
[16] 鐘曉君,劉德學. 服務業FDI、職工工資與行業收入差距——以廣東為例[J]. 國際經貿探索,2013(3):48-61.
[17] 朱 彤,劉 斌,李 磊. 外資進入對城鎮居民收入的影響及差異——基于中國城鎮家庭住戶收入調查數據(CHIP)的經驗研究[J]. 南開經濟研究,2012(2):33-55.
[18] Altonji,Joseph G.,Nicolas Williams. The Effects of Labor Market Experience,Job Seniority,and Job Mobility on Wage Growth [R]. NBER Working Paper,1992,No. 4133.
[19] Blomstrom,Magnus,Persson,Haka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 World Development,1983,11(6):493-501.
[20] Bratsberg,Bernt,DekTerrell. Experience,Tenure and Wage Growth of Young Black and White Men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8,33(3):658-82.
[21] Becker,Gary Stanley.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nd edition,1971.
[22] Driffield,Nigel,Sourafel Girma,Michael Henry,Karl Taylor. Wage Inequality,Linkages and FDI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R]. IZA Discussion Papers,2010,No. 4722.
[23] Feenstra,Robert C.,Gordon Hanson.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1979-1990[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907-40.
[24] Girma,Sourafel,Katharine Wakelin. Regional Under Development:Is FDI the Solution? A Semiparamitric Analysis [R]. GEP Resaer Paper,2001,01-11.
[25] Haddad,M.,A. Harrison.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42:51-74.
[26] Mincer,Jacob A. Schooling,Experience and Earnings [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27] Hering,Laura,Sandra Poncet.Market Access Impact on Individual Wages:Evidence from China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0,92(1):145-59.
[28] Kain,John F. Housing Segregation,Negro Employment,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5(2):175-97.
[29] Kamal,Fariha,Mary E. Lovely & Puman Ouyang,Does Deeper Integration Enhance Spatial Advantages? Market Access and Wage Growth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2,23:59-74.
[30] Han,Jun,Runjuan Liu,Junsen Zhang.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87(2):288-97.
[31] Lipsey,R.,F. Sjohol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in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415-22.
[32] Zhao,Yaohu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The Case of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1,12:4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