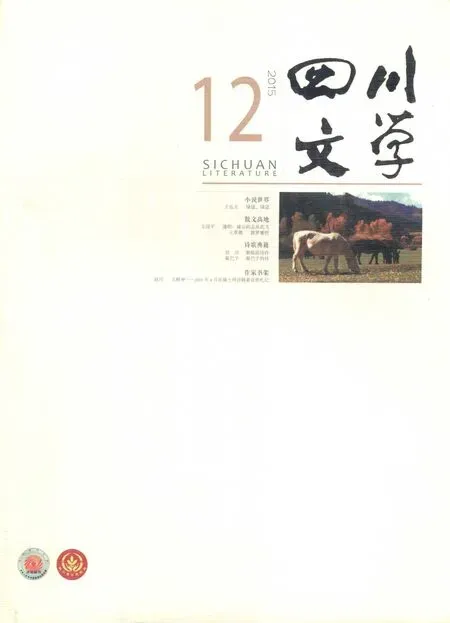活在漫寫的世界里
○ 圖文/邵小明
本人大名叫小明。屬相鼠。人生哲學:漫者無疆。
漫寫,對我來說就是畫畫,畫肖像,畫我周遭的人,畫夢,畫如夢般的人;繼而,竟發展到在宣紙上“畫字”……
漫寫,有時是一種宣泄:是一場短暫的、突如其來的、激情澎湃般的沖刺、格斗和廝殺;是一次"恨"之入骨般的陣痛,或許,更是一番大“愛”無疆后的疲憊……
因為漫寫,有人開始叫我“畫家”、“漫畫家”、“漫師”、“生活家”“一丁先生”……總之,無論是什么,也不知是否可以就此而“立業”?反正有點某某“家”(小孩童們愛做的游戲家家)的味了,也好!
漫,這個字和相關諧音的字我似乎都喜歡。慢慢地來,漫無目的地走;在慢中觀,在走中看;讀出自然,聆聽天籟,漫筆描出個真”情“,慢慢繪出個"真“像,謾筆寫就個心語……
漫寫,始于愛,好于動;行于場,歸于心。此中之愛源于喜,心動連手動,筆下留情!情之所場言非情場,乃情懷之境、人生道場;無華天地,水墨歸心。
漫與寫,終是道,吾必往之。凈心漫寫,為而無為也。
漫寫故事一:菲利普·勒加爾
一日,成都送仙橋的姚先生來電話,說有一位塞舌爾共和國的駐華大使菲利浦先生要邀約見我,出于禮貌如約前往。原來,這位來自東非島國的大使先生及隨從幾天前參觀成都民間藝術市場,途經他的篆刻小店時,看見門上有我為姚先生早年畫的水墨肖像頓感欣喜,便拜托篆刻先生約我一見,意在為他畫像。見得大使與翻譯官,幾番茶飲與交流下來,對菲利浦先生便有了幾許的敬意和了解:這個樸實的大胡子粗獷的線條下面蘊含著細膩而寬闊的文化情懷。于是,濃墨就著水韻,大使先生躍然于宣紙之上。
漫寫故事二:吳紹同
2011年春季的一天,因為攝影的緣分,朋友介紹我與臺灣著名的攝影家吳紹同先生認識。先生一生從事攝影,曾經在蔣介石身邊工作;他不僅僅是一位優秀的生態動物攝影家,還致力于攝影史書籍的收集和整理,退休后在大陸內蒙的赤峰市創建了別具一格的攝影圖書館,成為國內乃至世界攝影界的一道獨特的風景。對先生的敬仰移于筆端便成就了我和先生至今的友誼(在自貢贈送漫寫肖像);2014年2月還專程在臺北看望了九十高齡的先生。
漫寫故事三:魏愛吾
在四川大學文化與新聞學院從教的德國籍外教魏愛吾(中文名)先生是個有趣的家伙,我們互道:哥們。高高的個頭高高的鼻子,說起中文來抽動著面部豐富的表情;他喜愛東方文學入迷,甚至將他在捷克的書房取了一個中國式的雅名:捷薌廬(我題寫的)。此君還好飲四川白酒,初次相遇就不亦樂乎;快哉!為他留下尊容一幅。
漫寫故事四:樊建川
中國抗戰主題的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四川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是典型的“下過鄉、扛過槍”的老知青,后又任教、當官、辭官經商,再從實業到文化(收藏),可謂是一個“革命家”了吧?!革了誰的命?當然是他自己的命。如今,在大邑縣的安仁鎮搞出一個“建川博物館”來。如此這般的人物,穿行在民國的街頭巷尾,自然“拿下”為妙。
漫寫故事五:羅雪松
前不久,到四川郫縣的團結鎮喝茶,其間來了一個五十開外的漢子,此人頭戴草編“禮帽”,不修邊幅還滿臉堆笑,人稱:老羅;十足像一個“老農”。問起他在干啥?他言:藝術;頓時便生好奇起來。此君農忙下地,農閑忙“藝”,那可是當地的“才子”和“高人”:雕塑、快板、說唱、書法......樂此不疲;這正是高手在民間啊!
漫寫故事六:路明章
舊時四川等地的“館子”(飯館)里都有“堂倌”,就是在飯館引客鳴堂的招待人員,其責是迎客入席、鳴唱菜品、點菜、傳菜、端飯、結賬、送客。這種傳統風俗隨時代變遷如今已漸行漸遠。作為傳統膳食文化的歷史當事人和見證人,現年75歲有余的路明章先生,是現存“堂倌”唯一的非遺傳人。路先生的“絕技”和十足的底氣令人嘆服,記下老人的神貌當是對忘年之交的一次美好的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