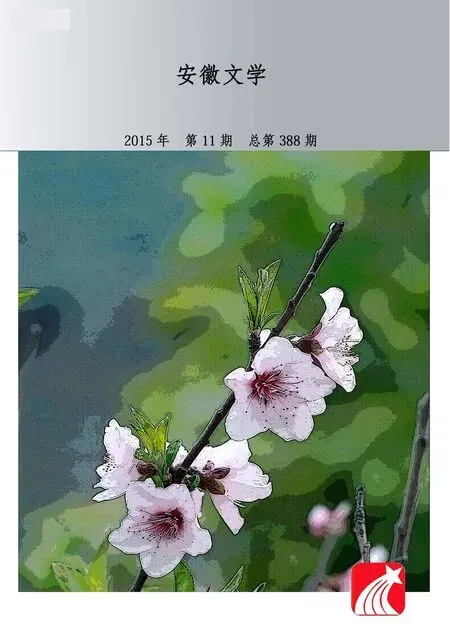福克納意識流作品的開放性結構:長句的運用
劉蜀云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
福克納意識流作品的開放性結構:長句的運用
劉蜀云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
美國南方作家的代表福克納以大膽的實驗性手法將意識流小說創作推向了巔峰。本文擬以其兩部意識流杰作《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為例,分析作家如何運用兼具連續性和包容性的長句來構建意識流小說的開放性結構,從而展現綿延不絕的內心生活之流。
福克納 意識流小說 開放性結構 長句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南方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深陷于傳統與變革尖銳的社會沖突之中。美國南方作家的代表福克納憑借前所未有的大膽手法和具有開放多元性的意識流小說創作再現出那一時期矛盾重重、分崩離析的現實生活。其豐富的創作背景和多元的藝術技巧早已使他的意識流作品載入文學的史冊,而其獨特的開放性結構無疑也是使其作品大放異彩的重要原因。這種開放性特征無論在他的句子結構中還是意識流作品的整體敘述結構中都展露無遺。
一、題材決定長句的使用
在句法層面,福克納復雜難懂、不斷延長的句子如此引人注目,因而在為他贏得聲譽的同時也招致不少批評。沃倫·貝克曾給他冠之以“一位極富獨創性和多才多藝的文體家”[1]53的名號,但他也同時指出,“沒有哪一位能與之媲美的當代美國小說家像威廉·福克納一樣因為自己的文體而被如此頻繁或嚴厲地批評過。”[1]53其文體導致的爭議在很大程度上因其在語法、標點、句子結構等方面無視邏輯和規則所致。對福克納而言,文體不過是作家用來達到其藝術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正如他在弗吉尼亞大學擔任駐校作家時所說:“文體可以是變化之流動性的一部分……文體必須隨著作家試圖講述的內容而變化。”[2]279
因此福克納長句的使用是由其題材所決定的,即他所極力描摹的人物內心在綿延不絕的鐘表時間中自由流動、彼此融合的心理狀態。福克納自己曾解釋道:“……沒有人是他自己,他是他的過去的總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他的將來的總和。而長句則是將他的過去,也許還有他的將來融入他現在做某件事的那一時刻的一種嘗試……”[2]84這種“把一切都用一個句子來表達”[3]的嘗試使得他能夠“凝結某個瞬間,并同時探尋它的全部復雜性。”[3]他一直在試圖表達內心超驗的感受,描繪意識那種種聯想性的、分析性的構成成分,而正是意識這些混雜在一起的組成部分使現在這一時刻延伸到了無盡的永恒。
他努力的成果便是那冗長的句子,句子中包含了多種多樣卻又彼此關聯的成分,例如對意識的對象的觀察、記憶、推測、解釋和修飾等等。到此為止,表面上看起來無窮無盡的長句也許是“作為小說工具的語言所最能接近意識本身的復雜瞬間”[1]62-63的形式了。在他的意識流名著《喧嘩與騷動》中,對康普生家的長子昆丁的一段意識的描述對此做出了充分的說明。昆丁在圣誕節回家的旅途中遇到一個老黑人,當火車漸行漸遠,他扭頭凝望老黑人的身影時,不禁對黑人的行為方式陷入了沉思。
“列車拐彎了,機車噴發出幾下短促的、重重的爆裂聲,他和騾子就那樣平穩地離開了視域,還是那么可憐巴巴,那么有永恒的耐心,那么死一般的肅穆:他們身上既有幼稚而隨時可見的笨拙的成分也有與之矛盾的穩妥可靠的成分這兩種成分照顧著他們保護著他們不可理喻地愛著他們卻又不斷地掠奪他們并規避了責任與義務用的手法太露骨簡直不能稱之為狡詭他們被掠奪被欺騙卻對勝利者懷著坦率而自發的欽佩一個紳士對于任何一個在一場公正的競賽中贏了他的人都會有這種感情,此外他們對白人的怪癖行為又以一種溺愛而耐心到極點的態度加以容忍祖父母對于不定什么時候發作的淘氣的小孫孫都是這樣慈愛的,這種感情我已經淡忘了。”[4]
昆丁自小生活在南方,黑人作為他家鄉南方的一部分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他對黑人非常了解,也對他們有著某種深厚的情感,對黑人可悲的境地以及黑人和白人之間奇異的關系洞若觀火。對黑人身上矛盾個性和處事方式的觀察及分析全被囊括進了一個句子,而正是這個長句將昆丁過去數年來的體會、記憶與眼前旅途中碰到老黑人的那一刻連結了起來并糅為一體,于是“此刻”便延伸到了漫長的過去。
二、擴展意象的插入
在人物陷入沉思默想或是對故事情節進行闡釋的時候,福克納也會把幻想或是擴展的意象插入人物的思緒或是話語中的一個句子里。當這些人物對事件進行冥想,或竭力描述細節,或是提出一個又一個假設的時候,他們的遲疑和臆測則會為讀者提供一個對現實本身的神秘莫測、難以理解的視角。福克納的另一部意識流小說《我彌留之際》中本德侖家的二兒子達爾是一個“先知”式的人物,敏銳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常使他能看透別人的內心,因而被周圍人所憎惡,甚至被視為瘋子,送進了瘋人院。達爾通過自己的“內心之眼”對已死去的母親的容貌的描述頗富弦外之音,“手”這一由遺容延伸而來的意象被賦予了生命和思想,因而產生了某種難以言說的神秘感。
“它在枕頭上像是綠銹逐漸增多的銅鑄遺容,只有一雙手還有點兒生氣:那是一件蜷曲的、多節的靜物;具有一種已筋疲力盡然而還隨時準備東山再起的品性,疲憊、頹衰、操勞尚未遠離,仿佛這雙手還在懷疑安息莫非果真來臨,正對這中止狀態保持著支棱著犄角的、小心翼翼的警惕,認定這種中止不會久長。”[5]56
盡管福克納的語詞之流滾滾向前,源源不絕,有時甚至讓人有接不上氣的感覺,因而招致啰嗦的批評,但他的“語詞鏈”在他分析入微、詳盡縝密的文體中似乎自有一席之地。這一系列詞語,以其特有的形式,非但不累贅,反而經過精心的排列,達到了一種累積的、漸進的效果。盡管看起來過長,它們卻往往是高度壓縮的表達方式。以長句為特征的所謂累贅迂回的文體并不會像有些人所宣稱的那樣,破壞敘述的節奏和重要性,相反,卻成功地將經驗的多個側面呈現出來,并使意義以逐步、持續和更為豐富的形式揭示出來。
三、長句帶來的閱讀體驗
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所展示的那樣,有時長句中所包含的意義極其豐富,再加上晦澀難解,讀者不得不面對一直要去搜尋和闡釋真正意義的挑戰。此外,令人目眩的句子長度常常令讀者,甚至是經驗豐富的讀者難以確定單獨懸垂的動詞的主語,或是一直重復出現的第三人稱代詞究竟指誰,后者在達爾關于他的兄弟朱厄爾的內心獨白中十分典型。在小說《我彌留之際》第四十二章達爾的獨白部分有一段關于朱厄爾的神情和動作的描寫:
“他臉上又出現那種木呆呆的神情了;那種冒冒失失、狠巴巴、血氣很旺、直僵僵的神情,仿佛他的臉和眼睛是屬于兩種不同木頭的顏色,那種不對頭的淺色和不對頭的深色。……他已經走回到馬身邊去了,正在把馬鞍卸下來,他移動時,他那件濕襯衫服服帖帖地裹在他的身上。”[5]171
全章出現了三十八個第三人稱代詞“他”,有的是指大兒子卡什,有的則是指朱厄爾,卻從始至終都未出現朱厄爾的名字。讀者只能根據前文提及過的朱厄爾的呆滯神情以及他酷愛馬的特點來推測此處是對朱厄爾的描寫。也正是透過不斷重復使用的這個冷冰冰的代詞“他”,讀者才窺見達爾對深得媽媽喜愛的朱厄爾的嫉妒和仇恨,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愿提起,而長句中所包含的對朱厄爾神情和一系列動作的詳盡的描寫卻又向我們展示出無時無刻不在盯著朱厄爾的達爾對他十分關注的矛盾內心。
四、結語
總之,包羅萬象的長句表面上仿佛在讀者的閱讀之路上設置了一系列連續不斷的障礙,而所有障礙事實上都指向同一個目的,那就是,“使形式和思想都保持流動和未完結的狀態,可以說,一直處于運動中和未知的狀態,直至(句子的)最后一個音節塵埃落定。”[6]福克納運用長句所創造的連續性和包容性正是他意識流作品開放性特征的體現,他所追求的其實是一個沒有停頓的媒介,這個媒介就是“現在”這個瞬間,或是由一個瞬間向另一個瞬間的就如生活本身一樣持續綿延卻又難以察覺的流動。
[1]Warren Beck.William Faulkner’s style.Robert Penn Warren,ed.Faulkner: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6:53,62-63.
[2]Frederick L.Gwynn&Joseph L.Blotner,eds.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M].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84,279.
[3]MichaelMillgate.TheachievementofWilliam Faulkner[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 286.
[4]福克納.喧嘩與騷動[M].李文俊,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91.
[5]威廉·福克納.我彌留之際[M].李文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56,171.
[6]John T.Matthews.The discovery of loss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The Sound and the Fury[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