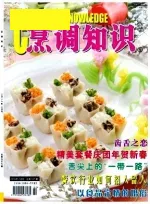親情“寶貝”菜
宋殿儒/文
霜降已過,媽媽就會腌制她的“御菜”了。
媽媽的“御菜”是腌制在老家的兩個“聚寶盆”里的。它們一個是肚大個大而脖子細的百年瓷壇子,另外一個是白里透青,口大腰肥,又矮又壯的青花瓷“甕兒”。這兩樣東西,媽媽說在我家已經祖傳好多輩人了,是家里的傳家之寶。其實,打我記事起,這些寶貝,并沒在家人眼中看作是什么價值連城的東西,而是它里面常常放的那些不值錢的東西倒真正的被視為“寶貝”。
打我記事起,每年的霜降一過,媽媽就開始清洗這兩個寶貝,清洗完后,就放太陽地上去曬,一直曬到它們里外都徹底的干了,才把它們重新收拾回去在廚房的門角放好,等待著放進去一年里最中用的“寶貝”。那些被視為“寶貝”的東西,其實也不是什么珍貴的東西,全是一些經過媽媽加工能讓我們一家人享用一個冬春的家鄉地道腌菜。有紅薯梗梗腌菜,有蘿卜櫻櫻腌菜,有雪里蕻腌菜,也有蘿卜干、油菜根等腌菜。那時候各家各戶都缺糧食,一年里半年菜地過日子,因而,這些能夠儲藏并享用大半年的東西,就被我們全家人視為寶貝。媽媽常說,人以食為天,有吃的能保命的就是寶貝。
記得我十歲那年,有一個駐隊的“工作員”到我家吃飯,吃了媽媽從“甕”中腌泡的雪里蕻菜的時候,就驚奇地問媽媽,“為什么你這翁里腌泡的菜這樣好吃?”媽媽說,“我也是和別人一樣的腌菜,只是,這個甕有些特別,這是祖上傳下來的,誰也說不清原因。”那一天,我看到,那個年歲半百的“工作員”就起身去細細審視了那倆老壇子。我看他對這兩件東西愛不釋手,雙眼好像還在放光。他臨走時還對媽媽交代,“你今后就是再窮,也不要賣掉這倆東西,它們可能是無價之寶。”還說,“你們在它里面腌菜是大材小用了,弄不好,這倆東西的肚里曾經腌的菜是給皇上吃的啊!算我今天有口福,吃到了‘御壇’腌的‘御菜’。”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什么是“御壇”和“御菜”。不過,媽媽還是很信“工作員”說的話,認為這倆東西一定很寶貴。因為媽媽知道那個“工作員”是上頭下來的一個文物專家。
困難時期過去后,土地責任給了各家各戶,我們家有很多可以種植蔬菜的水澆地,每年媽媽種的菜吃不完,全拿去給了鄰里們吃,而媽媽每到霜降后,卻仍然忘不了清洗那倆個“寶貝”壇子,仍然是,把那些蘿卜櫻櫻、紅薯梗梗什么的地道菜腌制在里面,待冬天來了,地面上沒有那些青青的蔬菜的時候,就打電話給我們,要我們回家吃她的“御菜”。媽媽也是個開朗人,往往是有人吃著她腌的菜嘖嘖贊美時,她就會說,“那當然了,你吃的可是皇帝才能吃到的‘御菜’呵!”
為吃媽媽的“御菜”,我和兒女們就會經常回家,媽媽就高興得忙前忙后一整天。這種腌菜是一次不能拿太多的,基本是一次拿夠一周用就可以了,多了就會變味變質,所以為了吃媽媽的“御菜”我們就有很多機會跟媽媽團聚,就會讓媽媽在為兒孫們的忙綠中幸福著。
媽媽說,人就是有個賤,在伺候這大小一家子中才會感到有福氣。天倫之樂,也許就建立在媽媽的忙綠之中。
我們為了媽媽這個天倫之樂,也形成了一個規矩,必須是一周回老家吃一次媽媽的“御菜”。兒子女兒都喜歡吃奶奶的“御菜”。他們吃奶奶“御菜”的時候常常是拿歌兒給奶奶來換,外加纏著奶奶的脖子。有時候,小女兒還經常拱到奶奶的懷里讓奶奶一口口的喂。往往是這個時候媽媽是最高興的了。
吃飽了媽媽的“御菜”,臨走時,媽媽總會送我們到村頭,對我們交代,記著下周回來。當我們最后給媽媽招手時,往往會看到夕陽下孤獨而微笑著的媽媽,已像一張彎弓一樣地把目光射向我們。我們會心中難舍,因而就緊緊地抱著媽媽的那些“御菜”釋懷。
人世間什么才是寶貝?往往是在我們離開媽媽的那一瞬間,答案就來到心上,親情,媽媽的親情才是我們真正的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