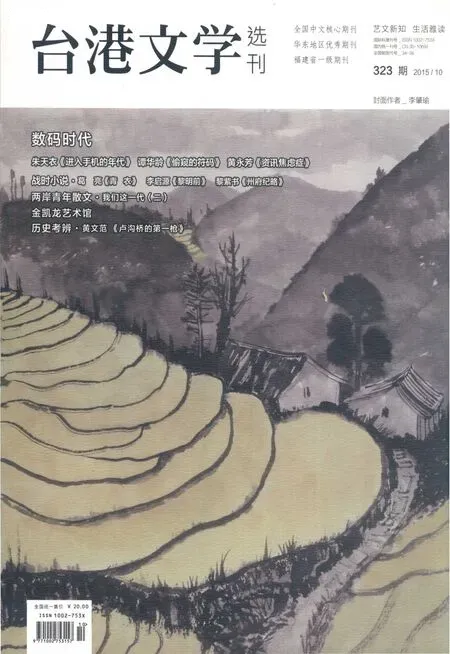州府紀略



黎紫書,本名林寶玲。著有短篇小說集《天國之門》、《山瘟》、《出走的樂園》,散文集《因時光無序》,微型小說集《微型黎紫書》。曾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小說推薦獎、散文首獎、世界華文小說首獎等。
喏,水月宮就在近打河下游。河灘上紅紅一間廟,梁上掛九九八十一對光明祈福燈。哎呀說起來整百年了,它一直在那里,年年雨季近打河水漲,沖走幾多雞雞鴨鴨,都趕它不走。唉,隔著河,像在眺望另一岸的天主教學校。
那學校也算古跡了,高墻厚磚,簡直城堡一樣。紅毛鬼留下來的,叫什么名字去了?對對對,圣米高。
李乾初
有個叫譚燕梅的,我記得。唱帝女花做皇帝女,唱功做手都好,以前舊街場京都戲院有義演,說是賑濟廣東水災,全場爆滿。戲院外面賣咸水花生都賣到發達。
真的,賣花生那個就是譚燕梅的契家佬,叫……雁生,姓羅。我們叫他生仔生仔,叫到熟,還一起看戲。他不多講話,只是傻乎乎地由頭看到尾,一有譚燕梅出場他就拍爛手掌。慈善社的人都這么講,說他和譚燕梅有路,每晚收了檔就在慈善社樓下等人,叫一部冷車兩個人坐,送到休羅街才分手。譚燕梅老公在樓上,一直咳,什么都沒說。
我當時還后生,十二三歲,老爸就是踩冷車的。載過他們好多次,回家對我老母講,那個譚燕梅一頂綠帽壓下來,肺癆鬼捱不了多久。對別的冷車佬就說賣花生的阿生仔有福,又說譚燕梅幾銷魂,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結果幾十年過去了,一個二個都死光,譚燕梅老公反而咳來咳去咳不死,聽說后來眼睛瞎了,也好啦,有眼屎干凈盲。前幾年跟兒子媳婦搬到新村里,不知現在死了沒。
其實譚燕梅也沒什么好出身,記得她阿爸幫一個大戶人家打工,識幾個字,就派去看管水月宮。喏,就在近打河邊,壩羅橋頭下面,紅紅那一間。本來是那戶人家的祠堂,叫壩羅觀音廟,不知什么時候開放,又改名水月宮。廟里的觀音菩薩靈得很,我老母常去上香,求
財,中了字九月十九就去還愿,順便在河里放生。很多烏龜在河灘上爭先恐后,說有多壯觀就有多壯觀,想起來真熱鬧。
我在廟里見過譚燕梅。那時她在萬福隆布莊做剪布,收工才到慈善社學戲。禮拜天布莊休息,她多數在水月宮幫忙。長頭發大開辮,瓜子臉單鳳眼,可惜就臉色看真了菜黃菜黃的,但也夠好看了。上臺做戲化了妝,臉上白的白紅的紅,那雙眼水玲瓏,連洗衣行太子爺都說會勾魂攝魄。洗衣行太子爺什么女人沒見過,他老婆廖秀卿是錫礦大王女兒,大美人一個,還包了幾個妖妖冶冶的阿二住在二奶巷。連他都被譚燕梅勾了魂攝了魄,你問譚燕梅有多美,我都沒法子形容。話又說回頭,洗衣行太子爺原來有個二奶,祖籍江夏,叫黃彩蓮的,跟譚燕梅姐妹一樣好。還是黃彩蓮先帶著她男人去捧譚燕梅的場,誰知捧出個大頭佛,她男人中降頭似的天天到慈善社等,跟那個賣花生的同人不同命;他在樓上一邊打牌一邊嗑瓜子,生仔孤伶伶地蹲在樓下。
后來不知道這兩個女人有沒有鬧翻,橫豎日本仔打來時黃彩蓮就不見了,不知是不是給抓去當慰安婦。第二年譚燕梅出門很久沒回來,丟下老公在這里,生仔也沒跟去,還天天替她拿飯給肺癆鬼吃,戒嚴時膽粗粗趕去,差點被日本鬼開槍打死。這樣過了幾年,譚燕梅突
然出現,帶著個野種,搬回來和肺癆鬼一起住。
在日本仔的手,三年八個月,餐慍餐食餐餐清,光復后我女人幫過譚燕梅帶孩子,做幾個月就被炒了。譚燕梅好挑剔,嫌我女人煲粥沒功夫,魚骨鯁到她兒子。又沒鯁死,巴巴閉閉,當天就叫我女人回家。這女人的丑事我知不少,不過人都死了,講出來好像很缺德,不
講了不講了。
后來譚燕梅沒唱戲,花生仔羅雁生跟住娶了個豆皮妹,生很多,好像是七個女兩個仔,追那兩個兒子追到豆皮妹變大肥婆。
張淼坤
起初是彩蓮扯衣袖拉我去的。她跟燕梅是好姐妹,聽她說十五六歲在水月宮遇見。女人跟女人很容易相處,一下子就蓮姐細妹的廝磨起來。譚燕梅是藝名,真名叫譚細妹,這也是彩蓮告訴我的。
記得那晚演的是《王寶釧拋球招親》,慈善社例牌籌款,救廣東水災。我約了牌友在閑真別墅等,打算戲演到一半就借尿遁。沒想到譚燕梅這么美,她演王寶釧,一出場我就看得眼定定,耳朵嗡嗡響,彩蓮說什么沒聽到,大鑼大鼓督督鏘也沒聽到,心想死了死了仙女
下凡。結果忘了閑真別墅的牌局,呆呆等到散場,陪彩蓮到后臺找人。譚燕梅下了妝一張臉出奇的素,眉清目秀,像什么呢像月亮。她是嫦娥托世,她是嫦娥嘛那個賣花生的就是伐桂的吳剛了。
那晚帶姐妹兩個去吃宵夜,萬里望客家佬云吞面。才知道她們以前常幫襯。燕梅吃很多,說自從彩蓮跟我以后就沒來吃過了。現在客家佬還在賣,為食街一個邋邋遢遢的小檔口,味道也相同,云吞大大粒,總是賣得比人家便宜。幾十年了,現在賣面的不知是客家佬第幾代。
我和彩蓮送她回家,坐我的汽車,她一個坐在后面。倒后鏡看到她很累的臉,打兩個哈欠,伏在彩蓮的座墊背上。到休羅街她的家,看到一個男人蹲在五腳基上。以為是誰,原來是賣花生的傻仔,塞給燕梅兩只叉燒包,打量我們一眼便訕訕走開。彩蓮咭咭笑,兩姐妹在那里手來腳往,拉來推去,笑好大聲。然后,然后騎樓的燈亮了,她們忽然收聲,昂起臉一起望著那盞燈。
以后幾個月我真的去追燕梅,有戲公演就去捧場,沒戲演就去慈善社等。其實我都不知自己等什么,還有一個花生仔,一起拍手,一起等,中邪一樣迷戀人家,剪布妹、半個戲子,憨到死。她假裝沒看見,每晚都跟那個花生仔走,寧愿吃他的叉燒包也不跟我去點心樓。我說在龍鳳訂了碗仔翅,她一個勁搖頭,叫我帶彩蓮去;她要回家,她家有老公。金戒指金項鏈玉墜子送去又退回來,托花生仔拿到閑真別墅,只交待說:受不起。
她有老公我知道,我雞嫖過了,寡婦玩過了,有老公的也偷過。打聽她的背景,嫁給那紙扎鋪窮鬼才半年,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有一晚花生仔沒來,我在慈善社賭魚蝦蟹,心緒不寧,輸好多。她排了戲下樓來,外面風大雨大,雷電交加,只好站在慈善社門口干等。我比以往追任何一個女人更有耐性,陪她躲在屋檐下,不說話。
現在想起來,當時是真沉默,因為確實有點心酸。她一直背對著我,雨下了整個鐘她就那樣背住我整個鐘,粒聲不出。等到雨勢小了,她拿了門外幾張舊報紙,想走,我忍不住喊她,細妹。燕梅怔一怔,回過頭。她說你回去吧,你再浪費時間,怎么對得住人家。
她說“人家”,人家是誰呢?我呆了一陣,腦里面亂七八糟。“人家”是哪一個,彩蓮?秀卿?金好?翠群?玉荷?她不知道我亂,拿報紙遮住頭,跑進雨里。喂,細妹。她頭也不回,碎花白衫褲在街燈下面發光。
追人家追到明目張膽,秀卿沒出聲,阿爸阿媽都看不過眼,吃飯時不斷數落我。阿媽一直說“那個打炮貨”,很難聽。我生氣起來擲了碗筷,去二奶巷,找彩蓮。想不到那個臭貨換了鎖頭,不讓我進去,在騎樓上扔幾盆花下來,想收買人命,謀殺親夫。彩蓮一直哭一直喊,她說你中意我姐妹就去找她睡,屌她。爛女人,兩只眼圈灰灰藍藍,鼻水掛在唇上,我好厭惡,簡直想嘔。搖搖頭,去巷尾翠群那里睡。丟那媽,臭貨,以為自己是大家閨秀,抑或是仙女下凡。呸。
后來就沒去等人了,連彩蓮也憎,成個死癲雞,見不見都罷了。我還有金好翠群玉荷,大把女人等著搬進二奶巷。二奶巷就在閑真別墅斜對面,隔一條街,一排有三、四間屋都是老頭子的。誰不知道洗衣行張家,我不怕沒女人,晚晚和不同的女人睡,睡三百六十五個都
行。譚燕梅要吊高來賣,扮清高,就讓她扮,活該她捱苦捱死一世。
沒多久,彩蓮就跟人走了。那年一九四一,蝗軍打來,我幾個月沒上去,也不給伙食,不知道她在外面勾佬,不知她老母死了,什么都不知。彩蓮弟弟來找我,問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才知道這女人跟人走路。二奶巷屋子里的東西給她賣清光,死婆娘夾帶私
逃;給我戴綠帽,給我做老襯。我說過不放過她。
黃其祥
大姐人很好。就算她勾佬累我被姐夫打,我還是覺得她很好。張淼坤不是好人,敗家仔,沒本心,他根本配不起我大姐。如果不是阿媽病到五顏六色,要住醫院,要開刀,要吃很多很多豬肝和人參,大姐不會跟那個男人,做二奶,給人講給人笑,幾凄涼。
我大姐個樣都幾好,雖然矮少少,鴛鴦眼,不過笑得甜,有小蠻腰,做女時很多男仔追。但是她心頭高,看中的都是讀書人,壞鬼書生。以前她中意一個讀英文書的,每日走路去圣米高等那男仔放學。圣米高,近打河邊那間鬼佬學堂,不收女生,女孩子去另一間女英華讀,我們叫姑娘堂。我大姐很想去姑娘堂讀書,她說讀英文書好,做上流人,同鬼佬去跳舞。阿媽聽到就說她貪慕虛榮,女仔人家,求求其其嫁得好,多生幾個仔女養兒防老。我大姐不出聲,我知道她怎樣想,阿爸死了幾年,阿媽割膠做泥水做到殘,如果她不嫁得好,下面六個弟妹,有的未戒奶,怎么養。
讀鬼書的大眼仔很快不見人,我大姐在學堂外面等了幾天,沒見著他,便猜到什么事。她回來時一路行一路哭,咒那個負心人。經過水月宮,看見一個梳孖辮的女孩爬上木梯掛紅燈籠,摔了一跤。我大姐過去扶她,幫她拍走衫褲上面的泥沙,拍下拍下,忍不住笑了。那
個女孩就是燕梅姐,大姐說她一直在忍痛,看到大姐笑,便很委屈地嘟起嘴,眼淚巴巴流下來,像開水喉。
緣分這東西真奇怪,兩個女孩就這樣好起來了,好到如膠如漆,誰也想不到以后會變成那樣。不是冤家不聚頭,真的,成了冤家。為男人,何苦?我想起她們心里就隱隱作疼。燕梅姐也是大好人,好得讓人不忍辜負。阿媽病得快要死,她天天幫忙煲藥,和大姐夾手夾腳,幫阿媽洗身。那時有了心病,可以對住整天不講話,可以同桌吃飯可以同床睡覺,就是嘴巴緊緊閉著,撬也撬不開。
其實兩個都心知肚明,千錯萬錯都是姓張的錯,花心蘿卜,大滾友。大姐搬過去二奶巷前一晚,請全部兄弟姐妹去龍鳳吃大餐,叫了滿滿一桌菜,我們的筷子都沒停過,唯獨她不吃,吃不下。吃飽了大家齊齊行路回家,行到屋子門口大姐就忍不住流眼水,拉住我,叫我
生性,以后看住弟妹,看住阿媽,一邊講一邊哭一邊把錢塞進我褲袋。我也哭了,叫她不好跟姓張的,做人家阿三阿四,作賤自己。大姐猛搖頭,她說阿媽已經躺在醫院里,醫院等著找數,她沒得揀。
我明白。之前阿媽入院,燕梅姐拿了個梳打餅盒來,很多年辛辛苦苦存的嫁妝錢,大姐幾乎要跪著才敢拿。這些人情,來世做牛做馬都還不清,更何況只是一個男人?大姐明白,可是她放得下張淼坤,卻放不下另一個;過得了這關,過不了另一關。是劫,是冤,是孽。
阿媽死那天,日本仔打到來。街上很靜又很亂,大家都不敢出門。阿媽睡了幾日幾夜,那天很早起來自己沖涼,還叫醒我說她快餓死,要吃蛋撻。我下到街,見到水靜河飛,行下行下覺得好驚,賣茶果的潮州婆沒開檔,成條街沒一間店鋪開門。我快快掉頭走,回到家里見阿媽仆在地上,死了。最小那個妹妹坐在旁邊玩煮飯仔,唱歌,阿媽整天唱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檳榔香摘子姜,子姜辣……那天日本仔打來,我一個人沖到街上,跑到舊街場二奶巷,找不到大姐。我一個人蹲在門口等,等到怕,等到餓,等到哭。晚上八點多才看見大姐,有個男人送她回來,很高大,一直站在暗處。我顧著哭,阿媽死了阿媽死了,都沒看清楚。
那幾天到處都是日本仔,沒有人敢開鋪,還是阿姐去棺材店拍門,叫門叫到聲都沙了,才買到一副棺材。老板不送貨,要我們幾兄弟姐妹,還有燕梅姐、那個男人,偷偷摸摸運回家。沒有人打齋,停棺停好久,十二天,尸臭都溢出來了,才有機會送到三寶洞火化。大姐由頭到尾沒有哭,反而燕梅姐一直眼濕濕,大姐忍不住開口問,你哭什么又不是你死老母。我聽見燕梅姐噗嗤笑了,她說誰叫你不睬我,我比死老母更傷心。
羅雁生
我同細妹由小玩到大,中意她也很正常。這種女孩子,打鑼找都未必找得到,我很小就認定她是我老婆。不過有時回頭想,她這么好,人又美,命就薄了。沒娶到她,或者是我好運。不過當時沒想到這些,只是一心一意愛她惜她,想要照顧她一生一世。后來才發覺她其實比我強,根本不需要我。她不在,我去照顧她老公,她老公趙錫賢,咳到肺穿窿,一日暈幾次,次次醒來都問我燕梅回來了嗎,他又知燕梅一定返。
彩蓮那個男人我見過,她阿媽出殯那天我去幫手,見他鬼鬼祟祟站在后面,躲躲閃閃的。后來知道他去參加華人抗日軍,原來是共產黨。英政府當他們是過街老鼠,抗日之后就趕他們上山。這種人一世都不得安定,可是女人當他們英雄,甘愿給他睡,還要等;等幾時共
產黨打贏仗,等他回來。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共產黨不會贏,英政府逼到他們沒路走,要上山,要吃樹皮,吃到皮包骨,人不似人鬼不似鬼,不死已經算好彩,怎么會贏?
細妹就是這樣對彩蓮講的,但是她聽不下去,終于跟那男人一走了之。那一晚我去慈善社接細妹,見她們兩個站在街燈下面談,兩個都臉青青,好似很大件事。細妹拖住彩蓮,叫她諗清楚,彩蓮點點頭,笑得很凄涼。我記得她講,人一世物一世,有時候要做一些自己中意的事。
講完她就走,見到我都沒打招呼。那種眼神,好像決定了要去自殺。細妹站在那里很久,面青口唇白,好似小時候不見了阿爸給她買塔香的錢,站在紙扎鋪前面,不講話,渾身抖。后來還是老板好心,送塔香給她,細妹一直都很感激那個老板,后來上了契,叫他契爺。她老公就是那老板的兒子,算起來是她契哥。到現在我還是這么想,細妹嫁給他,是報恩。
我只是猜想啦,一直不懂細妹的心思,她在壩羅古廟義校讀過書,成績很好,教書先生很疼她。人讀過書想法就變得復雜。復雜,又很細密。那年,我們去河邊抓魚,她偷偷告訴我,昨天有一個陌生人闖進水月宮,渾身血。我問她后來怎樣了,她只是搖頭,眼神閃閃爍爍,我猜她一定把人家給藏住了,可是我不明白為什么,為什么要冒險,拿整家人的命來冒險,政府會來捉啊。但我那時沒問,還傻傻地陪她到藥材鋪買止血散,買田七。回到家里才知道怕,怕被連累,那時政府很不講理,到處拉人,屈打成招,不認打到你認。
有件事我心里猜疑很多年,那人在水月宮住了十幾天,期間可能發生了我不知道的事。那人走后細妹一直心神恍惚,有幾個月失魂落魄。我問她,她口很密,但臉紅紅,頭低低,眼睛發亮,看得我心亂亂跳。一定發生過什么了,我有點生氣又有點傷心,我們一起長大,
一起在近打河沖過涼;我拖過她的手,把她當老婆,現在她瞞我,她有自己的秘密。那個男人到底是誰,那年頭會搞得這么狼狽這么落魄的,會是好人嗎。我敢打賭,他不是私會黨就是共產黨了,細妹蠢到死。
還好以后都沒遇上那人了。細妹契爺死了,說是供應糧食給共產黨,兩夫婦給英國人折磨死。趙錫賢是獨子,自小就一身病,父母死了命就賤,好在得細妹照顧。不過他命硬,一直死不去。日本仔當家時,細妹突然失蹤很久,有一天一班日本人沖進來,把趙錫賢拖到街上處決。日本人好殘忍,用塑膠管塞到他胃里灌水,灌到肚脹脹,又踩幾腳,水從眼耳口鼻倒流出來。我擠在人堆里,好怕,又不敢沖出去救人,心想姓趙的一定瓜柴。沒想到他爬回屋子里躺了整個月,看著要斷氣了又沒斷氣,醒來就問:燕梅呢,燕梅回來了嗎。以后還是吊住一口氣、一條命,一直在等細妹。光復以后,有一晚我收檔了拿一鍋粥去他那里,一開門就看見細妹,在喂他吃東西,兩個人都不作聲,好安靜,好像……兩夫妻。我見到細妹,居然沒有一點高興,反而很傷心很傷心,她見到我,笑得很友善,多年老朋友重遇的那種笑。我終于認命,細妹永遠不會變回以前的小女孩,她是人家的人了。
她帶回來一個男嬰,以后叫我契爺。我和肥婆結婚之后,生了很多個,日頭炒栗子,夜晚燒雞翼,捱到開茶室,日忙夜忙,都不去想了。
蔡碧玉
我跟亞生講,你先墊高枕頭想清楚,不要結了婚生了孩子才來后悔。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來我家拿我的生辰八字,要去挑日子。我看他眼睛布滿紅絲,應該沒睡好,就當他想清楚了。我知道他喜歡人家譚燕梅,可是我也早占到,不是門戶的事,也不是因為肺癆鬼,反正亞生高攀不上。你信不信人有分等級,那氣質,那風度,沒有就沒有,裝不出來,著起龍袍不似太子,一眼就可以看穿。我看人很準,有一套,雖然說不出理論來,可是從來沒看錯。
很早就看出亞生是個好男人,我不怕當面說我蔡碧玉要嫁嘛就嫁羅雁生這樣的人。別以為我丑樣就沒有要求,嫁老公是一輩子的事,不怕入錯行最怕嫁錯郎,而且我除了臉上豆皮多一點,其他的都不輸別的女人。割過膠洗過琉瑯挑過洋灰,還有本事七手八腳帶大九個兒
女,洗衣煮飯上床生孩子,我樣樣都周到,亞生要挑剔也無從著手。
情情愛愛的事我當然懂,又不是鐵人。看譚燕梅唱帝女花,唱祝英臺,也會心酸。后來看吳楚帆梅綺、看謝賢蕭芳芳、看劉松仁汪明荃、看周潤發趙雅芝,一樣眼紅紅流鼻水。不過明明知道那都是戲,現實里我才不去想這種傷感的事,管他心里掛住誰,他不嫖不賭,沒
做對不起我的事,我就肯陪他捱,捱一世都不怕。事實證明我沒看走眼,走寶的是譚燕梅。
亞生還是很關照她,知道她喜歡吃栗子,常常一大包拿過去。過年過節時,臘味蕉柑花生柚子月餅紅包,一定少不了。我生五妹頭時,丟那媽那個死龜公醫生亂亂來,害我產后血崩,一只腳踩進鬼門關。好怕人,以為自己必死無疑,昏迷中神智還清醒,想著身后事要怎么辦,矇矇朧朧竟然想到托燕梅照顧我的孩子。后來輸了十多包血,才逃過死劫,丟了半條命。醫院不賣血漿,要我們找人來還血,燕梅夠義氣,那時在建成制衣廠車衫,特地拿半天假,到醫院捐了兩大包血。看著她的臉轉青,頭暈暈。坐了月子我就拿當歸去找她,順路買來一大塊豬肝,還人情去。
去到她家里,燕梅正在沏功夫茶。都說了這是氣質的事,樣子干干凈凈,手腳利落優雅,像很好出身的千金小姐。我把當歸和豬肝塞到她懷里,拿去拿去,補補血氣,不然你要我血債血償嗎。燕梅沏了茶去熨衣,是蘇蝦上學的白襯衫。我靜靜喝茶,看她熨衣,怎么說呢兩個世界的人會有什么話題,連閑話家常也不知從何說起。衣服熨好了,燕梅猛給我灌茶,左一聲玉姐,右一聲玉姐。我看她瘦了好多,眼神干干渴渴的,一點沒有上臺時的神采,忍不住嘆了口氣。你的相那么好,命水怎么這樣差。燕梅好像不能會意,好一陣子才定過神,嫣然笑笑。
玉姐,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
情愛的事,我懂。燕梅她心里有人,亞生心里也有,但命里無時不強求。我以后待燕梅也如姐妹,做她孩子的契媽,我當作多一個兒子,他們家困難時我叫亞生拿錢去,幫得多少就多少。不是欠她血,是欠她人情。那天我送了當歸和豬肝,回來時開電視看興都片,居然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戲看出眼淚來,以后看戲分外容易感觸,我的兒女見怪不怪,早早預備紙巾,給我擤鼻涕。
過了四十歲,燕梅就發胖了。她胖也好看,福相,只是再演花旦就說不過去,騙不了人。亞生那天特別休息一日,帶整家人去捧燕梅的場,孩子哪坐得住,滿場飛,我追他們就夠累了,哪來時間好好看戲。那晚亞生特別靜,看戲看得很專注,那神情,簡直有點貪婪。看完戲一家人去吃夜粥,淡菜花生粥,煮得好濃,粘糊糊的,放進嘴里就開不了口說不出話,要咽下去也難。像眼淚,不是嗎?
亞生很勤力,過年只休息年卅晚年初一,一年到晚都在賺錢養家。到現在我還是常常對兒孫說,他是個好男人。好男人嘛,勤力啦,老實啦,長情啦,我知道。他退休之前,除了生病便沒偷懶過,只有兩次,一次是燕梅唱最后一臺戲,一次是燕梅出殯,他兩天坐在喪家那里,不吃飯,拼命剝花生,燒冥紙。
唉,人老了,遲早總會死。
趙錫賢
燕梅回來了嗎?
現在人老了,眼睛看不到,一天到晚黑漆漆。如果她回來,一定會盡量小聲,不想驚動我。她走的時候也這樣,把錢放在我的枕頭邊。記得那晚睜不開眼,像夢,她摸一摸我的額頭。燕梅的聲音柔柔膩膩,她陰聲細氣,好像在我耳邊說:賢哥,我走了,你等我回來。我含糊應了,好像往常她去慈善社練戲,沒有什么不妥。可是她這一去便去了四年。四年,是亞生替我數的日子。
娶燕梅那天,是我這一世人最快樂的日子。阿爸阿媽被英國人拉走,送回來兩具僵冷的尸體,店鋪又給兩個叔伯霸占了,只給我留休羅街一間店屋。我知道自己沒用,想死掉算了,一了百了。可是燕梅跟我說:賢哥,契爺叫我看住你,但你總要給我一個名份。婚禮都是她張羅的,在金陵擺兩圍;我的病突然好起來,跟彩蓮碰了兩杯。亞生沒來。晚上燕梅睡著了,我不敢碰她,又睡不著,開窗透透涼,看見亞生蹲在路旁,突然四目交投,他嚇得彈起來,快快走。
我知道外面傳他跟燕梅不干不凈,但我常常搞不清楚,是燕梅對不住我抑或我對不住燕梅。人家好人好姐,跟我這個病鬼,賠一世。我病到半生不死,對她有心無力,對自己也有心無力,不想過問她的事。一直到她半夜出走,第二天一大早亞生來,說燕梅昨晚找他,托他看住我,我們兩個干瞪眼,好像知道了,原來大家都不是真命天子。
日本人上門來,我才知道燕梅為什么走得這樣神秘,這樣急。她是抗日軍。日本人要我供出她的下落,我不知道,拼命搖頭。被拖到街上灌腸,像什么表演,很多人圍過來。平日的街坊鄰里,賣海南雞飯的福建佬、賣福建蝦面的廣西婆、賣福州姜酒雞的客家妹,還有亞生。我見他瑟縮在人群后面,嚇得好驚,臉色慘淡。日頭曬到路面熱辣辣,灼得我心好疼。我不是疼自己,我是疼燕梅,她什么都不說,自己一個人撐;一個女人家,再有把炮都只是一個女人,好陰公。
幸好他們沒拉到燕梅,如果被拖走的是她,多慘。日本仔沒人性,打起仗來個個都沒人性。聽說很多女共產黨員被抓到,又奸又打又殺,又用煙仔灼奶頭,又用蠟燭燒下面。英國手是這樣,日本手又是這樣,不同的只是施刑的手法。我在床上躺了很久很久,由朝到晚都在做噩夢,夢見燕梅被輪奸,她下面流很多血,流了一地,流到我整個夢都紅了,還有甜甜的血腥味。醒來看見亞生,我問他:燕梅返來了嗎?他不回答,屋里面點火水燈,很暗,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其實大家都很掛念燕梅,好想聽她唱粵曲,看她扮皇帝女,飲毒酒自盡。可惜她的帝女演得好,那個駙馬就差很遠,傻更更,聲底也不好。
卒之燕梅回來了。有一晚我起身飲水,聽見樓下有嬰孩哭,哭得好凄厲,陰歷七月聽到,心寒。還以為是回魂,難道燕梅終于出事?這邊猜疑,那邊就聽到哭聲愈來愈近,又有上樓的腳步聲。我不怕,燕梅人嫁給我了,鬼也是我趙家的鬼,不會害我。我拿一杯水,愣愣地看著木門“咿呀”一聲推開,想到那出余麗珍的《無頭東宮三太子》,竟然流下淚來。燕梅很瘦,眼睛大大的,暗夜里像是閃著鬼火,懷里抱著個嬰兒。賢哥。她叫我,聲音冷冰冰,眼睛火紅火綠,我一聽到這聲音,突然天旋地轉,站不穩,昏過去。
我知道我沒用,一世累人累物。我跟燕梅說,她遇到好人家就別再背我這大包袱了。那孩子,我們叫他蘇蝦,燕梅說是撿回來養的,我不追問,但心里準備好了,等著有一天燕梅和孩子的父親重遇,我就退下。其實從開始我就是多余的,到最后仍然多余,一直瞪眼睛看大家在我身邊來來去去。燕梅七十一歲死,心臟病發,來不及道別,曬衫時死在屋后。我等到傍晚沒有人煮飯,以為她又出走,便自己煮美極面,眼淚掉到湯里。蘇蝦四十八歲,做仵作,晚上回來才發現他母親躺在曬衫架下面,好多紅螞蟻爬上尸體,她整個人硬崩崩,臉上凝固著一種痛的表情。
有蘇蝦擔花買水,我守在棺材旁邊,燒金銀衣紙。黃泉路上順風順水喔。說出來你不信,燕梅死了我覺得好輕松,棺材旁邊睡得很甜。才知道有這么一塊心頭大石,不必擔心她又離開,不必想她是不是還掛念那人,蘇蝦的父親。一九八九年馬共走出森林,燕梅去過馬泰邊境一趟,拉著兒子去,托鄰居給我送飯。我心想她這次可能不回來了,但話還是問不出口。她一踏出門口我就發自己脾氣,摔破兩只飯碗,一座老鐘。現在老鐘還在,時間就停在那里,九點五個字,燕梅煮了早飯才出門。三年后,燕梅死,手上抓住一件蘇蝦的底褲,死得咬牙切齒。
以后還是常常夢見燕梅。因為盲了眼,夢里都沒有畫面,只有燕梅年輕的聲音,很輕很柔,似咬耳朵,她賢哥,我走了,你等我回來。
趙蘇蝦
阿媽同我去黑木山,搭火車坐二等艙。我都四十幾歲了,阿媽就快七十,不知她湊什么熱鬧,去看人家投降。阿媽叫我別問,看得出她好激動,在人堆里差點失散,找到時連忙抓住她,發覺她手抖,眼淚巴巴流,好像開水喉。七十歲人還像小女孩,慌失失,哭。
她有跟我講過,要找一個老朋友,不知是不是你說的金蘭姐妹。應該找不著吧,出來的人很多,大家都在看那個總書記。只有我阿媽盯住每個走出來的人,沒多少個,都老了。可能人老了會走樣,很難認出來,或者那人根本就死在山里了?到底在那種地方,生死有命。阿媽很失望,眼淚吊在眼角,嘴都扁了。我不知他們那代怎么想,共產黨都已經煙消云散,有人還不死心。什么深仇大恨,大選投票選反對黨就好了,哭有屁用。阿媽說我不懂事,天呀我四十好幾,懂也好不懂也好,不是都過去了嗎。
人都死了好久,尸骨都要化了。前兩年去拾骨,什么都沒了,就一副殘骸。不明白為什么要把舊事挖出來。我阿媽唱戲唱出名堂?譚燕梅,慈善名伶,什么帝女花祝英臺樊梨花,幾十歲人,皮都松了皺了,上了妝還很美。小時候跟契爺去看,衣服首飾金燦燦,看得眼都花了。阿媽是慈善社最美的一個,身段好,連香港的任白來參觀,都對她多瞧兩眼。那時阿媽帶著我,拍大合照時抱我坐在膝上,任劍輝拉她坐在身旁。照片上大家都眉開眼笑,我阿媽穿白旗袍,最靚。契爺說,任劍輝白雪仙都比不上她。
唱到四十多就不唱了,改做指導。沒有她劇社就沉下來,社慶時去看,舞臺一年比一年破舊,很多服裝面首都褪了色走了樣。慈善社三樓成了練功場,練功夫,李師傅教長拳短打,又耍大刀,我跑去學。那時不時興唱戲了,私會黨當道,沒功夫傍身不行。我們幾十人在臺下練,阿媽和幾個老家伙在臺上唱,那時覺得粵曲很吵,二胡聲依依啞啞,像喪家哭魂,很煩。
我是海山的,那年代華人沒有幫派很難過日子,一口安樂茶飯都吃不到。我去擺檔賣水果,今天給政府抓明天給私會黨趕,黑白兩道都要孝敬,剩下的不夠養自己。好在政府醫院拿藥很便宜,我常常替阿爸拿,有時候打架受傷,出院時順便連阿爸的藥一齊拿,很方便。小時候整天拽阿媽裙子出街,長大了不做裙腳仔,常常去榴梿街水嬌那里過夜,阿媽都不理。她說仔大仔世界,不如留一口氣把戲唱好。有一晚陳惠珍來怡保登臺,我去看場,看陳惠珍用下面開荷蘭水蓋,“噗”一聲,好厲害。散場后發現阿媽在門外,看陳惠珍的海報,她說陳惠珍長得很像以前一個好姐妹,有點風情,但桃花眼,命薄。
那一晚,我陪她走路回家。她想什么想很久,到了門口才轉過臉來說,蘇蝦你不是我們的親生兒子,你懂不懂。我有點傻,那年頭大把人養兒子送終,我女人水嬌都是人家的養女,不奇怪,也不覺得心傷,但竟然忘了問誰是我的親阿媽。那晚睡不著,聽到阿爸咳,感染我也覺得喉嚨癢癢的,一整晚都在吐痰。半夜阿媽掀開門簾,捧了一碗雞湯進來,田七燉老母雞,活血散瘀。進了海山以后,幾乎每次回家,阿媽都燉這種湯。我一口氣喝光,苦苦甘甘甜甜酸酸,說不清楚什么味道,真的生娘不及養娘大。
四十幾歲,同阿媽去泰國看共產黨投降,她幾天幾夜闔不著眼,回來時一上火車就睡覺,睡很久很久,醒來對我說,蘇蝦你的親生阿爸是共產黨,你阿媽跟他入山,你出生那天她就死了。
我不覺得怎樣。阿媽死我才真的傷心,那個共產黨阿爸阿媽,就和隱入深山的共產黨一樣,還沒有在我的生命里出現過,就煙消云散了,我甚至不想知道他們的名字。阿媽看著我長大!做工養我,燉湯給我喝,死前幫我洗衫洗底褲,她死,我才哭。
廖秀卿
我去過二奶巷,不知為什么。去水月宮拜觀音,回家時冷車經過二奶巷,突然好想進去看一看。好窄一條路,兩排雙層屋面對面,樓上打橫放十幾枝衣裳竹,曬很多女人衫褲。張淼坤個衰人日日在女人褲襠下面過,衰十世,終于敗完整副身家。洗衣行沒了,他要靠我娘
家,求我爸打本給他做生意,開了這家鴻福點心樓。廚房師傅從香港重金禮聘,蝦餃燒賣手工好,逢八月出月餅,賣斷市,打響名堂。一做幾十年,我做事頭婆,在柜面收銀,扣住錢。張淼坤爛賭爛滾,我不理,每個月給兩百元,后來加到四百,五百,六百,還要養家婆,養兒女,我當給薪水養一個雜工。他自己知自己事,嘻皮笑臉回來拿錢,拿了就滾,我不讓他碰,周身賤格,不知有沒有惹骯臟病。有了錢我就不怕,當自己守生寡,講話可以大大聲,連家婆都不敢吭一聲。
我去過二奶巷,見過彩蓮。那時她剛搬進去,最得寵。我聽說過了,張淼坤帶她去閑真別墅,打牌時讓她坐大腿。窮人家出身的女人都這么賤,有幾分姿色就變狐貍精。還有一個唱戲的譚燕梅,搞到一個兩個神魂顛倒。張淼坤在外面的風流韻事,唱通街,我怎會不知道。廣益金鉆行坐柜的是我舅父,張淼坤買好多金鏈耳環戒指給譚燕梅,著人送去慈善社。我沒面子,又不敢哭訴,當初是自己選的,貪他好樣,口甜舌滑,別說小鳥,老鷹也給他騙下來。
是啊我去過二奶巷,彩蓮在露臺洗頭發,一邊唱歌。她見我走過,不知我是誰,繼續唱歌。有個梳孖辮的女孩替她搓頭發,卷起衣袖,一直笑瞇瞇,有時陪著哼兩句,聲音很好聽。我走上人家的騎樓,偷偷看,兩個人好像一對孖公仔,彩蓮頭發濕漉漉,枕在人家的臂上,又哭又笑。這種人出身不好,很輕浮,浪蕩,偏偏男人最喜歡。后來才知道那孖辮女是譚燕梅,那時張淼坤還沒看上她,兩姐妹那份親熱勁,叫人看了生氣。沒想到以后會喜歡看譚燕梅做戲,她演皇帝女夠苦情,和駙馬殉情那段《香夭》,我看多少次哭多少次。當家以后有錢,自己帶兒女去看,結果成了譚燕梅的擁躉,給她送花牌。地球是圓的,山水有相逢,當初以為會憎她一輩子,一眨眼時勢變了,看她就順眼。男人算什么,尤其是張淼坤這衰人,為他流一滴眼淚都嫌浪費。我捐錢給慈善社,說明看在譚燕梅份上,她不唱我就不捐,保她唱到四十多歲,超過一百場,最后一出戲是《火網飛龍之夢會銀屏后》,張淼坤都有去,我坐頭位,散場看見他在后座,咸水花生殼扔了滿地。忽然發覺大家都老了,他有點尷尬,跟我說譚燕梅不唱了。是啊,多可惜。我應他,像兩個戲迷那樣聊天,出來時看見他也送來一個花牌,小小的,很簡陋,擺在我的花牌旁邊。
有人說譚燕梅是共產黨,抗日時她參加過抗日軍。那是真的,我有個堂哥暗中資助游擊隊,從抗日到抗英,到馬來西亞獨立就收手。他見過譚燕梅,跟幾個同志到礦場拿錢,譚燕梅唱戲的啊,聽聲音就認出來了。至于彩蓮嘛,誰知道呢。她們感情那么好,一起加入共產黨,也不稀奇。我沒有再見過她,自從二奶巷那一次,看到她在洗頭,把頭枕在譚燕梅肩上,發梢的水像眼淚一樣,浸濕譚燕梅的衣裳。
后來還有經過二奶巷。幾間老房子都被張淼坤押了,現在是古跡危樓,照樣住人,照樣幾枝衣裳竹橫架過去,掛滿女人衫褲。誰要是在下面走過,沾幾滴水,肯定衰十世。
廖兆國
談譚燕梅也好,黃彩蓮也好,不得不提劉軍。沒有人知道他,我猜劉軍也只是化名,許多化名中的一個。那時馬共出來行走的,誰沒有幾個化名。第一次跟譚燕梅接觸,她說她叫李素萍。當然我沒有揭穿,大家都在一個斗爭漩渦里,心照不宣。劉軍帶著她來收賬,我說
劉軍你怎么不把新婚妻子帶來,給我介紹。劉軍還是很端正的,眼眉都沒抖一抖,倒是譚燕梅有點尷尬,一直催促,行又不是站又不是,便出去礦場透口氣。
我跟劉軍很熟了,多少打聽到一點。他老護著譚燕梅,不承認,只說譚燕梅救過他一命,便沒有下文。聽說是很久以前的事,過后兩人都沒聯絡,后來才殺出一個黃彩蓮,讓他們重逢。姓黃這女人很有骨氣,敢愛敢恨,自己打包找到山里去,找劉軍。劉軍還有什么話說,一個女人千山萬水跟著來,不要也不行吧,會天譴。兩個人在山里草草結婚,不久譚燕梅才到。好像很多事都是命定的,怨不得人。其實譚燕梅老早就加進馬共了,但她在外面盯哨,不打仗,武裝斗爭時才正式加入軍隊,打游擊。可是一切都太遲了,黃彩蓮搗亂整個局面,秩序搞亂了,譚燕梅依然是后來者。
其實一個男人有兩個老婆也不算多,何必要劉軍為難。偏偏這兩個女的看似親如姐妹,以為一生一世都會好下去,誰知一個男人就難倒她們,才發覺彼此的感情沒有好到那種地步,好到可以共事一夫。這是我女人聽來的,譚燕梅和黃彩蓮在軍里都不說話,不瞅不睬,見到面像不認識。
劉軍很難做,看得出來他有他的苦惱。黃彩蓮不是不好,但草包一個,連什么是社會主義也不懂,只知道共產黨是反對黨,只知道人到了山里就回不了頭。她豁出去了,一心一意為劉軍,替他挨過日本人一粒子彈,算是死得轟轟烈烈。我記得那時兩個女人都挺著大肚子,是的,譚燕梅有懷過誰的孩子,躲躲藏藏遮遮掩掩的,很少露面,又穿松身衣服,幾乎看不出來。還是我女人眼尖,說她發尾焦黃腳踝青筋浮凸,像個孕婦。傳到黃彩蓮那里就不得了,半夜鉆入人家的營帳,扭打起來。兩個大肚婆一邊哭一邊罵一邊打,扯頭發撕衣服,比做戲更精彩。后來兩個被強行分開,領導把譚燕梅調得遠遠的,遠得見不著劉軍,也見不著黃彩蓮。她是后來者,她勾引人家老公,不管怎樣總是說不過去。
然后日本人就闖進來了,圍剿那個獨立隊。聽說那幾天一直下雨,山里濕氣重,劉軍風濕發作,身上幾個舊傷口都痛,敵軍突擊時他根本逃不遠,又拖著一個大肚婆,兩個躲在山壁的凹隙內,不知怎么被日本兵發現,黃彩蓮替他擋一槍。真實情況我不清楚,后來黃彩蓮生下孩子就挺不住了,反而譚燕梅在另一頭受了驚嚇,動胎氣,保住大人保不住胎兒,結果她抱著黃彩蓮的兒子看好姐妹下葬,哭得很慘,比死老母更傷心。沒多久她不辭而別,抱走那孩子,不知算不算是向劉軍報復,抑或是哀莫大于心死。
讓我想想,那時美國炸了廣島和長崎,日本仔都走了。
劉遠聞
我從監里放出來,外面的世界已經變樣。誰還記得馬共呢,還有誰在乎歷史。大家都像你一樣,寧愿去懷念譚燕梅,懷念一個戲子的風采,懷念舊街場的風情。好像也有人懷念陳惠珍,她跳脫衣舞,當年是賤貨、是淫娃。現在大家對住她的舊海報,閉起眼睛想象她搖晃
晃的大奶頭,想象那神奇的開荷蘭水蓋雜技,想念舊時代糜爛繁華的那一面。那些才是時代的背景,歷史只是拖在時代背后的影子。你要知道的譚燕梅,究竟是暗影里面還是外面的那一個?
譚燕梅比陳惠珍好,她唱戲是認認真真的,是藝人。我偷偷看過她唱戲,那一年那一天,我沒有告別,拆了繃帶,摸黑離開水月宮。走的時候心里很牽掛,猶豫了很久,終于繞道去慈善社。那天公演,很多人,燈火亮燦燦。我擠在里頭,看見燕梅,才十幾歲的女孩,演丫頭,已經很搶戲。我站了一陣,看到她退場,才悄悄走。走時買一包咸水花生,路上吃。
原以為很多事情就這樣可以了結。哪一天英國人吧,日本人吧,馬來人吧,一槍開過來,什么都完了,哪敢承諾什么。我甚至不知道燕梅什么時候成了同志。那天彩蓮母親出殯,我去,遇上燕梅。之前完全沒有想過重逢這回事,但遇見了眼光再也躲不開,她長大了;仿佛在那臉上頸上,還有我以前留下的吻痕。說真的我感到心虛,不是因為拖著彩蓮的手,而是因為當天不告而別。她那種倔強又黯然的眼神,讓我覺得自己好像有什么虧欠她,拖了很久很久還沒做。
然后在山里,我忍不住要了她。拖她進矮青芭,現在想起來似乎很粗暴,在她手腕留幾條黑青的瘀痕。當時卻以為在履行那拖延很久的責任。她不喊不叫,但咬著唇嗚咽地哭,完事后才看見血,我整個傻住了,陽具上有血,處女的血。那種心情不懂得怎么形容,有喜有悲,有驚嚇有悔恨,人家給我少女的身體。是留給我的嗎?隔了幾年,她都嫁人了,還保住很久以前,替我包扎傷口時清清白白的身體。但,如果不是留給我的,豈不是白白糟塌了人家。我愣愣的,睜著眼看她穿衣服,看她扯開了粘在小腿上一只吸飽血的水蛭?看她走。
其實她一直克制住自己,總是躲我,甚至躲開人群。她使我苦惱,患得患失,晚上抱著彩蓮,昏矇中想象是她,便狠了,特別興奮。躲我嗎躲我嗎偏不讓你躲。有一回帶她去廖兆國那里,辦完事坐巴士回,中途上來兩個錫克兵,舉著槍一個一個檢查,說要拿共產黨。燕梅嚇得臉青唇白,兩手猛抖,好像可以聽到她的心撲通撲通亂跳。我攬住她,叫她老婆,你忍著點就快到醫院了,到了醫院馬上可以開刀。那兩個錫克兵倒好心,只看我們一眼,下車時還叫那司機趕快開車,人家老婆肚子疼。路上燕梅不斷冒冷汗,好像死里逃生,剛下車就蹲下來嘔,把早上吃什么的都嘔出來。我輕輕掃她背脊,覺得口腔很干,吐出來的口水苦澀穢臭,好似黃膽水。
兩個女人都有了,一個歡天喜地,一個像快被槍斃,肚子里都有我的骨肉。那段日子愁云慘霧,沒辦法高興起來。隊友們都在背地里謠傳,風聲傳到彩蓮那里。我早知道瞞不了多久,女人的肚子會像氣球那樣隆起來,怎樣瞞。彩蓮去打人家,一聲一聲賤種、臭貨。我趕去扯開她們,燕梅一條手臂被擰得紫紅烏青,臉上張開一個巴掌印,火辣辣,竟然沒哭,只是吃力地干枯地抽泣,哮喘一樣。彩蓮連我也打,臉上被她刮出幾條血痕來,留到現在。你說我該怎么辦,隊長搖搖頭,說由他來收拾爛攤子,便要燕梅住到溪邊的一間爛木屋。浮腳樓,屋頂的亞答葉擋不住風雨,雨天里直漏水,滴滴答答。大家在背后指指點點,我狠起心腸,索性不理;晚上睡到別的誰的營里,被子蓋過頭,任自己,也任她們自生自滅。
那年頭誰的命不像林里的野蕈一樣,賤,在枯木上也能茂盛成長。因為喝酒過量,到雨季時風濕發作,竟然痛得快要站不起來。說起來像天意,日軍就在這時圍堵我們的基地,死傷好多人。彩蓮跑來扶我,拖拖拉拉,我認出來是要到溪邊的路,可是走不遠,不如躲起來,在一個獸窟里,洞口有野芋掩護。外面槍林彈雨,日軍還擲手榴彈,我們聽到女同志的慘叫聲,突然記起燕梅。我說燕梅一個人好可憐,要嗎我們死在一塊。便跑出去,聽到彩蓮在后面哭叫,心便軟了。不知怎么有個日本兵打叢林里殺出來,開槍。到今天我還搞不清楚那一槍是怎樣開的,那角度,明明是要射我,但倒下來的卻是彩蓮,她背上中槍,仍然跌跌撞撞向我撲來,眼睛睜得大大,好像不相信身上的痛。
我跟她說過卷進政治就剩爛命一條,隨時會死,她不聽,還是頑固地跟來,其實連政治是什么也弄不明白。我來不及掏槍,被對方射中肩膀,昏了過去。昏矇中聽到槍聲交接,四五聲槍響,有女人呼叫、哭喊,有雨聲,有蚯蚓在泥土里交頭接耳。不知睡了多久,醒來看見烏鴉站在樹梢,邪惡地注視我。烏鴉不祥,你也知道,馬上感知彩蓮已死,果然尸首都涼了,燕梅抱著一個嬰孩陪那尸體。嬰孩呱呱爛哭,像烏鴉的聲音。告訴你,我不知道孩子是誰生的,按燕梅的說法,是彩蓮臨死前產下活的胎兒,而她卻在陣痛中趕來射殺那日本兵,然后躺在彩蓮身邊,誕下一個死嬰。我不曉得該不該相信,太巧合,又很神奇,沒有親眼看見,大概到死那天還是不敢盡信。
她是在一個清晨離開的,有雨。不知她抱那嬰孩往哪里去,只留下一句話,說要代彩蓮把孩子養大。也好,不能讓孩子在山里長大,難道以后要娶山番,入贅給原住民?光復后我去過怡保幾次,走過休羅街,經過水月宮,都過門不入。馬來亞獨立那天出來逛,莫名奇妙被盯上,抓去坐監洗腦,關了二十年。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二十年。放監出來燕梅一家已經搬走,晚上去二奶巷走一趟,那里不住二奶了,小巷子成了夜市場,我蹲在以前彩蓮家的屋檐下,連吃兩大碗牛腩粉,加兩條薄餅,芽菜雞,一杯羅漢果龍眼涼茶。肚子撐不下,便漫無目的,走出人來人往的二奶巷。巷口有一檔蜜糖燒雞翼,我認得賣雞翼的男人以前在京都戲院賣花生,是燕梅的朋友。再見時又肥又禿頭,顧著賣雞翼,認不得我。
那時沒有想起應該到慈善社走一走,以前在那里看過燕梅唱戲、印象很深,她演丫頭,只唱幾句,也可以搶花旦的戲。當晚乘火車來到這馬泰邊境落地生根,娶泰國妹,和老戰友一起搞馬共村,帶游客參觀我們以前的基地。報紙上母雞大的標題寫著“馬共巢穴大開放”,像秘聞曝光。馬共繳械走出森林那一天,好多人湊興去緬懷歷史,我們村里人山人海,一天走二十多轉,根本沒空,也不想去看人家投誠。
世界變了,誰還在乎。初識燕梅時,我騙她我叫劉平,對彩蓮我說我叫劉亞鳴,后來她們都沒改口,平哥是我,亞鳴又是我。要到監獄里面,錫克兵問我叫什么名字,我才省起自己的原名叫劉遠聞,報生紙上這樣寫的,以后報死紙也一樣,我竟然把它遺失這么久。但不
要緊,誰在乎,連我自己都不在意。
李銀桃
年初二開年時,這廟里人頭涌涌,龍香燒七日七夜,還有塔香,里里外外像傘那樣罩下來,那濃煙熏得人人流著淚拜觀音。水月宮有百多年歷史了,廟里的觀音像當年從中國運來,那時近打河床深,幾艘大船都可以開進來。你見過我爸爸李乾初,有沒有聽他說起以前有個很出名的大戲花旦譚燕梅,在這廟里長大。我老公其祥見過她,說她很美人很好。以前她每年大年初二都來,人老了,看不出來以前有幾風光。照例上香和放生,有時放龜有時放鳥,還有例牌添香油要掛祈福燈。這么多年都一樣,燈上寫黃彩蓮的名字,為她祈福,還指定燈要掛在外面的屋檐下,望得見對岸的圣米高。
她們發生過什么事,我哪知道。人活久了總會一身恩恩怨怨,到死都解決不了。以前的事那么遠,我連我大姑黃彩蓮的面都沒見過,哪曉得那么多。其實事情過去了還問來干什么,我只知道那時候怡保都不叫怡保,有些人到死那天都把這里叫“州府”,你知不知道?
(選自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新加坡青年書局聯合出版《獨角戲》)
本輯責編__馬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