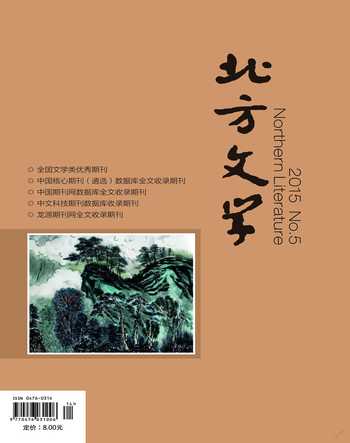“啟蒙”之外的啟蒙
張曉婷
摘 要:《伏羲伏羲》講述的是有關亂倫的愛情故事,在故事中的人物追尋幸福的過程中,伴隨著生命延續的種種形態,作為生命原動力的結合受到了倫理文明的阻滯。同時,小說表達的背景彌漫著歷久而彌新的自然氣息,鄉土背景下的情節透露著作者對啟蒙的另一層反思,在現代文明難以侵入的文化形態中,人們是否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延續進化與成長的征程。
關鍵詞:倫理;原始力量;啟蒙
一、欲望、情感與教化下的生命沖動
劉恒給《伏羲伏羲》起的原名是《本兒本兒》。在洪水峪,這個詞的本意就是指男性的生殖器。小說的結尾附了名字的由來,“本兒本兒本者,人之本也。又本者,通根,意及男根也。以本兒本兒命之陽具者奇,命之以谷禾者大奇。食色并托一物,此幽思發乎者謂之佳才,可乎?”,“食色”敘事這個劉恒一直關注的話題在《伏羲伏羲》里異常地鮮明。小說正式發表的名字則在生命色彩之外增添了更濃郁的倫理意味,這也更恰切地呈現了它的復雜性。
慈母一般的嬸子讓十歲便成了孤兒的天青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溫存,天青的欲望在嬸子美好的外貌以及善良本分的關心中不斷升級,他走火入魔一般的欲望化作發自肺腑的熱戀。愛和欲望把他折磨得異常殘酷,同時也讓他生發出了更多的勇氣,以至于忽略了他的叔叔以及這個人所代表的權威。天青作為男兒的天性在這個女人的關注下漸漸發酵。而勤勞仁義卻飽受壓榨的靦腆侄子也成為了嬸子在家里唯一可以親近的人,一個可以寄寓感情的同路人。兩個人所迸發出的愛的火花升華了原始的欲望。
“封建宗法制婚姻特別講究后嗣血脈的承續和純正,因此,封建意識要求人們在婚姻關系中講究夫婦人倫,杜絕婚姻關系的混亂”,種的延續在人們脫離了蠻荒時代的生育和繁衍的困難之后,在道德人倫的約定中演變為單線的承繼。天青是楊金山收養的親侄子,但也正是因為血脈純正的希望,他在骨子里他把天青的身份分得徹徹底底清清楚楚,養育天青數年,卻難以生出父子的情分。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完成傳宗接代的夙愿,這份在平常人看來輕松的事情卻成了楊金山最沉重的壓力,但是他從不認為這種飽含了屈辱的壓力給予他的是痛苦,至少說他從沒有想過要丟棄這種壓力和希望。和大多數人一樣,這是深入骨髓的一種天經地義的義務和責任,對他來說,完成這個畢生的愿望是一種莫大的幸福。當他離幸福越來越遠的時候,楊金山對菊豆的虐待也變本加厲,是他認為理所應當的。
最終讓楊金山欣喜若狂的兒子并非己出,孩子是侄子和嬸子亂倫的產物。《易。系辭》曰:“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可見,唯有婚姻符合“陰陽合而雨澤降,夫婦合而家道成”的“天人契合”的傳統觀念,唯有婚姻成為種的繁衍的合理方式。盡管天青是他的親侄子,但他在骨子里他把楊天青的身份分得徹徹底底清清楚楚,養育天青數年,卻難以生出父子的情分,一半是因為他本性殘暴,一半則是因為誰說楊金山他自己不是一個可憐的人呢,背負著沉重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給予他的從來都不是痛苦,至少說他從沒有想過要丟棄這種壓力,深入骨髓的一種天經地義的義務和責任,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幸福。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讓秘密的制造者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他們剛剛從一種原始沖動的壓迫中掙脫出來,就又被投送到另一種社會約定的圍剿之中。楊天青和王菊豆深知他們結合的危險,然而當欲望、道德不能夠在與巨大的悲苦和強烈的悲憫的戰爭中處于上風時,一切都變得百無禁忌而又順理成章。生命的原始欲望使得絕望的人重新燃起了生的欲望,人倫的不合也在他們痛苦的“贖罪”中漸漸獲得了諒解。
二、鄉村生態中倫理的原始意義
《伏羲伏羲》讓我們在這種折磨里看到是歷史積淀下來的穩定的東西對人們的影響,而不是政治變動所引起的紛爭。鄉村圖景的不變與親和反襯著人物內心日復一日的變動與掙扎。劉恒想借助這種原始的生命渴望來進一步地探尋除去外界的原因而更多出于人們內在動因的反抗。展開一幅幅生動的鄉村圖景時,劉恒淡化但沒有抹削外界的政治變動和歷史變遷,他一面通過鄉土的自然的敘述來突出這種原始性和本能性,一面呈現了歷久積襲的倫理道德所具備的具有原始意味的力量。
發生在洪水峪的故事幾乎是每一個中國鄉村都經歷著的故事,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靜日子里,只要沒有觸及到生存這個最切近的問題,那么外部發生的動蕩對他們來說反倒是一種不變。互助組,識字班,掃盲活動在這里輕描淡寫,識字遠遠沒有自己家的對著田地的耕作更有意義。而天青終于還是成為了破壞倫理與道義的那個人,但劉恒沒有批判道德倫理對人性的絞殺,也沒有炫耀破壞者沖破藩籬的驕傲,他在主人公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痛苦中告訴我們:即使是有違人性的倫理道德,也有它存在的必要,在對秩序的維護中,人們獲得的是安寧和成長,道德的約束反而會成為人性美善的助力。
我們不能忽視他在這個過程中始終難以割除的戰戰兢兢的恐懼。顯然,欲望的原始性和倫理的深刻性在他的身體內同時爆發著,在以后許多個可以殺死楊金山的機會面前,他都沒有辜負“天上的爹娘”教給他的東西,在菊豆一次次想要和他私奔的時候,他用對土地的眷戀、對安定的渴望阻止和勸慰著同樣飽經磨難的女人。天青的懦弱顯示出來的正是劉恒想要表達的,倫理的牢固性以及由欲望和倫理的沖突所構成的人類內部的自我平衡與成長。
三、進化征程里的沖突與自覺
中國鄉土小說的兩條路子,一條是站在批判立場的寫實風格,一條是站在歌頌立場的浪漫風格,作為八九十年代“新寫實”一類作品的《伏羲伏羲》,表達出的不僅僅是二者其一的意義。劉恒既沒有義正嚴辭地批判鄉村傳統文明的落后閉塞,也沒有溫情脈脈地贊頌事實上已經開始改變、不復存在的田園生活。在還原與創造真實的鄉村中,他所描寫的是在不同的表達立場的一種新的深入嘗試。
在鄉土小說的譜系中,許多作家都借用這一別樣的空間述說了他們各自的立場, “劉邦慶、蘇童、畢飛宇們顯然是站在民間底層的立場發掘現世美。弱勢小人物是小說的主角,對這些羸弱者的移情釋放了作者內心的一種快樂;對現世美的發掘體現了對傳統美德的弘揚,這對于物欲橫流對現代文明的確是一種有益的營養,或者說是承擔了一種美的教化作用。溫情脈脈的小說家似乎只準備認同世俗人生,他們筆下很少主體意識高揚、個性獨立鮮明、由堅定的自覺追求的人物,順從人生是他們遺傳的生命基因密碼,缺乏超越和提升。”劉恒沒有在現代文明與民間立場之間的沖突中尋找支點,盡管他書寫的是小人物,但沒有回復到京派類似的田園牧歌的方式來贊頌人性,也沒有在構建傳統文化柔情一面的過程去對照現代文明中人性的丑惡。他直接走到了人性丑的那一面,用以贊揚人性的美。“1990年代開始,雖然作家相對于鄉村社會還是他者的身份,但是他們已經擺脫精英姿態開始以平等的態度對村莊社會進行主體在場式的言說,對村莊社會的實際問題進行殷切的關注和深刻的思考,從而為鄉村社會的未來尋找出路”。劉恒向我們宣稱的同樣是亙古不變的人性的美,只是這種美具有張力,需要在艱難的環境中迸發。他筆下的人物同樣在面對倫理、道德、欲望時弱小卑微甚至畏縮退卻,但是他更強調的是這些人物在經歷了種種折磨后的某種映照了“啟蒙色彩”的進化。
面對鄉土與現實,劉恒不再念念不忘“啟蒙”的邏輯,他一直將自己視為魯迅“永恒的信徒”,但是劉恒看到的魯迅鄉土世界中啟蒙顯然不是它的唯一,至少在《伏羲伏羲》里,我們并不記得農民的愚昧和國人的弱點。正如文字并不能夠引起他們太多的興趣一樣,他們擁有屬于自己的文化,盡管面對著激變的生活他們擁有的經驗已經難以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