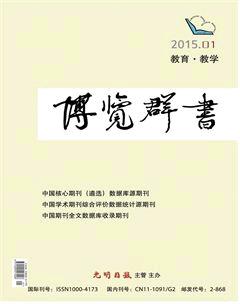從《傷逝》看在愛中謹慎前行的魯迅
郭翔
《傷逝》是魯迅所有小說中最難讀的,最早對魯迅的小說創作有較為深刻全面理解的評論家茅盾,在《傷逝》問世兩年后,還坦率地承認:“《傷逝》的意義,我不大看得明白”。此后半個世紀以來評析《傷逝》的專文不能說少。20世紀80年代,《傷逝》被改編成電影,關于電影《傷逝》的評論也不少。其中著名學者王朔先生認為魯迅的《傷逝》沒有真正寫出男女過日子的情形,他說“男女過日子的事,他老人家實在是生疏”。我認為王朔先生意在說魯迅沒有男女過日子的經驗,在文本中沒有寫出男女過日子的情形。王朔先生不僅從文本來觀照作家,更是從作家來觀照文本,得出這個結論是必然的。魯迅的小說《傷逝》較之于劉震云的《一地雞毛》和池莉寫實小說的寫實性,是遜色了。《傷逝》確實沒有過多的生活描寫,因此,我們對王朔先生的評論無可厚非。
魯迅在與許廣平的戀情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向不敢”,不敢愛就不會全身心地投入到愛情中去,對于愛情和婚姻的體驗和感受就會很少。從這個層面來考慮王朔先生的評論就更加覺得合情合理了。
然而,當我再度解讀魯迅以及他的作品《傷逝》時,我發現王朔先生對于《傷逝》的解讀也是不全面的。看來,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答語實非易事。
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中,關于《傷逝》,周作人只是指出小說中寫到的景物—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與魯迅的個人生活有關系。除此之外,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有關涓生和子君創造素材的信息。魯迅自己說過:“我還聽到一種說法,說《傷逝》是我自己的事,因為沒有經驗,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難了。” 這也許是魯迅自己唯一一次談到《傷逝》的文字了。他對《傷逝》的創作動機諱莫如深,簡直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可供探索的資料。
既然《傷逝》如此費解,我們只有深入去探索《傷逝》的創作過程,特別是直接的創作動機和創作靈感的觸發點。我們可以分析魯迅寫作《傷逝》前后的生活來尋找蛛絲馬跡。我認為可以從魯迅和許廣平的戀愛生活中出現的某些重大事態來探索魯迅創作《傷逝》的創作動機和創作靈感的觸發點。
在魯迅和許廣平的這場戀愛中,魯迅不能說是被動者,然而許廣平顯得更主動、更積極、更熱情、更無所顧忌,因為許廣平畢竟是27歲的新潮女性。這在許廣平所作的《同行者》和《風子是我的愛》中可以得到完美的詮釋,許廣平不顧一切決然向道德家和流言家挑戰,甚至愿意犧牲自己的事業照顧好魯迅的生活,使魯迅沒有后顧之憂。魯迅雖然對許廣平的愛情同樣深沉熱烈,但在表象上我們看到的魯迅卻是謹慎的,然而現實確實需要他謹慎:第一,魯迅有一個由母親做主,比魯迅大三歲,結婚將近20年卻毫無情感可言的結發妻子——朱安女士。封建舊道德影響太深刻了,這種影響有的隱藏在潛意識深層,即使常作無情的自我解剖,也不一定全部都能夠意識到;即使意識到了,也不一定能克服它而按照新的人道主義的道德標準自行其是,因為魯迅必須顧及母親和朱安女士的意愿和利益。第二,許廣平比魯迅年輕17歲,而且還是魯迅的學生,年紀懸殊,又是師生戀愛,都是舊道德的大忌,更重要的是倘若他們公開關系,魯迅就會處于進退兩難的困窘局面。第三,魯迅已是文化名人,眾目睽睽,而且在向封建營壘無畏的進攻中,自然四面樹敵,魯迅在個人生活方面必須小心謹慎,不給他的論敵以制造流言蜚語攻擊他的口實。
謹慎的魯迅和許廣平約定,也就是后來實現了的1926年8月,魯迅和許廣平一起離開北平到上海,兩人分開,魯迅去廈門,許廣平去廣州。許廣平這樣回憶:
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廈門大學任教。……政治的壓迫,個人生活的出發,驅使著他。尤其是沒有半年可支持的生活費,一旦遇到什么,那是很危險的。我們約定:希望在比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頭苦干兩年,一方面為人,一方面也稍可支持,不至于餓著肚子戰斗,減了銳氣。
因為個性都未必安分,而又不放心對方的獨自戰斗,……而最能使戰斗者氣餒的,就是首先計劃到圍攻之后的生活困難。我們想,假使有半年的積聚,可以有支持幾個月的生活費,那么,戰斗起來必定減少顧慮。……曾經交換過一件:“大家好好地給社會服務兩年,一方面為事業,一方面也為自己生活積累一點必需的錢。”
許廣平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的第四個顧慮——錢。魯迅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講中的講話《娜拉走后怎樣》這樣說過:“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可見錢在當時社會中的重要性,可見魯迅對此重要性認識非常深刻。
我以為,《傷逝》是魯迅和許廣平確認愛情關系后,為“我們約定”而作的。這是魯迅創作這篇小說直接的動機,也是創作靈感的觸發點。
子君和涓生相愛了。子君違逆了在北京胞叔和在家里的父親,勇敢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權利干涉我的權利!”毅然和涓生同居。為此,涓生也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結果兩個積蓄用完了,接踵而來的是社會壓迫是涓生失業,是生計難以維持,是愛情變淡,變質和窒息,終于離異。子君回到父親家里,默默死于無愛的人間,剩下只有如地獄的毒焰般燒灼涓生的悔恨和悲哀。造成悲劇的主觀原因,正是他們對社會壓迫缺乏足夠的精神和物質準備,他們的同居不具備經濟力量作后盾。
悲劇性的總體構思是通過子君涓生這兩個形象而顯示了它的藝術深度的。魯迅告訴我們《傷逝》所展示的深層意蘊是:
第一,個性解放,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是好的,批判了男尊女卑和封建婚姻制度。子君和涓生以非凡的勇氣爭取到了這份自由。然而在沒有人道傳統的中國封建社會,爭取到了這份自由并不代表什么幸福都爭取到了,能不能達到預期的幸福,還要看雙方共同“培植” 、 “保養”。魯迅與許廣平的約定是一種“培植”,一種“保養”,這“培植”和“保養”使他們免遭子君和涓生的悲慘境遇及結局。
第二,要對戀愛后可能遭遇的一切做好足夠的精神和物質準備,魯迅與許廣平約定的第二條,就是魯迅出于對封建文化現實的深刻認識提出來的。子君和涓生沒有這種物質準備,所以他們的愛情最后只能以悲劇告終。精神準備在小說里蘊含得更深,一方面,有足夠的物質儲備,也是對生活在封建社會作出的一種精神準備。另一方面,是更為深層的,在取得戀愛成功后要警惕傳統意識的泛起而使愛情變質和庸俗化,在社會壓迫面前,更要警惕自私被竊和虛偽的膨脹而窒息了愛情。
魯迅站在思想的高度上去寫作《傷逝》,也許沒有過多的“男女過日子的情形”,然而現代文學之父的魯迅運用他那冷峻的藝術風格表現的涓生和子君的生活更讓人覺得有藝術張力。
對于“男女過日子的事”,他更是想得多,他并不是一味沉醉于愛情的甜蜜中,他沒有跟著感覺走,而是冷靜而周密地理智分析,得出精神儲備和物質儲備這兩個重要的準備在愛情中的重要性,并用實際行動實踐著自己的分析。
生活中存在著許許多多不確定的因素,魯迅用他的小說告訴我們在愛情的路上要有準備。魯迅自己在愛中也是有諸多準備的,在愛的路上他是謹慎前行的。從他的謹慎中我們可以看出男女過日子的經驗,他的經驗并非是通過一次次戀愛得來的,而是憑著他對愛情以及他與許廣平愛情所在的社會土壤的認識而來的。我認為這樣的經驗更加深刻,更能警示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