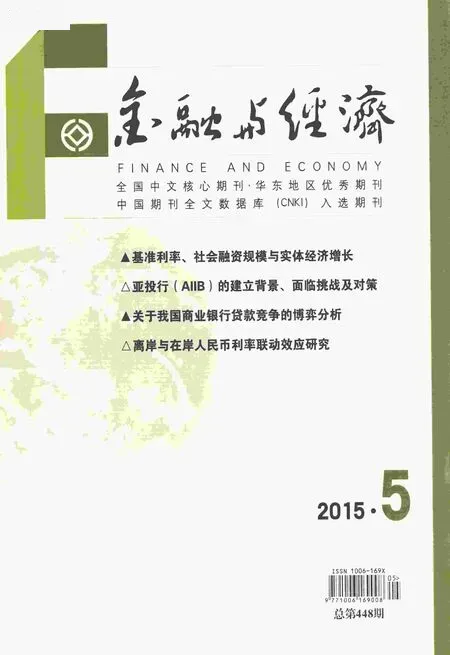金融分權與地方經濟增長
■ 董雨翀,萬 方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一)經濟、財政、金融分權
分權問題整體的表述是“經濟分權”,分為“財政分權”和“金融分權”。在中國,兩者具有高度的互補性和互動性,中國式經濟分權是財政金融集分權既互相獨立又共軛前行的過程。
錢穎一等學者首先提出“中國式分權”,并闡述了“中國特色的財政聯邦制”地區競爭,認為這一競爭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增長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周期平穩化趨勢貢獻巨大(錢穎一、Weingast,1997)。 自此之后,圍繞財政分權、稅收競爭及其對經濟增長績效的文獻不斷涌現。張宴和龔六堂(2005)實證檢驗了財政分權的跨時和跨區域差異。
談儒勇(1999)最早就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做了相關實證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有顯著推動作用,但是隨后大量的計量研究結果卻并沒有得到一個統一的結論。巴曙松等(2005)分析了地方政府和銀行系統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互動,認為地方政府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出于自身利益需求,以不同的方式利用銀行體系金融資源,由過去的直接干預到施加影響,再到通過逃廢銀行債務間接獲取金融資源。這之后,地方政府行為逐漸成為學者們研究的一大熱點。
地方政府的行為從多方面得到了解釋。首先是內在的動因:地方官員為了追求GDP增長,對金融資源進行爭奪。第二是客觀的渠道:李揚(2010)闡述了地方政府融資渠道狹窄促成地方政府爭奪金融資源。第三是隱性“負責任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債務獲得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保,減少了地方政府的相關風險(巴曙松等,2005),無形中弱化了地方政府對風險的考量。
(二)財政、金融分權互動
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將財政改革或者金融改革作為平行線索,并單線條地研究。事實上,財政與金融密不可分,兩種互相聯動影響地方政府和市場的行為,并最終影響經濟。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仿照蘇聯形成了所謂“大財政、小金融”的體制,即財政體系而非金融體系擔當了分配資源的核心功能。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極大限度地調集了有限資源,對于新中國的穩定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后,為了不斷適應新的市場機制,我國進行了大量的改革嘗試,最終形成了“財政分稅制”與“金融集權”的框架體系。兩類改革的歷次反復見表1。
錢穎一和Roland(1998)最早從預算軟約束和通貨膨脹角度對財政集權分權與金融集權分權的四種組合進行了研究。隨后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與理論的觀點,而缺乏實證分析研究。

表1 改革開放后財政改革與金融改革時間表
基于以上,我們將研究焦點放在中國2003年之后出現的金融分權上,通過實證分析考察近年來以地方金融創新、社會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多元化為主導的金融分權經濟績效。并將近年來與金融分權高度密切互動的財政分權納入考量視野,探尋二者聯動關系。
二、計量模型與指標選取
分析我國自2003年以來的地方金融統計數據不難發現以下兩個特點:1.金融機構地方化,小額貸款公司、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已經逐漸融入社會投融資體系;2.地方金融辦越來越實權化,在構建地方金融體系、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銀企合作等方面作用顯著;而中央在直接管轄地方金融建設方面能力有限;地方政府自籌資金上項目(預算外集資、銀行貸款)現象普遍。
(一)金融分權指標度量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設計了一組分權指標:
1.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投放社會貸款指標
MDloan=1-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投放社會貸款總額/地方所有金融機構投放社會貸款總額。王安(2013)用此指標從銀行業資源的角度度量了地方金融分權。這一指標直接反映了當前趨勢下地方經濟建設資金來源情況,代表了2003年后傳統以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發生的主要變革。
2.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吸納社會存款指標
MDdeposit=1-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吸納社會村款總額/地方所有金融機構吸納社會存款總額。這是從社會融資角度衡量的地方金融系統分權化程度。
3.非國有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數量指標
MDworker=1-地方國有金融從業人員數量/地方金融業從業人數總數。該指標是對有形金融分權的直接度量。
4.非國有金融機構從業人員薪酬指標
MDwage=1-地方國有金融從業人員薪酬總量/地方金融業從業人數薪酬總量。企業的盈利水平與其對員工的工資發放總量正相關,該指標是對金融機構經營盈利情況的良好替代。

表2 各金融分權指標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2是這些分權指標的相關矩陣,均根據2005~2008年各省的數據計算而得。顯然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很高,而從業與薪酬之間的相關系數非常高,機構與業務兩大塊之間的相關系數雖然略低,但仍然為正。
(二)計量模型
參考張晏、龔六堂(2005)等,我們將相關分析的回歸模型設為:

這里我們采用了面板數據(panel data)。變量Sit表示變量S在i區域、t時間的值,α、β、γ和η是系數矩陣,εit是擾動項。Yit是人均實際GDP增長率,控制變量Xit中的變量包括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一階滯后變量、進出口、投資增長率、價格水平、教育發達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各變量均經過必要的人均及通脹調整。Dumit是虛擬變量。特別的,控制變量中包含了財政分權水平,這里我們取全國總財政收入中地方財政收入所占比重。我們選取了2004~2012年這九年間的數據,涵蓋了25個省級行政單位①我們遵循慣例,不包括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并去掉了海南這一較為特殊的省份;同時五個民族自治區由于享受較大程度的經濟自主權及國家政策優待被剔除。。
三、實證結論:各省經濟增長與金融分權
我們采用多種分權指標分析數據樣本。White檢驗以0.2066的p值無法拒絕同方差原假設,因此無需對模型中的殘差作特別處理。F檢驗在1%水平下表明,相對于混合面板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更加適合;相應的Hausman檢驗均在1%水平下拒絕隨機效應——故以下的分析將主要基于固定效應模型。表3給出了采用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

表3 各省經濟增長與金融分權
從樣本全國整體角度,存貸款占比指標、從業人員金融分權指標前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從業人員工資金融分權指標前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為負。
(一)金融分權的地區差異: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
我們根據2008年各省人均GDP值進行排序,將樣本分成兩部分:前11個省份,我們將它們劃為較發達地區子樣本;后14個省份劃為較落后地區子樣本。我們考慮回歸模型:

根據(2)式,我們對全體樣本進行回歸,得到表4各列。相應的F檢驗在1%水平下拒絕沒有固定效應,White異方差檢驗以0.4937的p值無法拒絕同方差。后14個較不發達地區MDworker的系數顯著,而DumD×MDworker的系數顯著為負。
如果我們繼續在樣本中刪除4個在地方經濟體制有較大特殊性的直轄市,結果MDworker保持在10%水平下顯著為負,代表區域差異的DumD×MDworker的系數仍然在5%水平下顯著為負。

表4 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經濟增長與金融分權
這些結果說明,在較落后地區經濟增長與金融分權存在一定程度上顯著的負關系,而較發達地區中這種負關系則更強。
(二)金融分權的地區差異:東部、中部與西部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將樣本以所在地域分類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可以發現,東部省份具有較高的人均GDP和金融分權程度。此時使用DumE、DumM兩個虛擬變量,我們考慮回歸模型:

根據(2’)式,我們對總體樣本進行回歸,得到的結果如表5所示。西部地區MDworker的系數非常不顯著;而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MDworker的系數顯著為負,兩者與西部地區存在顯著的差別——DumE×MD-worker、DumM×MDworker前的系數均顯著為負。
綜合前面,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的金融分權對經濟增長的消極作用要大于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西部地區并不存在明顯的金融分權負績效,東、中部各省金融分權負面效應要比西部地區嚴重。

表5 東、中、西部經濟增長與金融分權
四、分權的經濟互動效應:金融分權與財政分權
我們選擇了代表全國性、政策性的財政分權指標FD,與前面使用的地方性、機構性的金融指標MD進行回歸,分析這一對經濟中的嬗變組合。考慮回歸模型:

得到的結果見表6。
首先,我們考察了僅加入對整體樣本的金融分權與財政分權交互項后的回歸結果:1.交互項CROSS的系數顯著為負;2.金融分權MD的系數在加入了CROSS交互項后,變為顯著為正 (而不是負)。這是一個經濟意義非常強的結果,表明:1.在金融分權程度被給定的情況下,提高的財政分權程度將導致更大的負經濟績效;2.金融分權在排除掉與財政分權的經濟交互之后,其本身對經濟發展是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的。
隨后,我們分兩次單獨向整體回歸模型中加入區別金融分權區域性經濟績效差異的DumE×MDworker、DumM ×MDworker和 DumE ×CROSS、DumM ×CROSS,見(2)(3)兩列。從獲得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兩種分樣本回歸均展示出地區差異——東、中部地區金融分權負績效顯著高于西部地區。
進一步,我們將(2)、(3)中的分類虛擬變量同時加入整體回歸模型。此時,在我們所主要關注的變量中,除了MD和CROSS兩個解釋變量依然保持在1%水平下顯著,其他涉及地區性差異的四個變量全部變為10%水平下不顯著。這說明DumM×MDworker、DumM×MDworker和 DumE×CROSS、DumM×CROSS 兩組解釋變量之間具有可替代性。因此我們得到了又一個重要的結果:在金融分權水平一定的情況下,金融分權經濟績效的地區差異可以部分由財政分權的地區差異解釋。

表6 經濟增長與金融分權-財政分權
五、處理內生性問題:工具變量
需要說明的是:1.金融分權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2.其他第三方“中介”的影響也可能影響對于兩者間關系的檢驗。因此我們有必要引入工具變量處理回歸模型中潛在的內生性問題。
(一)工具變量的選擇
1.政治資源
Poli=具有本省籍貫并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人數。張平等(2012)提出中國中央政府官員對于其籍貫省份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對于他們歷職的非籍貫省份經濟增長促進作用不明顯;并且這種促進作用是通過提高投資率的方式實現的。
2.1949 ~1956年社會基礎設施
infra=1949~1956年間地方私有成分工業年度產值最大值。該工具變量僅反映省區差異,無時間差異。徐現祥、李郇(2005)使用這一歷史指標作為當代社會基礎設施的工具變量,實證檢驗了它對經濟社會發展顯著作用。顯然,這一工具變量與當今金融體制有較高相關性,并與除“制度、政策”外的經濟變量無關。
3.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
doubt=地區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胡勇鋒(2014)使用地區金融風險水平研究金融分權在地方對于金融資源控制力差異角度上的成因。我們認為,地方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攀升與近年來地方性金融機構發展有較強聯系。同時可以認為該變量與金融分權體制變革外的經濟變量具有一定的外生性。
(二)處理模型與結果
我們采用2SLS處理內生性問題。第一階段的回歸模型設為:

我們將MCworker的估計量記為MDC,并作為第二階段回歸中的新解釋變量,重新回歸得到表7各列,總體上維持了原有結論。

表7 內生問題—工具變量第二階段回歸
六、問題原因分析
前人就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兩種對立的解釋。
一方面,充分的金融分權能夠緩解“金融供給抑制”,可以作為中央政府適時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葉志強等(2011)使用了改革開放30年間的數據論證了金融系統的高度國有壟斷擴大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而適度的金融市場化、自由化則能夠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消除二元經濟結構。
另一方面,過度的失去監管的金融分權卻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和不良貸款率上升,不利于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并“倒逼”中央政府加強經濟集權。
(一)負的經濟績效
政府在金融分權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合理的行政干預抑制了金融分權發揮其理論優勢。近年來,一些市、縣級地方政府為了在GDP競賽中表現優異,強制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為當地基礎設施和企業進行資金支持,背離了許多機構的經營目標。有些地方的中小金融機構甚至為此背負了大量的不良資產,近期一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帶來的風險積聚就是例證。而大型國有金融機構對風險有嚴格的控制,其“寧缺毋濫”的經營原則使得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則被動地承擔起了中小企業的生存供給。
第二是法律保障、行政監管不完善。我國目前對于地方金融機構準入制度、運行監管制度和市場退出制度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僅有的《商業銀行法》并沒有對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做出明確的權利、義務的規定,而《擔保法》雖為相關經濟事務立法卻并沒有對專業的擔保機構做出權利義務法律規定。
最后是借貸信用環境不良。以震驚全國的“溫州老板跑路”事件為例,一些企業發生債務拖欠,甚至以各種轉移賬戶、假破產等手段逃避銀行債務,而這樣的市場對于經營規模較小的金融機構危害尤其嚴重。
在不良外部環境下,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內部狀況同樣堪憂。2008年以來,地方性銀行機構資產規模擴張使得資本充足率下降,其補給達標壓力巨大。不少中小金融機構僅是“單獨門戶”,沒有系統內的聯行。這些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生存發展舉步維艱。
(二)分權聯動
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提升了償付相關債務的能力,促使地方政府進一步弱化了對于風險的考量,行政干預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經營將加重。2010年以來,廣東銀行系統在對貸款償還的分析中發現,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存在最主要的兩大風險是還款來源和資金挪用。不少市縣政府負債率較高,這些投資項目的還款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等不穩定因素對中小銀行類機構造成風險隱患。
(三)地區性差異
以農村信用合作社、信托公司、小貸公司為代表的各層次金融機構涵蓋不同層次的資本服務,在國有大型銀行壟斷經營、其他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不足的背景下這些機構對于不發達地區金融服務體系有“補缺罅漏”的作用。
我國金融排除在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程度更強。統計表明,中國90%建立在銀行基礎上的信貸有2/3流向了國有企業,盡管這與其經濟貢獻完全不匹配。東部地區相對于西部地區有更多的優質客戶資源,因此中小企業則益發不是銀行主要的市場目標。他們不能或者必須付出更大代價才能完成所期望的融資目標。因此,反而是西部地區金融機構多層次化提供了正經濟績效。
從產業分布角度看,東部省區第二、第三產業相對較為集中,西部省區第一、第二產業相對集中。中小金融機構對于第一、二產業十分明顯,對第三產業的支持作用不明顯;國有商業銀行恰恰相反。因此地方金融分權在第一、第二產業密集的西部較不發達地區對于促進經濟的作用更大。
回到政府的視角,分析能夠被干預的金融主體。東部地區已基本形成了各類銀行并存的多元化金融格局,西部地區金融供給的主體是國有金融機構,這為東部發達省份地方政府提供了充分施加行政影響的對象。另一方面在對于不發達地區轉移撥付的資金中有大量為專項使用資金,限制了地方政府對其使用范圍;而東部地區則獲得了使用權限更為寬松的財政資金。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東部發達省份地方政府更加積極主動參與或者干預到經濟投資競賽中,并造成了非市場化、非穩定可持續的經濟績效。正是上述多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了金融分權績效的地區性差異。
[1]Qian Y,Weingast B R.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Barry Weingast,1997,11(4):83~92.
[2]張晏,龔六堂.分稅制改革、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C].經濟學季刊,2005:75~108.
[3]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53~61.
[4]巴曙松,劉孝紅,牛播坤.轉型時期中國金融體系中的地方治理與銀行改革的互動研究[J].Journal of Finance,2005,(5):25~37.
[5]佚名,李揚.完善地方金融管理解決融資平臺問題[J].農村金融研究,2010,(12):74~74.
[6]Qian Y,Roland G.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Gérard Roland,1998,88(5):págs.1143~1162.
[7]王安.中國經濟轉軌中的中央控制力:作用及其調整[D].山東大學,2013.
[8]張平,趙國昌,羅知.中央官員來源與地方經濟增長[J].經濟學季刊,2012,11(2):613~634.
[9]徐現祥,李郇.中國省區經濟差距的內生制度根源[C].經濟學季刊,2005:83~100.
[10]胡勇鋒.中國經濟轉型中的金融分權[D].西南財經大學,2014.
[11]葉志強,陳習定,張順明.金融發展能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嗎?——來自中國的證據[J].金融研究,2011,(2):4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