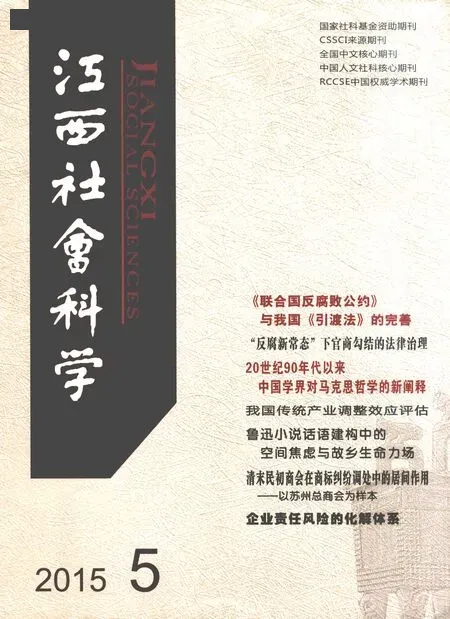魯迅小說話語建構中的空間焦慮與故鄉生命力場
■張春燕
在魯迅的話語系統中,故鄉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言說立足點。故鄉是魯迅啟蒙話語的觀照和言說對象,也是魯迅流寓者身份確立和掙扎的空間、精神參照物,是魯迅生命體驗言說的出發點。它作為魯迅體驗與言說的中樞,輻射出魯迅話語的基本語匯。于是,故鄉成為魯迅的核心話語點,圍繞著這個核心,在不同層次和空間內部形成一種聚集力量,衍生出一個獨具魯迅氣質的話語的場域,其中蘊含著魯迅話語的言說實踐和規則。顯然,魯迅的故鄉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域背景或者穩定的空間意象,它的內部既凝聚和衍生著意象、主題、意志,又存在著不同層面的話語的生成規則。在這一話語建構的過程中,空間焦慮內化為主要因子,支撐著故鄉話語的成型,甚至決定著這一話語的走向。
魯迅的小說中,主人公們的活動大多集中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場域中。李歐梵在《鐵屋中的吶喊》中說:“從一種現實基礎開始,在他25篇小說的14篇中,我們仿佛進入了一個以S城(顯然是紹興)和魯鎮(她母親的故鄉)為中心的城鎮世界。”[1](P66)李歐梵不但注意到魯迅對于空間的關注,也指出魯迅作品中的空間建構是以他的故鄉為模本的。魯鎮、S城、未莊、平橋村、咸亨酒店、一石居、茶館、社廟、土谷祠……當我們將這些地理空間并置的時候,凸顯出的正是魯迅話語的一個現實觀照點:故鄉。魯迅小說的展開幾乎統統依賴于這個以故鄉為原型的世界。這是魯迅故鄉話語的初步生成,即作為原型存在的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故鄉。它作為小說主人公們的活動背景存在,是魯迅作品情境建構的出發之處。
魯迅以密集的空間概念建構了原型故鄉的同時,又賦予故鄉以內核性的人格,諸如畸形、荒涼、冷漠、殘忍、陰暗,生活其間的民眾掣于“吃人、觀賞吃人、被人吃”的網羅不能自拔,也不自知。這一生存網羅即是故鄉自身的人格和生命特質,其實質正是故鄉民眾的群體性人格。在魯迅的文本世界中,故鄉因為內部眾人的群體性人格疊加而有了自己的生命人格,它以自身的生命質與內部主人公們并置為小說的言說對象,從而發出了自身的話語。魯迅故鄉話語的建構過程,實則也是故鄉這一空間參與敘事與言說的過程。故鄉如何以地理空間意象成為文化建構、價值體系建構的中心,又如何作為文化、價值參照實現言說者自我身份的確立,是本論文要探討的問題。
故鄉作為空間概念,有著自身的層次,它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是密布著權力關系和價值秩序的社會文化空間。人與空間的關系,人在空間的生存,成為魯迅故鄉話語的著力點。而其間觸目驚心的是魯迅以及他筆下人物的空間焦慮。即,人與生存空間(故鄉)不能相容,不能和解的緊張關系。對空間焦慮的直接言說在魯迅的小說中不勝枚舉:
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萬分沉重,動彈不得。(《狂人日記》)
太大的屋子四周包圍著她,太空的東西四面壓著她,叫她喘氣不得。(《明天》)
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里高墻上的四角的天空。(《故鄉》)
魯迅筆下的主人公們,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阿Q、瘋子、呂緯甫、魏連殳,幾乎無一例外地生存在這逼仄、氣悶、秩序環繞、人情冷漠的世界里,時時感受到來自這一空間的威逼和壓迫。每一個人身上都帶有不安和焦灼感。魯迅的關注點始終在這些封閉空間內部主人公面臨的焦慮。這一以焦慮為核心的關系結構和感受結構就是魯迅故鄉話語的精神本質,也是故鄉從地理意象上升到群體性人格象征的內在話語機制,并且暗示著魯迅對于世界的認知和把握方式。
一、整體上的“囚牢”模式
魯鎮之于祥林嫂、未莊之于阿Q、吉光屯之于瘋子、咸亨酒店之于孔乙己、S城和寒石山之于魏連殳……都是一種圍困力量。不管物理空間如何轉移和置換,始終沒有擺脫這一逼人的“囚牢”模式。在這種人與故鄉空間的關系中,空間是先在而主動的,人是被動的;空間是掌握話語權的,人是被評判和規約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眾人的調笑中淪為笑料,祥林嫂是魯鎮人注視中的“陳舊的玩物”,瘋子和狂人更是被真實地囚禁在祖屋和社廟里……他們始終處于以囚牢形式出現的空間里,被圍困而無力掙脫。故鄉就是通過這種令人窒息的囚禁實現對于內部人眾的虐殺。這些小說的內部,都傳遞出黑暗、冷漠、殘殺、恥笑、死亡、孤獨等體驗,糅合的焦灼感在文本中發酵、繁衍、變形、演化。正是這種內在的空間焦慮的影響,故鄉在言說過程中演化為鬼域:故鄉—社會空間(等級、秩序和文化空間)—牢籠—地獄,通過焦慮情緒的傳遞,以一系列空間意象的相互置換完成空間概念和空間性質的相互指涉,最終使故鄉與鬼域成為同質同構的空間概念。
魯迅的故鄉話語內部,首先突出的是實有的空間,魯鎮、未莊、S城、社廟、祖屋、酒館、山村、土谷祠,甚至花轎、墳、棺材,魯迅不厭其煩地重復著這些充滿桎梏感的意象,以這些具體而封閉的空間營造出逼仄的 “無法呼吸”“艱于呼吸視聽”的空間感受,正是這種逼仄產生的焦灼感,將實有意象不斷置換為感知意象,從而將具體空間意象變形化,無數涌現的空間意象以一種內在的同質——焦慮——無限推演下去,衍射至不同權力控制的空間內部,漸次演化成了 “高墻上四角的天空”“鐵屋子”“地獄”“非人間”“無物之陣”“獨頭繭”“人肉筵宴的廚房”,甚至“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至此,實有的空間意象經由感知意象的中介,進入到以囚牢為形式、以吃人為內質的象征性意象。從空間對人的囚禁,最后到空間對人的虐殺和吞噬。故鄉與鬼域的同質性正是通過這一系列意象的置換完成的。這一話語規則是:故鄉=地理空間=社會/秩序空間=牢籠=吞噬/吃人=地獄。而從實有的空間意象到感知意象,再到象征意象的轉換契機,正是空間焦慮。在這種言說規則中,空間焦慮內化為敘事的主要因子,故鄉經由這一因子的內在運作,最終變成鬼域。這一內核性質的感受結構成為故鄉與鬼域之間轉換的核心規則,并支撐起故鄉的生存、文化景觀。
故鄉的囚牢本質和無形殺傷力作為故鄉話語的顯在層面,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需要指出的是,這是從敘述者的角度呈現出來的話語,是將故鄉作為啟蒙對象的空間想象與空間重建。鬼域故鄉的建構與啟蒙話語的建構是同步的。我們注意到,鬼域故鄉的言說者為空間之外的人,他是冷眼旁觀者,也是故鄉的異己者。即敘事者與故鄉的對話關系中潛藏著一個 “文明世界”(理想世界)作為參照,故鄉成為魯迅話語中的“他者”。敘事者與其所在空間的距離感使得他建構的這個眾鬼喧囂的空間成了與他異質的存在,啟蒙話語正是經由這異質性提供的言說角度進入到故鄉話語系統中。
在“我”這一帶有啟蒙者眼光的歸鄉者不出現的文本中,唯有狂人、瘋子和夏瑜這種脫離了正常生活軌道的叛逆者,能夠跳出生存的空間看到故鄉的囚牢性。狂人和瘋子出現的意義就在于,以他們的非常態的生存方式和話語方式在故鄉話語內部打開非常規的感受維度。這種觀察視角和感受維度是故鄉自身無法自發出現的。因為故鄉話語背后,是文化范式的規約。狂人和瘋子的瘋言瘋語正是以打破規約的方式撕開這密閉的空間的一角,他們不斷警示著人們存在場域里的危險性。夏瑜更是對阿義說 “可憐”,他們都因為反常規性而獲得與故鄉的距離,而同時,狂人被關在祖屋里,瘋子被關在社廟里,夏瑜被關在大牢中。他們的身份特征使他們在體驗世界里將故鄉與監牢這兩個意象進行并置。從這個層面看,囚禁意象的設置就具有對故鄉整體的象征意義。主人公因為瘋癲或者叛逆而獲得即使身在故鄉也并不屬于這一空間的特點,魯迅反復將這“不在場”身份與囚牢意象并置,實則將囚牢模式的發現納入到啟蒙話語的框架之下,于是,囚牢意象不僅僅是故事事件的呈現,而且是作為一種感受結構去進行意象之外的故鄉人格的想象和故鄉話語的建構。
二、內部的阻隔模式
如果說囚禁是從敘事者的啟蒙觀照中生成的故鄉話語,那么對于故鄉這一“囚牢”的在場者(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而言,故鄉又呈現出不同的意味,這一層次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感受結構是阻隔,其內核是被拒斥感。焦慮不僅僅是來自空間的壓迫,還來自于人無法進入空間內部,與空間始終隔膜。魯迅故鄉話語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一阻隔模式推動的。《祝福》里祥林嫂的故事對于敘事者“我”來說,是“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跡的斷片,至此也聯成一片”,由這種整體觀照的角度,祥林嫂的一生是被囚禁、被圍困的一生。然而推動著這些斷片構成小說的內在驅動力,卻是由祥林嫂的角度感知到的阻隔以及祥林嫂想要沖破阻隔進入到這個空間的努力。《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呈現出的阻隔是以曲尺形的柜臺將人群分割開來,對于內部的眾人而言,取笑孔乙己,成為他們聯合一氣的途徑,他們借此獲得一種穩定的團體感或者安全感。孔乙己難堪的失語狀態說明他與魯鎮文化空間的疏離。“穿長衫”卻只能“站著喝酒”,則意味著他在任何空間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永遠游離于空間之外的焦慮成為孔乙己身上的標簽。
如果說從敘事者的角度,以“囚牢”模式展示了故鄉在話語中如何變成鬼境,那么,在這個話語層面上,令人觸目驚心的則是,故鄉內部的人如何變成鬼卒。其內在的話語運作機制是空間焦慮迫使下的人的本能掙扎。這種焦慮的運作過程體現的是無數的個人拼死向著群體靠攏。于是,這一層面上的故鄉話語沿著這一規律言說和深入:鄉民=空間中的人=認同秩序和規則的人=被空間馴化的人(被吃者)=排斥秩序之外的人(吃人者)=鬼眾。
以《祝福》為例,祥林嫂的一生濃縮在幾個空間之中:魯鎮(初到)、賀家墺(被迫改嫁)、魯鎮(被看、被嘲笑)、陰間(想象與恐懼)。初到魯鎮,地理空間就在四叔的皺眉中成為文化、秩序空間,她做的唯一的努力就是拼命干活以獲得認可,進入到這個空間內部;賀家墺是“深山野墺”,象征著空間的隔絕,祥林嫂由改嫁被隔絕在魯鎮社會空間之外,她以死抵抗的心理動因,其實正是她對于所在的社會空間秩序的認同和恐懼;阿毛被狼吃,將她再次送到魯鎮,阿毛的被吃,正是祥林嫂被吃的隱喻,而祥林嫂看到的卻不是這個空間的吞噬性,她以不斷重復阿毛的故事來獲得這個空間的同情和接納。即便這個空間以注視、鑒賞、嘲笑甚至防備形成密不透風而無法打破的囚牢,她所做的努力也仍舊是捐門檻以期得到救贖,重新獲得魯鎮人的接納。祥林嫂自始至終感受到的,都是阻隔,而不是囚禁,她的所有努力,也都是為了獲得空間內的立足之地,而從未想過沖破這個囚牢。
同樣,那個雖然滿口“之乎者也”卻拼命想要與人交流的孔乙己,希望短衣幫對他接納,結果卻是“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只好向孩子說話”。那“排出九文大錢”的孔乙己則是以這樣“闊綽”的一個舉動,想要進入穿長衫的群體。同理,阿Q渴望姓趙、欺負小尼姑,也都有一種打破阻隔,期望與他人融為一體的意愿,也因此,他的革命夢想不是打破鐵屋子,沖決出去,獲得新生,而是意味深長的“同去同去”,他要的不是“去”,而是“同”。可以說,阿Q的所有生存意志都是進入而不是逃出秩序空間。
我們站在敘事者的角度看到故鄉由實有空間漸漸演化為社會空間、牢籠、吃人場、地獄。但這個言說層次中的主人公們卻個個茫然而恐慌,他們看到的不是鐵屋子,而是阻隔,是“高墻”“厚障壁”……被拒絕的焦慮指引著他們去迎合這個空間內部的所有規范,以此獲得自我身份、價值的重構。鄉民甘愿被這一空間馴化,其目的是要尋找到自身在這一空間中的位置。正是害怕被空間排斥的焦慮促使他們變成空間的認同者和維護者。于是他們成為相互敵視、防備、既是吃人者也是被吃者的鬼眾。故鄉這一空間既規約了其間的鄉民,使他們成為鬼卒;同時,鬼卒們也不斷支持、維護和加強這種空間的壓迫力量。于是,經由這種規約與支持的互動,魯迅在故土言說中營造了人間煉獄,主人公們統統變成游魂。
雖然都有在空間壓迫中的焦慮,但在鄉者與離鄉者(叛逆者)在面對故鄉時感受到的自我與空間的關系結構完全不同,其根源在于,個人性的有無。離鄉者因為與故鄉的距離獲得了觀照故鄉時的整體性視角,帶有啟蒙視角的離鄉者首先關注的是個體與故鄉整體的關系。因而他感受到的是自我與空間的對立,以及空間的圍困。對于在鄉者來說,他們人格中的“自我”、“個人”是缺席的,而甘愿作為鬼卒生存,以此在鬼境中獲得立足之地。以狂人為代表的掙脫空間束縛的個人,是以從群體中抽離的方式獲得自我的身份認同,甚至是自我的價值和道德上的崇高感。而以祥林嫂為代表的在鄉者則是通過不斷地將自我放置到群體中這樣的努力來尋找安身立命之處。對于在鄉者而言,他們慣于以適應空間規則的方式獲得存在的舒適感。這一層面上的空間阻隔,指向的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生存的困惑,即人的離群的恐懼。魯迅這一步走得比囚牢模式中的啟蒙觀照還要深遠,他直接超越了對故鄉或傳統中國的文化和倫理審視,而直接進入一種現代感知和追問,這一追問針對的不僅僅是生存形式,還是進入到生存邏輯本身的困境:人對于群體的依附所造成的存在困境。
在這種故鄉話語的建構過程中,被圍困的焦慮和與空間疏離的焦慮并存,成為魯迅故鄉話語無法避開的內在情緒,并以囚禁和阻隔兩種模式推動著故鄉從原型/背景意義上向著鬼域發展。這種焦慮引導著魯迅營造壓抑別扭的故鄉,直指人與鬼相生相克的生死場。
三、還鄉模式與自我追問
魯迅的故鄉小說形式上幾乎都采取了 “還鄉”模式,而“還鄉”進入文本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是用以銜接啟蒙話語與故鄉話語的媒介,不斷出現的“我”的離鄉與還鄉從形式上暗示了在故鄉話語系統中啟蒙話語的參與。二是話語主體的多重性和自我分裂性媒介于還鄉模式得以展現。
離鄉者與在鄉者的兩種不同的感知結構,意味著對生存狀況的不同把握方式,也展示著完全不同的生存狀態。因而二者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兩種相互悖反的認知結構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焦慮的途徑:穿破阻隔進入秩序空間和從囚牢中突圍。鬼域故鄉建構的過程,正是自我從傳統世界出逃以及自我確立的過程。敘事者的置身事外透露出暗藏信息,即敘事者以自身從故土的抽離將自己變成故鄉的旁觀者,從而以啟蒙的眼光觀照故鄉,以此完成故鄉話語到啟蒙話語的轉換,同時也完成了自身由故鄉的鄉民到故鄉的異己者、啟蒙者的轉換。于是,啟蒙話語建構的過程可以還原為“我”從故土的出逃過程。魯迅的矛盾和痛苦在于,他將故鄉話語納入到啟蒙話語的解釋框架之下,那啟蒙話語必然有進入故鄉話語內部的需要。而作為啟蒙者(故鄉的不在場者),他看到囚牢本質之后,他的價值和文化選擇是向外突圍。可是作為啟蒙話語與故鄉話語的中介,這個啟蒙者在行動選擇上又必須是向內的進入。于是,隨著魯迅故鄉話語的不斷深入,兼具了“離鄉者”(不在場者、突圍者)和“回鄉者”(在場者、進入者)身份的“我”避無可避地進入敘事文本,而還鄉成為“我”的自我追問的形式。
從《故鄉》開始,魯迅其后的故鄉小說(《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出現了一個高度介入的還鄉者“我”。言說主體不再是置身事外的敘事者,而是離鄉后的返鄉者。隨著還鄉模式在故鄉話語中的不斷強化,由敘事者、在鄉者、故鄉構成的對話關系,變成了更加錯綜復雜的敘事者1(離鄉者“我”)、敘事者2(還鄉者“我”)、在鄉者、故鄉之間的對話關系。“我”的分裂性在這種不斷強化的對話中凸顯:故鄉的言說者與面對故鄉的失語者、故鄉的背叛者與企圖進入故鄉者、啟蒙者與失意者共存一體。“我”的身份在這種對話中喪失了確定性。對于自我的追問在還鄉文本中越來越緊逼。不斷重復的還鄉模式,更像是在為自我認知的追問尋找一個價值的參照。
當離鄉者“我”在文本中變成了還鄉者(故鄉的在場者),敘事過程中“我”的“在場性”就必然導致“我”也深有阻隔體驗,而不僅僅是外在觀照中看到的囚牢。在還鄉模式出現的小說里,還鄉者面對故鄉的真切感受恰恰是阻隔,無法進入,而且都是以故人相見為場景和契機表現的。在《故鄉》中“我”與楊二嫂,象征著還鄉者與掌握著鄉土話語的在鄉者之間的彼此拒斥,“我”始終失語,無法進入這個世界。“我”與閏土的相見,同樣是“隔了一層厚障壁”,“四面的高墻將我圍困”。《祝福》里“我”與祥林嫂的遭遇更是將“我”甚至是“我”代表的啟蒙話語無法進入到故鄉內部的現實展示得淋漓盡致。《在酒樓上》“我”訪友不得、見舊友而無法親近、呂緯甫遷葬不見尸骨,處處碰壁,處處被排斥,也凸顯了這種阻隔。
還鄉者感受到的阻隔有更深層的內在,他們不同于祥林嫂和阿Q的是,他們不是要融入那個世界來獲取自身的安全感,而是想通過啟蒙言說的介入對其進行改變。這種基于還鄉者立場上的阻隔感,在魯迅的言說中以另一種感知意象出現,那就是“沙漠”和“荒原”:“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2](P439)《故鄉》開始的“還鄉與失語并存”的模式將“我”與故鄉的斷裂推送到言說表層。也由《故鄉》開始,對于啟蒙者自身的存在追問再也無法停止。之后的《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以重復的還鄉進入不斷的自我審視、自我質疑、自我追問、自我譴責。理性認知將“我”從傳統道德和倫理中抽離出來的結果,并不是給了“我”一個新世界,卻只是將“我”變成故鄉的異己者,“我”被故鄉拒絕和放逐。啟蒙者的荒原感未必只有寂寞,還有無地容身的焦慮。“我”的自我意識給“我”的是新的生命形式的衡量標準,卻以自我的存在空間的傾覆為代價。《祝福》中祥林嫂的陰間歸屬的追問實則暗藏著一個關于啟蒙者精神和文化歸屬的問題。無地容身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分裂開始成為顯在話語。魯迅自身的最大焦慮正是在這一境遇中,迷失了自我身份以及自我的容身之地后,生命主體面臨的“我是誰”以及“我在哪里”的雙重焦慮。
四、尋路模式與流寓者身份的確立
當故鄉話語的展開以鬼域及鬼眾的成型收場,話語主體摧毀了自身的容身之地,凸顯的問題是:以故鄉為參照的這個主體的身份定位是什么,又是以什么方式獲得確立?在以故鄉為核心的這個多邊對話的體系中,分裂的話語主體是如何穿透生存危機,實現分裂自我的重新組合的?其言說的秘密正在于文本中尋路模式的開啟。路、行走意象在魯迅的小說中是與“我”的出現捆綁在一起的。如前所述,“我”從《故鄉》出現,正是自我身份焦慮的開始,也是自我分裂的開始。而路、行走作為與“我”捆綁出現的意象,其意義正是以其行動意志實現分裂自我的整合。
與社會空間的不能相容是魯迅的心理和精神的基本因子。于是,人與空間的對立與不能和解必然成為魯迅故鄉話語的核心語義。在與故鄉的對話關系中,作者自身的空間焦慮全部潛伏在文本內部,成為話語意向的牽引力。《孔乙己》中曲尺形的大柜臺構成的阻隔感受,幾乎無異于少年魯迅 “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2](P437)所感知到的生存結構。孔乙己和祥林嫂在魯鎮所感受到的阻隔,蘊含著魯迅對世界基本結構的認知,那就是世界與自我的對立。當他在啟蒙話語的框架之中書寫這個世界,他能夠以不在場的離鄉者身份建構故鄉的囚牢性,但進入到文本內部之后,他對故鄉的判斷,無不滲透著自身經歷在情感世界中的遺留。
魯迅在現實中的“走異路,逃異地”,也正是他在被囚禁、被圍觀的異己空間中無法生存而不得已的出逃。從紹興到南京、日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他行走的每一步,幾乎都伴有著無法擺脫的空間壓迫。汪暉在《反抗絕望》中說:“魯迅‘反傳統’的內在動力還不是對某種價值信仰的追求,而是一種更為深沉、也更為基本的危機感——生存危機。”[3](P58)汪暉所說的“生存危機”是從人與民族的存亡角度闡釋的,但魯迅自身的存在危機也必然是應有之意。所以他的故鄉言說過程中始終貫穿著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解決自身與所在空間的不相容性和對抗性?魯迅選擇的方式是,將他在現實中的一次次出逃帶入到文本,這種從異己空間的突圍行動進入到言說中,即成型為尋路與行走的文本結構模式。將魯迅的以尋路、行走作為儀式性動作的精神選擇放置在他的故鄉話語系統中去觀照,所有的行走都意味著與所在空間 (故鄉)的齟齬,凸顯的正是空間意義上的魯迅身份:流寓者。它的同質的語匯還有異鄉人、過客。行走與尋路的頻頻出現,既是魯迅空間焦慮的暗示,也直指言說者魯迅的生命存在的流寓狀態,即始終行走在打破囚禁和尋找立足之地的路上。尋路和行走成為他的故鄉話語建構中的潛意識。這意味著他在故鄉話語建構中,是將自身在空間里的異化感糅合成精神選擇上的主動的拒絕。被摒棄、被放逐與主動告別、主動摒棄交織成近乎悲壯的生命存在方式。這些才是魯迅精神體驗的類似原點性質的語匯。而魯迅的故鄉話語正是在這一個維度上建構和衍生的。
行走意味著拒絕和告別。“我”參與到敘事中之后,魯迅對于“我是誰”“我在哪里”的追問已經無法停止,這一存在本質的追問愈來愈迫切,當自我無法進行回答的時候,唯一能夠確定的,恰恰是“我不是誰”和“我不想在哪里”。于是,這些分裂的自我在所有文本最后都統統選擇與故鄉告別,行走以其告別性使分裂的自我通過斬除舊我而實現人格的統一。譬如《故鄉》文本的言說目的,正是“為了別他而來”。通過書寫“我”與故鄉這一空間的隔膜,通過“我”與楊二嫂、閏土的對照徹底斬斷“我”與故鄉的精神聯系,從而實現“我”的對于傳統世界的拒絕。“這樣的還鄉作為儀式使現代知識者的文化結構得以真正意義的完形。”[4]“我”最終的離鄉雖然仍著筆于“四面有看不見的高墻”的焦慮,但是生命存在的意義卻通過那段著名的關于“路”的言說而彰顯。同樣,《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的結尾也是以“我”的“走”而結束。而這一動作的暗示即是通過與所在空間的決裂,所有的“我”都成為故鄉的出逃者和新的空間的尋路者,而至此,“我”也徹底成為故鄉的游子和過客:“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5](P196)從這種拒絕與告別中浮現出來的,是行為主體流寓者身份選擇的自覺性。自我身份的焦慮還不能消除,但是“我”的走,已經將自我變成主體,開始以行動說“我不”。拒絕成為自我潛意識里強有力的人格:“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6](P169)堅決而理智的否定性是生命主體的理性選擇。尋路和行走的模式正是以這種否定性解決了魯迅的問題,使他成為過客反抗精神的踐行者。
所以,行走也是內在精神世界迸發出來的意志強力。徐麟認為,從《故鄉》的結尾“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生命的焦慮是如何在行動的契機中釋然的:地上本沒有路,但大地卻是一個堅實的‘有’,他賦予了大地以存在性”[7](P115)。魯迅的存在焦慮也正是在路的 “無”與大地的“有”之間實現消解。也就是說,魯迅已經放棄尋路,而更注力于行走。他選擇以走為路的生命姿態。即使自我沒有容身之地,行走本身會開拓出一個行動場,這個場是人格的立足之地。他已經不再追問“我是誰”和“我在哪里”,而是進入到以行走本身為目的和意義的精神的空間。而言說主體的這一生存姿態在《過客》中得到完整的詮釋。來處和終點都不重要,生命的意義和秘密只在于行走本身。他已然超越對現實空間、文化空間的訴求,他以行走這一行動本身建構了生命力量的場,魯迅正是以此立足的。
[1]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魯迅.《吶喊》自序[A].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何平.《故鄉》細讀[J].魯迅研究月刊,2004,(9).
[5]魯迅.過客[A].魯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6]魯迅.影的告別[A].魯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7]徐麟.魯迅:在言說與生存的邊緣[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