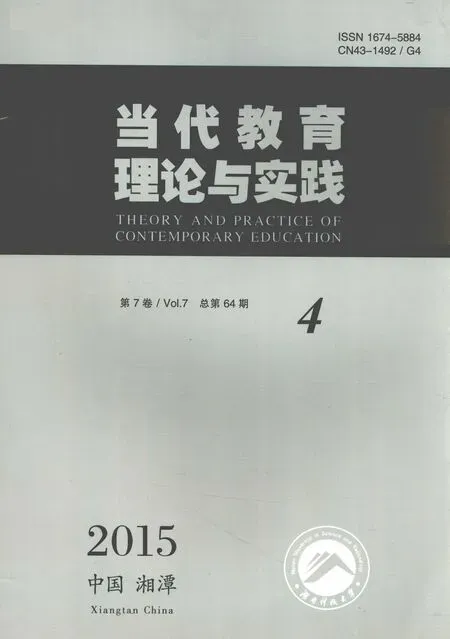從唐·德里羅“9·11”小說看美國女性形象
羅姣惠
(湖南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001年的“9·11 事件”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繼“珍珠港事件”之后遭受的最嚴重的襲擊。自此之后,文學領域出現了一系列以“9·11 事件”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在亞馬遜網絡書店中有一個“9·11”小說書單,該書單的創立者克雷格·范格拉斯提克將“9·11”小說定義為“所有涉及‘9·11’襲擊及美國之后的外交政策和社會等議題的小說”[1]。依此定義,可以肯定地說當代美國作家唐·德里羅顯然是一位“9·11”作家”[1]。本文結合文本細讀法,研究德里羅《人體藝術家》和《墜落的人》中典型女性人物的女性氣質,旨在通過分析這兩部小說中女主人公勞倫和麗昂的創傷生活經歷來表達她們在男性受到嚴重創傷的情況下,勇敢地面對現實生活,走出創傷,重建自我,承擔各方面的責任,追求生命的蛻變。
1 從人體藝術表演中走出創傷,實現救贖的勞倫
《人體藝術家》描述了一個平靜的早晨,人體藝術家勞倫和她的丈夫雷在廚房里烤著面包,心不在焉地交談著。早餐準備好后,兩人坐下來前言不搭后語地聊著。兩人之間的對話簡短、零碎。可第二天,勞倫就接到了雷突如其來的死訊,他在第一任妻子的曼哈頓公寓里開槍自殺。雷的自殺給勞倫帶來了沉重打擊,在參加完葬禮后,勞倫斷絕與外界的聯系,將自己封閉在他們原來租住的破舊小屋里。然而,一個來歷不明、幻影般的無名人物與她相伴。他甚至能像錄音機一樣惟妙惟肖地模仿勞倫和雷生前的所有談話,勞倫給他取名為塔特爾先生。勞倫把他留了下來,希望可以從他身上找回與雷共處時光的記憶。塔特爾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模仿激發了勞倫對過去的回憶,讓她沉浸在雷的自殺帶來的傷痛之中。但與此同時,塔特爾先生的重復模仿,使得勞倫慢慢理解創傷事件,并獲得頓悟。
丈夫的突然自殺給勞倫帶來痛苦、失落和困惑。她打電話給雷的第一任妻子伊莎貝拉,想從她那里了解一些有關自己未了解到的雷的情況。雷的性格有著雙重性,讓人感覺到很恐懼,“他一直都有自佩手槍。不管在哪兒他都帶著槍。”[2]在和伊莎貝拉通話之后,勞倫了解到了雷不為人知的一面。當雷的律師打來電話告訴勞倫說雷欠了許多債時,這個消息沒有讓她很驚訝。雷和勞倫一樣,都身為藝術家,但雷卻沒能像勞倫那樣從現實與藝術之間找到平衡點。最終,藝術沒有成為他的避難所。在與塔特爾的交流中,勞倫重拾創傷記憶,在呈現、剝離、審視的過程中,她逐步加深對丈夫的理解,生活的真實面目——殘酷、脆弱和破碎,慢慢地被展現出來。她意識到丈夫的死已是事實。她準備擺脫過去,以全新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她的那段表演“人體時間”反響熱烈,獲得了大量好評。她的這次表演通過敘述創傷來引起觀眾的共鳴。首先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一個古代日本女人,她出現在空蕩蕩的舞臺上,“按日本能劇的表演程式做著動作”[2]。接著是一個盛裝出行的婦人,“她拎著一個手提箱,看了一下腕上的表,揮手招呼出租車。”[2]最后是一個裸體的失語男人,“在表演持續了七十五分鐘之后……羸弱不堪又不能言語,卻拼命想告訴我們什么。”[2]當得知雷突然自殺的死訊,勞倫感到傷心,備受折磨。但是后來她選擇坦然面對雷的死亡、雷的過去,接受殘酷現實帶來的挑戰,讓生活充滿意義。最終,勞倫通過藝術獲得救贖,重建自我,勇敢地面對生活,實現了對真實自我的尋找和精神的回歸。
2 走出創傷,服務他人的麗昂
《墜落的人》中的女主人公麗昂沒有因為丈夫的墮落而墮落,她不僅擔當起自己家庭成員的責任,而且還負責對“9·11”受害者的無償心理疏導工作,勇敢地面對過去、走出創傷。
作為女兒,她秉承孝義,對母親百般照顧。父親的自殺對母親妮娜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因擔心母親的生活問題,麗昂把母親接到紐約來一起居住,盡可能地滿足母親的一些愿望。作為妻子,她賢惠聰敏,全心全意。當“9·11”發生后,基思卻毫不猶豫地帶著滿身的創傷,“一個滿身塵土、滿身碎片的男子”[3],回到已分居妻子的家中。母親妮娜強烈反對麗昂接受基思,但麗昂沒有絲毫猶豫,幫助他療傷、照顧他,并嘗試了解基思的思緒,試圖幫他恢復以前的形象。后來麗昂試圖談論起他們復婚的事,基思一口否認,“我們沒有什么可說的。”但麗昂并沒有因為基思說出的這些刺耳的話語而放棄復婚的打算。盡管她知道,把丈夫和男人放在一起完全是另外一個詞。在最后,麗昂也表明她的態度,為了家庭,他們兩個能夠避免摩擦,過著幸福的生活。作為監護人,麗昂同時扮演著“父親”和“母親”的角色。一方面,為了維持家庭生計,她必須努力工作;另一方面,為了兒子在父親缺席的情況下能夠健康成長,她時刻關注兒子的思想動態,盡管有時會因為工作、生活的壓力而勞累至極,但她從未放棄過。她會時常帶兒子去書店,享受涼爽和清凈,“他們瀏覽了科學、自然、國外旅行和文學圖書。”[3]也會時常關心兒子的學習狀態,“你在學校里學到的最好的東西是什么呢?”自從雙子塔倒塌后,兒子和他的小伙伴時常用望遠鏡觀察天空,看是否會有恐怖活動發生。為了盡可能減輕兒子的焦慮,麗昂及時了解兒童眼中的“比爾洛頓”,試圖引導兒子少說單音節詞語,和兒子調侃、開玩笑。“這可不是你在學校里學的哦。是我告訴你的哦。”[3]看似這樣的調侃并帶有一點戲謔的意味,實際上包含著母親對兒子深深的愛。在麗昂和基思的引導下,賈斯廷較少運用單音詞詞語,說話也變得順暢、流利。作為一名社會人,麗昂在關注自己家庭成員的同時,更是毫無怨言地做起社區義工工作。在面對一群阿爾茨海默病人的時候,麗昂扮演著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因為她清楚地知道“傾聽和講述現在是挽救他們的辦法”[3]。她經常組織那些患有老年癡呆癥的老人講述個人經歷,并將這些內容記錄下來,“通常,她和組員們討論,談一談世界上發生的事件和他們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分發印有格子的便簽紙和圓珠筆,讓他們寫作文。”[3]她尊重這些老人,與他們建立聯系并互相理解。在一次次的傾訴中,老人的焦慮得以釋放,精神獲得解脫。在傾聽時,那些老人同樣要求麗昂將她自己的經歷說出來。通過這些傾訴,麗昂也得到了釋放。
3 結語
在男性不負責任,甚至缺席的情況下,女性勇敢承擔起對個人、家庭、社會的責任。勞倫在經歷丈夫自殺的嚴重家庭創傷后,出現過創傷癥候——孤獨自閉、幻聽。但她沒有一蹶不振,而是通過人體藝術的表演獲得救贖,重建自我,勇敢地面對現實生活。麗昂在丈夫逃避家庭后,勇敢地擔當起家庭頂梁柱,對兒子進行了無微不至的照顧。同時,她充當老年癡呆癥人群的傾聽者,幫助他們走出創傷。總之,在這兩部小說中,德里羅展現了現代社會中女性的理想人格氣質。女主人公面對巨大的家庭創傷,敢于面對現實,實現自我救贖,追求生命的蛻變。
[1]張加生.從德里羅“9·11”小說看美國社會心理創傷[J].當代外國文學,2012(3):77-85.
[2]唐·德里羅.人體藝術家[M].文敏,譯.南京:浙江文藝出版社,2012.
[3]唐·德里羅.墜落的人[M].嚴忠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