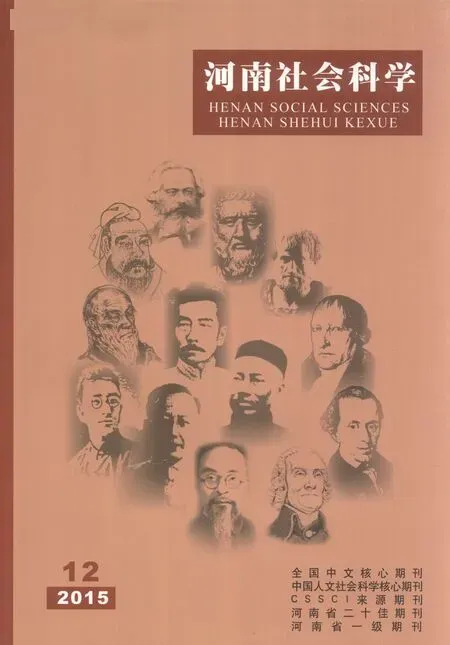美國民主理論演變探析
——從殖民地時期到改革時代
劉以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100872)
美國民主理論演變探析
——從殖民地時期到改革時代
劉以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100872)
美國的民主觀念和理論的演變都是基于當時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在不斷爭論與平衡之中形成的。從最初對直接民主的敵視情緒到對代表制民主的認可再到對精英式民主的推崇,美國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民主理論演變就是一個從理想到現實的轉變過程,是不同理論流派之間競爭后占優勢一方話語權的勝利。因此,當前我國民主理論研究應該借鑒的是美國民主理論為解釋政治制度而因時因地不斷被改造、平衡與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而非單純照搬其理論來試圖解決本國民主發展中遇到的困境。
美國;殖民地時期;改革時代;參與式民主;精英式民主
“民主”一詞自誕生以來就未淡出過人們的政治視野,與民主有關的理論研究已然占據了各個國家政治學領域的中心位置。然而直到19世紀,“民主”二字仍帶有貶義色彩,和它相連的往往是暴亂、無知、愚昧等字眼。但是,隨著時局的變遷,尤其是冷戰后蘇聯的解體和美國一超多強的世界新格局的形成,美國的競爭選舉式民主觀開始成為自由與民主的代名詞,美國式民主思想開始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二戰后獨立的國家中被不斷地推廣、借鑒和應用。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甚至斷言自由民主已然成為“歷史的終結”。美國的民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如何脫離早期的“暴民統治”觀念而逐漸被建構成今天為人們所熟悉和接受的自由民主觀的?美式競爭選舉式民主真的可以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衡量標桿嗎?想厘清在20世紀初期為何美國的民主觀念會發生180度轉變,就需要將民主理論的考察置于歷史的視野之中。因此本文選取美國二戰之前幾個較為重要的歷史時期作為美國民主理論演變的研究對象,希望厘清美國民主理論演變的脈絡,進而為破解我國民主化進程中國家的民主理論發展和民主道路選擇提供借鑒。
一、限制民主:殖民地時期的民主觀
追溯美國民主理論的發展脈絡,首先需要回顧英國殖民地時期對于美國建國后民主觀念的影響。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為美國民主觀念的形成和鞏固以及民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其他國家和地區所不能比擬的優越條件。這片沒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等級制度以及特權觀念的土地為民主的種子提供了充足的養分,也注定了美國的民主思想生而不同。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J.Boorstin)曾經指出,美國式的民主是一種“拼命追趕中形成的民主”,美國先民們基于一些主觀或者客觀的因素在新大陸不斷靠近、融合,相互之間在“追趕”中求同存異相互融合,這樣一種磨合的過程使得人們獲得了更多追求平等與自由的機會[1]。因此,美國成為理想的“民主的實驗室”。美國民主的發展與演進則如同一部“民主的實驗史”,站在英國業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借助平民化的社會和趨于同質性的文化背景,美國先民們逐步探索出了一種有別于英國的民主制度,以解決啟蒙時期遺存的大國無法推行民主的問題。
在成為英屬殖民地之前的美國大陸是沒有深厚歷史根基的,而它的民主政治發展則是建立在17世紀英國歷史發展基礎之上的。因此,厘清美國殖民地時期民主理論的流變,就需要回溯到17世紀英國人所普遍接受的混合制政體理論中去進行觀察和分析。英國的混合制政體觀是綜合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者優點而形成的,在當時被認為是能夠克服暴君專制、貴族寡頭制和直接民主的暴民統治的優良政體。這樣一種政體理論濫觴于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政治人本主義”政體理論,經由古羅馬政治思想家們改良和發展成為最初的共和主義理論。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其著作中就曾將共和政體闡述為混合制政體[2]。伴隨著文藝復興思潮傳入英國,混合制政體理論被彌爾頓等“新羅馬共和理論家”所繼承和發揚,隨后又被殖民地時期的北美大陸的精英們所接受。作為英國殖民地,北美有著與其宗主國相同的議會、法庭和陪審制度,這樣的制度安排維持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者的平衡,任何一方的擴張都不利于殖民地的統治,而這其中又以民主的過分擴張最為危險[3]。古典民主理論中純粹的直接民主觀在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受到了從殖民地精英到清教徒們的批判和否定,除了在某些基層治理中被實踐之外,直接民主并沒能得到更廣泛的運用。國家萌芽時期可能會有這種純粹的民主的生存空間,全部的權力可以集中于人民的手中,然而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已經度過了這樣一種幼年時期而進入了更為成熟的時期,作為政體意義上的直接民主理論也就沒有了生存的空間[4]。清教徒們感到大眾容易被居心不良或不理智的人所影響,進而無法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來理性地管理自身與社會[5]。因此,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民主理論發展更多的是停留在“規范性”民主概念的層面上,而在實踐上更多的則是對民主,尤其是直接民主的懷疑、拒斥和限制。
然而,在美國殖民地時期對直接民主這樣一種古典民主的拒斥并不意味著殖民地對民主思想的否定,而是要將民主限定在混合制政體的一個分支中,以此來確保民主的運作不會對英國當局的殖民統治造成威脅或妨害。總而言之,殖民地時期的美國還只是停留在限制民主過度擴張以防止危害宗主國統治的階段。在價值觀層面上,這一時期的民主理論已經開始顯露出精英式民主的傾向;而在實踐層面上,這一時期并沒有形成新的經驗性的民主理論,只是在英國代議制理論的基礎上通過下議院選舉出代表民意的議員來實現有限的民主。
二、有限的代表制:建國時期的民主理論
1775年4月19日,美國的列克星頓打響了獨立戰爭的第一槍。伴隨著獨立戰爭的勝利,美國社會也進入了一個制度、觀念和思想劇烈變革的時代,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激進派和保守派圍繞著國家政體的走向展開了持續的論爭。激進派希望建立人民可以直接控制和監督的政府,通過把權力交給人民,以實現最多數人民的最大福祉。他們認為,民主就應當意味著人民是掌握權力或者直接控制掌權者權力的人,只有這樣的政府對人民而言才是最安全的[6]。但是建國精英中的保守派們卻認為美國地域廣闊,社會結構復雜,民眾的政治素質和治國能力都是值得懷疑的,因而希望把人民的民主權力限制在間接的民主參與范圍之內,通過讓人民賦權于選舉出來的代表來形成一種可以篩選民意的精英制民主。
這些保守派和激進派的區別并不在于對“民主”的認同與否,因為保守派從未有過否定民主理念之意圖,他們所反對的僅是古典民主理論所宣揚的那種“由人民直接掌握并支配政府”的訴求。作為自由主義的堅定捍衛者,保守派們同樣以捍衛自由為名來抨擊激進派的民主觀念,認為當時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病和無序狀態證明了對民主過度訴求是對自由的濫用,而這種對自由的濫用走到盡頭就會導致民主的專制和人民的暴政[7]。最終,雙方在1787年憲法制定的爭論過程中逐漸達成了共識,占據多數的保守派建國精英們做出了讓步和妥協,他們將古典的共和理論與代表制民主思想相嫁接,巧妙地借用并改造了民主的話語,建構起一種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純粹民主”的新型民主理論,也即一種將人民控制并監督政府的權力讓渡給選舉出來的精英代表的“代表制民主”。這樣一種新型的民主理論實質上是借“人民主權”來賦予新政體以政治合法性,進而為占據強勢地位的保守派精英所支持的政體進行辯護的產物。
自此開始,美國的民主思想擺脫了其自誕生以來就受到的批評和譴責,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正面評價以及肯定,而民主制不再是一種受人唾棄的政體,它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一種值得為之奮斗的優良政體。但是相較于后一時期對“經驗性”民主理論較為系統的闡述和論證,殖民地時期和建國時期的自由民主理論更多的是為國家建構服務,民主理論也更多停留在“規范性”民主的層面上,并沒有形成具有較強操作性的實踐性理論體系。
三、改革時代的民主理論基礎
在經歷了南北戰爭和工業革命之后,美國進入了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高度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然而伴隨版圖的不斷擴張、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資源的不斷整合,諸如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和資本壟斷等問題日益困擾著美國政府和公民。經濟體制的急速發展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變革與之相匹配而導致的社會動蕩不安引發了“改革時代”的到來。“改革時代”指的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羅斯福新政時期。這段美國社會大轉型、大變革的時代被認為是“決定了20世紀美國政治基調的時期”[8]。在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中,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矛盾都開始暴露出來,國家迫切需要在混亂中建立新的秩序以遏制工業社會中最為明顯的不平等現象。社會的改革、政治的發展以及思想的演進都使得美國的民主理論在這一時期呈現出新的變化趨勢。
首先,進步主義運動中政治方面的改革加強了以總統行政權力為主的國家權力,總統權力的增強對這一時期的民主理論的發展方向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由于自由主義政治下的政府過于弱小而無法適應經濟高速發展后帶來的急速擴張的社會需求,導致了這一時期的美國面臨一系列政治經濟危機,而進步主義則是希望通過政治改革來加強政府權力以期實現國家發展社會穩定。19世紀末美國政府政治腐敗嚴重,上至聯邦政府下至許多州政府都為利益集團所操縱,民主制度下的一切問題都成了錢的問題[9]。進步主義者希望通過分化日益集中的社會權力來限制富人集團的特權;由于此時的憲法并未對總統權力做清晰的規定,所以經過威爾遜和羅斯福兩任總統的努力推動,進步主義運動對聯邦政府的權力結構做出了改革,加強了國家的行政干預和管理能力,到羅斯福當政時期,政府的權力中心已經從議會向總統傾斜,總統的行政權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因此,在經過一系列政治改革之后,受總統行政權力擴大以及對建立強大政府以穩定社會秩序的需求加強的影響,美國的三權制衡格局發生了變化,美國的自由民主政治也相應地較之前的民主傳統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精英制傾向逐漸明顯。美國的民主理論更多地開始服務于現實需求,出現了從規范性理論研究向經驗性民主理論研究轉變的傾向。
其次,改革時代的政治哲學發展同樣在研究方法層面對于美國民主理論的演進有深刻的影響。由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建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于19世紀后30年中在美國思想界盛行,而威廉·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mner)則是這一時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學界代表。薩姆納認同物競天擇理論并用生物進化論駁斥了人類的平等性,他強調應該推崇競爭以使強者淘汰弱者,如此一來就可以優化種族并且確保社會進步。雖然這樣一種進化論科學顯得對傳統民主理念抱有敵意,但卻和早期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觀念訴求不謀而合,深得壟斷資本家們的認可。
緊接著到來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眾多社會變革——工業化、城市化和新的產品技藝都明確地證明了科學亦是一種獲得權利的方式,而對于民主之深度和廣度的探討也在這一時期有了新的轉變。隨著新科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傳播,美國學界開始從社會達爾文主義中脫胎自己的理論,從薩姆納的斗爭是人類生存進步唯一法則的理論轉向一種完全從自然和經驗出發的自然主義,以此來避免薩姆納的反民主的生物決定論。受自然科學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歷史比較分析著重強調從研究對象中尋找共同法則并加以提煉形成概念來解釋和分析政治現象。到20世紀30年代之前,這種重視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在美國政治學研究中都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因此,從19世紀末至一戰后的這段時間內,基于政治哲學轉變而發生變化的美國民主理論開始向相對的、更為經驗性的研究方向發展。為了適應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而進行的民主理論調試也更加明顯,這一時期的學者們開始充當民主政體與理論的“闡釋者”和“清道夫”角色,在描述政治制度的同時也開始轉向對民主制度和理論的符合當下國情的解釋性分析。
四、轉型的關鍵動力:參與式民主與精英式民主之爭
在改革時代這一大背景之下,美國的民主理論演進的關鍵推動力來自當時最為重要的兩個民主理論流派——以杜威(John Dewey)為代表的參與式民主觀和以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為代表的精英式民主觀,二者關于民主的規范性以及實踐性的爭論直接改變了之后美國主流民主理論的走向。教育水平的提高、政治意識的增強都使得這一時期美國民眾的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和參與意識不斷增強,而由于新形勢下美國的社會經濟等方面發生的重大轉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這段時期傳統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紛紛將關注的重點從政治領域轉向社會改革領域。被譽為“偉大的進步主義知識分子”[10]的約翰·杜威則是其領軍人物。與通常所認為的民主是一個政治概念、是一種國家形式的觀點不同,通過比較傳統民主觀念的內涵,杜威強調了民主不僅僅是各種制度,更是一種倫理理念。在杜威看來,“民主的主旨是每一個成熟的人都必須參與制定規范人們共同生活價值的過程。所有被社會制度影響的人都必須在制度的產生和管理上有決策權”[11]。根據杜威的表述,作為一種高尚的道德信仰,民主是一種著眼于未來的生活方式,它不應該屬于某些階級或者利益集團而是應該屬于每一個參與民主的人。此外,民主作為一種道德理想可以起到呼吁人們建立分享大眾生活所必需的機會與資源的共同體的作用,并使人們的才能和權利能夠在參與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過程中得以實現。正是這種激進的民主理想和信仰,使得杜威的參與式民主觀同當時美國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相區別。
然而,隨著“鍍金時代”的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經濟大蕭條的沖擊,美國社會出現了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使得在這一時期盛行的科學自然主義學者們必須面對如何調和科學與民主之間關系的問題。在20世紀前30年中,科學自然主義都在致力于揭示傳統民主理論的缺陷以及建構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的民主理論。首先,科學自然主義拆除了民主理論的道德基礎,不承認在人法之上的高級法之存在。其次,科學自然主義拒斥了民主政府的三個基本原則:法治而非人治、人類行為的合理性以及平民政府的實踐性[12]。這也即是說,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開始認為民眾的行為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并不能夠保持理性,他們也不能夠肩負起傳統民主理論中的公民責任。這樣一種對傳統民主理論的解構使得杜威所呼吁的民主價值的培育和民主品格的塑造被以科學自然主義為指導原則的民主現實主義者所拋棄。此外,20世紀初行為主義的逐步盛行以及主流心理學與政治學的結合,都為民主現實主義者的主張提供了大量有利的理論素材。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民主現實主義者不再重視民主的價值訴求,而是突出民主的程序性和實踐性,并且強調政治精英而非國家公民才應該肩負起實行民主權利的責任。在這樣一種觀念導向下,民主被重新定義,民享型政府取代了民治型政府而被認為是符合時代需求的最優形式。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以李普曼為代表的堅持民主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們開始對杜威寬泛的民主理念進行抨擊。這一時期的大多數自由主義學者所希望建構的為當下政治服務的民主理論已然和杜威所提倡的理想民主政治相去甚遠了。民主現實主義者奪取了美國民主思想的控制權,迫使杜威本人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逐步走向邊緣化[11]。根據杜威表述,他希望通過教育來對公民的民主品格進行塑造,進而創造出一種全社會所共享的民主文化,雖然在杜威看來大眾的民主素質也難免會有缺陷卻可以通過培養和教育進行改善,而民主的提高則有賴于公民的素質。與杜威的觀點相左,以李普曼為代表的民主現實主義者認為,在現實中非理性的美國大眾對社會穩定而言是嚴重的隱患,他們的膚淺無知與易于被操縱使得他們缺少明辨公共事務和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這些民主現實主義者并不相信普通大眾有足夠的能力并且愿意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社會政治生活的決策中去,在他們看來只有具備專業知識素養和統治能力的精英群體才能手握決策權。因此,不具備貴族精神和素質的普通人缺乏進行統治的能力,他們不懂得“該選擇戰爭還是和平,武裝還是不武裝,干涉還是撤退,繼續戰斗還是談判”之類的重大問題[13]。這樣一來,參與式民主所希望實現的民主積極的、實質性的訴求被消極、程序性的教條式現實主義民主觀所取代,而這也為形成于二戰后的熊彼特式的程序性精英主義自由民主理論打下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這些民主現實主義者在民主政治實踐的過程中既希望掌握權力的精英能夠肩負起重大的責任,同時又不希望這些精英承受非理性大眾所帶來的壓力。因此,相互競爭的精英和利益集團的領袖成為決策的最終制定者,而普通公民則成為被動的決策承受者,充其量,公民擁有的是一個民享的政府,而不是民治的政府。
由此可見,以杜威為代表的參與式民主觀和以李普曼為代表的民主現實主義的分歧不僅體現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之上,而且還體現在對民主作為一種根本的價值的不同理解上。在杜威看來,自治是個人目的和群體目的之和諧交融,而對民主現實主義者而言,自治只是人類眾多需求之一,而且可能還是并非最重要的一種[14]。但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現實主義者對參與式民主理念的排斥不等于對民主價值的否定,而是主張認清民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通過從程序性入手來保證民主的實施。總而言之,面對新形勢下的內外壓力,民主現實主義理論在改革時期占據了壓倒性優勢,其所推崇的是一種從民治政府向民享政府轉變的精英式民主觀,希望把民主縮小到政治機器上來確保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自此之后民主開始從一種價值取向更多地向一種更富實踐性的制度安排轉型,民主理論的話語建構也更多地被實用主義和精英主義方法論所占據。
五、結論
縱觀美國從殖民地時期到一戰結束這一百多年的歷史,不難發現“民主”從未淡出人們的視野,相反,它作為一種最高的善的理想而不斷地被學者根據當時歷史情境下的政治、社會與觀念的改變而對其理論進行著解構和建構。從殖民地時期遏制民主與推崇混合制民主到20世紀初期的杜威激進的參與式民主被一戰結束后的現實主義精英式民主所取代,每一時期的主流民主觀念與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都是由于美國不同的歷史階段內不同民主理論和觀念相互競爭,最終主導話語權的一方獲勝的結果。正像某些政治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民主是一種本質上存在爭議的概念,是永遠不可能呈現中性的概念,永遠會在道德、政治的沖突中糾纏不清,民主政治從本質上講就是永遠不會完結的話語政治[15]。因此民主就像是一部反應靈敏的感應器,隨時探知外部世界的變化來不斷改變其內部構造,以此來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新環境并推動社會發展和穩定。杜威在其著作中就曾深刻到位地指出:“每一代人必須自己再造一遍民主,認識到民主的本質與精髓乃是某種不能從一個人或一代人傳給另一個人或另一代人的東西,而必須根據社會生活的需要、問題與條件進行構建。”[16]因此,一百多年前的主流民主理論和美國現在所推崇的以自由民主作為價值導向的競爭選舉式民主理論既一脈相承又各有不同,但是民主理論逐步走下最高價值理想的神壇,在經過不同歷史時期的改造、“包裝”和調試之后變得越來越趨于程序化和實際化的趨勢卻是在理論的演進過程當中趨于明顯。
總而言之,將美國民主理論放置于歷史的脈絡中進行研究后不難發現,在美國這樣一塊宜于民主生長的沃土中培育起來的民主理論是逐步將價值與事實相分離之后的產物,是為了適應特殊社會政治與觀念環境所建構起來的產物,并不具有普遍適應性。因此,處于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對于美國民主的借鑒應更多參考其因時因地不斷改造、平衡與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而非單純照搬其理論來試圖解決本國民主化進程中遇到的困境。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而言,我們需要堅持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從自己的歷史脈絡中探尋和挖掘推動民主理論發展的動力,學習和借鑒美國民主理論的建構能力和符合當下國情的民主理論解釋能力,而不是簡單用美式民主二分法來衡量我國民主理論建設的水平。當前我國民主理論發展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根植于歷史之中的具有解釋力和生命力的理論思想,只有根據我國國情提煉出來的民主理論才能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應有的貢獻。
[1]Daniel J.Boorstin.The Americans: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
[2]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卷)[M].鄧正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Jack P.Greene ed..Gres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M].New York:Harper&Row,1970.
[4]李劍鳴.美國革命時期民主概念的演變[J].歷史研究,2007,(1):131—158.
[5]RichardLBush.FromPuritantoYankee:Character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Connecticut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6]The Interest of America,Letter II[EB/OL].http:// infoweb.newsbank.com.
[7]Hamilton,Madison,Jay.The Federalist Papers[M]. London:Penguin Classics,1987.
[8]吳春華.當代西方行政理論[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9]唐書明.從自由主義到國家主義——美國進步主義時期的政治變動[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114—118.
[10]Robert Morse Crunden.Ministers of Reform:The Progressives’Achievement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1889—1920)[M].Reprint: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
[11]羅伯特·威斯布魯克.杜威與美國民主[M].王紅欣,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2]Edward A.Purcell,Jr.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M].Lexington:TheUniversityPressof Kentucky,1973.
[13]Walter Lippmann.The Public Philosophy[M].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9.
[14]徐賁.民主社群和公共知識分子:五十年后說杜威[J].開放時代,2002,(4):65—72.
[15]WilliamE.Connolly.TheTermsofPolitical Discours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83.
[16]約翰·杜威.新舊個人主義——杜威文選[M].孫有中,藍克林,裴雯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D5
A
1007-905X(2015)12-0045-05
2015-09-20
劉以沛,女,河南鄭州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