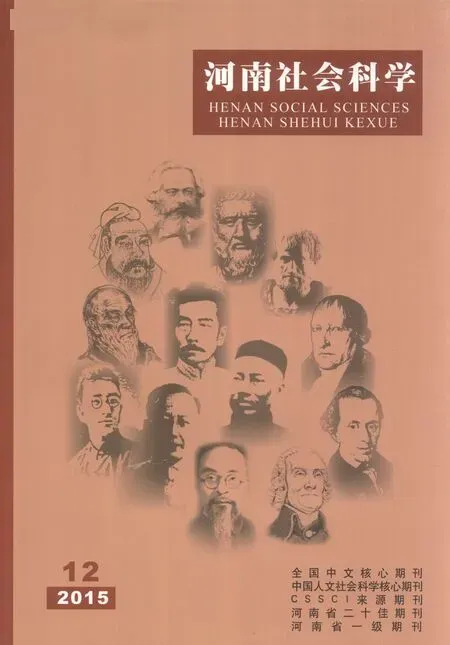論儒家思想中的價值信仰及其實踐性
吳 云
(阜陽師范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2)
現代性“道德謀劃”的失敗,使得社會“倫理共契”碎片化,道德觀念之一致性的喪失,成為最為深刻和危險的現代性危機。究其原因:其一,改革開放經濟加速轉型而導致的經濟理性,其巨大的宰制作用,使得人的意義世界消退。其二,單子化的單一個體所組成的現代社會失去了可能整合的社會認可,社會階層、貧富差距、生活方式、態度意識的“碎片化”便成為不可避免的現代性后果。其三,道德義務論者片面強調道德的內在動機性,忽視“道德心理”的相互性,“正義動機的條件性和不穩定性在無法律保障其相互性的”[1]環境下顯現出來。這樣在道德發生的客觀外部機緣和道德主體的內部機緣的雙重層面產生了危機,不同的文化共同體中產生了“共鳴”——信仰危機、道德信仰危機。
一、儒家文化形態與價值信仰
(一)儒家文化的理性化形態
馬克斯·韋伯通過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對基督教神學思想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改造,從而生產出“新教倫理”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精神基礎。而中國文化的理性化進程,它的“價值理性的建立過程,是與對天神信仰的逐漸淡化和對人間性的文化和價值的關注增長聯系在一起的。它是由夏以前的巫覡文化發展為祭祀文化,又由祭祀文化的殷商高峰而發展為周代的禮樂文化,才最終產生形成的”[2]。漫長的演變,歷史的積淀,為儒家文化的產生賦予了濃厚的理性色彩。其邏輯推理縝密,思辨具體而不抽象;理論建構完整,系統而不華麗;具有實踐的和實用的品格。李澤厚先生將之歸納為“實用理性”:一方面同思辨的思維模式形成對照;另一方面凸顯其倫理實踐。梁漱溟先生指出,儒家文化“沒有什么教條給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條而已。除了信賴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賴其他人”;使得“中國自有孔子以來,便受其影響,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3]。因而,不管文化形態上的“以道德代宗教”,或是在民眾生活中體現的“實用理性”,都體現出儒家文化的理性化。
(二)儒家文化的超越性特征
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根源于道德理論的前提預設和德性生成的修養功夫。人性論是儒家道德理論的出發點,從探究人性之性入手,孟子認為是“人皆有之”“我固有之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對于孟子而言,人性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因此,孔孟極為強調人之性分所蘊含之仁義的絕對性、普遍性、無條件,認為此仁義作為一無條件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標準,其價值在貧富、貴賤、榮譽等一切外在的利害關系之上,甚至在人的生命之上。其終極性和超越性體現為人心的內在超越性。這種絕對價值,在宋明理學家那里進一步升格,客觀化為“天理”“天道”,而通過成圣和超越自我的精神修養來體現這種絕對價值——“天道”“天理”。這樣,“天理”“天道”為道德提供了本體論的根據,成為價值信仰的終極依據。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先生認為儒者之“天”與“天道”乃是具有形而上的精神、生命的絕對實在。天道既超越又內在,具有主客不二的特性,是一種和合的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4]。這就進一步把天與人、超越世界與倫理世界溝通了起來,道德便直接被賦予了超越時空的絕對性和至上的權威性,而成為康德式的道德律,價值信仰的終極理由仍被留在了現世。但是,從本源意義上又不同于西方宗教信仰,需要借助一中介——“上帝”來認識、體驗和實現終極關懷,因而西方的宗教信仰成于天人分離。儒家文化的價值信仰成熟于天人合一,在儒學“天人合一”的宇宙倫理模式中,理想人格既是天人關系的中樞,又是天人關系的化身。因此,儒家文化中的“價值信仰”的完成,落實在現實理想人格的塑造上。
(三)儒者價值信仰的建立
有的學者認為,儒學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在“士”階層之間,發揮的作用是一種準宗教的作用。依此視界,從儒學的歷史功用來看,就是對個體人生價值、生命意義確立的終極根據的尋證,并有超越的形上的關懷。這一方面是來自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為人之道,以社會內在的文化秩序和價值原則化成天下,使人們有了堅定的生活信仰;另一方面,儒者自身將生命與理想、信念融成一體,其人文理想和價值世界與敬天、法祖,上帝、皇天崇拜,對天與天命、天道的敬畏、信仰,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救民于水火”“即世間即出世”的神圣感、使命感、責任感、擔當精神、憂患意識和力行實踐的行為方式,特別是信仰上的終極理想,與宗教徒無異。但儒者又生活在倫常之中,不離日用常行,在凡痛中體驗生命、體驗天道,達到高明之境[4]。而這一過程,即是儒家謂之的“修道”。
儒家修道之功夫,無論是從方法、過程還是從歸宿來看,都是在客觀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儒者的價值信仰便具有了鮮明的客觀實踐性特征。這是就價值信仰發生的客觀的現世社會領域來講的,內在的則要從修道之途徑、發生機制等方面探討。
二、儒家價值信仰的實踐性
(一)修道:價值信仰之精神層面的確立
儒家從孔孟的“仁”“性”學說到宋明“天理”之說,沿襲了“性與天道通而為一”的學理架構。孔孟所強調的人之性分所蘊含之仁義以及人之踐行仁義具有絕對性、普通性、無條件性的主張,后來為二程、朱熹等宋明理學家所繼承和發揚光大(文碧方,2005)。因為,孔孟認為只需“直下肯定”人性就能具有仁義,即謂“此天之所與我者”,人性通過直觀即達天道。這種簡陋的體道學說到宋明時期得到完善。尤其是朱陸等人解決了問題的關鍵——“通”以及“得道”。
在“性”與“天道”通的方式上,宋明儒學采取了一種先驗性的理解形態(文碧方,2005)。在這種先驗性的理解進路中,他們不僅認為性與天道相貫通,而且視性與天道為一。而二者的互證存在(天道、人道的相互呈現)關系,使得個體以人道體現天道的方式得道。這就突破了“得道體驗的個體性”之局限,而以“社會性、普遍性”的天道為歸宿,因而也是離不開社會實踐的。
而由認同此理到實踐此理,則是一個向外擴充的過程,也是一個向下落實的過程,其終點是道成肉身式的踐行,它不只是主觀的精神境界問題,更是客觀的道體流行,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的現實歸宿處,并且,“只有當人親身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只有當人用全部的生命領悟到了它的可信、可愛、可敬和可畏,并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托付于它,與它融為一體,才算真正得道”[5]。因此,具有神圣性、絕對性、普遍性的天道(道德律)又在于人自己去彰顯、去遵從和履行。正是在這種自主的行動中,個體的道德品質得以提升,道德理想得以建立,道德人格也在人文實踐中不斷完整和超越。這一過程具體在行道中得以落實。
(二)行道:價值信仰之經驗層面的踐行
儒家的修道對個體價值信仰的作用,實際上就是從主體內在出發認同“天道”這一人生價值、存在意義的終極依據,從而達到信仰,建立價值信仰。但若停留在這個層面,儒學就無異于佛老之學,其文化氣質也就轉化為思辨模式。然而,儒家在確立天道之時,其中便體現了“人的社會生存的普遍價值”。從行道方面來看,修道又是行道的準備。從修道到行道,又是儒家文化的人文實踐的理性化特征使然,使人在現世倫常生活中踐行“道”。因而,儒者真正認同了“道”,建立了價值信仰,就必然在現世“人道”生活中體現出來。即是要在滿足個體生命之安身立命需要的同時,喚醒個體自我的社會擔當意識,自覺投入改造現實社會的偉大實踐中去。
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儒家行道方式和堅持的原則也是不同的。在早期儒家的政治實踐中,儒者以“三代之治”為理想,堅守道義,甚至以生命捍道。早期儒者的政治理想主義的特征,試圖將政治秩序納入文化秩序的治理之道。然而結果多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結果。但儒者堅定的信仰并未使其否定行道的社會價值和意義,進而選擇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盡心上》),甚至“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盡心上》)的豪邁行徑。
但是,禮樂崩壞的事實至少說明了社會客觀上已步入一個并非僅以文化秩序即可規范整合的新階段。因此,漢初,漢儒援法入儒,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學法家化,扭轉了儒家政治實踐的被動局面。漢儒對孔孟學說有一定程度上的損改,但這種改變更多的是在實踐層面上,是修道所做的功夫的改造,而非道、修道的改變,具體在治民和教民兩個方面實踐之。
宋明之際,隨著封建專制主權的鞏固,皇權與綱紀、皇帝之私欲與社會之公義之間的矛盾尖銳。于是朱熹像所有的儒者一樣,只有一條路可走,即改造現有的皇帝以阻止其沿著非理性的方向獨斷專行,這便是“格君心之非”。朱熹堅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的儒家道義論立場,寧可死守山中。由此,不難看到,只有建立虔誠的信仰,普遍價值才能成為決定自我生命之意義的唯一絕對的標準,永遠處于未決狀態的生命才能獲得一個安身立命之地;而只有立定道義立場,現實的價值抉擇才能排除一切非理性因素的干擾,從而“凡其所行無一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文集》三六,《答陣同甫》八),并由此通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處世之路[5]。
三、儒家價值信仰的資源性意義及不足
(一)儒家價值信仰的資源借鏡
1.儒家價值信仰對個體的道德品質提升、道德人格完善以及道德理想建立的有效作用機制,尤其是由內而外的道德修養功夫應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澄清,融入公民道德人格培養和道德理想的建立中,為現代公民重塑安身立命之所。
2.儒者強烈的道義擔當、社會責任意識和對國家社會的義務感,在面對社會、國家的道義衰落時能挺身而出,堅守道義、公義,不失志,始終保持崇高的道德責任。社會主義公民的法權身份在《憲法》中得以保障,而在現實生活更應激發出其主人公的崇高道義感。
3.儒家價值信仰的修道、行道功夫,使修身和政事二者關聯起來,使修身成為政事的必要準備,政事成為修身的功夫。在不同的階段,二者互為體用,從而使儒者的道德人格與政治人格相統一。在社會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現代化社會,社會公民的社會角色和個體自我認同間的張力使公民人格分裂,成為現代社會對公民“異化”的另一個事實。儒家的價值信仰為彌合個體人格分裂提供了價值基礎。
(二)儒家價值信仰的不足與克服
當然,儒家價值信仰的不足方面也是致命的:一是道德教化的主體定位問題。有人指出儒家文化中的精英倫理定位,其道德主體是定位了當時社會的士階層或者是士大夫階層的,而根本上不是對普遍大眾的道德關懷。這對現代民主法治下的公民道德建設無疑是有害的。二是儒家的道德教化即修道、行道,而修道的出發點是人性,終極依據是精神的;而行道的政事活動也是“事君以道,不合則去”的原則,而即使有道義的擔當也只是改造統治者違背仁義的非理性行為——“格君心之非”,即便一個皇權代替另一個皇權,儒者這種道義擔當仍然不變。
因而,這種不具有社會改造力和無法創造新生活秩序的精神形態,在社會轉型時期無疑無法開出新的意義系統。
在信仰理想和秩序一旦發生某種松動的時候,重塑信仰、堅定理想和整飭秩序,對文化本身的發掘是最直接的思想武器。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中也指出:“一個社會每當發現自己處于危機之中,就會本能地轉眼回顧它的起源并從那里找癥結。”因而,以傳統文化中優秀道德資源重整社會文化價值基礎克服信仰危機、道德信仰危機,就尤為必要和緊要。同時,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人們可資利用的道德資源和走出困境的方式又是不同的。
實際上,現代儒家一直致力恢復儒家義理對公共倫理秩序的治權,它有兩個方面:一是重新整合禮與樂,這在梁漱溟的“鄉建運動”中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是從熊十力到牟宗三的當代“新儒學”的心學復興(劉小楓,1998)。前者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一方向未能成功;后者因缺乏基層社會群體的關系,無法推展其道德意識的社會功能。因而,傳統儒家優秀道德資源的發掘,首先要在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文化背景下進行;其次要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民為主體定位,反對傳統倫理的精英定位,以培養和實現現代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為指向。
(本文為安徽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項目號為:AHSK11-12D229;安徽省教育科學規劃項目,項目編號:JG12149)
[1]慈繼偉.正義的兩面[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2]陳來.古代宗教和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3]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郭齊勇.儒學: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態[J].文史哲,1998,(3):36—38.
[5]趙峰.朱熹的終極關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