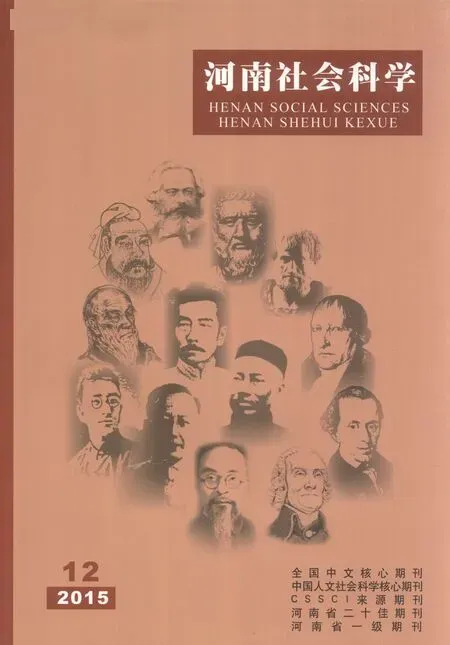《論語·學而》篇首章新釋
盧夢雨
(中央財經大學 文化與傳媒學院,北京 102206)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
現行的初中語文課本對其中的一些詞語是這樣注釋的:“習:溫習,復習。說:同‘悅’,愉悅。朋:朋友。君子:指有道德有修養的人。”這三句話合起來,即譯為:學習并且能經常地溫習知識,不是很高興的事嗎?有朋友從遠方來了,不是很高興的事嗎?別人一時不理解自己,但是自己不生氣,不也是君子的行為嗎?
在大學教育中,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做了如下翻譯:
孔子說:“學了,然后按一定的時間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處來,不也快樂嗎?人家不了解我,我卻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1]
應當說,上述的兩種理解和翻譯方式,都源于南宋朱熹的《論語集注》。朱熹集中闡述了“學為君子”的義理。朱氏注曰: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悅,同。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2]
其實孔子的這三句話本來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朱熹的“誤讀”使其語義產生整體偏離,變成了枯燥干癟的道德訓示,在語言的深層邏輯上變得相互矛盾,無法自圓其說。我們稍加深入,便可以發現這些解釋的乖謬之處。
釋“時”為“時時”或“按一定的時間”、釋“習”為“溫習、復習”。心理學告訴我們,長時間地重復學習同一材料會導致注意力的下降和學習興趣的減少,那么“喜悅”從何而來?
釋“朋”為“朋友”或“志同道合的人”。“朋”自“遠方”來,則“樂”。那么,近處之“朋”來訪,又當如何?難道心情的愉悅程度會隨著空間距離的遠近發生變化?
釋“人”為“別人”或“人家”。一個素昧平生的人不“了解”自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知者不為怪”是人之常情,為此而“不慍”,那對“君子”的道德要求豈不太低?
那么,到底該怎么理解呢?
一、釋“習”與“時”
歷代注家對“習”字的解釋往往從“學”字著手。他們往往先對“學”的內容加以界定,再解釋“習”字。
漢代注家認為“學”的內容是書面知識,“學”是從書本上求得知識。
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悅)懌。[3]
從宋代朱熹的文集和語錄來看,他也傾向于“學”即“讀書”這一觀點,把“學”的內容界定為書面知識。因此,漢、宋兩代學者釋“習”時,都與書面知識的學習方式聯系起來,予以解釋。
清代一些學者開始認識到,“學”的內容不應僅僅限于書面知識。孔子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射”“御”等操作性技能,自然也屬于孔門弟子的學習內容,靠“誦習”“溫習”之類的手段,根本無法掌握這些實踐性很強的內容。可見,“習”字在實踐層面上的意義不容忽視。顏元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單純靠口耳相授,根本無法掌握“六藝”,“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4],“某謂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4]。在指導門生時,他強調:“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言語、文字上著力。孔子之書名論語,試觀門人所記,卻句句是行。”[4]很明顯,顏元認為“習”即是把理論知識付諸自身實踐的一種行為。
漢宋注家在解釋“學而時習之”這句話時,有個潛在的邏輯順序,即把“時”與“習”連在一起理解,確定“習”義之后,再對“時”字做出解釋。這種邏輯次序在朱熹的《論語集注》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先說“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這一句,然后才是“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因此,將“習”解釋為“溫習,復習”后,那么以“時時”釋“時”,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時”在《論語》大致有“時令”“時刻”“時機”“機會”四義。我們可以根據“時”字出現的語境,確定其具體意義。
“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四時行焉”(《論語·陽貨》);“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在這三句中,“時”為“時令”之義。“不時,不食。”(《論語·鄉黨》);“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論語·季氏》)。在這兩句中,“時”指某一特定的“時刻”。無論“時令”,還是“時刻”,都與宇宙運行,即“天”相關,即按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行事。楊伯峻把“時”解為“按一定的時間”,正是從“時令”“時刻”這一層意思出發的。在《論語譯注》中,他還為此專門加注說明:
“時”字在周秦時候若作副詞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時入山林”的“以時”,“在一定的時候”或者“在適當的時候”的意思。王肅的“論語注”正是這樣解釋的。朱熹的《論語集注》把它解為“時常”,是用后代的語義解釋古書。[1]
楊伯峻認為,朱熹將“時”解釋為“時時”是錯誤的。因此,他用自然規律上的“時令”“時刻”解釋“時”。不過,很遺憾,楊伯峻忽略了“時”字在世間人事變化這一層面上的意義。
孔子在《論語》中經常強調,說話做事要注意把握“時機”,這也是“時”。“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論語·憲問》)。孔子在“時機合適的時候”才會說話,所以不會惹人討厭。“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論語·鄉黨》)雉雞對誘餌嗅而不食,謹慎地避開潛在危險,所以孔子(或子路)才會由衷地感喟:“(它)很善于把握時機啊!”“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涂”(《論語·陽貨》)。陽貨想見孔子,孔子不見,他就留下禮物——“豚”,迫使孔子按照當時的禮節回拜他。孔子不愿見他又不愿失禮,所以就“趁其不在家的時候”去拜訪陽貨。這三句中的“時”,即是對恰當時機的合理把握,可解為“時機”或“趁機”。
綜上所述,“習”字可釋為“使用”,“時”可釋為“有機會”。如此,“學而時習之”的意思也就很明白了,即“學到了本領,而又有機會去使用”之意。這不但符合孔子“學以致用”的一貫主張,而且也符合正常的心理情感發生規律。學有所成,而又獲得施展才能的機會,自然也就“不亦說乎”了。
二、釋“朋”
在《論語》中,“朋友”八見,“友”字十八見。從出現的具體語境分析,它們存在著意義重疊現象,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論語·學而》)“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子張》)“朋”字則比較特殊,除了見于“朋友”八次之外,僅在“有朋自遠方來”這一句中單獨出現過一次。因此,我們無法借助《論語》的語料來考證它與“友”和“朋友”之間也存在著意義重疊現象,可以直接翻譯為“朋友”。
漢代人認為,“朋”與“友”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存在著比較嚴格的社會屬性區分。鄭玄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5]包咸曰:“同門曰朋。”[6]皇侃綜合了他們的觀點,并做了進一步的闡釋:“同處師門曰朋,共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6]依據漢注,“朋”字指代的是一種在學習知識過程中建立的社會關系,即“同師”或“同門”。而在《論語》中,需要單獨表示“同師”或“同門”這種社會關系時,都是使用“門人”一詞。如: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門人不敬子路。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
很明顯,將《論語》中的“朋”字釋為“同師”或“同門”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楊伯峻在《論語譯注》把“朋”翻譯為“志同道合的人”。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朋”字出現的頻率很高,學界普遍認為,“朋”是商周貨幣“貝”的計量單位。此義在《詩》和《易》中也有運用,如“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詩經·菁菁者莪》);“或益之十朋之龜”(《易·損》)。正因為“朋”由同類的“貝”所構成,因此可以用來表示“數量較多的同一類事物”,便衍生出“群”“成群”之義。因此,“朋”字之義與“類”“群”有著密切的關系。“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凡是有共同目的或相同性質的“人群”或“物類”,皆可以稱為“朋”。在《詩》《易》《尚書》等典籍中廣泛存在,如:
《詩·豳風·七月》:“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易·坤·彖》:“‘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尚書·益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朱熹也以“類”“群”之義來解釋“朋”字,“朋,同類也”[2]。
在春秋時代及其以前,“朋”字的使用有兩種情況,或單用,或與“友”字組成復義詞。不過,“朋”字在戰國時期的運用,則出現了新變化。“朋”字開始與“黨”字組合成詞,并在意義上趨同。“朋黨”一詞大量出現在文獻中,如:
《荀子·臣道》:“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韓非子·有度》:“交眾、輿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
《韓非子·飾邪》:“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
《戰國策·趙策二》:“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
“鳳飛,群鳥從以萬數”的景象恰恰與春秋時代大量出現的“學團”組織,特別是“孔子學團”非常類似。孔子自詡為“鳳鳥”,那么“三千弟子”也就是“從以萬數”的“群鳥”了。因此,“有朋自遠方來”,描述的便是大批學生從各地趕來向孔子求教的景象,這與《史記·孔子世家》中“弟子彌眾,至自遠方”的描述也相吻合。
三、釋“人”
“人”字在《論語》中出現頻率高,意義指向極為廣泛。假如我們將“人不知而不慍”中的“人”泛泛地理解為“別人”,就必將使孔子陷入一種不能自圓其說的道德陷阱。在《論語》中,孔子以“君子”“小人”之辨來建構他的道德體系,“君子”是他道德理想具體化的縮影。因此,他對心目中的“君子”提出了比較高的道德要求,絕不輕許別人以“君子”之名。假如僅僅達到“別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卻不生氣”的要求,就可以成為“君子”,那對“君子”的道德要求也太低了!
在《論語新探》一書中,從語料的具體分析看出,春秋時代的“人”享有很多政治權利,可以“使民”“教民”“誨人”“立人”“舉賢”,這些權利并非平民所能擁有。因此,春秋時代的“人”多為貴族或官吏,指士大夫以上各階層的人。
春秋時代的貴族或官吏負有向上級舉薦人才的義務。仲弓擔任季氏宰后,詢問孔子如何舉薦人才。欲“舉”人必先“知”人,所以孔子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季氏》)故被“知”往往意味著可以出仕。
孔子周游列國幾十載,卻終究未獲一“知”。“不知”孔子之“人”,不就是那些“國王、諸侯”嗎?“學以致用”方能快樂,終生未獲一用胸中怎能沒有牢騷?可是面對政治理想落空的巨大人生痛苦,孔子對“不知”之“人”卻“不慍”,這是一種極高的道德修養。
四、結論
對“習”“時”“朋”“人”做出新的解釋后,可以發現“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三句話之間有著嚴密的邏輯關系,是孔子晚年對平生遭際的自我感喟。試譯如下:
學習、掌握了(治國之術)后,又有機會去使用,不也讓人快樂嗎?大批學生從四面八方趕來(向我求學),不也讓人高興嗎?那些國君、諸侯不了解我、不重用我,我卻并不因此怨怒,這難道不是君子的德行么?
楊伯峻、錢穆、南懷謹三人都認為,《論語》由孔門弟子精心編纂而成,各章之間有一定的組織脈絡,章節下的各條語錄互相聯系、密不可分。孔門弟子將“學而”章置于篇首的目的,就是要在《論語》開篇,用孔子自己的話對他做一個總結,而且要符合他們的共識。
孔子一生,仕途坎坷。周游列國,處處遭拒;晚年回魯,亦不見用。傳統文化對人的評價往往著眼于“立德、立言、立功”,孔子的自我評價即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聯成一個整體,循環往復、頓挫有致,各句之間有著嚴密的邏輯遞進關系:第一句正話反說,拿自身境遇解嘲,著眼于“立功”;第二句用比喻的方式委婉肯定自己的文化業績,著眼于“立言”;第三句含蓄地指出終生不能出仕的原因并不在于自身,但自己卻不怨天、不尤人,能夠坦然接受這種“天命”,著眼于“立德”。放眼《論語》,恐怕也只有這三句話,能夠如此簡潔、周到、準確地概括孔子生平。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1985.
[3]何晏.論語集解[A].新編諸子集成(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4.
[4]顏元.顏元集[M].王星賢,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5]周禮注疏[A].十三經注疏(卷十)[C].
[6]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一)[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