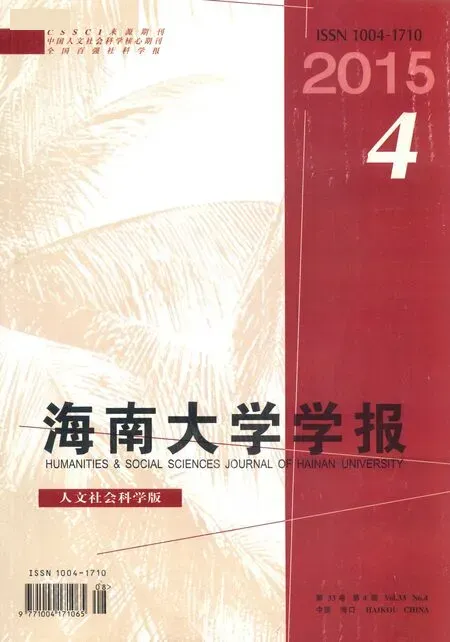無法忽視的“傳統”
——“延安魯藝”辦學經驗對共和國“作家培養體制”之啟示
畢紅霞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300071)
無法忽視的“傳統”
——“延安魯藝”辦學經驗對共和國“作家培養體制”之啟示
畢紅霞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300071)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建立了專門的機構來培養作家,即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后改名為“文學講習所”和“魯迅文學院”,延續至今。這套培養體制與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以下簡稱“延安魯藝”)存在很大關聯。它們不僅共同分享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而且在制度建設和具體培養經驗方面都存在很多共通之處。在如何處理政治和藝術的關系問題上,“延安魯藝”的辦學經驗給新中國的“作家培養體制”提供了啟示。
延安魯藝;作家培養;魯迅文學院;政治;文學教育
一、“作家培養”:《講話》精神的傳承
1949年10月24日,由“全國文協”創作部草擬了《創辦文學院建議書》上報文化部。《建議書》明確指出文學院要培養作家,而且要幫助兩類青年文學工作者進行提高的工作:一類是已有豐富實際生活經驗,但還沒有寫出好作品的;另一類就是已經寫出一些作品,但是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還比較低的。文學院要幫助他們提高,從政治和藝術上組織他們系統學習,同時還可以組織他們從事集體創作。總之,要在黨和政府有計劃的領導下培養文學人才。
這樣的思路顯然是對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精神的直接繼承。成立專門的文學院,“在黨和政府有計劃的領導下培養文學人才”,與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對“新社會—新文化”的構想及實踐緊密相關。20世紀40年代初期,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①收入《毛澤東選集》改為《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不僅確認了中共文化的現代轉型繼承者和領導者的地位,而且通過鑒別和選擇,指明了所要斷裂和延續的各種傳統,重新規劃文化秩序,實現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圖景。在此基礎上,《講話》進一步完成了對于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的設想。
作家歐陽山說他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實際上是帶著問題去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一方面把文學活動跟中國革命活動聯系起來,一方面又把文學創作跟人民群眾隔離開來,那么這個目的怎么能夠達到呢?”他認為不僅自己困惑,其他作家也認為這是“一個長期沒有解決的中國文學藝術界的共同的根本問題。”[1]而毛澤東《講話》的開頭部分正是論述此問題的: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2]804
習慣“自由”的延安文化人,起初并沒有意識到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以及共產黨即將進行的文藝政策的調整。舒群擔任《解放日報》文藝欄主編,對于當時要召開的座談會并不重視,毛澤東作《結論》那天晚上,還因為酒喝多了忘記通知黎辛去參加座談會[3]。作家知識分子顯然把它看作同以前一樣的文藝討論會,“參加這次盛會的文藝界代表約100人。大家發言踴躍,爭論得十分熱烈。會一天沒有開完,于是又用了兩個星期日接著發言”[4]。蕭軍甚至還在座談會上放肆“發炮”,號稱作家需要“自由”,作家是“獨立”的,胡喬木不同意蕭軍的意見,忍不住起來反駁他,說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雙方論爭得很激烈②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頁。。
與此相反,毛澤東實際上對座談會的召開作了精心的準備,1942年5月12日毛澤東指示《解放日報》,在其副刊版開辟一個《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專欄,發表馬克思主義文藝經典著作和文藝家對文藝工作的意見。5月14日,《解放日報》在第四版頭條位置刊登《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專欄的按語是從毛澤東處送來的,全文是:“最近由毛澤東、凱豐兩同志主持所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是一件大事,尤其對于關心當前文藝運動諸問題的讀者,本版決定將與此有關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見,擇要續刊于此,以供參考與討論”③編者按,參見黎辛:《關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講話〉的寫作、發表和參加會議的人》,《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2期。。
隨后的一個月,在《解放日報》上陸續刊登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的經典著作。1942年5月20日,《解放日報》重新刊發魯迅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并加編者按語:“這是1930年3月20日魯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其中對于文藝戰線的任務,都是說得很正確的,至今完全有用。今特重載于此,以供同志們研究。”這則按語同樣是毛澤東處送來的。雖然對“五四”新文學評價并不高,但毛澤東對魯迅十分推崇,《講話》甚至將其抬高到文化“首領”的地位,宣稱“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④正式發表時改為“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見《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頁。。在座談會上,“當談到魯迅‘總司令’領導文化軍隊時,全場響起了掌聲和笑聲。”[5]毛澤東的這一說法獲得了延安文化人的廣泛認同。恰恰是列寧和魯迅,構成《講話》的權威性,賦予了毛澤東文化意識形態和文藝思想的合法性。
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⑤20世紀80年代的譯法改為《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不同尋常之處在于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理論,從一般的理念推進到了具體的文藝體制上。列寧提出了“黨的文學”這一概念,強調“文學事業應該成為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一個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全體覺悟的先鋒隊使之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學事業應該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底工作組成部分”[6]。與馬克思恩格斯同時注重文學的政治和藝術價值不同,列寧更關心“文藝”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的價值,將“文學”打造成革命機器的“螺絲釘”,而在這一點上無疑符合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對于文藝的建構和要求,實際上“‘黨的文學’是文藝整風后延安文學觀念或后期延安文學觀念的核心部分,也是其至為關鍵的存在形態”[7]。可以說,《講話》其基本的話語和理論合法性都來源于列寧“黨的文學”這一論述。
在《講話》中,雖然沒有涉及到具體的“作家培養”問題,但在“結論”中,《講話》所要處理的兩個問題,一是“文學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以及“如何服務”的問題,正因為“規定”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以及政治標準第一,也就決定了“作家培養”將會成為一個核心問題開始受到注意,符合新的文化形態建構的需求。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毛澤東接續了列寧的探索,將無產階級文學轉化為‘黨的文學’,更通過《講話》的理論與實踐,將無產階級文學變成了現實。《講話》無疑是對左翼文學的無產階級文學觀念的繼承,但以《講話》為標志展開的將無產階級文學制度化和體制化的實踐,卻具有開創意義。——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的確可以承認《講話》是‘劃時代’的。‘黨的文學’成為了建國后中共的基本文藝政策”[8]。
按照這樣的文藝政策精神,在黨的組織下建立“文學院”,有計劃地培養無產階級作家就是必然的結果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50年被文化部同意建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雖是新中國創辦的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國家級培養作家的機構,但它與“紅色圣地”延安有著斬不斷的血緣聯系。它的精神臍帶扭結在《講話》當中,它在制度上的實踐也有前例可循,那就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這兩樣東西將作為20世紀40年代的遺產一直影響“中央文學研究所—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的辦學實踐。
二、“延安魯藝”的“作家培養”經驗
1984年改名的“魯迅文學院”和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都以魯迅命名,絕不是簡單的巧合。對于建國后的作家培養體制來說,“延安魯藝”不僅提供了革命情感教育資源,更關鍵的是它積淀出來的制度保障和培養經驗。亦即邁斯納所說:為毛澤東主義者所著力贊揚和高度評價的延安傳統,“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遺產,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價值觀念方面的遺產”[9]65。
對于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來說,制度方面的經驗和“遺產”顯得極為重要。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顯然無法依靠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因為國民黨自己在文藝方面的政策可以說是極其失敗的⑥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國三十多年中,對革命文學上下戮力“圍剿”,但所采取的辦法似乎也就是一味地從外部來“禁”,至于內部如何建構一種組織化的文學制度及控制手段,卻始終懵然無知。參見李潔非,楊劼:《解讀延安》第13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新中國必須構建全新的積極的文化形態和體制。在借鑒蘇聯老大哥的經驗上,并在具體處理中國自己問題的探索過程中,共產黨就在逐步積累管理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經驗。但實際上這些經驗也是在不斷摸索和調整中,是在波折當中逐步豐富起來的。比如,周揚等與魯迅的矛盾,1936年左聯解散等暴露出的左翼內部的觀念沖突,不僅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問題,它實際上一直影響到延安,影響到建國后。
以毛澤東為核心領導的共產黨人早就注意到了文藝的重要性,更掌握到了對文藝工作者進行組織化管理的必要性。在毛澤東1939年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當中,他開門見山地指出黨吸收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0]。在文件的最后,他重申:“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10]。當然,他如此強調吸收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關鍵是“利用”,因為“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10]。可見毛對知識分子是有等級區分的,“原有”和“自己”的當然不同。態度自然也是功利的,對待“原有”的強調“有用”和“忠實”,吸收之后要加以教育,磨練。
邁斯納認為雖然毛澤東一直強烈關注中國社會的客觀階級狀況,但是他同樣也傾向于按照道德和思想標準而不是按照客觀的社會階級標準來確定人們的“階級地位”。對他來說,社會主義的載體是那些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人,這些人可能獨立于任何社會階級而存在[9]64。這種唯意志主義的傾向和毛的民粹主義思想混合在一起,反映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獨特理解,也可以用來理解毛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知識分子是可以利用的,但是這個利用的過程當中必須要不斷對他們進行“教育”,完成對他們的精神改造和思想改造。
精神和思想存在于主觀思維領域,落實到“改造”層面就必須依賴組織和制度來實施。所以在思想上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基礎上,黨必須著手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和制度對他們進行管理、規約和“教育”。而且對知識分子的管理也可以進行分類。邁斯納在分析共產黨“百花時代”的知識分子政策時,注意到了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和人文知識分子的區分,這一點非常有啟示意義。毛澤東于1949年6月30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主要提出了建國后的兩大任務:其一是“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其二就是“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11]。尤其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經濟建設的任務顯得格外緊迫。這個時候需要大量利用自然科學知識分子,鼓勵他們的積極性。因為自然科學相對來說幾乎沒有階級性,在政治上可以更“中立”[9]227。但是人文類的,比如文學藝術、哲學等當然更具有階級性,因而要更為敏感。
相對于建國后面臨經濟建設更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不同,在延安時期,更需要團結和爭取的對象是更具現實“革命影響力”的人文知識分子、藝術家。早在1936年11月22日,由丁玲任主任的中國文藝協會就在保安成立了。毛澤東出席了成立大會并講話。他指出“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12]。除了組織和管理已有的作家、藝術家,繼續培養符合需求的文藝干部也迫在眉睫。1938年,毛澤東親自領銜發起創辦“魯迅藝術學院”。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核心領導人物親自發起創辦“魯藝”,主要是基于藝術形式對于發動、組織群眾的作用,他要把藝術作為革命武器,而共產黨必須“培養”自己的干部來掌控這“武器”。在教育史上,它是一項創舉。當然,人們將來會意識到,“培養”專門的文藝干部不止是個教育問題,更具有參與意識形態建構這種更宏大的作用。雖然面臨著要在偏遠而艱苦的延安城領導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雙重歷史任務,毛澤東作為黨的核心領導人,并沒有將他對“魯藝”的關注停留在創建階段。他不僅僅后來在周末到“魯藝”參加舞會,事實上他一直密切關注,并親自掌控“魯藝”的發展方向。
“魯藝”正式宣布成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就親自到“魯藝”發表講話,講話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此次講話對“魯藝”教育方針的具體實施產生了重大影響。初期“魯藝”實施“開門辦學”的方針,采取“三三制”教學模式,先在校學習3個月,然后由學校統一安排到前方抗日根據地或部隊實習3個月,再返校繼續學習3個月。全院第一次較大規模實習活動,是1938年11月由文學系代理主任沙汀和教師何其芳,帶領文學系第一期以及音樂系、戲劇系和美術系第二期的部分學生,跟隨八路軍120師師長賀龍,到抗戰前線去[13]61。之后第一至三期的學生都被派赴前方部隊或地方實習,普遍受到歡迎。有些實習期滿甚至被留下,不讓回校。這些學生畢業之后也大多被派往前方工作,成為部隊和地方的文藝骨干。
不過1939年底周揚接任“魯藝”的副院長主持工作后,開始改變辦學方針,趨向“正規化”和“專門化”,并對教學體制和組織機構方面進行大規模調整,“結束了早期魯藝教育行政和教學程序總是被不斷舉行的晚會所支配所紊亂的那種不正常的狀態”⑦周揚:《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魯藝學風總結報告之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與自我批評》,參見《延安文藝叢書》(文藝理論卷)第824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這樣的嘗試卻引起了毛澤東等人的不滿。后來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被批評為“關門提高”。“‘魯藝’的正規化、專門化的嘗試和實踐所受到的責難,反映出在文藝的服務對象、文藝的作用和功能、文藝的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以及大學的教育體制等問題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前方軍事將領與魯藝的文化人之間的存在著某些分歧”[13]86。
毛澤東密切關注著這些分歧,并要努力消弭這些分歧。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包括“魯藝”的負責人和教師30多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后,受周揚的邀請,毛澤東親自到“魯藝”發表講話,并針對“魯藝”的工作,著重講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問題。這次講話后,“魯藝”的整風運動就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周揚于1942年9月9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藝術教育的改造——魯藝學風總結報告之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與自我批評》,深刻剖析了“關門提高”錯誤的根源乃是在“提高與普及,藝術性與革命性的分離上”⑧周揚:《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魯藝學風總結報告之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與自我批評》,參見《延安文藝叢書》(文藝理論卷)第821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尤其有針對性地檢討了對待古典作品和繼承藝術遺產方面的錯誤,剖析了“技巧”和“思想”之間的關系,指出藝術作品不是只單純包含技巧,還必定表現一定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可能就有毒素,比如說19世紀資產階級現實主義文學,可能就會助長個人主義思想,喚起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共鳴。針對有些同志對蘇聯藝術文學的蔑視態度,他也作出了批評。在檢討基礎上,周揚提出了今后改進的方案,比如:多研究當前藝術文學運動,關注現狀問題;克服宗派門戶之見;多與地方保持聯系;主動服務于政治斗爭;加強學生實習工作等。整風運動之后,“延安魯藝”結束了它正規化、專門化的探索時期。1943年“魯藝”并入延安大學,也告別了它作為第一所由中共領導人發起的專門“培養”青年藝術工作者的黃金時代。
“延安魯藝”的黃金歲月留在了歷史里,但是它開創的共和國對藝術家的集中“培養”制度卻作為“延安傳統”的一部分得以延續。建國之后的“中央研究所”—“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不論命名如何更迭,都始終抹不去“延安魯藝”的影子。在“延安魯藝”,文學系算不上最醒目的,賦予它光環的主要是那些大名鼎鼎的教師。因為在那個戰爭年代,相比于文學,可能戲劇、音樂、美術更能直接地發揮效應。魯藝的文學系直到第二期才開始招生,而且單從藝術成果的角度講,真正造成影響的也并不多。但是作為黨“培養”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早期探索,它的辦學方式、理念,比如:招生方式、規模,授課方式,課程設置等,都對建國后的“中央文學研究所”—“文學講習所”—“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產生影響。不僅如此,“延安魯藝”時期遇到的“正規化”問題;如何對待文學遺產;如何學習古典文學;如何處理思想與技巧的關系等問題以后也會繼續存在。
三、政治和藝術教育之關系
在具體的辦學過程中,“延安魯藝”也經歷了從非正規到正規化又到強調“實踐”重要性的不斷調整過程,因為對于社會主義實踐來說,“如何培養自己的作家”都是一個全新的、帶有實驗性色彩的、不斷摸索的過程。如何處理好政治和藝術教育的關系問題,是其中很復雜也是能夠給后來共和國“作家培養體制”帶來啟示的關鍵性問題。
“延安魯藝”初期的辦學很難算是正規的,基本上算是個文藝宣傳隊。這種情況到了1939年底周揚接手之后發生轉變。周揚致力于將“魯藝”辦學往正規化方向發展。這種正規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學院化”,縮短實習時間,延長在校學時,將課程進行重新規劃設計,保證學生充足的聽課和讀書時間。為學員們津津樂道的聽周立波講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大家到圖書館搶書回來手抄閱讀都發生在這個時期。但是這種“正規化”很快遭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不滿。尤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周揚更親自對魯藝追求“正規化”時期的教育進行了檢討。針對“關門提高”的批評,他說這四個字出色地概括了魯藝教育方針錯誤的全部內容。他具體檢討了不正確地學習西方古典作品的錯誤:“許多同志完全沉潛于西洋古典作品的世界,由這培養了一種所謂的‘高級’的欣賞趣味。”這種趣味會助長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傾向。他保證,今后魯藝還是要把整個藝術教學活動建立在與客觀實際的直接而密切的聯系上,以此作為改造魯藝的首要的、中心的問題⑨周揚:《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魯藝學風總結報告之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與自我批評》,原載1942年9月9日《解放日報》,《延安魯藝回憶錄》第40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年版。
其實“正規化”問題反映了一個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據龔亦群回憶,正確處理提高與普及的關系并不簡單和容易。魯藝八年,曾進行過三次工作檢查,基本都是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第一次在1938年末到1939年初,沙可夫副院長在總結中確認,前一段時間沒有貫徹“普及第一”的方針,就是說,抗戰急需部隊文藝大批人才,而魯藝還不能適應;第二次在1941年,周揚副院長在總結中提出了傾向于正規化、專門化的方案;第三次是1942年文藝整風,周揚副院長在總結中檢查了前一段時間(1941年左右)“關門提高”的錯誤傾向[14]。
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之所以不好把握,從毛澤東的《講話》對此問題的闡述當中也可以體會得到。他說:“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2]862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又不能截然分開。因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斷提高,普及工作就不能一直停在一個水平上。人民要求普及,跟著要求提高。這種提高要在普及的基礎上進行。
毛澤東的《講話》確認了新文化建設的一個核心目標,那就是“為人民”的原則。但這個“人民”是“一個朝向未來的‘想象的共同體’”[8]。就普及和提高的水平而言,“人民”達到哪種水平,是不固定的。毛澤東在《講話》當中對普及和提高關系的解釋從操作層面來講也是模棱兩可的,這是由《講話》本身攜帶的“權宜”性質所決定的。“作為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講話》恰恰是要從根本上變革傳統中國的文化政治,使其服膺于‘最先進’的和超民族的‘無產階級’所主宰的‘美麗新世界’。”[8]這個“美麗新世界”多少帶有烏托邦的性質,在追求的過程當中,毛對很多問題采用了策略性的靈活處理手段。但正因為這個靈活,就留下了很多空間。在這個空間當中,如何處理藝術教育和政治教育的關系,在藝術教育當中如何處理文學遺產的關系,對于“魯藝”的辦學者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要求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所以即便是在所謂“關門提高”時期,“魯藝”也是堅決強調這個標準的。1939年,在“魯藝”成立一周年紀念日上,羅邁作了《魯藝的教育方針與怎樣實施教育方針》的報告,報告中明確談到“政治教育在魯藝的重要性”:“具體來說,魯藝所進行的教育,不僅要從藝術上去培養干部,而且要從政治上去提高干部。魯藝是一個藝術的學校,但它絲毫不能忽略藝術教育與政治教育的一致性,以及政治教育對藝術的重要性。……魯藝以后需要比過去注重并加強政治的教育。”[15]出現了“關門提高”問題后,“魯藝”就進一步加強了政治教育工作,把馬列主義、中國革命的問題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等課設為必修課程。整個課程的配備,原則上是藝術與政治并重。除平時的政治輔助教育外(課外讀物、座談會、討論會、演講等),每周政治必修課為6個小時[16]。
除上述的政治必修課程外,他們還經常請中共中央的領導者,來延安的名流學者,前線歸來的將領,戰地歸來的群眾工作者,實習歸來的文藝工作干部到校講演。在政治處指導下,有教職學員組織的時事研究會,定期向全體教職學員作時事報告,經常舉行政治、時事問題討論會、辯論會、問答會、戰斗故事座談會,等等。
“魯藝”整風期間,文學系系主任何其芳專門在《解放日報》撰文談文學系如何改造藝術教育與政治教育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文學遺產;如何根據抗戰需求培養人才的問題。他首先檢討了過去培養工作中,學生埋頭讀書,有問題只請教教員;強調學習古典作家,主要的是那些資產階級現實主義作家,而且在創作實踐上主張寫熟悉的題材,說心里的話;也不大考慮將來畢業后到哪里去,作什么工作的思想錯誤[17]。明確教育的目的必須具體地服從政治的要求,根據實際需求培養以下幾大類人才:通訊工作者(包括自己當通訊記者,或者作通訊組織工作,或者教人家寫通訊等);文化教員(包括根據地的中級學校以上的和部隊中的國文教員,或者文學教員);編輯(地方和部隊中的一般刊物、報紙,或者文藝刊物、文藝副刊的編輯);以及其他宣傳工作的寫作者;通俗化工作者,等等。教學方法上也要改變學院式的講學方式,要把材料和問題先經過同學們研究、討論,然后由教員來作結論的方式作為主要的教學方式,采用啟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教學法。
這顯然是何其芳以自己的切身體會所作的對于新文化和新的文學培養方式的反思。從“傷感的個人主義者”轉變為“革命者”的何其芳后來在回憶早年“寫詩的經過”時說:“在我參加革命以前,有很長一段時期我的生活里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出現在文學書籍里和我的幻想里的世界。那個世界是閃耀著光亮的,是充滿著純真的歡樂、高尚的行為和善良可愛的心靈的,卻是缺乏同情、理想,而且到處伸張著墮落的道路的。我總是依連和留戀于前一個世界而忽視和逃避后一個世界。”[18]在延安時期的何其芳看來,“有著兩條文學之路:一條是從文學到文學,一條是從生活到文學”,“過早地受專門教育就是使我們自己過早地脫離那種生活”[19]。
何其芳后來的憶述顯然是對以往自己的反思和懺悔,“他已不再是那個耽迷于夢中道路的青年了。”[20]207這一文學史上著名的“何其芳現象”,其背后的實際內涵,是對作家文學創作的理解以及學院文化和實際生活對于作家創作的影響,也顯示了延安文化教育和現代大學教育方式的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講,延安“新中國—新文化—新教育”的設想很大程度上是對自現代以來過分強勢的學院文化的反抗和調整。現代學院重要的功能便是現代知識分子或者“現代技術工人”,而并非與現實生活有著更多聯系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培養“自由”、“獨立”精神往往被視作是現代學院文化教育的重要內容和功能。但毛澤東一貫對于“五四”式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表示反感,在《反對自由主義》中他指出,“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應該“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21]。如果將毛澤東對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僅僅歸結于某種創傷記憶的結果⑩有一些研究者依據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時期與胡適等人產生的誤會而認為毛澤東對教授等知識分子充滿芥蒂。,顯然忽略了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發展的邏輯以及毛澤東更深層次文化變革需求的追求。
現代學院文化過于強勢的一個后果就在于使得文學、文化的習得越來越趨于精英化,正是由于現代學院教育的這一特征,現代中國的學院文化與民間文化尤其是左翼革命文化之間存在著諸多的矛盾和縫隙。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現代教育與文學教育、文化生產之間既互相依存又矛盾沖突的關系就已經引起了研究者們的關注。實際上,學院文化和革命文化之間一直存在著對文化和現實生活干預的文化領導權爭奪。學院文化從來就不是如想象般固定生產知識,而是有著自身的發展邏輯。一般學院文化開始了文化生產,為保持其穩定性,其固定的模式就是產生知識化的“精英”,而與現實政治、生活產生一定距離,作家、現實生活與文學教育之間關于主體的爭斗的矛盾也就逐漸暴露出來。
季劍青在分析20世紀30年代北平詩歌界的爭論所指出的,“20世紀30年代在北大、清華等校從事寫作的教授和學生,在當時即以被指為‘學院派’,后來這一提法也為研究者所沿用。從站在學院之外的立場(特別是某種左翼立場)出發,對‘學院派’的命名,往往包含著有指責學院寫作脫離現實、追求‘形式主義’的意味。面對這種壓力,學院寫作則試圖在‘現實世界’與‘藝術世界’之間進行區分,并傾向于強調后者對于寫作的重要性……通過強調‘文學經驗’對于‘現實經驗’的優先性,肯定自己寫作的意義。”[20]200-201
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還能夠允許身處北平“文化城”的教授、學生有相對自由的生存空間,那么,在延安需要培養新的文化工作者完成“反現代的現代”新文化建構以對抗“現代文化”時,文學的產生、作家的培養,“文學經驗”就已然不是最為重要的資源。過于依托或者糾結于對某位以為作家或文學經驗的沉迷,甚至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于是,作家的“培養”也必須通過一種新的方式來完成。
“延安魯藝”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專門培養文學藝術干部的學校,在《講話》前后它的辦學方針不斷在調整。初期,它比較偏重實踐;“正規化”時期它最具學院色彩,基本采取的是現代大學模式的教學。《講話》過后,“延安魯藝”重新加強了政治性和實踐性。辦學的不斷調整也說明,在具體的藝術人才培養中,由于培養“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畢竟是新任務,在世界范圍內也只有蘇聯有一些經驗,但蘇聯的影響在延安時期又主要體現在《講話》這種政策層面,實際操作上還得靠自己摸索,所以“延安魯藝”的辦學經驗實際上后來會對新中國創辦的“中央文學研究所”這些機構產生很復雜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人事方面,因為一部分在“延安魯藝”學習和工作過的人日后會參與甚至主持“文學講習所”的工作。更主要的影響還在于它們在制度上的延續性。這就使得“延安魯藝”對于共和國“作家培養體制”來說,不能不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傳統”。
[1]歐陽山.我的文學生活,延安文藝回憶錄[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67.
[2]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毛澤東選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3]黎辛.關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講話》的寫作、發表和參加會議的人[J].新文學史料,1995(2):203-210.
[4]張誠.追記三位代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N].文藝報,2002-05-18(3).
[5]艾克恩.延安的鑼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前前后后[N].人民日報,1992-05-21(5).
[6]李志英.秦邦憲(博古)文集[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515.
[7]袁盛勇.“黨的文學”:后期延安文學觀念的核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3):1-25.
[8]李楊.“經”與“權”:《講話》的辯證法與“幽靈政治學”[J].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13(1):3-21.
[9]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M].杜蒲,李玉玲,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毛澤東選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620.
[11]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毛澤東選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6.
[12]毛澤東.毛澤東論文藝[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3-4.
[13]王培元.延安魯藝風云錄[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86.
[14]龔亦群.魯藝——革命文藝教育的歷史豐碑∥延安魯藝回憶錄[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80.
[15]羅邁.魯藝的教育方針與怎樣實施教育方針∥延安文藝叢書:文藝理論卷[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91.
[16]宋侃夫.一年來的政治教育的實施與作風的建立∥延安魯藝回憶錄[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57.
[17]何其芳.論文學教育[N].解放日報,1942-10-16(4).
[18]何其芳.寫詩的經過∥何其芳.何其芳全集:4[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316.
[19]何其芳.文學之路∥何其芳.何其芳全集:6[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506.
[20]季劍青.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1]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毛澤東選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0-361.
[責任編輯:吳曉珉]
“Tradition”That Cannot be Ignored:Enlightenment of the School-Running Experience of“Yan’an Luyi”on the“Writer Cultivation System”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I Hong-xia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 specialized institution,the Central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was established in 1950 by the country to cultivate the writers,which was later renamed as Literature Learning Institute and then Lu Xun Literature Academy until the present.This set of training system is greatly associated with Lu Xun Academy of Art,briefly“Yan’an Luyi”,which was founded in Yan’an in 1938.While commonly sharing the spirit of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they also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specific training experience.In terms of the problem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art,the school-running experience casts light on the“writer cultivation system”of New China.
Yan’an Luyi;writer cultivation;Lu Xun Literature Acedemy;politics;literature education
I 206.6
A
1004-1710(2015)04-0104-08
2015-04-20
畢紅霞(1976-),女,湖北浠水人,南開大學文學院2013級在站博士后,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