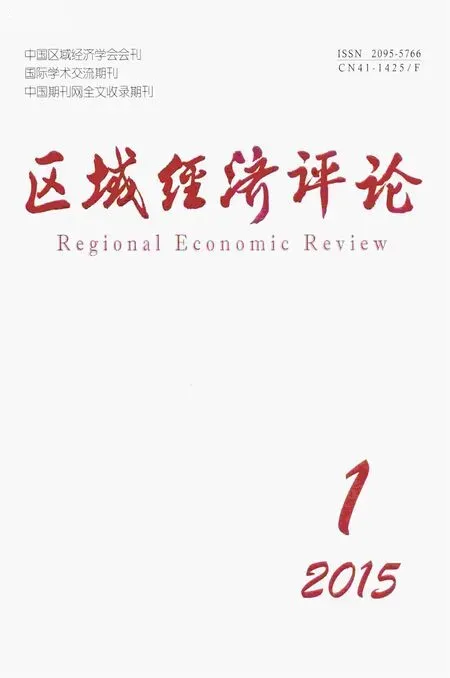構建我國一級與次級銜接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夏永祥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宏觀區域發展戰略由均衡發展向非均衡發展的轉變,我國的區域發展差距急劇擴大。這種區域發展戰略固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不斷擴大的區域發展差距確實有悖于共同富裕這個總目標,而且會引起諸多的經濟和社會矛盾。鄧小平早在1992年對我國的區域發展差距調控就做出了明確論述,提出了調控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據此,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中,明確把“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為一條重要的發展方針。進入21世紀以來,國家先后推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加快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和支持東部地區加快發展等四大戰略,意在控制和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上述四大戰略實施十多年來,通過國家在人力、財力和物力方面的傾斜性支持,前三個地區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四大地區的發展差距擴大勢頭得到遏制。但是,與此同時,我國的區域發展差距調控出現了新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次級區域發展差距被忽視,由此帶來了四大地區內部,特別是省市區及以下的行政區內的發展差距沒有得到國家應有的重視和調控,成為區域發展差距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據朱成亮等人的測算:1978—2010年區域間經濟差距對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的貢獻率處于78.4%—89.6%,平均貢獻率為85.6%,而區域內經濟差距對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的貢獻較小,1978—2010年貢獻率處于4.9%—8.3%,平均貢獻率為5.9%。而從動態演變趨勢來看,區域間經濟差距對地區經濟差距的貢獻呈現倒“U”型,拐點在2004年;區域內經濟差距對地區經濟差距的貢獻呈現“U”型,拐點在1999年。
201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并創新區域政策,縮小政策單元,重視跨區域、次區域規劃,提高區域政策精準性。長期以來,雖然各個地區也在努力縮小本地區內部的發展差距,但是效果參差不齊,不盡如人意。由此,我們提出對我國區域進行一級劃分與次級劃分、一級調控與次級調控,以及相應的一級調控與次級調控的銜接問題。這是完善我國區域發展戰略以及區域政策的重要課題。
二、一級區域劃分及其發展差距
區域劃分是研究區域發展關系的基礎。從經濟視角劃分區域,不同的區域之間應該具有異質性,而同一區域內部則應該具有同質性。所謂的同質或者異質,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交通運輸、科學技術、對外開放的便利程度以及原有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等相關因素。
關于我國的區域劃分,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從“一五”計劃開始,我國把全國劃分為沿海與內地兩大地區,沿海地區包括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和廣西,其余為內地。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根據當時準備打仗的背景和需要,我國采用一、二、三線地區劃分法,一線地區基本上是指前述之沿海地區和東北、西北和華北的幾個邊境省區,三線地區其大致界限是: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韶關以北、烏鞘嶺以東的區域,具體包括四川、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廣西、湖北、湖南和陜西的全部或部分地區,其余則為二線地區。從“七五”計劃開始,又把全國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東部地區基本上是指以前的沿海地區,包括遼寧、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以及后來增設的海南省,中部地區則包括內蒙古、山西、吉林、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省,西部地區包括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云南、貴州、四川、西藏以及后來增設的重慶市。進入21世紀以來,則把全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四大地區,東部地區包括以上除遼寧、廣西外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省;西部地區包括以上的西部地區和內蒙古、廣西以及湖南的湘西、湖北的恩施兩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上劃分都是最高層面的劃分,由此劃分的區域,可以稱之為一級區域。與上述劃分相交叉,我國還曾經把全國劃分為若干個經濟區,以便開展經濟協作。
按照上述劃分,相應地就產生了不同區域發展差距,例如,在沿海與內地的劃分下,就產生了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差距,沿海地區發展快而內地發展慢;在三線地區的劃分下,就產生了三大地區的發展差距以及資源傾斜配置格局;在東中西三大地區的劃分下,就產生了東部地區發展快、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發展慢的格局;按照最新的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四個區域劃分,就產生了在以上三大地區發展差距基礎上再加上東北地區的發展差距。這四大區域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發展差距,從整體上看,發展水平自東向西依次遞減,東部地區發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低,東北地區雖然資源豐富,發展基礎好,但是由于資源枯竭和體制弊病,在新的歷史時期,遇到了很多問題。這四大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形成了我國的一級區域發展差距,這是在最高層次和最大尺度上,對我國區域的劃分和對區域發展差距的判定。
三、次級區域劃分及其發展差距
次級區域劃分是相對于一級區域劃分而言的,具體是指省、市、區以及以下的行政區內部的更低層次的行政區。在我國的經濟體制下,經濟活動一般是按照行政區劃進行組織和調控的。目前,我國的行政組織包括5級,即中央政府、省(直轄市、自治區)、市(地區)、縣(縣級市、區)、鄉(鎮)。在一級區域劃分下,每一個一級區域中,都包含若干個省市區級行政區,它們都被包括在同一個一級區域中,被作為具有同質性的地區看待,享受相同的國家區域政策。而在省市區內部,又包括若干個,甚至十多個地區或者地級市,再往下又包括數十個縣或者縣級市和區,再往下就是我國的基層行政區,即鄉(鎮)。
我國幅員遼闊,區情復雜,不僅不同的大區域之間存在著異質性,而且同一個區域內部也存在著異質性。這些差異在空間上表現為犬牙交錯狀態,在整體發展條件好的地區內部,也有條件差的小地區,而在整體發展條件差的地區,也有條件較好的小地區。
根據次級區域劃分,相應地就產生了次級區域發展差距。次級區域發展差距是指用更小的尺度,對省、市、區及以下四級行政區內部發展差距的概括和判定。在這些行政區內部,由于諸多主客觀原因,發展也很不平衡,存在著明顯甚至很大的差距。在全國31個省、市、區內部,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有一些地級市或者地區率先發展和富裕起來了,而其他一些市和地區則仍然處于落后和貧困狀態。例如,作為我國名列榜首的經濟大省和強省的廣東省,人們一般都把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佛山、惠州、中山、江門等狹義珠三角地區作為代表,認為全省的發展水平都達到或者接近它們,然而事實上,在廣東省的21個地級市之間,就存在嚴重的南北、東西之間的差距,狹義珠三角地區發展水平很高,但是,粵北、粵東和粵西的有些地級市和縣,還相當落后和貧困,有些甚至還處在國家級貧困縣的水平。再如,在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省,也存在著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大地區的差距,蘇南地區發展水平固然很高,已經達到了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水平,但是蘇中、蘇北的有些縣,還處于國家級貧困縣的水平,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經濟大省山東省,也存在東部、中部與西部的發展差距,有人稱其為全國區域發展差距的縮影。在另一個經濟大省和強省浙江省,也存在浙南與浙北的差距,地處浙北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杭州、寧波、溫州、紹興和臺州等市發展水平很高,但是地處浙南的麗水、衢州和金華市則與之差距很大。甚至在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和重慶市這四個直轄市內部,同樣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特別是北京市與重慶市,還存在著千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與中心市區的繁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一種斷崖式的落差。
反過來看,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其整體發展水平當然低于東部地區,但是在其內部,也有不少相對甚至絕對的發達地級市和縣、鎮,例如內蒙古和陜西,整體上雖然是落后地區,但是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市和陜北的神木等縣,由于擁有豐富的煤炭和石油資源,其人均GDP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遠遠超過東部地區。其余各省(區)的次級發展差距,莫不如此,對此我們不再詳列。
如果再深入到地區級和縣級、鄉鎮級行政區,也可以發現其內部有著明顯的發展差距。例如在經濟大市蘇州市,最好的鎮年地方財政收入可達40多億元,手頭闊綽,而最差的鎮年地方財政收入不足1億元,連工資等基本開支也無法保證,要靠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對于這些區域發展差距,我們把它們統稱為次級區域發展差距。
與一級區域發展差距相比,次級區域發展差距具有不同的特點:一是所涉及的空間較小,只是在一個省、市、區甚至更小的范圍內,具體在幾十平方公里到幾十萬平方公里之間,遠遠小于一級區域劃分下的上百萬平方公里;二是所涉及的人口較少,只是在某一個地方性行政區內部的人口,多則在一億人左右,少則可能只有幾十萬人,也遠遠小于一級區域劃分下的數億人口;三是調控主體不同,它的調控主體一般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級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區、縣政府等。
四、一級與次級區域綜合視角下的發展差距格局
引入次級區域劃分以及次級區域發展差距概念后,我國的區域發展差距就不是簡單的四大板塊發展差距的描繪,而是一種犬牙交錯狀的分布格局。如果我們以縣為單位,以不同的顏色表示不同的發展水平,那么,在全國的版圖上,就不是只有單調的4種顏色,而是斑斕紛呈的多彩畫面。綜合上述對一級與次級區域劃分以及一級區域發展差距與次級區域發展差距的分析,可以看出,區域發展差距呈現出異常復雜的分布格局,既有絕對標準上的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劃分,也有相對標準上的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劃分。在發達地區中,也有欠發達地區,是謂發達中的欠發達,這種欠發達既可以是本級區域內部的相對意義上的差距,甚至可以是全國一級區域之間絕對標準上的欠發達;而欠發達地區中也有發達地區,是謂欠發達中的發達,同樣,這種發達既可以是本級區域內部相對標準的發達,甚至也可以是全國一級區域之間絕對標準上的發達。對于這些區域發展差距,我們可以劃分為不同的層級,即一級區域發展差距與次級區域發展差距。
綜合一級區域發展差距與次級區域發展差距,可以看出,全國的區域發展差距格局是:在東部地區,整體上屬于發達地區,其內部次級區域細分為,以發達次級區域為主,但是也有部分欠發達落后地區和個別絕對落后地區;在中部地區,整體上屬于欠發達地區,其內部次級區域細分為,以欠發達地區為主,也有部分相對和絕對意義上的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在西部地區,整體上屬于落后地區,其內部次級區域細分為,以落后地區為主,但是也有部分相對發達地區和個別絕對發達地區;在東北地區,整體上屬于問題區域,雖然原有發展基礎較好,但是由于資源枯竭和體制僵化,相當多的次級區域發展陷入困境,也有少數次級區域仍然具有發展活力,可以在一段時期內保持較好的發展勢頭。
五、略去次級區域下的一級區域發展差距調控
在對區域發展差距的調控上,在中央政府層面,主要根據一級區域劃分來制定區域政策,而略去了次級區域劃分及其發展差距。在二分法下,國家根據沿海地區與內地長期形成的發展差距,實行均衡發展戰略,即在全國資源配置上,重點向內地傾斜,包括存量資源與增量資源的配置。1956年,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論述中,提到的第二個關系即是“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他認為:“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依靠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在存量資源配置上,用行政手段使沿海地區大批企業舉廠內遷,許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向內地搬家,生產設備、教學和科研設施隨之流向內地。在增量資源配置上,國家建設投資也主要向內地傾斜,其所占比重一直超過了沿海地區。這種區域調控政策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這一時期,沿海和內地的發展差距開始縮小。
在三線建設時期,國家投資則主要向三線地區傾斜,所謂的三線地區,全部屬于內地。為了進行三線建設,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多年時間中,投入了數千億元資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崇山峻嶺之中,建設了一大批以國防工業為主的現代化工廠,隨之嵌入了一批新興工業基地和城市,成為內地的經濟增長極。這種區域政策繼續縮小了前一時期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差距。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國家的宏觀區域發展戰略發生重大轉變,從均衡發展向非均衡發展轉變,其指導思想就是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具體地說,就是讓條件好的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和富裕起來。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際形勢的緩和,三線建設停止,在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的劃分下,國家資源轉而向東部地區傾斜,既包括存量資源,例如部分中西部地區企業的東遷,也包括增量資源,例如國家新增建設資金向東部地區的重點投入;既包括物質資源,例如人力、物力與財力向東部地區的流動,也包括政策資源,例如國家給予經濟特區、保稅區、開發區的大量優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在市場化取向改革下,市場也在發揮區域間資源流動的調節作用,它與國家的調控方向是一致的,在東部地區高收益的引導下,大量民間資源也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作用機制,使得在短短的十多年中,我國三大地區的發展差距掉頭急轉,不僅沖抵了前20年間的縮小量,而且進一步擴大了它們的發展差距,東部地區發展最快,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慢,從東向西,依次遞減。
1992年是我國區域發展戰略轉變的又一個拐點。20世紀80年代迅速形成的地區發展差距顯然與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終極目標是相悖的。于是,鄧小平提出了在20世紀末對區域發展差距進行政府調控的構想,由此促使國家的區域發展戰略從非均衡發展向非均衡協調發展轉變。從“九五”計劃開始,國家加大了對區域發展差距的調控力度。為了實施這一戰略,從2000年開始,國家先后依次推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并且根據東北地區的特殊區情與問題,推出了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戰略,又根據中部地區發展滯后、面臨“塌陷”的問題,推出了中部地區快速崛起戰略,對于東部地區,并不能坐等其他三大地區的追趕,而是要在動態發展過程中縮小差距,于是,又明確了鼓勵東部地區進一步加快發展的戰略。至此,我國一級區域以及基于這種劃分的區域政策已經形成,成為我國最高層面的區域發展戰略與政策。從統計數據看,十多年來,這四大區域發展戰略與政策均收到了初步成效,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勢頭得到遏制,趨向收斂,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發展速度加快,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當然,東部地區挾其優勢,依然在強勁發展,四大地區的發展差距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尚難完全消除。
六、引入次級區域下的區域發展差距調控
在實施上述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時,國家并沒有過多考慮次級區域內部的發展差距,其中存在著政策尺度過大、過于泛化、調控過粗等問題。由此造成新的區域發展差距問題,即在一級區域發展差距縮小的過程中,次級區域發展差距依然存在并且加劇。我國存在著嚴重的次級區域發展差距,其危害性同樣不可忽視,因此必須納入國家調控視野。
從經濟角度看,次級區域發展差距不利于次級區域內部的分工協作。在次級區域內部,由于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也需要開展分工協作,以便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是,在存在發展差距的情況下,落后地區的資源不能得到有效開發,不僅制約了自身發展,而且也會制約發達地區的發展,使某些要素供應不足,從而使整個次級區域經濟不能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
從政治和社會角度看,次級區域發展差距會造成區域內部不同地區之間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從整個區域的層面看,無論是總量指標還是人均指標,可能都已經達標,但是卻掩蓋了內部的差距,其中的落后地區,總量和人均指標都大大低于平均水平,也沒有達到標準值,這部分居民,也不能平等分享發展成果。這樣的小康社會和現代化,都不是全面的,甚至是畸形的。如果差距達到一定水平,就會造成居民之間的矛盾和隔閡,其危害性不亞于一級區域發展差距的危害,這顯然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例如,最近幾年,不僅在中西部貧困地區,而且在東部發達地區,都出現了一些影響較大的危害社會安定的重大惡性案件,甚至東部地區的惡性事件數量更多,危害性更大,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內部的發展差距,在東部地區內部,也仍然存在著一定數量的貧困人口,他們的利益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他們的一些生計問題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由此導致一些人鋌而走險,以危害社會的方式發泄自己的不滿,使無辜群眾遭殃。
從國家的區域發展差距調控政策效果看,如果不考慮次級區域發展差距,勢必會降低調控政策的效果和調控資源的配置效率,甚至造成浪費。因為國家的區域調控政策從政策目標來看,應該有利于縮小差距,調控政策的制定應該更多地堅持公平原則,調控資源的配置應該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但是,如果不考慮次級區域發展差距,就有可能出現政策的實施缺乏精準性和針對性,具體表現為下列情況:從受援的一級區域看,在整體上,它們確實是落后和貧困地區,需要幫扶,中央政府和發達地區也確實給它們提供了大量幫助,但是,在受援資源的內部分配上,卻忽視了一級區域內部省、市、區之間以及省、市、區內部和更低行政區內部的發展差距,實現平均主義式的分配,結果,那些本來發展較好的次級區域,也得到了幫助和救濟,這部分資源,就沒有發揮雪中送炭的作用,而是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而那些真正需要幫助和救濟的次級區域,相對而言,就沒有得到應有的幫助和救濟,蒙受了損失。從施援方看,除中央政府外,還有發達地區。在我國,區域調控政策和方式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結對幫扶,例如江蘇省對陜西省的支援,以及整個東部地區對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幫助。為了落實支援任務,東部地區的一些省、市甚至具體落實到地級市和縣的層面,某地區對口支援某地區,某縣對口支援某縣。在這個過程中,就有可能出現偏差,即忽視了東部地區內部次級區域的差距,使東部地區那些相對甚至絕對落后的地區也要承擔對口支援任務,實際上,它們是沒有這個能力,也不應該承擔這個任務的,它們解決自己的發展問題尚且自顧不暇,如果再要它們承擔幫扶任務,無疑增加了它們的負擔。
正因為如此,縮小次級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內部的協調發展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中央政府層面,需要在一級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我國的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劃分和調控尺度,使區域政策避免大而化之,更加精準和具有可操作性,使政策資源真正配置到需要扶持的較小范圍,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從而使區域協調發展從大到小、從高到低,更加具體,落到實處,最終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真正變為現實,使全體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在次級區域層面,各省、市、區甚至地級市和縣、鎮也應該站在這樣的高度,認識自己內部的發展差距,確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而不能任其擴大。特別是對于那些整體發展水平已經較高、區域發展差距較大的省、市、區,更應該及時調整思路,彌補這一缺陷。
七、構建一級與次級銜接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綜合上述分析,在統籌考慮一級區域與次級區域及其分級發展差距的基礎上,為了完善我國的區域調控政策體系,應該著力構建一級與次級銜接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具體包括以下內容:
1.縮小區域劃分尺度和政策單元,盡可能細化調控對象和范圍
從受援方來看,要進一步分析本行政區內部的發展差距,據此分配中央政府和東部地區的幫扶資源。對其中絕對發達和高收入的地區和個人,可以不分配幫扶資源;對其中相對發達地區和高收入者,可以少分配幫扶資源。讓該得到者確實得到,而讓不該得到者確實沒有得到,讓該多得到者確實多得到,讓該少得到者確實少得到,最終使幫扶資源真正使用到急需和應該使用的地方。
從施援方來看,在對口支援和結對幫扶中,則不宜過分細化,可以落實在省市區層面,不宜進一步向下延伸。也就是說,東部地區的那些經濟大省、市和強省、市,從整體上看,確實具有支援中西部落后地區的能力,也應該承擔相應的支援任務。這些省市可以從其財政資金中拿出一部分支援中西部地區。這部分財政資金,從其來源看,主要來自內部的發達地區,因此,最終實際上是其內部的發達地區承擔了支援任務,而落后地區則免去了支援任務,減輕了它們的負擔。如果為了落實責任,需要向下細分,對口支援,則應該止于地級行政區,不應該細化到縣級行政區。對于地級行政區,也應該充分考慮它們的發展差距,區別對待,不應該要求所有地區都要承擔支援任務,對于那些絕對落后的地區,就不應該分配支援任務;對于那些相對欠發達和貧困的地區,就應該少承擔支援任務。這樣做,同樣有利于提高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2.明確調控責任主體,構建分級調控體系
為了構建一級與次級銜接的區域調控體系,必須明確和落實分級調控的責任主體。一般來說,每一級行政主體適合調控本級行政區以內的區域發展差距,而同級別行政區之間的區域發展差距,應該由上級行政主體調控。據此,對于一級區域發展差距,其調控主體應該是中央政府,只有中央政府有權力調動全國資源去支援落后地區,而且有權力組織四大區域之間的對口支援。每一個省、市、區政府都沒有權力做到這一點,它們只能在中央政府的組織下,分別扮演施援者或者受援者的角色,完成相應的任務。
對于次級區域發展差距,中央政府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沒有可能去進行調控,而適合由省、市、區及其以下的行政主體去進行。省、市、區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內不同地級行政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調控;地級行政區行政主體負責本行政區內不同縣級行政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調控;縣級行政區行政主體負責本行政區內不同鄉鎮之間的發展差距調控;鄉鎮政府則負責本鄉鎮內部不同村和社區之間的發展差距調控。這樣,就形成了從上到下、權責明確的分級調控體系,覆蓋到各個層次的區域發展差距調控,不留死角。
3.次級區域發展差距的調控,可以借鑒一級區域發展差距的調控經驗與方式
我國具有長期的一級區域發展差距調控歷史,積累了豐富的調控經驗。相對而言,各個次級區域的調控經驗及效果則參差不齊,既有像江蘇省這樣調控效果好、經驗豐富的省份,也有大量調控效果較差、經驗不足的省份,地級及其以下的次級區域發展差距調控差別更大。從一般原理上講,次級區域發展差距的形成和調控與一級區域發展差距的形成與調控是相通的,所以,次級區域發展差距的調控,可以適當借鑒中央政府對一級區域發展差距的調控經驗與方式,然后結合本區域特點,進行創新和具體化。而且,不同的次級區域之間,也可以相互借鑒和交流。第一,無論是哪一級次級區域,政府都應該高度重視本區域內部的發展差距,不能放任不管,要像中央政府那樣,把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條重要指導思想和方針,特別是發達地區,越是發展水平越高,越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越要關注和化解由于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所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第二,在調控政策體系上,要多種政策并用,互相搭配,形成合力。調控政策包括財政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產業政策、空間政策,等等。通過這些政策,引導本次級區域內資源配置從發達地區向落后地區的流動。第三,可以借鑒地區對口支援方式,組織本次級區域內不同行政區之間的幫扶活動。通過對本次級區域內不同行政區發展差距的分析,確定受援行政區名單與施援行政區名單。其中,也不能簡單地搞“一對一”,而是要具體分析,對于那些自身發展水平不高,低于本區域平均發展水平,特別是低于全國平均發展水平的行政區,就要豁免它們的對口支援任務,讓它們集中力量,搞好自身發展。
4.按照產業轉移規律,推動產業在空間轉移
產業轉移是區域調控的重要內容,對于落后地區的幫扶,最根本的還是要培育其“造血”功能,這就需要培育產業,發展經濟,逐步做到自立自強。在這個過程中,推動發達地區的產業在空間上按照梯度轉移規律向落后地區轉移,是一條重要途徑。在產業梯度轉移中,地方政府一般是主張和推動在本次級區域內的轉移,把它作為調控本級區域發展差距的重要手段,對此無可厚非。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產業轉移也可能會突破本級行政區范圍,而直接在更高的次級區域之間,甚至跨越一級區域,進行轉移。例如,蘇南地區的一些產業,可能并不是向蘇中、蘇北地區轉移,而是直接轉移到安徽省甚至轉移到西部地區,對此更無可厚非。由此,在產業轉移中,不應該受行政區的限制,不一定非要遵循由低級次級區域逐級向上級次級區域、最后才進行跨一級區域轉移的程序與路線,而完全可以一開始就突破次級區域之間以及與一級區域之間的界限,直接進行大跨度的空間轉移。在這一點上,要相信市場調節的功能,相信企業家的智慧與判斷力。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在全局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1]毛澤東.論十大關系[A].毛澤東選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0.
[2]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A].鄧小平文選(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5-376.
[3]朱成亮,岳宏志.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的演變及區域分解[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4,(1):40-51.
[4]楊小軍.建國60年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變及基本經驗[J].現代經濟探討,2010,(2):8-11.
[5]夏永祥,等.中國區域經濟關系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3-10;228-232.
[6]夏永祥.重視對次級區域發展差距的調控:以江蘇省為例[J].區域經濟評論,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