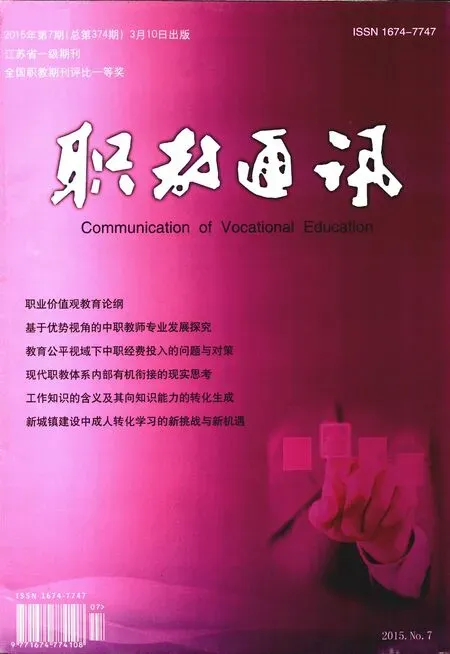美國視角中的中國職業教育
湯霓
美國視角中的中國職業教育
湯霓
每年11月的感恩節,我的外導都有一個傳統,會邀請這一年來自世界各國的聯合培養博士生和訪問學者去他家共進晚餐。感恩節是美國每年非常重要的節日之一,而我在收到邀請之后就一直憧憬著感受美國家庭的感恩節文化。那一天終于來了,除了同一個研究所的同事,當晚導師還邀請了他的諸位至親好友,其職業有攝影師、律師,還有新聞工作者。而在場的除了我和另外一位來自武漢大學的博士生外,其他都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而當晚,我們兩位中國學生,竟然成了眾人的“爭寵對象”。當我一邊翻閱那位攝影師的作品集,一邊聽他和我們講述在中國的經歷,他不斷地向我們強調自己是有多么喜歡上海,總覺得在那就感覺像在家一樣。而我的外導夫人,一位著裝十分優雅卻在外導面前也會頑皮地耍著小性子的可愛老太太,也是UCLA的教授,更是拉著我的手說個不停。她說早在七十年代她就去過中國,那是她第一次去中國。她描述到,當時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周圍的路人沒有一個不投來齊刷刷的注目禮,她感覺自己是個十足的“異類”。而在時隔三四十年后的2012年,她第二次去中國的時候,被周圍環境的變化驚詫得目瞪口呆。那些建筑和道路已經完全不是她腦海里中國的印象了,而路上的行人也待他們非常尋常,不再讓她感到緊張或者覺得他們有什么異樣。“中國的變化太大了,發展太快了!”這是所有人在和我談起中國時都會感嘆的話。
這種感嘆不僅發生在他們去中國訪問或參觀后,也體現在他們對中國教育的研究和思考上。一次,我所在的研究小組組織了一場匯報討論會,主題之一是關于中國遷移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問題。會議在一間不大的教室舉行,卻座無虛席、人滿爆棚。來聽會的有來自教育學系、社會學系、地理系等系所的博士生和教授。開講前,主持人問大家,有多少人去過中國。令我震驚的是,在場居然有80%的人舉手,甚至很多表示自己不止一次去過中國,還去過中國的很多地方。即使是在討論過程中,在提到一些專業詞匯例如“戶口”時,臺下大多數人都頻繁點頭,甚至外導的解釋比我們更為專業。而在提到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遷移勞動力的數量和接受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大規模時,臺下人無不發出驚呼的聲音:“fascinating!(太精彩了!)”他們認為,在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方面的舉措無疑是中國政府使中國從人口大國成為人力資源強國做出的卓越貢獻,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會后,還有好幾位說著普通話的美國學生跑上來和我們反饋在中國調研遇到的一些有趣經歷,讓我們甚是覺得“受寵若驚”。在這些交流中,我往往能明顯地感受到美國研究者對中國短短幾十年來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驚嘆和興趣,在座的那些教授和學生們也比我想象中更要關心和了解中國。
然而,中國的職業教育在美國人眼中也真是如此“美好”嗎?事實上,這些美國人并不是那么好“對付”的。在一次教育學院的博士生課堂上,輪到我做匯報,我選的題目是中國的職業教育體系。當我用宏大的篇幅來呈現中國職業教育體系的結構,呈現中國在改革開放這短短三十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時,臺下的博士生們無不對宏大的數據露出驚訝的表情。但在介紹世紀之交中國高等教育擴招的大背景下,中國在短短的幾年間做到了高等教育階段和中等教育階段新生入學的普職比達到1∶1時,教授卻打斷了我的匯報。他問道:“這個非常有趣,中國的學生怎么會突然都跑去讀職業教育了呢?而且這個比例還這么平均?”頓時,我居然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卡住了。我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我能告訴他這是政府行為嗎?猶豫半晌,我還是如是回答了。教授聽罷,眉頭緊鎖。很顯然,他對這個回答很不滿意。氣氛就這么僵住了,突然一個聲音竄出,我心想終于有人出馬救場啦。“是不是政府在這幾年把職業教育辦好了?”一位博士生說到。這一句話拋出,課堂上立馬像炸開了鍋。“你這么說的前提是中國的職業教育不如普通教育咯?”一位中美混血的學生反問道。這時,另一位學生朝向我說:“中國的職業教育素來也會被貼上二流選擇的標簽嗎?”我堅定的點了點頭。“既然這樣,怎么能在短短的幾年間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呢?”他繼續追問我。我覺得這時我已經被問得“體無完膚”,實在不知道該如何繼續下去了。見我一臉尷尬,一位女同學說道:“我覺得這個在美國也是一樣的,如果要在大學和社區學院之間選擇,有條件有能力的當然會選擇去上大學啊!只是我們腦海里沒有這樣一個1∶1的概念,或者說即使政府完成1∶1,那又怎樣呢(So what)?”聽著同學們左一句右一句的爭論,教授終于按耐不住了,說:“我非常了解中國政府在執行重大決策時權力的集中和實效性,但是在這1∶1背后學生的真實意愿是什么呢?為什么是1∶1,而不是其他比例,這個比例是如何被決策出來的?”聽到這,我立馬補充道:“確實在擴招的那幾年,中國職業教育的招生面臨著很多困難,各地經常聽到招不到學生的聲音。”“如果是這樣,那我就要懷疑這個數據的真實性了。”教授立馬回答:“我以前在OECD的項目,每次涉及到中國數據時就會讓我們很頭疼,很多報告的中國部分都缺數據,或者是一些不太全面的數據,很難看到我們想看到的真實東西。”最后,見我面露難色,教授還是對我所匯報的內容做了一番肯定性的總結,而同學們和教授提出來的各種問題也就這樣在課堂上不了了之了。
回來后,我心情卻久久不能平復,不斷思考課堂上教授提出的問題。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首先,他們對中國的職業教育肯定是沒什么概念的。但其次,他們又比你想象中更了解和關心中國,甚至是中國的職業教育。而最關鍵的是,這樣一種矛盾的表象折射出的是他們在看待中國教育乃至中國職業教育時,其關注點和我們是全然不同的。在他們眼中,中國職業教育短短幾年的成績令人矚目,中國政府的決策力和效率讓他們印象深刻。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對其背后的機理和緣由卻更懂得思考。在他們眼中,受教育完全是一件非常個體化的事情,如此上升到國家戰略布局的強制性教育規劃和決策反倒讓他們非常不理解。而在我們眼中,職業教育的擴招意味著職業教育的繁榮,而這已經上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那就證明這是對的,理所當然的要這么去做,而對于為什么要這么做我們似乎從來沒認真思考過。
這恐怕就是美國視角的中國職業教育,他們看得到國家,看得到政府,卻看不到中國職業教育體系中的學生個體。對于他們來說,中國的職業教育就是一個龐大物,宏大而抽象。這里面到底發生了什么,這其中學生的真實感受是什么,對他們來說卻總是“黑箱”。當然,教育的決策和執行和每個國家的國情也是息息相關的。對于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現代聯邦制的國家,他們更加注重個體主義,要想統一執行一項教育決策是極其困難的。但在中國,政府主導往往是各項教育決策執行的源動力,成效立竿見影。但我們在信奉集體主義的同時,卻往往不能尊重彼此,丟失自我。這種視角的不同發人深省,回想起我所接觸到的美國社區學院的學生,都是有著非常獨立個性的活蹦亂跳鮮活的個體。他們可以“輕松”地轉學到美國頂尖的大學,也可以輕松地去學任何感興趣的東西。而當我想要描述一下中國職業院校的學生時,我卻似乎無法形容,哽咽在喉。這或許也是中國職業教育研究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在宏大的政府政策背景下,我們的研究似乎也多是停留在宏觀借鑒階段。然而,深入到“黑箱”的職業教育研究,展現鮮活的學生個體,似乎才是美國研究者們更關心的東西。
[責任編輯 曹 穩]
湯霓,女,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2012級博士研究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勞工與就業研究所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職業技術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