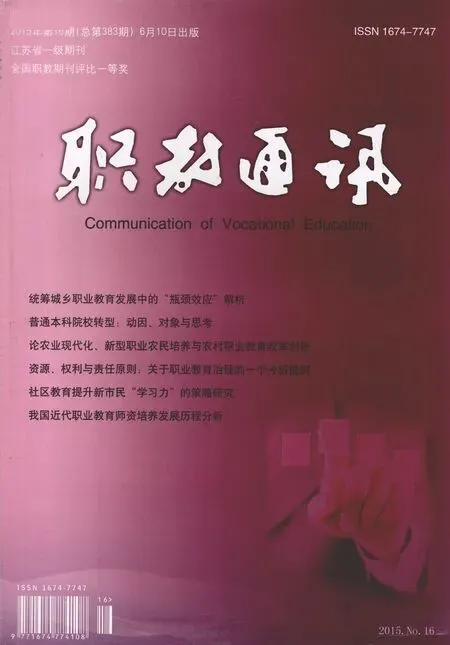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緣起與思想特色
尹艷秋,許念英
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緣起與思想特色
尹艷秋,許念英
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際,中國社會處在動蕩多舛的時期。為強國富民救亡圖存,黃炎培、顧樹森等一批有志之士倡導發起了職業教育,并在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課程設置、辦學模式等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使我國早期職業教育呈現了社會性、平民性、實踐性、育人性等可貴的思想特色。這些特色雖然是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折射,但至今仍然閃耀著時代的意義與光輝。
職業教育;實業;緣起;思想特色;近代
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充滿動蕩與變革的時期。“中國向何處去?”這一與民族生死攸關的問題嚴酷地擺在了國人面前,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憂患的主題。從此,中華民族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開始了“救亡圖存”之路的艱難跋涉。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正是與“救亡圖存”這一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的,是伴隨著學習西方的潮流而興起的,也是緊隨著“救亡圖存”這一急切問題的解決而逐步成熟的。
一、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緣起
(一)民族工商業的崛起,為職業教育的興起奠定基礎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國門,中國開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無論是歷史的選擇、政治的要求,還是社會的需要,都疾呼發展實業以自強。為此,在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影響下,洋務派以“富國強兵”為目的,開始大力興辦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同時,為了適應軍工工業和民用工業的發展,還設置了一批軍工性質和實業性質的學校,開始了軍事技術教育特別是實業教育的實踐。
甲午戰爭后的《馬關條約》,允許外國商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建立工廠,使我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重創。但另一面,這也增強了中國民族資本家團結的凝聚力,從而以各種形式籌措資金創建工廠。據統計,從1895—1911年,官方投資總額為2 544萬元,私人投資總額為12 242.9萬元,共創辦企業786家,其中,官辦58家,官商合辦31家,官督商辦3家,商辦694家。[1]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專制統治,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迎來了“鼎盛時期”:一方面,因為西方列強忙于戰爭,無暇顧及中國市場;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工業剛剛起步,市場競爭并不強烈,且西方列強因戰爭急需戰略物資,這給我國民族工商業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據統計,從1913年—1915年,平均每年有41.3家工商企業在農商部注冊,遠遠超過1904年—1908年年均注冊21.1家的速度。[2]
民族工業的大力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迫切需求有實際能力的人才,以提高生產能力。但是,當時學校的實業教育卻遠遠落后于這一需要,所培養的人才難以適應大工業生產的需求。穆藕初對這一現象感嘆道:“吾國各業之不振,皆由于缺乏適用人才,并缺少獨樹一幟之人才耳。”[3]為企業提供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的職業教育便因此而被呼吁。
(二)教育與實際生活脫節,呼喚以職業教育解決謀生
近代之初,伴隨國民的覺醒,民族工業的進步,加上歸國留學生帶來的新教育理念,中國新式教育得到了發展,中小學的課程設置開始注重與實際生活的聯系,開設了一些實用課程,還設立了具有職業教育性質的實業學校。然而,這些課程在實施的過程中,并未達到預期的結果,并很快暴露出問題:學校教育重書本輕生活、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十分嚴重。進步教育家黃炎培敏銳地觀察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人不能舍此家庭絕此社會也,則亦教之育之,稗處家庭間、社會間,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適宜的應付”,[4]但我們的學生卻是“往往受學校教育之歲月愈深,其厭苦家庭鄙薄社會之思想愈烈,扦格之情狀亦愈者”,其結果是“……習算術及諸等矣,權度在前弗能用也;習理科略知植物科名矣,而庭除之草不辨其為何草也,家具之材不辨其為何木也。”[4]以當時實業界需求人才的類型、品質、技術管理素質、動手操作能力等多方面要求來衡量,普通教育雖也培養出不少畢業生,但不具備專業素質,無法供實業界使用;而實業教育所培養的畢業生,因只懂書本知識不會應用操作、職業素質太差也難為實業界所歡迎。大量畢業生涌入社會成為無業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如何使學校教育適應于社會生活、改變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狀,培養實業界急需的人才,成為當時教育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也為職業教育提供了催生的土壤。
(三)國外先進經驗,為我國早期職業教育的創辦提供思想啟蒙
1912年1月1日,中國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歷史舞臺,對教育進行了調整與改革。蔡元培借鑒西方經驗,就中國教育與實際生活嚴重脫離的現狀提出“實利主義教育”。機緣巧合的是,在蔡元培提出“實利主義教育”后不久,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創始人黃炎培針對教育與實際生活脫離的問題開始了自己的調查研究。他于1914年辭掉江蘇省教育司司長的工作后,以記者的身份對國內25個市縣的88所學校進行了詳細的調研。1915年,他又以隨行記者的身份去美國考察,僅兩個多月的時間,對美國25個城市的52所學校進行細致的考察,切實認識到職業教育是“方今之急務”。1917年,黃炎培等人通過對日本和菲律賓教育情況的考察,更加感受到職業教育對國家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量,堅信職業教育是解決中國現狀的重要對策之一。
與此同時,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另一位創始人顧樹森,在研究了國外職業教育后,于1917年寫成了《德美英法四國職業教育》一書及系列文章,具體介紹了德美英法四國的職業教育狀況,尤其以對各國職業教育學制的宣傳為重點。這些為我國早期職業教育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許多教育家為尋求救國之路紛紛介紹國外先進的教育思想與實踐。特別是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引入,對當時的中國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成為中國近現代之初職業教育興起的重要思想淵源。
二、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產生與演變
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產生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其根源卻是“舶來品”。19世紀晚期,西方職業教育思想開始在我國萌芽。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隨后,王韜、鄭觀應等人建議設立實業學堂,培養實用的人才,但是這些建議并沒有付諸實踐;后經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努力,創建了一批實業學堂,如:農務學堂、茶務學堂、蠶桑公院等;1903年,張之洞又主張“實業學堂所以振興工商各項實業為富國裕民之本計,農工商各項實業學堂以學成后各得治生之計為主”[5],該主張雖沒有明確“職業教育”,但實質上就是職業教育。1904年,學部頒布《奏定實業學堂通則》,形成了簡易實業學堂(三年)、中等實業學堂(四年)和高等實業學堂(三年)三級體系,為我國早期職業教育提供雛形。只是由于條件的不足,該通則沒有實行。1911年,陸費述在《教育雜志》上提出:“國民程度之高下,恃國民教育;國民生計之贏細,恃職業教育耳;國勢之隆替、教育之盛衰,厥惟人才教育。”[5]這是國人首次提出“職業教育”的概念并以書面的形式出現。此后,黃炎培、蔡元培及顧樹森等人努力探索實業與教育相結合之路。
(一)初步探索期
鴉片戰爭的爆發和西方列強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傳統教育也相應遭遇沖擊,一部分具有先進思想和懷揣救國理想的人士開始探索救國之路,向西方學習成為了潮流,我國實業學校開始創辦。因此,恰恰是在19世紀中葉民族生存遭遇危機的背景下,我國近代實業教育正式拉開序幕。
鴉片戰爭的慘敗,洋務派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一方面學習西方,把開辦洋務學堂、培養人才作為自強救國的主要途徑;同時,承傳著儒家的“經世致用”,堅持“中體西用”。但實踐證明,在不改變封建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只學習西方器物層面的技術難以達到自強御侮的目的。為此,維新改良派呼吁: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不僅是器物層面如洋槍利炮的先進,更要看到其背后所隱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制度因素。在改良派的推動下,1902年,《壬寅學制》頒布(即《欽定學堂章程》),這是我國近代第一個較完備的學制。該學制雖然沒有實行,卻使人們對實業教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904年,《癸卯學制》(即《奏定學堂章程》)頒布,這是在全國首次實施的學制。該學制第一次在法律意義上確立了實業教育體系,標志著實業學堂被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之中,其對實業教育的完整規劃,使實業教育得以迅速發展。據1909年第三次教育統計,全國有初、中、高等實業學堂(含預科及其他)254所,學生數達16 649人。[6]
(二)初步調整期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實業界對人才的強烈需要,直接對當時學校教育的人才培養提出了呼喚。1912年2月,蔡元培發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提出公民道德教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美感教育等教育主張。他認為,中國資源豐富,只是社會各界受傳統觀念的束縛,一直忽視實業教育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從而導致畢業即失業、所學非所用的現狀。“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寓于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特別是,“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之多,而國甚貧”,因此“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7]
在蔡元培提出的包括實利主義教育在內的“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的基礎上,經過社會各界人士的努力,1912年,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壬子癸丑學制,該學制對實業教育做出了更為完備的規定,推動了實業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民國元年,全國有甲種實業學校共79所,學生14 497人;乙種實業學校346所,學生17 257人。民國二年,全國有甲種實業學校82所,學生10 256人,乙種實業學校399所,學生19 534人。”[8]
(三)正式確立期
從清初“經世致用”思潮的興起到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改革,從維新變法到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實業學校紛紛興起,實業教育得以不斷發展。但是,在實業教育實施過程中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引發社會的日益不滿:實業教育內容脫離實際生活,所培養的畢業生在素質上難以滿足實業界需求;工商業主因找不到合適的人才,不得不高薪聘請洋人,而受制于洋人。人才供需的巨大矛盾引發了清末民初人們對普通教育及實業教育的批判,導致了人們對實業教育制度的失望和懷疑,以及對職業教育思想和制度的提倡。[9]在此形勢下,1917年6月,黃炎培、顧樹森等人在對西方教育職業教育深入學習和考察后,聯合實業界人士在上海發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將實業教育正式改名為職業教育,標志著職業教育的形成。
顧樹森先生還通過對國外職業教育的考察,認識到實業教育與職業教育的不同,進而對職業教育的內涵做出了全面的分析:(1)職業教育專為多數不能升學兒童補習關于各種職業上之知識技能;實業教育專為少數升學之子弟習農工商之專門教育。(2)職業教育專以養成一般生徒有相當之職業為目的;實業教育專以造就實業界之中堅任務為目的。(3)職業教育之學科,多在技術方面,故偏重實習;實業教育之學科又含學理的性質,理論于實習并重。(4)職業教育所以補普通教育之不足,范圍廣而程度淺;實業教育所以發達農工商各種之實業,范圍狹而程度高。[9]顧樹森總結了世界各國教育分普通教育、專門教育、職業教育三種。大部分國民在受完最低一級普通義務教育后,都要轉入職業界謀生。為此,各國在普通教育終了后為對這部分不再繼續升學者特設一種制度來實施職業教育。這種制度在國民義務教育之上,是普通教育的結束,可以為一般國民謀生,可同時增進國民生產能力。顧樹森主張改革中國現行學制,把職業教育制度列入學制的適當位置。[9]
在這些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18年6月,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了一所專門的職業教育機構——中華職業學校,顧樹森出任該校的第一任校長。中華職業學校成為中華職業教育社實施職業教育的成功典范。
(四)孟祿來華與《壬戌學制》,指明了我國職業教育的辦學方向
新文化運動之初,美國教育家孟祿等人多次來中國講學、進行教育調查,從事文化交流活動。1921年,正值國內教育改革、新學制的醞釀時期,孟祿來中國積極參與其中。孟祿在對我國教育的調查中,發現中等教育是當時整個學校制度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并就此提出三項改革建議:(1)延長中等教育的修業年限,改為6年制;分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兩部分。(2)實施選科制。他認為,設置中學課程應該充分考慮社會和學生的需求。開設選修課的目的是使學生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來自由的選擇課程。(3)增加職業教育,滿足學生就業需要。他建議中學改為6年制后,前三年為普通科,后3年為職業預備科。
孟祿對還對教學法的改革提出建議。他多次批評道:“中國研究文學方法較為可取,唯研究科學方法尚欠精密。”“書本之講習似乎太多,實習之訓練似乎不足。”[10]“學而不行,等于不學。”[11]孟祿認為,學校中普遍存在著上完一門課也就代表著這門課結束的現象,根本就沒有考慮到實際應用,這一點嚴重違背求職的原則。他主張,職業學校的創辦應該遵循下列五條標準:(1)接受過職業教育的人,其謀生能力得到提高;(2)學生所生產的產品,在社會有銷路;(3)職業學習與教育必須相統一;(4)職業教育的工藝和方法應與時俱進;(5)利用地方特色。中國的職業教育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職業學校只教給學生如何使用機器,而這在工廠里卻是花幾個小時就能學會的,何須在職業學校里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學呢。
孟祿對中國教育的調查與分析,不僅推動了我國教育制度的改革與創新,特別為中國近現代之初的職業教育指明了發展方向。1922年的《壬戌學制》,便是20年代初期我國教育改革的一個重大成果。《壬戌學制》就職業教育作了如下規定:把實業學堂和實業學校改名為職業學校;將普通學校、師范學校和職業學校的課程綜合為一體;小學高年級可以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加開職業教育課程,初級中學、高級中學必須設立職業教育科;有兩種教育機構可以開展職業教育:一種是中學機構開設的職業科和職業課程,另一種是專門開設的職業學校和專門學校。另外,該學制提出“謀個性之發展”的職業標準,直接規定了職業教育的目的。
可見,《壬戌學制》預示著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中國近代教育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之后,職業教育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迅猛發展。1920年,全國共有531所實業學校,經過3年的時間迅速發展到842所。
三、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總體特征
(一)職業教育的社會化
我國近代的職業教育是伴隨生產發展和社會變革的需要而興起的,因此,滿足社會發展需要是職業教育的出發點與歸宿,它體現在職業教育的招生、課程設置、培養規格和專業設置、辦學方式等各個方面。
作為中華職業學校的創始人,黃炎培曾多次強調:“辦職業教育,是絕對不許關了門干的,也絕對不許理想家和書呆子去干的”[12],職業教育的社會化即“辦理職業教育,必須注意時代趨勢之應走之途徑,社會需要某種人才,即辦某種學校。”[13]職業教育課程的設置應“要看職業界的需要;定什么課程,用什么樣的教材,要問問職業界的意見”[12],“完全須根據那時候當地的狀況”。[12]在聘請教員時,他認為要聘用有實際經驗的人,“有時聘請教員,還要利用職業界的人才”[12],職業學校校長除了具備德行、經驗、熱誠和學歷以外,“社會活動力”也非常重要。
在黃炎培看來,實業界之所以找不到合適的人才、畢業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工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職業教育的辦學沒有考慮到社會的供求關系。黃炎培認為,社會性是職業教育最重要的精神,職業學校“最要緊的一點,譬如人身中的靈魂,‘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什么東西呢?從其本質來說,就是社會性。從其作用來說,就是社會化。……職業教育機關唯一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社會化。”[14]
在職業學校創辦之前,顧樹森等人還曾對國民學校學生家庭做了詳細調查,發現在學生祖輩中,從事鐵工和木工行業的人數最多,而社會對這兩種行業的人才需求量較大,因此,在職業學校剛成立時便設置了木工和鐵工兩門學科。另外,顧樹森通過查閱近幾十年來江蘇省教育會的海關貿易資料發現,琺瑯和紐扣的進口數量在不斷增多,國內可以較容易地進行這一技術的生產,于是1919年上半年,在中華職業學校設置了琺瑯科,培養此項專業的人才,促進琺瑯制造業的本土化,以抵制日貨。
中華職教社是以民間力量成立的教育團體,教育界的知識分子是其中的核心力量,同時,也得到了民族實業家的鼎力相助,如金融界的宋漢章、錢新之、陳光甫,紡織界的穆藕初、聶云臺、張謇,新聞界的史良才和南洋華僑陳嘉庚,等等,都是職教社的永久社員。這樣,在中國首次實現了教育界和實業界的合作。也正因為實業界的支持,不僅使得職教社得以屢屢渡過所遇的經濟難關,取得卓著成效,而且,在社會上也享有了一定的聲譽。中華職業教育社從創辦到發展的幾十年里,定期邀請教育、金融、工、商各界專家集會,以了解社會需求和聽取各界對學校畢業生的反映,促進職業教育的不斷改進與發展。
(二)職業教育的平民性
職業教育是面向社會的,而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是平民,因此,開展職業教育,必須實施平民教育。
黃炎培作為近代職業教育的倡導者,他認為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這集中反映在他的平民教育思想里。當他看到社會上還存在著為生計而恐慌,大量的失業失學青年為生計而忙碌的現狀時,他極力倡導興辦職業教育,試圖通過職業教育的大力推廣,來改變中國當時所面臨的難題,以利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在他創辦職業教育期間,雖然不同時期職業教育活動的重心有所不同,但他堅持職業教育的平民性的終極目標始終沒有變過,“因勞工占社會大多數,一切問題,皆以大多數的平民為目標”,于是教育“安得不重視平民教育?”[14]他選定上海市西南區作為中華職業學校的校址,也是因為“上海之西南區,民之貧困無業者,較他處之多。”[13]在他看來,職業教育就是要來“解決平民問題”。[14]
黃炎培是我國20世紀20年代前后對農村進行教育改革的主力軍,他將自己的教育平民化思想付諸于實際活動。他認為:“社會的重心應該在基層而不在上層,社會的組成是以人民為基本的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會健全,必先注意人民,如果只注意到政府,不關心民眾的教育和民眾的建設,這樣的社會是很危險的。如: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和民生都是以人民為主的。因此,與做官相比,我更愿意做教育事業以服務社會。”[15]黃炎培在江蘇徐公橋等地展開農村教育實驗,探索職業教育的發展道路,從理論與實踐方面都對農村教育改革做出了具有開創意義的探究。
在黃炎培的積極倡導下,近代職業教育的一批發起者都堅持走平民化的道路。如,顧樹森主持中華職業學校工作期間,確立的招生原則是“應收寒素子弟求學,費用務使減輕。”[13]中華職業教育社還創辦了很多職業補習班,目的是幫助那些失業失學人員以及在職人員提高文化知識和基本技能水平。
(三)職業教育的實踐性
近現代之初中國教育在教學上強調實踐性,這與杜威及其學生五四期間來華的教育演講及陶行知“教學做合一”觀點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作為與實際生活有著最直接、最緊密聯系的職業教育,更應該重視學生職業實踐活動的參加和職業技能的訓練。為此,中國早期職業教育家黃炎培、顧樹森等人在職業教育的實施過程中一直堅持實踐性,中華職業學校就是典型的表征。
以黃炎培、顧樹森為代表而發起的中華職業學校,目的是為工、商界培養管理人才與中等技術人才。學校確立的教育方針之一就是注重學生的實習,力求使學生掌握“純熟之技能”,所學知識真正能“學以致用”。學校從1918年到1952年的34年間,共辦過土木科、鐵工科、商科等16科,其中,鐵工科(后改為機械科)辦了34年,時間最長。以該校1937年制訂的“機械科課程表”為例,課程的總體情況是:職業中學分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兩個階段,初級階段開設10門普通學科、3門職業專門科、1門職業級本科即工程實習,其中,前兩個學期、三四學期、五六學期的工廠實習課程占總課程的百分比分別是40℅,33℅,25℅;高級階段開設8門普通課程,5門職業專門科、6門職業級本科,其中,前兩個學期、三四學期、五六學期的工廠實習課程占總課程的百分比分別是33℅、26℅、27℅。同時,隨著年級的增高,職業專門科和職業級本科的課程門類也成正比例增長。[16]
中華職業學校對于學生實習的重視不僅表現在課時的安排上,還體現在學校為學生努力創造實習條件、加強對工廠實習的管理上。該學校設置了鑄工、鉗工、木工、鍛工以及機械工等實習科目,近200多名學生可同時在工廠進行操作實習。在每個實習場所都配有導師,主要負責訓練學生和管理工場的大小事務。在實習過程中,導師不僅要檢查學生制造的產品,還現場提出問題,以增強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
(四)職業教育的育人性
職業教育的基本職能是要滿足人們求生的需要,使人獲得謀生的基本技能,同時,職業教育還要滿足人們自身發展的需要,注重職業道德的養成,只有這樣的職業教育才是完整的職業教育。在我國近代職業教育創辦過程中,黃炎培、顧樹森、鄒韜奮等人都強調在職業教育中學生職業道德的培養。顧樹森先生曾明確提出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培養青年身體、意志、情感、智力各方面,使他平均發達,將來適宜于職業界而能自謀生活,同時并養成他有服務社會精神,謀共同生活的幸福。”[17]學校提倡在掌握“純熟之技能”的同時,學生還必須具有“善良之品行”,注重培養學生“自治,提倡共同作業,養成其共同心、責任心,及勤勉誠實克己公正諸美德”,從而成為足以“立身社會”的“善良之公民”。
在我國近現代之際的社會背景下,人們以“讀書做官”為榮,以“讀書謀事”為恥。所以,雖然職業教育在西方已經發展,但在20年代的中國,那些頑固派卻對職業教育深惡痛絕,并把它稱為“作孽教育”、“吃飯教育”。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一般的青年也對職業教育不屑一顧。也正因為如此,黃炎培才被當時所謂的“正統”教育家視為“飯桶”教育家。針對這一情況,黃炎培大力倡導“敬業樂群”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要用職業道德觀、價值觀等來消除“讀書做官”、“勞心者治人”等封建思想對人們長期的束縛,努力培養出有一技之長、創新精神和有服務精神的社會棟梁之才,借此來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生計問題。“敬業指對所習之職業具嗜好心,所任之事業具責任心”,“樂群指具優美和樂之情操及共同協作之精神。”[13]他還認為,職業教育能夠增加社會財富,并能夠調整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激發人們創造力、事業心以及工作積極性的重要動力就是對職業的理解、熱愛和強烈的興趣;職業教育應該促進學生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的思想觀念的形成,養成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遠大的社會理想,使之成為“良善的社會公民。”
鄒韜奮對我國近代職業教育提出過全面的、系統的思想。他認為,職業領域所需要的人才絕不僅僅是掌握理論知識和方法,良好的職業道德情感和職業素養在職業中更為重要。鄒韜奮認為,對學生的“職業指導”是長期的工作[18],它分為職業陶冶期和職業訓練期兩個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教師要經常提點、潛移默化,促成學生道德行為規范和職業規范的養成。
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快速的發展,但是,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一些行業開始出現萎縮,對職業人才的需求也大量減少,很多求職者喪失了信心。針對當時的這種現狀,鄒韜奮經常引導青年們積極改變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樹立職業信念與信心,培養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鼓勵青年們朝著光明前進。他還倡導青年根據自身特點去尋找適合自己的職業,找準定位,量力而行;號召廣大青年對待工作要有滿腔的熱情,“樂吾所業”,“對于所做之事,從不肯忽略,是即服務之徹底精神,其事業之顯著,宜也。”[19]
綜上所述,在近現代之際中國社會動蕩多舛的時期,黃炎培、顧樹森等一批職業教育的倡導者們,懷揣著“教育救國”的理想并身體力行,在建立職業教育制度、確立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探索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及辦學模式等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與嘗試。這些努力與嘗試,使中國職業教育在當時艱難的局勢下得以起步并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至今仍閃耀著時代的意義與光輝。
[1]杜拘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33.
[2]鐘祥財.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家經濟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59.
[3]黃嘉樹.中華職業教育社史稿[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8.[A].穆藕初先生演講實業上之職業教育觀[J].教育與職業,1918(7).
[4]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教育文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4,14.
[5]舒新城.中國職業教育思想小史[J].教育與職業,1928(100).
[6]李藺田.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簡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15.
[7]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8]民國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M].上海:開明書店,1934:375.
[9]劉桂林.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30,123,147-148.
[10]孟祿博士與山西閻督軍之談話[J].新教育,1922 (4):634.
[11]孟祿.教育與實業之關系[J].新教育,1922(4):587.
[12]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征求同志意見[J].教育與職業,1925(71).
[13]田正平,周志毅.黃炎培教育思想研究[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238,242,235,243.
[14]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488.
[15]黃炎培.四十年來服務社會所得的甘苦[J].國訊,1942(302).
[16]唐群.近代職業教育課程內容的進步性及特色的分析[J].大同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3).
[17]顧樹森.職業教育種種問題的研究[J].新教育,1922(4).
[18]中國韜奮基金會韜奮著作編輯部.韜奮全集(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90.
[19]中國韜奮基金會韜奮著作編輯部.韜奮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95.
[責任編輯]金蓮順]
尹艷秋,女,蘇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學原理;許念英,女,蘇州大學教育學院2013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學原理。
G719
A
1674-7747(2015)16-00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