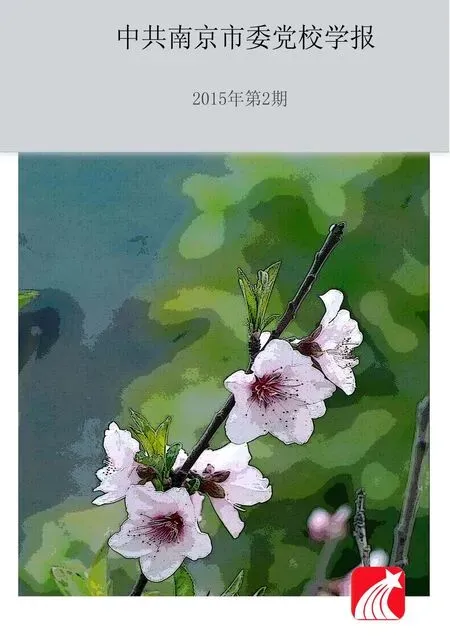和諧社會視角下公共意識培育何以可能?
黃 琴
(蘇州工藝美術學院思政部 江蘇 蘇州 215104)
?
和諧社會視角下公共意識培育何以可能?
黃 琴
(蘇州工藝美術學院思政部 江蘇 蘇州 215104)
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應當在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尋求公共意識雙向建構的可能性。社會公共領域的不斷擴大和公共生活的豐富實踐為公共意識的培育提供了領域(空間)的可能性;公民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公民社會意識的覺醒使公共意識的培育具備了意識準備的可能;倫理的內攜、網際的支持、人際的傳承(傳播)的相互補充和交融增加了公共意識傳承(傳播)的現代性和廣闊性。
公共意識;培育可能
構建和諧社會無法回避“公共性”的問題,也無法回避對公民公共意識的考量。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任務下,社會的和諧發展與個體的公共意識覺悟的高低及行為的養成關系密切。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社會性或群體性存在,公共生活是人的社會生活的基本樣式之一,正是社會轉型帶來的由私人生活向公共生活的轉型,才為構建理性的、民主的、平等的社會關系與和諧社會結構提供了重要條件,沒有真正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就難有公共意識的現代生成,而沒有市場社會催生就沒有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
目前對公共意識培育的基本哲學立場,大致可以分為個人權利向度與公共責任向度兩種類型,但是這兩種向度的研究在理論和實踐中不能很好地整合。因此,和諧社會建設背景下,應當在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尋求公共意識雙向建構的可能性。社會公共領域的不斷擴大和公共生活的豐富實踐為公共意識的培育提供了領域(空間)的可能性;教育的不斷完善,公民社會意識的覺醒使公共意識的培育具備了意識準備的可能;倫理的內攜、網際的支持、人際的傳承(傳播)的相互補充和交融增加了公共意識傳承(傳播)的現代性和廣闊性。
一、公共領域(空間)生長的可能性
(一)社會的公共領域
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已經具備公共意識培育的個體基礎和集體基礎。個體基礎是指具有自我行動、自我決定、自我選擇的理性意志的成員,集體基礎是指有別于傳統的“虛幻集體”的真實集體,這種真實性體現在:已經存在著依托市民社會又獨立于政治國家、介于國家政治權力和市民社會之間并聯結溝通兩者的“中間地帶”,也存在著獨立于體制之外凝聚公共意識的公共場所、公共傳媒、社團組織和社會運動等公共空間為外在形式的社會交往和文化批評領域。[1]具有自我理性意志等特征的個體成員以普遍性的公共倫理為基礎、以公共善和公共正義為共同目標組成了真實的集體,進行公共協商、倫理交往的公共實踐活動,使社會的公共領域得以顯現,社會的公共領域成為現實。
社會公共領域的生成,為公共意識的培育提供了最堅實的“母體”:1.保障參與者在雙向或多向的信息交流中實現充分溝通;2.公共領域紙媒、流媒、新媒體、社團組織和社會活動等多樣的媒介形式提供了廣泛的協商基礎;3.由“私人”組成的“公眾”能夠通過公開、平等而自由的協商達成共識,達成共同理性;[2]4.公共領域的存在激發公民的參與意識,強化公民的理性意識,養成公民的公共精神。“在公共領域中,至少在自由的公共領域中,行動者能獲得的只能是影響,而不能是政治權利。……但只有當這種輿論政治影響通過民主的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建制化程序的過濾、轉化成交往權利、并進入合法的立法過程之后,才會從事實上普遍化的公共意見中產生出一種從利益普遍化的角度出發得到了檢驗、賦予政治決策以合法性的信念”,[3]這就說明公共意識只有在公共協商和倫理交往中才會得到強化并發揮作用。
公共領域作為個體討論公共事務的場域,具有凝聚社會力量、整合群體認同的功能,從而為公共意識的培育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合法性的時空基礎,也保證了公共意識傳播以及和諧社會公共生活運行所需的合法性資源基礎。
(二)學校、社區等公共領域
學校、社區等作為重要的公共領域,幫助個體在公共生活的實踐中自覺理解和認同公共意識,強化公共意識,傳播公共意識。
以公共交往為基本的生活實踐賦予學校、社區等以公共領域的特征,個體在學校、社區等的公共領域中由私己領域走向公共領域,學校、社區等的公共生活給公民帶來理性、民主、平等的道德基礎,也育化為公共意識。在教育公共性的正確導向下,個體可以通過參加學校、社區等的各項公共活動、志愿者服務等形式,強化為社會公共服務的意識,積累公共生活的技巧經驗,感受個體與社會相互依賴的社會情感,體會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公共意識發揮的效能感,形成和諧的人際交往和共好的社會公共領域。
學校、社區等公共生活是培育公民公共意識的重要場域,幫助個體理解、認同公共生活的基本價值、公共善的意涵。學校、社區等公共生活本身就是培育公共意識、公共善的重要實踐,公共意識的知識性教育在學校、社區等公共生活的實踐中不斷被理解、接納、強化,同時也為公共生活與公共意識培育之間的奠定了合法的倫理基礎。[4]個體在學校、社區等公共生活中的實踐不僅對公共意識的培育有著重要的預備作用,同時又因為學校、社區等公共生活時刻與其他的社會公共生活有著密切聯系,各個公共領域的聯結更加有助于強化個體的公共意識和擴展為全社會的公共意識。
二、意識準備的可能性
(一)教育的可能性
當個體還未有獨立自覺的公共意識時,教育對公共意識的培育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學者金生鋐認為:教育是一種超越任何利益集團的由公共價值導向的以擴大公共利益為目的的實踐,具有公共善的本質。是教育,幫助個人獲得個人利益的福祉,更幫助個體站在公共立場上去為他人的福祉及社會公共利益付出;是教育,幫助社會實現相互合作、實現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相互統一;是教育,成就具有公共德性、平等意識和民主意識等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公民;是教育,培養個體通過公共參與,形成自己的公共立場或觀點,發展出自己觀察周圍事務的判斷力和道德感,學會以正義觀或公共善而非自己的利益偏愛實施自己的社會行動,學會與他人相互協商的理性精神,學會履行公共職責和義務。[5]
教育是一個公共部門,受教育是公民的一項權利,教育的公共性在于堅持通過“公民共同體”“共同維護”“公共價值導向、擴大公共利益目的”去進行的“公共事務實踐”。[6]公共善既是教育的本質,也是公共意識的基石,教育幫助個體進入公共生活并學會與他人、社會、自然和諧相處和合作,教育的公共善幫助個體認識公共善并擴展公共善,在人際中傳遞公共善。可見公共意識是通過教育來生成和傳遞的,“教育使個體在縱向上共享人類的經驗傳統,使得個人通過人類的共同善而發展自己,在當下的范圍內,使得每個人能夠享用其他人的能力發展所帶來的善”。[7]因此,借鑒他的觀點,筆者認為在捍衛和發揮教育的公共性前提下,教育是實現公共利益和培育公共意識的根本方式,教育也是通過公共善的意識傳播助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支柱。
(二)個體意識的自覺可能
公民個體的公共意識自覺不僅有利于自身適應和諧社會建設公共生活的要求,成為公共人,同時也有利于保障現代社會公共生活的有序運行,從而維護構建和諧社會所需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
公共意識的培育與每個公民的個體意識密切相關,因為公共意識是個體對公共利益意識的重疊和抽象,同時也只有當公共意識在每個公民的個體意識中具體化以后,公共意識的培育才成為可能。那么,公共意識的生成是否會“覆蓋侵占”個體意識的發展呢?在自由主義理解的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個體具有自主自決的主體性且不依附于整體而存在,但只有當具有同等價值、尊嚴和權利的個人出于自覺和自愿結合為共同體而存在時[8]社會才不至于凌駕于個人之上。“一個公正、和諧的共同體,必定是充滿愛的社會;而一個人人之間充滿愛的社會,也才可能是一個公正、和諧的共同體”。[9]
馬斯洛認為“民主、自治的社會必須由自我行動、自我決定、自我選擇的成員組成,他們必須具有自己的觀點,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我意志”。[10]按照現代美德倫理學的理論,一個有完善人格和美好品質的人在任何情景下作出正確的道德選擇,都會把私人生活中的優良品質推擴到公共生活中。[11]漢娜·阿倫特說:“人身上的這種個性因素,只能在一個有公共空間存在的地方顯現出來。而這就是公共領域所具有的更深刻的意義,它遠遠超出了我們平常所知的‘政治生活’這個詞所意味著的東西。公共空間也是一個精神性領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馬人成為humanitas(人性)的東西才在其中顯現出來”。[12]事實是個體意識和公共意識兩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得益彰。公共意識培育在強調對個體私人性超越而追求公共意識的同時,也正是對個體主體性與意識的張揚;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同時,也是對個體私人性利益合理性的肯定;在培育個體對公共利益認同和維護的意識同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也保障對公民私人領域的尊重以及私人性意識的寬容。
公共意識的產生必須具備公共性(為他人)、道德心(為他人盡義務)、合理性(遵守法律規范)三要素。[13]公共意識的產生在于個人要有他人感(他人情懷),即道德利他基礎,人要有對他人(情感、利益、要求)的顧及和關心,是人走出自我、走向他人的意識,其指向的重點始終是自我之外的他人。[14]因此,和諧社會視角下公共意識的培育關鍵在于個體能否具有以利他方式對公共領域的關注、維護、改善等的意識和觀念。“那些能夠充分理解自身的道德標準內涵的學生更有可能把這些標準用于實踐,會為那些為了私利犧牲道德標準的想法感到不安”,[15]在對公共生活領域的有關規則規范完整理解、對其內在依據充分掌握后,人性內在的提升自覺與學校公共生活的實踐幫助個體建構起公共交往與實踐的內在合理性,使公共意識意識自覺強化。
個體并非是公共意識培育和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被動客體。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要求公民公共化,即不是只充當被動員、依靠、教育、領導的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判斷、沒有個人意志的蕓蕓眾生,而是需要個體沖出自己的個人私域,在公共生活世界中成為有自由思想、有獨立判斷、有個人意志的社會成員。公民公共意識的個體自覺,就是明確個體的主體地位,明確個體的自主性、獨立性和創造性都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機構成部分,個體自覺地以人的主體性價值作為公共意識培育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歸宿,只有充分凸顯人的主體性價值,和諧社會才能避免非理性、盲目性,并彰顯人文關懷。如此,和諧社會建設才能奠基堅實的人文價值基礎。如果說個體的法律身份是自然國家給予的,那么個體需要把這種務虛意義的身份通過政治、倫理和社會參與的方式在現實中彰顯。公共意識首先在于對自身法律公民身份的意識覺知和實在運用,然后是對公民政治身份和倫理身份的自覺意識(公共理性)。
在現代生活中,個體參與公共協商、倫理交往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即:1.個體參與有真實信息的交流和流動和機制,利于聚合;2.個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途徑是理性的、現實的、協商的、合法的;3.個體既自由又能自我約束、既獨立又有集體責任的理性。個體要成為敢于擔負起參與公共性議題和公共性行為的公眾的有效成長因子,因為單個的個體必須在與其他個體的合作與分享過程的過渡和成長中成為有實質意義的公民。只有當個體具備了自覺與自律的意識,在面對公共事務時,個體才能對自身的行為是否符合公共領域的要求進行內審。個體自覺地提出和介入公共議題,自覺的關注公共利益并主動表達和行動,自覺形成公共行為的穩定動機。
三、傳承(傳播)的可能性
(一)倫理內攜的傳承(傳播)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傳統社會之間存在著倫理內因上的共時性與歷時性關系,傳統的“熟人社會”推崇個體的人性完善,強調群體意識,強調仁愛的情感意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僅需要個體人性更完善,也需要個體群體意識更理性,更需要個體公共意識更深切穩定,因此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公共意識的培育,不可能完全脫離傳統的倫理習慣,為更順應社會和諧、民主健全、政治文明,則要建構起傳統與現代兼容并存的雙軌倫理框架,一方面建構以公共理性為核心的新型公共倫理,同時發揚和修復傳統的以仁善規則為核心的個人美德倫理。[16]
(二)網際傳承(傳播)
大量的網絡公共參與的事實證明,網際的公共領域效應已經凸顯,網絡技術與平臺的支持已經大大擴展了實際人際交往中公共意識達成一致的廣度,并且也突破了時間與空間以及組織等的界限,公民通過網際的聚合、對話協商、公眾輿論、社會實踐的形式參與公共事務,維護公共利益,弘揚公共正義,這種以網絡媒介為中心的公共意識傳承(傳播)策略不僅拓寬了滲透渠道,也推進了國家與社會實現良性互動,還促成了市民社會中有利于國家建設、社會導向的理性實踐行動。這種由公民自覺自愿選擇的方式提高了公共意識的個體自覺的可能性,相較于主流媒介的強行滲透其效用更易接受,也更利于公共意識的傳承(傳播)。
(三)人際傳承(傳播)
借助教育,使得公共意識得以生成,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公共意識的傳承(傳播)更多的是通過人際交往達成的。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認為:1.行動主體可通過交往行動相互理解,在理解基礎上把握知識,傳播、更新、共享知識理念與價值范疇,促進主體間思想交流、碰撞,凝聚“底線”共識,在主體互動上促進公共意識的生長;2.行動主體在社會關系上的自主性與協調性有利于群體的團結和社會目標的實現,為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人們在公共生活中必然會展現共同精神面貌和共同行動,進而促進公共意識的生長;3.是行動主體的自主意識與自我規范有利于擺脫孤立的目的性,能夠使行動主體認同社會規范和價值取向,為公共意識的生長夯實共同價值導向之基礎,從而促進行動主體公共意識的生長。[17]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交往行為更加深入理性,公共交往的意識與文化傳承(傳播)功能為當今和諧社會建設和公共意識培育提供了最為廣泛和牢固的人際基礎。
具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素養群體比如大學生群體,更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其公共意識生成更有優勢,其人際傳承(傳播)的輻射性也更廣闊,個體可以通過自身在公共生活領域的自覺意識和良好示范,影響社會,通過人際、網際向整個社會傳承(傳播)公共善的意識理念、價值精神,推動整個社會的公共意識狀況的完善。群體公共意識傳承(傳播)的人際輻射作用不僅表現在當下,也會長遠地延伸到未來的社會發展。具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素養群體如大學生群體必然是社會公共意識培育的引領者、促進者,也是建設和諧社會良好公共社會秩序最直接最有效的意識培育群體。
事實上,在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國家所倡導的中國特色治國方略、堅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立場、推行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使得公共意識的人際、網際傳承(傳播)與道德建設內蘊的倫理傳承和發展相互補充和相互交融,這種相互補充和相互交融也彌合了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時的斷裂,為個體特別是大學生公共意識的培育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并使其成為有益的事實。
[1]陳付龍.中西公共意識生長的文化路徑辨析[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3).
[2]楊仁忠.公共領域與中國政治權威合法性基礎的建設[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3,(2).
[3][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3.459.
[4]葉飛.公共交往與學校公民教育的實踐建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2,(9).
[5][6][7]金生鋐.保衛教育的公共性[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7,(3).
[6]金生鋐.保衛教育的公共性[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7,(3).
[7]金生鋐.保衛教育的公共性[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7,(3).
[8][11][16]肖群忠.儒家傳統倫理與現代公共倫理的殊異與融合[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1).
[9]黃裕生.論愛與自由——兼論基督教的普遍之愛[J].浙江學刊,2007,(4).
[10][美]亞伯拉罕·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許金聲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70.
[11]肖群忠.儒家傳統倫理與現代公共倫理的殊異與融合[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1).
[12]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M].王凌云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65.
[13][14]高德勝.人權教育與道德教育[J].全球教育展望,2011,(2).
[15][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M].徐小洲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9.
[16]肖群忠.儒家傳統倫理與現代公共倫理的殊異與融合[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1).
[17]陳付龍.當代中國公共意識生長的文化觀照[J].理論與改革,2012,(3).
(責任編輯:育 東)
本文受江蘇省教育廳2010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指導項目“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公民公共意識培養研究”(2010SJD880108)支持。
2015-03-16
黃琴(1972-),女,江蘇常熟人,蘇州工藝美術學院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C915
A
1672-1071(2015)02-006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