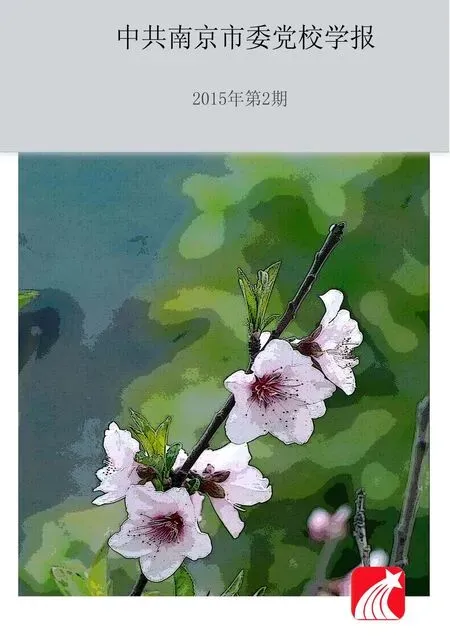東方“顏色革命”,西方“始料未及”嗎?
李愛敏
(湖州師范學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
東方“顏色革命”,西方“始料未及”嗎?
李愛敏
(湖州師范學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冷戰后20多年來,“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東方社會呈階段性、連鎖性頻繁上演,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方面大呼“始料未及”,一方面以積極的姿態介入這些國家的內政,操控的黑手鬼魅般如影隨形。從西方這種荒誕的邏輯入手,筆者力圖通過解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輸出”路線、“北約東擴”路線、“改造中東的計劃”路線與東方國家發生“顏色革命”路線之間的內在聯系,來揭露西方“‘民主輸出’——策動‘街頭政治’、‘顏色革命’——介入內政”的意識形態霸權邏輯,以警示國人認清西方國家意識形態霸權本質,強化“守土”意識。
顏色革命;始料未及;民主輸出
如果從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開始算起,到2014年烏克蘭變局和香港“占中” 行動,這種通過發起大規模群眾運動,并將訴求直接指向國家或地區政權的“街頭政治”或“顏色革命”,25年來從來沒有缺席過西方國家的身影。西方國家一方面大呼“始料未及”,一方面以積極的姿態通過各種渠道、動用各種力量全方位、迅速地介入這些國家的內政,最終使整個事變朝著符合西方國家國際利益和意識形態訴求的方向發展。因此,從所有政治變局的整個發生發展進程來看,仿佛西方國家只是在左右“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的結局方面發揮了作用和影響力,有時甚至還充當了救世主的角色。這種用偶然性邏輯來思考問題的方式,是導致二十多年來,“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一再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在世界上重演的重要原因。
一、荒誕的邏輯:“顏色革命”始終在場的西方國家總是“始料未及”
“始料未及”是在“顏色革命”發生時,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匯,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在接受中國之聲《國防時空》記者采訪時,指出“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動蕩最大的特點就是始料未及”,[1]他說,“事件發生之后,美國和西方,包括北約,只是抓住時機充分利用了這場危機。就危機本身發生來看,不管美國,歐盟,俄羅斯、中國,全世界始料未及。”[1]周明、曾向紅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與虛擬社交網絡》一文中,根據“伊斯蘭例外主義”和社會運動理論模型,并引證了許多外國學者的觀點①,指出“‘阿拉伯之春’產生之后,學術界、政界、西方情報界等均未能預測到其發生,已是人們的共識。”[2]在這之前,原蘇聯東歐當時的劇變更被全球各界稱為“始料未及”,陳樂民發表于1990年《世界知識》第1期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即是《西歐對東歐的劇變始料不及 兩德關系走向成為關注的焦點》。而發生在2014年的烏克蘭變局和中國香港“占中”行動的發展態勢好像也遠遠超出了西方學者和政界人士的預期。
這些學者所稱的“始料未及”是何種意義上的呢?筆者經過分析,總結為如下幾種:其一,事變的導火索十分平淡無奇,例如作為整個“阿拉伯之春”開端的“茉莉花革命”的導火索,是一名突尼斯的大學生小販自焚;其二,事變的群眾參與數量與參與熱情讓人始料未及,大多數國家走上街頭的人數都達幾萬、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其三,事變發生轉折的速度令人始料未及,原東歐地區的革命從最初的七個月執政黨下臺,發展到后來變成70天、7個星期、7天,而突尼斯、埃及執政長達二、三十年的威權統治者只短短一月或十數天就紛紛丟掉政權;其四,由于變局發生比較突然,后續一些國家同樣革命大多被看作是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往往容易讓人將其直覺為偶然性事件。即使有政治家和學者力圖揭示深藏于這些偶然性內部的必然性,也大多被引到從“顏色革命”國家內部去尋找原因,至多不過強調西方歐美國家在“顏色革命”期間的主導作用;其五,這些變局的革命性質花樣不斷翻新,突尼斯的變局被稱作“維基革命”,埃及的變局被稱作“Facebook 革命”或“虛擬社交網絡革命”。這些新的革命形式是信息時代的產物,它與傳統執政方式相對應而體現出來的“不可思議”,也是這種“始料未及”的思想來源之一。
這些“始料未及”給西方國家的“民主輸出”披上了隱形外衣。這樣的“障眼法”蒙蔽了許多國家當權者的心智,大多數后來被“顏色革命”所困的當權者當時何嘗不是聲稱國情不同、控制能力不同、長期執政或本國發展前景較好,而一直抱有僥幸心理。事實上,這些國家發生的政治變局從一開始就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意識形態演變戰略和路線緊密聯系在一起。而這些所謂“數量”、“速度”、“模式”方面的始料未及,也都是全媒體時代西方意識形態話語“呈現性權力”②持續放大的結果。
二、對應的路線:西方的意識形態霸權路線與東方的“顏色革命”路線
(一)相合:中東歐和獨聯體的“顏色革命”路線與西方的“北約東擴”路線
如果我們將西方歐美國家在冷戰結束以來20多年的國際戰略進行總體考察,可以發現,整個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發生“顏色革命”的路線,與美國為首的北約東擴的路線是大致吻合的。關于這一點,張中云教授也曾在《要重視“街頭政治”的效應》一文中有過簡短的表述,他說,美國和歐盟“共同推出的歐盟與北約東擴計劃,第一步是吸收前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加入,進展比較順利;第二步是瞄準獨聯體即原屬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首先是通過選舉干預更迭政權,使親俄政府變成親西方的政府,然后再分別吸收他們成為歐盟和北約的成員,使之完全親西方。”[3]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兩極格局解體之時,華沙條約組織作為與西方軍事對抗的集體安全組織已然解體,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非但未解體,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間不斷進行東擴,這條軍事上東擴的路線與西方民主輸出的路線相互配合。從中東歐到獨聯體國家,西方在這條路線上,民主東輸為軍事東擴鳴鑼開道,軍事東擴為民主東輸掃除障礙。北約在東擴過程中,不僅將原成員國從最初的12個變成如今的28個,從偏安西歐和北美的小北約成長為囊括歐洲大部分疆土的大北約,而且通過長期“民主輸出”使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奉行親西方政策。
細數北約東擴的國家,與發生“顏色革命”的版圖,幾無二致。位于歐洲心臟地帶的波蘭、捷克、匈牙利在1999年3月北約第一次東擴中加入,其中以“天鵝絨革命”為代號的捷克也正是東歐劇變時“顏色革命”的最初發源地。同樣自這一年3月起,北約發起了對阻擋北約東擴計劃的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反美政權的軍事打擊和“顏色革命”攻勢,造成南斯拉夫解體,米氏政權淪喪。而且在這次打擊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還創造了一種新的“民主話語”——“人權高于主權”。 2004年的第二次東擴批準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7個國家加入北約,至此北約將其防線推到俄羅斯邊界。同樣就在這期間,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2004年12月和2005年3月,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也相繼發生“橙色革命”(又名“栗子花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也正是自北約第二次東擴前后,“顏色革命”才成為國際社會一個高頻的“經典”詞語,成為有關國家在獨聯體地區借助非暴力手段促使政權更迭的政治代名詞。第三次北約東擴雖然在法德的強烈反對下,只批準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入盟,暫時沒有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納入,但這兩個國家所具有的在大國競爭之下的地緣命運,注定這兩個國家不再能處于平靜之中,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爭、2009年的俄烏斗氣風波、2014年的克里米亞公投,使得這兩個國家頻繁被“顏色革命”所困擾。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2007年曾明確指出,“北約東擴政策是政治倒退,是冷戰思維殘余。”而“顏色革命”又何嘗不是呢?
現在我們必須要問的一個問題是,西方策動“顏色革命”的下一個目標是哪里?
不言自明,這就是遠東的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美國、法國、德國等大國都曾不止一次利用中國臺獨、藏獨、疆獨向中國發難,這些地區的反對派力量不斷得到歐美國家精神支持和物質援助,甚至人員培訓、武器裝備。2008年以來,在西方的煽動與支持下西藏和新疆的緊張局勢不斷加劇。當下,連回歸中國后在“一國兩制”政策下繁榮穩定了17年的香港也上演了在美國編寫劇本的“占中”大戲。
由此可見,所謂“始料未及”不過是西方國家有意掩蓋其意識形態霸權戰略的煙幕,整個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都與西方“民主輸出”存在直接而內在的聯系,而美國在東方國家“顏色革命”發生時的內政干涉,是隨時準備好的戰略策略的一次次演練,從對反對派的財力支持,幫助過渡政權的維和,以及為反對派爭取所謂的政治民主、自由和人權而開展的武裝干涉,都只是為完成歐美國家意識形態霸權而預備好的不同策略手法的輪流運用而已。
(二) 相悖?:“阿拉伯之春”路線與“改造中東的計劃”路線
如果僅僅將“顏色革命”看做是資本主義陣營國家壓縮、削弱和爭奪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勢力地盤,將其視做冷戰思維的延續,則低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戰略意圖,至少美國所計劃的版圖遠遠不止于此。早在2005年,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接近尾聲之時,就有學者撰文指出,“勾勒發生‘顏色革命’的區域,可以了解美國戰略的大致走向,也可以預測將要被策劃發生‘顏色革命’的區域。主要包括:能源區域和輸油管線區域,戰略預想區域。換句話說,這些地區如果沒有確保美國利益暢行無阻的前提,可能成為美國發動‘顏色革命’的場所;沒有‘顏色革命’的可能,則須考慮發生軍事打擊的可能。”[4]這段話不僅點破了美國追求全球霸權的本質,而且指出了美國實現這種霸權的兩種策略手法。
但就阿拉伯世界的復雜性來講,這種兩手策略顯然過于粗糙,美國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就是最好的佐證。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勢力、極端民族主義勢力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常常讓美國籠罩在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危機的陰影之下。美國為首的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和武力征服都不得不采取迂回的戰略。 美國為首的西方自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所謂“改造中東的計劃”:1995年歐盟提出所謂“巴塞羅那進程”③;2008年歐美在巴黎啟動“地中海聯盟計劃”;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政府判定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敵意已經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進而布什在2004年6月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正式推出 “大中東計劃”。 其主要做法就是,以西方的金融援助為誘餌換取中東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和推進民主的社會變革,力圖通過這樣的計劃加速阿拉伯世界發生“華約集團”式的演變。
但是在整個計劃的執行過程中,西方歐美大國為了實現對阿拉伯世界分化的目的,一方面全力對整個阿拉伯世界進行“民主輸出”;另一方面為拉攏自己的傀儡盟友,平衡所謂“邪惡軸心國”和其它反西方勢力,而不惜讓民主屈就于“假共和”的威權體制。阿曼多·B·希內斯,在2014年1月20日發表在西班牙《起義報》的一篇文章中對這一點進行了深刻揭示,他指出,“帝國主義依靠其勢力范圍內現有的客觀條件,企圖歪曲社會政治訴求,將之引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道路……在阿拉伯國家的目的是扶持為新自由主義全球能源掠奪利益服務的傀儡盟友政府,無論其是否具有極端主義色彩。”[5]
該評價可謂一語中的,它將西方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改造中東的計劃”的險惡用心和西方在阿拉伯世界貫徹扭曲畸形的民主的真面目揭開。而這也恰恰可以為阿拉伯世界“顏色革命”的發生路線為何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預期相悖提供說明。西方在阿拉伯世界搬起的畸形“民主”之石誤傷了自己的“全球資源利益”之腳。
21世紀第一個10年伊始,蔓延于中東北非地帶阿拉伯國家的“顏色革命”又被稱作“阿拉伯之春”, 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近20個阿拉伯國家發生了政權更迭或被“街頭政治”所困擾。從西方期待阿拉伯世界發生“華約集團”式的革命演變角度出發,這本應是符合西方愿望的。但讓整個西方大跌眼鏡的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在阿拉伯世界設置的多米諾骨牌倒下的并不是符合美國預期的板塊。在這場連鎖式的“顏色革命”中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大多是親歐美的政府,尤其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權、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也門的薩利赫政權等。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顏色革命”發生后迅速調整策略,以犧牲對這幾個親歐美政權的支持為代價,繼續放任“顏色革命”的推進,并極盡能事地把革命引向西方最期待的敘利亞和伊朗政權。
由此,從阿拉伯世界“顏色革命”組成的完整圖景中,我們可以確定無疑地獲取的信息就是:即使阿拉伯世界政治變局的發生路線可能真的讓西方“始料未及”,卻依然是由西方世界一手締造出來的,只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事先錯估了自己對阿拉伯世界的操控能力。
西方在阿拉伯世界實際造就出來的邏輯是怎樣的呢?其一,西方為了自己的全球能源利益而采取分裂整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戰略,為利用在阿拉伯的傀儡盟友扼制反西方的各種力量而放任這些國家借“民主”之名(假共和制)行“獨裁”之實。這些親歐美國家的當政者罔顧民生,腐敗獨裁,對反對派采取極端主義的鎮壓政策,為民眾和反對派推翻這種“威權體制”埋下了伏筆。其二,西方的“擴展民主”戰略在這些親歐美的阿拉伯政權下爭取了更大的空間,盡管這些典型的“警察國家”也對民眾實行高壓政策,嚴格控制民間輿論,但都或多或少有不被嚴格控制的“虛擬社交平臺”。如,在突尼斯有大量網站被禁,但Facebook是開放的,10個突尼斯人中就有一人擁有Facebook賬號;在埃及,Facebook、Twitter等虛擬社交網絡或新社會媒體網絡則都不受限制。加之阿拉伯屬于“青年膨脹”④的世界,大量受過良好教育、在網絡環境中成長起來、又受到嚴重的失業形勢威脅的青年,最終成了借助“虛擬社交網站”平臺發動“顏色革命”的主體和中堅力量。其三,西方的維基解密曝光了美國外交官有關突尼斯政府腐敗的電文⑤,成為“阿拉伯之春”真正的推手,同時美國在阿拉伯世界推行“假民主”的虛偽面紗亦被揭開。其四,阿拉伯世界不同教派之間的矛盾,阿拉伯世界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以及各大國圍繞著中東、中亞、北非等問題上的博弈給阿拉伯世界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由于西方的自以為是而被低估。
總之,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講,阿位伯世界的“顏色革命” 都是西方“改造中東的計劃”結出的果實,并不能因為這些“果實”不符合西方國家的最初預期,就否定“顏色革命”與西方“改造中東的計劃”之間的內在聯系。
三、應對的策略:意識形態工作的戰略地位提升與戰略思想轉變
經由對西方國家策動的“顏色革命”路線圖的勾勒,反觀2014年底在中國香港上演的“占領中環”行動,一切都不該“始料未及”。如果我們仍然將其視作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起偶然性事件,就可能犯極大的錯誤。當前對于堅持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來講,務必重視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在認清西方國家意識形態霸權本質的前提下,科學評估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戰略地位,避免在國內外反對勢力的夾擊之下無準備應戰,丟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二是堅定“守土”決心,確立“有守有為”的意識形態安全戰略思想,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將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霸權攻勢推回。
(一)科學評估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戰略地位
當下的中國正成為西方輸出或策動“顏色革命”的新靶場。2014年第四季度暴發的香港“占中”事件給了中國一記猛擊,它預示著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戰車已經推近到了中國,“顏色革命”的標識也已經被西方強制性地貼在中國頭上。美國政治智庫研究員卡塔盧奇為此提供了佐證,他在題為《整個“占中”行動在華盛頓寫劇本》(Entire "Occupy Central" Protest Scripted in Washington) 的文章中爆料,“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早在2014年4月訪美時,就已和美國國務院轄下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 撰寫好‘占中’劇本。”香港反對派人士“占中”的真正目的,“并非讓香港人獲得真普選,而是將‘占中’背后、由外國勢力支持的政治陰謀集團,送上權力位置,實現將香港軟性殖民化,進一步分裂中國。”[6]
基于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必須清醒認識這場思想領域新戰役的嚴峻性。事實上,在“阿拉伯之春”的警示下,中國自十八大以來已逐步把意識形態工作提到一個新的戰略高度來認識。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八·一九”講話,提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7]這是黨中央在全面衡量、通盤考慮各方面工作緊要程度的基礎上,對意識形態工作在當下的重要地位做出的戰略性評估。這一評估既有力呼應了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意識形態工作的新要求,即“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8]又彰顯了當前時代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7]的根本性、戰略性和全局性意義。這不是危言聳聽,烏克蘭變局和香港“占中”行動發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一步覺醒:“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9]
(二)確立“有守有為”的意識形態安全戰略思想
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在新的形勢下,要想打贏意識形態領域斗爭這場硬仗,必須知己知彼,也即除了認清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霸權本質與基本策略手法外,還必須清醒認識我國自己的特殊國情,準確把握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薄弱環節,盡快實現意識形態工作由被動應戰向“有守有為”戰略思想的轉變。
所謂中國的特殊國情,主要指中國易于被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攻擊的軟肋。概而言之,堅持意識形態霸權理念的西方,會利用中國仍然未實現完全統一,利用中國仍然存在民族主義分裂勢力,利用中國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可能出現的危機與問題,利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存在的諸多結構性矛盾和差距,借機在中國煽動“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而這些深層次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和完善的。這就要求黨的各級宣傳部門必須加強思想輿論領域的“守土意識”,以主旋律和正能量引領意識形態潮流,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9]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占中”問題上的態度與做法,就旗幟鮮明地反映了處于反意識形態新殖民主義重大轉折點上的中國毫不動搖地“守土”決心。
所謂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薄弱環節,主要體現在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話語權”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將中國當前思想輿論領域的格局概括為“三個地帶”,即由主流媒體和網上正面力量構成的“紅色地帶”,由網上和社會上的負面言論構成的“黑色地帶”,以及處于二者之間的灰色地帶。由于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的縱深發展和在中國的全方位覆蓋,中國思想輿論的黑色地帶和灰色地帶呈擴大趨勢。西方國家在香港“占中”事件中,一方面在幕后進行全程策劃,對反對派和學生進行技術培訓并提供物質援助,另一方面又堂而皇之的利用由西方社會設置的國際權力話語框架對中國進行施壓,使香港政府處于不鎮壓就破壞經濟和社會發展,鎮壓就違背民主的兩難困境。
要走出這種困境,防止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就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確立起“有守有為”的意識形態安全戰略思想,并據此而構建“積極防御”的意識形態安全戰略體系。所謂“有守有為”,實質上就是一種“積極防御”戰略,這一戰略把防御和進攻辯證統一起來,在防御中有進攻,攻防結合,交替運用。守,即堅決守住和努力拓展“紅色地帶”;“為”即有效治理黑色地帶,轉化灰色地帶。半個多世紀以前,毛澤東曾經用這一戰略在軍事戰場上贏得了國內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今天,在我們的思想領域一樣處于敵強我弱、敵眾我寡、敵霸權我反擊的情況下,我們不僅要積極捍衛自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正面揭露西方意識形態霸權陰謀,而且要主動聯合第三世界國家甚至世界人民一道,爭取各種意識形態兼容并蓄、多樣并存。
綜上所述,只要中國不屈服于西方意識形態霸權之下,針對中國的“顏色革命”就遲早有一天還會到來。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講,不僅要將鞏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作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務的緊要一環,更要將意識形態工作本身作為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來抓。
注釋:
① Angela ,Joya,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Potential for Democratic Politics",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8,No. 129,2011,p.368; Erin A. Snider and David M. Paris,"The Arab Spring: U.S. Democracy Promotion in Egypt",Middle East Policy, Vol. 18,N o. 3,2011,p.49; William A. Gamson, "Arab Spring, lsraeli Summer, and the Process of Cognitive Liberation",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17,No. 4,2011,p. 463.轉引自周明、曾向紅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與虛擬社交網絡》,《外交評論》2012年第2期。
②“呈現性權力”(representation power),是一種通過生產出關于客體的影像意義、規范、價值、知識等話語,使主體得以影響并改造客體心智、習慣、思維方式與世界觀的力量。這一概念來源于后建構主義理論,主要代表學者是美國的賈尼絲·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n),后建構主義的理論核心是語言、敘述、身份和國際秩序,認為語言本身具有語言力(language power),是一種權力,語言通過表象過程造就社會現實。
③“巴塞羅那進程”,即歐盟和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西亞國家進行政治對話、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以此推動中東國家社會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
④“青年膨脹”,是指中東國家人口結構年青化現象,中東大部分國家25歲以下人口約占總人口比例50%左右,其中突尼斯為42.1 %,利比亞為47.4%,埃及為52.3 %,伊拉克和也門則分別達到60. 6%和65.4% 。
⑤2009年6月的一份電文形容本·阿里家族猶如黑手黨,控制著整個國家經濟的方方面面。另一份2009年的電文描述了在本·阿里女婿的豪宅里舉辦的一次宴會:羅馬時期的文物隨處可見;客人們享用著用私人飛機從法國南部小鎮空運來的酸奶;一只寵物老虎在花園里漫游。還有一份電文題為“突尼斯的腐敗:你的就是我的”,文中稱,“在突尼斯,只要是總統家族成員看上的,無論現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終都得落入他們手中。”
[1]“阿拉伯”變局 全世界始料未及[DB/OL]. http://military.china.com/critical2/23/20120113/16985777.html,2012-01-13.
[2]周明,曾向紅.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與虛擬社交網絡[J].外交評論,2012,(2).
[4]張中云.要重視“街頭政治”的效應[J].高校理論戰線,2005,(5).
[5]云杉.美國的“顏色革命”戰略[J]. 瞭望,2005,(51).
[6]外媒:美歐策動虛擬革命 社交網絡充滿意識形態陷阱[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8/c_126071822.htm, 2014-01-28日(阿曼多·B·希內斯.詩意的春天,虛擬的革命[N].起義報(西班牙),2014-1-20) .
[7]信蓮.美智庫研究員爆“華盛頓撰寫‘占中’劇本”[EB/OL]. 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10/07/content_18702012.htm,2014-10-07.
[8]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08-21 ( 1 ).
[9]本書編寫組.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M].北京:學習出版社 紅旗出版社,2012.9.
[10]王偉光.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N].人民日報,2013-10-8(7) .
(責任編輯:育 東)
江蘇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KYLX_0652);湖州師范學院2014年人文社科預研究項目(2014SKYY10)。
2015-03-06
李愛敏(1977-),女,黑龍江省東寧縣人,湖州師范學院政治學院講師,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D26
A
1672-1071(2015)02-00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