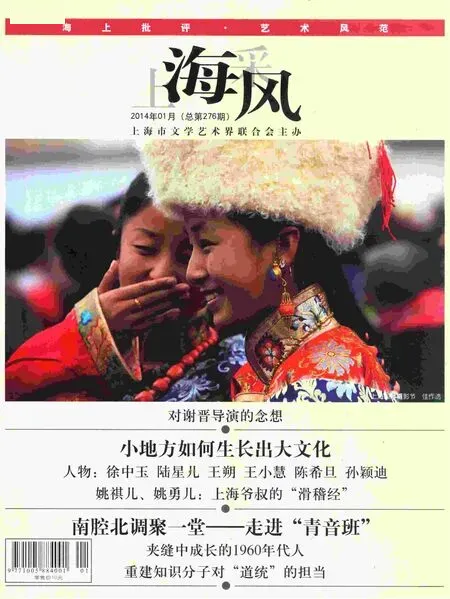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文/資中筠
上世紀五十年代,無數知識分子被“改造”過來了,包括許多大知識分子。他們到底是被迫的,還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慮?
從外部講,當時那種壓倒性的大氣勢沒法抗拒;從歷史講,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國家富強,毛澤東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幾乎打動了所有的人。大家認為,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共產黨能夠使得中國強大起來。在這種前提下,黨說我們需要改造,我們就誠心誠意接受改造。因為廣大勞動人民是那么苦,是他們養活了我們,讓我們享受優越的生活,所以我們都有一種原罪感,而且越來越自卑,只能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毛澤東講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憐蟲”。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話,將被歷史所拋棄。知識分子特別在乎。慢慢就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不斷追趕潮流,試圖經過改造進行自我救贖;每一次運動都覺得自己跟不上,認為一定是我錯了,于是在自責中更追求積極的潮流……我自己當年是“無知青年”,一直追趕到“文化大革命”。
知識分子怎么就變成這樣?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是那時還有人敢于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么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由自己的經歷,我悟出一個道理來。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兩千年皇朝時代,雖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獨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誰來繼承儒家之道?誰來解釋儒家?這個權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這就是道統。
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得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認為可以做“帝王師”,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據理力爭,即使被帝王懲罰,但是在“士林”會得到認同、尊重,甚至得到擁戴,殺了頭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師沒有“合二為一”,沒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論”。“士林”會以“道統”判斷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導師和領袖“合二為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自信。一個人如果不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話,怎么能夠堅持呢?“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要堅守,至少得自信主義是真的。
自信完全喪失了,因為判斷是非的權力沒有了,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局面。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是從蘇聯來的,列寧就是導師,斯大林也是導師。就是說,政治領袖必然是思想導師,所以知識分子就沒有自由思想了。沒有自由思想,何談獨立精神?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其實那時連審美標準也國有化了。
或問:為什么知識分子愿意繳械,不要判斷是非的標準?答案是:一個是因為愛國,相信它能夠把中國搞好;第二個是因為“世界潮流”,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代表未來,資本主義陣營代表沒落,當然要站在“歷史潮流”一邊。另外,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一種“劣根性”。有一種對于君主的歌頌傳統,我稱之為“頌圣文化”。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樣,即使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擺脫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總希望有一個“明君”出現可以救中國。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之后,“頌圣文化”就大行其道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一邊是思想禁錮毫不放松,一邊是有利可圖的商業大潮,兩下夾擊,就造成“逼良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氣都消解了。更加愿意粉飾太平,所謂歌頌盛世。
當年那些知識分子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人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已經麻木了,正義感已經非常淡薄了,對過去不可容忍的事習以為常。九十年代以后,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我發現,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來大家都過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遠處多想一點,就憂心忡忡。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圣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年學生,要理直氣壯地弘揚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現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問題是怎么樣能夠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所以,現在是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