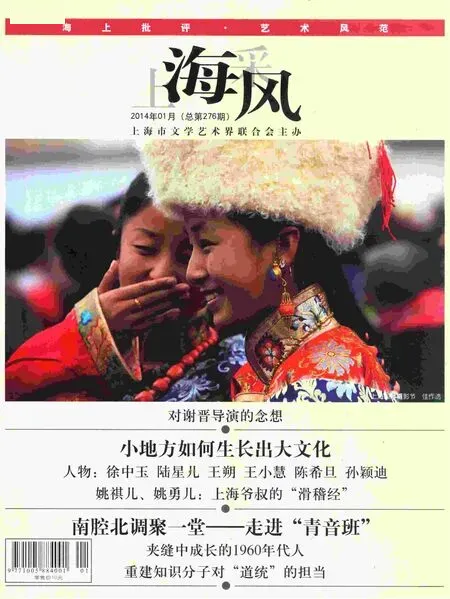語言的貧困(外一篇)
文/劉 瑜
“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新詞包括大海、高速公路、遠足旅行……大海是一種皮質沙發,當你累了,你可以說,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陣強烈的風。遠足旅行則是一種堅硬的材料……”這是電影《狗牙》的開場白,《狗牙》是一部希臘電影。這個電影說的可不是現代詩歌的創作,它講的是一個奇特的封閉家庭,但這個家庭有著極權主義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墻把房子給圍了起來。他們反復告訴三個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墻外面的世界兇險殘暴,只有高墻里才安全幸福。他們還告訴孩子,只有開車才能出門,而要學習開車,必須等到他們的“狗牙”掉落。他們家沒有網絡報紙,沒有電視廣播,沒有任何關于外界的信息。孩子們在安靜的房子里日復一日地玩著單調的游戲,當一只野貓闖入庭院,兒子毫不猶豫地殺死了這個不速之客,父親夸他干得漂亮:“貓,是一種及其殘忍的動物,專門以吃人為生。”
在這個父親的治理術中,有暴力——孩子們經常挨打挨罵;有洗腦——錄音機播放的永遠是“愛家主義”宣傳;有賄賂——父親給孩子們買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給兒子送來性伙伴預防他逃跑……總之,父親實施的是“教科書式”的極權統治。在這個統治模式里,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對語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險的事物。它蔚藍,遼闊,深不可測,喚起孩子們的憧憬,簡直是亞當夏娃面前的那只蘋果。而沙發多么安全舒適,它上面只能坐著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義成皮質沙發。當所有深不可測的都被定義成安全舒適的,神奇的都被定義成平淡的,飛馳的被定義成呆滯的,孩子們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個“脫敏”的世界。兒子從妓女那聽說一個新詞“鬼”,他問“什么是鬼”,媽媽面無表情地說,鬼是一種很小的黃色的花。
一切專制者都試圖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無法進駐人的大腦,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達。語言因此必須被消毒,被馴化。一些詞被妖魔化,另一些詞被扎上蝴蝶結,一些詞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詞則被噴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農民起義”,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說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剝削”,一說到“國民黨”,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歷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這些被“加工”過的詞匯在意識深處留下的情緒反射卻經久不去。以條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個詞語在展開其內容之前散發出某種“氣味”,正是此類教育的成功之處。
重新定義詞語只是閹割語言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則直接取消某些詞匯的存在。《1984》里,大洋國發明了一種新的語言,叫做“新話”。賽麥是大洋國的字典編輯,他興奮地告訴主角溫斯頓,新話是世界上唯一詞匯量在逐年縮小的語言。“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縮小思想的范圍?最后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不可能有任何語言來表達這些思想。”
讓反動思想不可能找到詞語來表達,這可真是一個控制思想的絕招,幾乎相當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燒水就是找不到容器。當然,不斷增加敏感詞的代價就是語言變得越來越貧乏。極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報體,全都是“打倒”、“萬歲”、“毒草”、“怒火”這樣干癟的詞匯,漢語從一個水美草豐的田野變成不毛之地。思想的鉗制造就語言的饑荒,但語言的饑荒也惡化思想的貧困。一個政權的專制程度,總是和它的詞語豐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馴狗師說:“狗可以像泥土一樣被塑造”。這樣的隱喻真叫人驚恐,但果真如此嗎?秋菊不懂得“人權”這個概念,但是她知道要個“說法”。普通人鮮有使用“民主”這個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實的情感總要找到它的語言出口,就像有翅膀的東西總想張開它的翅膀。
《狗牙》的結尾,大女兒砸掉自己的牙齒,藏在車的后備箱里逃了出來。有一天,她將穿過高速公路去遠足旅行,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那時候,父親再也不能向她隱瞞這個世界有多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