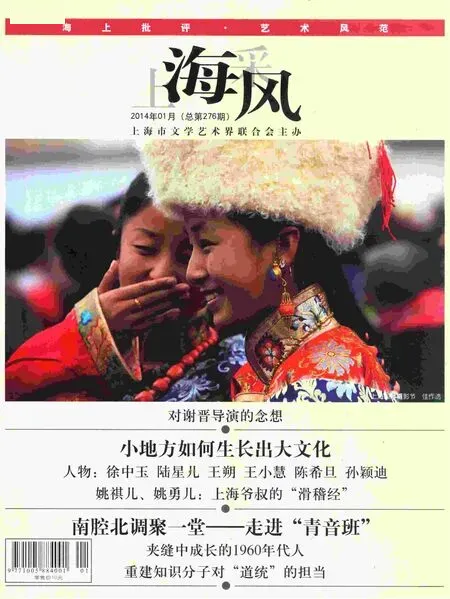觀點集粹
打開解放思想這個“總開關”
人民日報刊文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在論及改革條件和目的時,把“解放思想”列于首要位置,并特別強調其“總開關”作用。如果說,過去的解放思想更多是“頭腦風暴”,今天解放思想則要面對現實的利益博弈。一些人嘴上說思想解放,骨子里怕思想解放;一些部門抽象地贊成思想解放,具體地反對思想解放。說到底是一個利益問題。從調節分配到簡政放權,許多時候,影響改革的思想障礙很多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尤其來自各種既得利益的羈絆。正因如此,中央反復強調,要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全局和局部、長遠和當前的關系,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堅決克服地方和部門利益的掣肘。在新的時代場景中解放思想,不僅要有時不我待的歷史主動,更要有自外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擔當。只有以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跳出條條框框限制,克服部門利益掣肘,改革者才能擺脫局部利益的狹隘,穿透短視思維的迷霧,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實現長遠可持續的發展。試想,如果沒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破冰,怎么會有蘊藏于農村中的生產潛力的充分釋放?如果害怕競爭拒絕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又怎能分享全球化帶來的紅利?正是看到這一點,約翰·奈斯比特才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感嘆:“解放思想是中國社會變革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支柱。”當然,敢于解放思想,更要善于解放思想。呼喚解放思想的勇氣,激發大膽探索的豪情,并不意味著脫離實際、盲目蠻干。解放思想是探索規律、追求真理的過程,必然立足于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指導思想,如果不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所謂“解放”就可能走向反面;解放思想,為的是解決中國問題,如果只是閉門造車拍腦袋決策,所謂“解放”不過是頭腦發熱。我們強調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即便是摸著石頭過河,也要按照已經認識到的規律來辦,而不能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今天思想解放不可能是一聲令下的活動,也不是靠等“指示”、等“批準”就能實現的。警惕解放思想“口號化”、“標簽化”,不僅需要統攬全局的頂層設計,也需要具體而微的基層實踐;不僅要沖破思想觀念障礙,還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甚至還可能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從這個角度,解放思想是一個系統工程,離不開個人的勇氣擔當,也有賴于良好的社會環境。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好的意見不那么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么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35年后,只要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只要有利于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只要有利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就要大膽試、大膽闖,就要堅決破、堅決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四個只要有利于”,既是推進改革開放的基本共識,也應成為銳意探索者的底氣所在。
黨內也有民粹思想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說,民粹情緒,不要說是底層社會,其實在執政黨內也是存在的,只不過這種民粹情緒和民粹意識,黨內可能都沒有清晰意識到。看我們在黨內,我們對民主的理解這么簡單,我們的政黨起來的時候,就沒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受幾千年的專制政治的文化傳統影響,容易走向民粹而不是走向民主。比如,什么東西都是多數人說好,無論是選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表面上唯票是舉,好像是搞民主,其實是民粹。表面上投票,但是并不當場公布,宣布的時候就借著多數票的名義,實際上仍然是少數人意志。把表面的多數票和骨子里的少數權力意志,很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客觀上形成的負面效應是非常大的。在干部問題上是這樣,在處理社會矛盾的時候,為了平息民怨,立馬就把一個干部免職,為什么?那么被處理的干部是不是有問題?不問體制機制的缺陷,把干部當成體制機制的替罪羊犧牲掉了。還有工程項目上,為了迎合社會公眾的情緒,造成決策隨意多變。骨子里是偏向于既得利益的,但是外在的處理手段,受民粹情緒影響,通過安撫、迎合,其實它是被民粹綁架,對不對?所以學者們擔心,我也擔心,官方和民間看起來對立,其實大家都是民粹思維。因為法制權威沒有起來,沒有形成不同利益群體在法制框架內理性博弈的機制,所以決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綁架。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和民營企業家呼喚民主法治,但也不能不看到,資本對社會底層老百姓的壓榨也是很殘酷的。但現在的狀況是不少底層民眾對毛時代很懷念,推崇重慶模式,就是因為底層社會直接感受到的是權力和資本的雙重壓榨,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權力和資本更強勢的更大權力,呼喚清官,呼喚明君。因此學者們要呼吁兩個東西:一個是在權力面前,我們都應該朝著民主方向去努力。第二個是不能回避社會公正問題,要運用民主法治遏制資本對底層群體的利益侵占。
中國老人變“壞”了?
鳳凰網關于“中國老人變‘壞’了?”的調查引起極大關注。目前關于老人的新聞層出不窮:先是唐山老人的廣場舞打擾到附近學校,高中生站立抗議,卻遭到了老人的羞辱;緊接著,廣東汕頭兩名高三學生扶起了騎電動車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老人誣陷訛詐,報警后才獲清白;更有甚者,西安一位老人因為女孩不肯為其讓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大江南北,莫不如此,讓人疑惑中國老人為何集體變“壞”了?于是,不少人開始懷念過去,懷念過去的老年人是多么有教養,多么講道理,懷念過去的社會是多么的“平靜與安詳”,不似現在這般“赤裸裸”。而老年人不講道理、“變壞”的原因也被歸咎于社會的發展,認為正是因為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復雜甚至浮躁,才造成以前那么純樸的老年人現在變得如此這般的不講道理。可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教化并不差,現在的困境不能賴賬到老祖宗;這也不能怪西方文化的傳入,不能說改革開放讓大家學壞了。隨著越來越多人出國,大家都知道了西方社會的道德水準社會風氣并不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老人變“壞”呢?
老人變“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成長時期他們的生活、經歷已經所接受的教育,而把責任推給他們成年后的社會開放,顯然是不公平的。眾所周知,近幾年出現的“新晉老人”大多出生于1949年前后,在他們的成長時期,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匱乏”。在他們長身體的時候,卻正好遇到“三年困難時期”,食品短缺和饑餓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物質觀念的形成。哪怕到了物資充裕的時期,記憶中的“匱乏恐慌”還是會使他們試圖占有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源,而為了物質甚至不惜大打出手甚至鋌而走險。與物質相對應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在物質長期匱乏的背景下,人類的活動唯一目的幾乎就是生存下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并且伴隨著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國社會傳統的道德觀念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觀念又不存在,為了生存下去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在物質和精神雙重匱乏的環境下,這一時期的人們也并沒有得到良好的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他們是喝著狼奶完成啟蒙和基礎教育,得到的是一種叢林里比劃誰的拳頭大的價值觀。而最要緊的是,沒有什么禁忌也沒界限。想想看,道德的底線在哪里?尊老愛幼,尊敬師長,孝敬父母,這些就是底線。很不幸,老人家們成長的年代正是惡沒有底線的年代。而狼奶教育的另一個嚴重后果,就是理智和知識的缺陷。老人家們都不適應多種聲音的局面,不知道如何理性地辯論,他們習慣一人獨語的一言堂。訴諸理性,寬容異己,這種理智和道德上的品質,恰好是洞穴教化無法造就的。而知識上,老人家們當年成長時期的中西經典誦讀幾乎空白,沒有一點詩書禮樂的熏陶,這導致他們的粗野無知。
當初種下的惡果,如今就到了“收獲”的季節。于是,他們不覺得廣場舞可能會對他人造成困擾,不覺得讓座是一種關愛而并非理所應當,甚至可以顛倒是非、誣陷他人,成長時期基本公共教育的缺失,使他們認為一切都理所應當,甚至可以不擇手段的利己。
當然,除了教育之外,還與另一種他們的親身經歷密切相關。政治運動,把人性中最惡的部分激發了出來。很不幸,老人家們成長的年代正是惡沒有底線的年代。歷次的政治斗爭激發出人性中最惡的因素。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父母師長都可以批斗,連同床共枕的夫妻之間都可以相互揭發,還有什么可以信任?還有什么壞事不可以做?無論他們之后還經歷過什么,在價值觀形成期所經歷的一切已經足夠影響到他們中的很多人了。人,是看著父輩的背影長大的。品行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賴家庭和周圍的長輩言傳身教,靠的是耳濡目染。恰恰是這一代人,成長期間有許多空白,也有很多盲點,最該接受道德哺育、情操導引、汲取文明的時候,不是浩劫,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結果,等到當了父母輩或者祖輩,以身作則,也就無從談起了,而為老不尊,則更成了一景。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
老干部的“兩頭真”現象
文史博覽刊文說,“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這是2000年,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撰寫《悼胡繩》時,援用蔡仲德評論他老丈人馮友蘭的話。楊繼繩據此歸納出“兩頭真”——意即“年輕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后大徹大悟,真誠地面對社會現實”——這個詞迅速成為黨史研究熱詞。2004年,原中顧委常委、國務院原副總理張勁夫更主動“對號入座”,發表《我也是個“兩頭真”》:“年輕時,面對要當亡國奴的危險,提著腦袋找共產黨,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國;年老時,經歷了黨內外諸多有疑問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當糊涂人。”蒙受13年牢獄之災的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反思文革時,也檢討自己:“我做中央宣傳部長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錯誤,斗這個斗那個,一直沒有停。許多是毛澤東同志囑咐的,我照辦了,我有對毛澤東同志個人崇拜的錯誤,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當然由我負全責。”老人們還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運動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經濟學家于光遠,都是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選擇追隨共產黨。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幾個老干部吃飯,突然放下筷子問:“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么?”見大家面面相覷,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