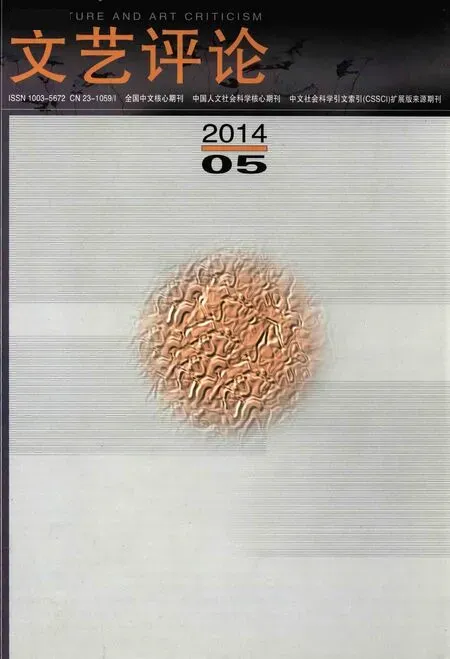影視與文學:百年論爭的再審視
○薛晉文
當前,關于影視與文學關系的討論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有的學者認為影視的基礎是文學,文學對影視的母體作用不可動搖,將影視看作文學的衍生體和小兄弟而津津樂道。有的學者認為影視的基礎未必是文學,影視若無法扔掉文學的拐杖就不會獨立行走,寄人籬下的影視永遠不會建構獨立的藝術體系。其實,兩種非此即彼的極端論斷均不可取,爬在文學樹梢上俯瞰影視的慣性思維有些不合時宜,早在1905年中國電影誕生之初,文學曾帶著異樣的口吻將電影喚作“西洋鏡”或“影戲”,時過百年,談及影視言必稱文學的論斷依舊鋪天蓋地,這多少有些“欺負”影視的味道。同樣,站在影視屋頂上嘲弄文學寒酸的貴族心態要不得,畢竟文學作品曾為影視的繁榮立下過“汗馬功勞”,電子媒介崛起并不意味著印刷媒介退場,兼容吸納并為我所用是新媒介高效傳播的明智之舉。嚴格意義上講,影視屬于典型的電子媒介范疇,文學屬于典型的印刷媒介范疇,倘若將兩種不同范疇的媒介彼此混同而爭論不休,本身無意義和價值可言,倒顯出了幾分蠻不講理。坦率而言,應將兩者置于平等的位置去探究各自存在的優劣,方可對“百年論爭”仍懸而未決的話題得出客觀公允且令人信服的研究結論。
一、兩種媒介各有傳播優勢
文學作品本質上是一種時間藝術,是在時間綿延中按特定思維邏輯并借助文字符號建構的時間藝術。文學作品中約定俗成的書寫符號將人類的抽象思維進行了物化表達,連貫性的文字記錄、渾整性的信息聚合與移植性的信息裂變使得文本內容遠遠大于媒介形式,對于信息的完整保存和思想的精深表達擁有極大的優勢,而且閱讀的主動性體驗和個體性視角,讓獨立思想與自由闡釋獲得了較為充分的尊重,讓精深思想的尋覓與深度共鳴的追索獲得了充分滿足。一位西方學者曾精辟地指出“書面文獻將字詞從它們的言者和它們最初的上下文中分離出來,削弱了記憶的重要性,允許對信息內容進行更加獨立和更加從容的審視”。①由此可見,平面的時間敘事帶來了線性閱讀的文學傳播特征,讀者主要是以文字為載體想象復原故事情節并拓展延伸人物形象,需要經過想象的努力和感悟的專注,需要維持感覺平衡且投入豐富的想象力,方可實現從文字符號向現實生活的有形過渡和圖景還原,思考置于感覺之上的閱讀體驗通常是理性化和深層性的,讀者因自身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的差異,往往能在靜觀凝思和獨立審視中,讓文本內容更加豐富開放,讓文本意義不斷獲得累積增值。例如,位列四大名著之首的《紅樓夢》,其厚重深邃的文化內涵讓無數文人駐足沉思,歷代名家在解讀中各顯神通且各展其妙,至今無人能窮盡其博大精深的藝術氣象,以至發出了“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林黛玉”的慨嘆,但每一次闡釋都是對藝術世界和實在世界之間各種可能性的挖掘與補足,都是在努力縮小文字符號創作中能指與所指碰撞后的疏離與間隔,也是對文本真實內涵的無限逼近與深度傳播,而且這種傳播活動是一種遠距性或不在場的虛擬傳播,在時空穿越與意義再生中引發了歷代讀者的極大閱讀興趣和闡釋沖動。與此同時,文學作品的媒介屬性注定了其傳播的私密性與人際性,致使其傳播范圍、傳播效果與影視媒介相比難以望其項背。
影視作品本質上是時空藝術,是按蒙太奇邏輯并借助視聽符號延續的時空綜合藝術。倘若說線性的印刷文字需要努力維持感覺的平衡方可有效傳播,那么影視作品中聲畫直通感知神經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想象力的努力程度,感覺的不平衡削弱了文學閱讀中經驗的抽象性和想象的虛擬性。也就是說,立體的空間敘事特征和畫面預設的生產特點,讓文學作品中讀者習以為常的線性閱讀、從容審視和深度審美的接受習慣變得無所適從,撲面而來的是空間閱讀、瀏覽瞥視和印象審美的欣賞習慣,直觀逼真、生動具體的視聽形象代替了想象虛幻、若隱若現的內心視像,觀眾主要以鏡頭為載體直觀畫面內容和注目事件變化,快速剪輯的運動畫面很難讓觀眾靜默沉思視聽內容的意義與價值,既定內容的單向高速傳輸,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交互對話的空間和余地。影視文本的開放程度和意義增值程度較之文學難以深度爆發和細膩呈現,特定的生產特征注定了影視傳播中感覺和直覺的比重大于閱讀中思考與凝視的比重,視聽形象的大眾性和普適性削平了文學傳播中精英化和階層化的接受門檻,影視藝術的大眾化傳播程度和化大眾傳播成效遠非文學作品能及,將私密性的文學接受推進到大眾性的新階段,讓人際性的專享獲得了全民性的共享,視聽的孿生、不在場傳輸特性突破了文學傳播中的時空局限性,可以將傳播效果無限放大,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大眾傳播媒介則不然,它們有巨大的能力使單方向的傳播增大無數倍并且使它在許多地方都能收到。它們能克服距離和時間引起的問題。視聽媒介還能超越發展中地區由于文盲而造成的障礙”。②譬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駱駝祥子》和《茶館》在改編成影視作品后,不僅以乘數疊加效應擁有了幾個億的觀賞群體,讓遙遠的觀眾都能欣賞到名著的視聽盛宴,即使目不識丁的觀眾也能對視聽內容略知一二。再如,四大名著經過改編影視劇和幾輪翻拍之后,觀眾基數翻倍增加,恐怕一般的世界名著都難以企及,上述效應正是由于活動的畫面和動作表情成為了主導性的傳播符號,實現了文字向影像的飛躍轉換,降低了文字符號的比重并弱化了抽象的傳播效果,視聽媒介具體化和形象化的優勢在四大名著傳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又如,許多躲在書店角落中默默無聞的文學作品,或許因為內容抽象而無人問津,或許因為故事平庸而被人遺忘,但它們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后一夜間家喻戶曉,恰是視聽媒介生活化的表達、活靈活現的身體動作語言激活了那些孤獨的文學作品,成為所謂的暢銷讀物而名噪天下,傳播渠道的變化對此類文學作品而言扮演了救贖者的角色,傳送媒介的置換讓它們收到了意外的驚喜。
不難看出,影視與文學兩種媒介既有競爭關系,同時也有合作關系。尤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影視制作中內容的預定特征和可操控性為文學作品的當代闡釋注入了新的活力,人類進入讀圖時代之后,中華文化的傳承顯得尤為重要,如何實現傳統經典文化的當代轉換和當代闡釋?是攸關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命題,對此影視與文學的合作共生至關重要,作為重要的時代媒介,它們有義務在合力共進中讓中華文化發揚光大,而影視生產中的可控性讓兩者的合作共贏變成了可能。比如,新版電視劇《三國》中對曹操形象的公允評價和重新審視讓人印象深刻,對千百年類型化的扁平歷史人物進行了立體還原和深度修復,值得充分肯定。再如,新版《水滸傳》中當閻惜嬌(原名閻婆惜)的奸情被宋江發現后,宋江以豁達的胸襟寫了休書并同意“成人之美”,這種巧妙的當代闡釋,不僅無傷宋江英雄的整體風范,而且給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為“宋江殺妾”固然正義凜然,但選擇理性放手何嘗不是成大事者的另一種坦蕩胸懷?時代空氣中彌漫的“以人為本”意識和“人性關懷”意味在這里隱約可見,而原著中的殺戮氣息和尚武情結在新版《水滸傳》中幾乎不復存在。此類名著改編劇,借助影視生產的內容預設特征,將時代的價值觀點和精神訴求熔鑄其中并借助大眾傳播媒介獲得觀眾廣泛認同,讓當代人的價值理想依托兩種媒介的互補實現了相得益彰的有效傳播,堪稱影視與文學成功合作的典型范例。就此而言,作為時間藝術的文學作品與作為時空藝術的影視作品各有優長,在媒介發展的長河中正是有了各具特色的傳播媒介形態,我們的藝術殿堂才更加五彩斑斕和豐富多彩。
二、敘事功能優劣清晰可辨
文學作品的敘事主要是借助文字描述故事情節、人物行動和環境背景,通過語言符號間接傳達人物的情感波瀾與內心體驗,并依托讀者的“抽象闡釋”獲得文本與受眾之間的共鳴和通感。文學敘事有許多優勢,它善于在文字內濃縮厚重深邃的思想,像孔孟經典中經常言及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仁者愛人”、“德不孤、必有鄰”,雖然寥寥幾語,其思想密度卻博大精深;它善于將感情和思想蘊藉在敘事符號之中,讓讀者行走在“感目”、“會心”和“暢神”③的審美體驗中如癡如醉,受眾在主動欣賞和自覺認同中各得其所,閱讀視角和闡釋結論很難輕易被“他物”所操控和左右;它善于在敘事中采用完整的起止、遞進的情節、間或的小高潮、立體多元的人物變化以及封閉的結構去講述故事內容,因而戲劇化的敘事手法往往是文學作品制勝的重要法寶。當然,讀者也可以控制文字信息傳送的速度,在其需要反復咀嚼和重點思索之處自主“叫停”,可以“囫圇吞棗”、也可以“細嚼慢咽”,信息傳輸的速度和信息的流量盡在讀者的掌控之中。
影視作品的敘事主要是依靠鏡頭的聯接組合去表情達意,視聽兼備的“具象感知”敘事替代了文學作品的“抽象闡釋”敘事,蒙太奇就像語言文字中的“主謂賓”等語法那樣,本質上是一種影視敘事的語法規則,某種意義上具有反文學敘事的特性,它將蟄伏在文字背后的深層聯系,變成直觀形象和通俗易懂的連續性畫面內容,以往在文學中需要想象才能完成的“虛幻”形象變成了可視可聽的“仿真”形象,需要思維再加工的萬物聲響變成了輕松悅耳的直感聲響,需要冥思苦想去體悟的內心情感變成了逼真生動的動作表情。影視敘事的具體特征比較明顯,其一、它具有較大的時空跳躍性和動作展示性,在敘事的縝密性和深邃性方面與文學敘事相比稍遜風騷,對此費瑟斯通有過精辟論述,“觀眾們如此緊緊地跟隨著變化迅速的電視圖像,以至于難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聯接成一個有意義的敘述,他(或她)僅僅陶醉于那些有眾多畫面疊連閃現的屏幕圖像所造成的緊張與感官刺激”。④譬如,作為電視劇的《紅樓夢》與文學作品的《紅樓夢》相比,前者在敘事的集中性、視覺性和造型性方面優勢明顯,但在敘事連貫性、豐富性和深化性方面和小說相比還有不小差距。其二、敘事主體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和滲透性,他們會根據自身的喜好和市場的口味更換和滲透敘事內容,如電視劇新版《紅樓夢》結尾處“林黛玉裸死”的敘事情節,新版《水滸傳》企圖說服觀眾對“憐香惜玉”的西門慶和“風情萬種”的潘金蓮予以同情和諒解,這些都是敘事主體將自己的價值理想強加給觀眾的典型體現。其三、敘事的非理性傾向比較鮮明,影視作品往往將文學敘事中的完整起止束之高閣,甚至弱化故事背景、故事情節和人物復雜性,將新奇的構思、人物的動作表情和刺激的聲畫效果作為敘事的主要著力點,比如,根據莫言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紅高粱》就是如此,它在當時不論對傳統文學敘事,而是對經典電影敘事而言都是陌生化的“他者”形象。此外,觀眾對影視敘事的信息傳輸速度難以支配,特別是面對某些意味深長的鏡頭進行思索時無法駐足凝思,觀眾支配權的弱化對于影視敘事內容的深度傳播是一種莫大的遺憾,同時觀眾對信息傳送的內容難以形成有效回應,影視敘事的“中轉站”特性和群體化傳播特征,使得審美體驗中的思索時空與交互反饋質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然而,新媒介的出現并非意味著對老媒介的放逐,而是在相互滲透中實現了媒介功能的疊加與整合,在借鑒吸收中造出了一種新的媒介文化生命,因為“各種門類的藝術家總是首先發現,如何使一種媒介去利用或釋放出另一種媒介的威力”。⑤蒙太奇敘事既承接了文學的敘說功能,又延伸了文學的表現功能。首先,影視媒介的出現解放了接受者的聽覺功能,將印刷媒介時期只靠眼睛“單渠道”接受的視覺藝術,推進到主要依靠眼睛和耳朵“雙渠道”視聽接受的新階段,“因此,視聽媒介在傳達一定題材、一定數量的信息上,要比單純的聽覺或視覺媒介要更為有利一些”,⑥它降低了參與者文化儲備與思想積累的門檻,讓大眾文化的普及和意識形態的直接傳播成為了可能,例如,電視劇《解放》、《辛亥革命》、《一九四二》,讓無數基層觀眾因此而加深了對中國革命與社會演進的基本了解和常規認識。其次,影視敘事突破了傳統文學敘事中嚴肅審美的范式,使得娛樂、刺激、宣泄、狂歡、感性等世俗敘事由邊緣向中心躍進,當代社會的公共場域逐漸浮出地表,敘事價值取向更加多樣和自由,敘事的自由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的自由。比如,以部分好萊塢歌舞片、警匪片、卓別林喜劇電影以及肥皂劇為代表的影視作品,它們依托世俗敘事將大眾的娛樂訴求,以及宣泄欲望做了妥帖表達和積極回應,使得個體生命的靈魂棲息在世俗敘事中獲得了安慰和寄托。再如,熱播電視劇《幸福來敲門》,該劇在世俗敘事中敘說著有關幸福的家常瑣事,但頃刻間引起了全民對幸福缺失現狀的思索和追問,幸福話題成為了大眾交往與互相傾訴的焦點媒介,幸福看似一個小話題,實際上屬于一個時代大主題,由電視敘事引發的公共場域效應至今讓人記憶猶新。再次,影視敘事的集體制作特性,讓文學生產抵達了由個體創作向集體批量生產的新天地,以往充滿私人性和神秘性的昂貴精神生產成為了普羅大眾的共有物,在人人手握DV機的時代,全民精神生產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一個時代精神自由的程度往往是社會文明程度高下的晴雨表。譬如,一年一度的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各種中外DV作品大賽的熱鬧場景即是精神生產從“天上”回歸“人間”的最好說明,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和生活褶皺進入了影像藝術世界,影像媒介給他們帶來了許多溫暖和救贖,由于敘事媒介的變革,以往需要仰視和跪拜的精神生產逐漸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也許一種感官的解放會伴隨著另一種感官的萎縮,影視敘事在延伸視聽感官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弱化了文學敘事的某些優秀功能。例如,面對像李清照詩詞中“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樣復雜的內心表達,當下的影視敘事顯得捉襟見肘,有時能借助獨白和音樂去實現直接表達和間接烘托,但思想意蘊和精神內涵多少有些打折。再如,遇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這樣充滿哲理意味的詩句,影視作品多使用理性蒙太奇去予以表現,倘要深刻闡釋詩人內心孤獨迷惘的博大情懷,對于蒙太奇敘事而言有些犯難。又如,像《阿Q正傳》那樣意蘊深邃的名著,用鏡頭組合演繹的視像與語言文字建構的小說相比還是讓人意猶未盡。事實上,視聽藝術完全有能力進行深度表達和理性敘事,同樣可以承擔為生活提供意義的重要功能,⑦如電影《公民凱恩》中“玫瑰花蕾”的隱喻蒙太奇,電影《戰艦波將金號》中姿態各異的石獅組成的隱喻蒙太奇至今讓人拍案叫絕,只是這種深度敘說能力有時被資本邏輯和娛樂至上掏空了,有時被傳統文學話語所誤解了,讓世人誤以為視聽藝術就是淺表文化的代名詞,以至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小報里沒有任何東西稱得上是《李爾王》這樣的悲劇,但它可能是電視時代合適的文學”。⑧總之,文學敘事不等于影視敘事,文學敘事功能的蛻變是媒介發展的必然趨勢,影視在接續并延伸文學敘事的同時,也應該正視敘事中平庸化、低俗化和拜金化的誤區,只有這樣才能在媒介整合中實現自身的高效傳播與深度表達,這抑或就是媒介更迭的辯證法。
三、劇作與文學不應簡單混同
文學作品是影視劇作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外許多優秀的影視作品改編自文學作品的不在少數,文學確實給了影視藝術許多滋養,尤其是故事性、動作性和表現性較強的文學作品更容易獲得制作者的青睞和光顧。在我看來,少部分還保留著文學語言,具有情感豐富性和思想深邃性的劇作依舊是文學,比如,像英格瑪·伯格曼、佛朗索瓦·特呂弗的劇作就是文學作品的典型代表,他們不僅用文學的語言進行創作,而且內蘊著濃郁的文學情感和思想精神。然而,許多源自文學改編的劇作已不再是文學作品本身,盡管他們都富含“文學性”,但“文學性”不等于“文學”,“文學性”的闡釋各有千秋,本文認為其主要是指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的思想內涵與價值意義的總和。而“文學”是指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符號、依托特定語法規則以及敘事手法反映人生的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包括小說、散文、戲劇和詩詞等諸多表現形式,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文學性”等同于“文學”,它們正確的關系當是,文學需要劇作去拓展其普及空間,劇作需要文學性去提升其藝術品質,劇作未必是文學,但劇作不能沒有文學性,沒有文學性的劇作必將滑向粗鄙和淺俗的另一端。一句話,文學性不只是優秀劇作的靈魂,更是一切優秀藝術的靈魂,文學性的覆蓋范疇遠遠大于文學作品本身,將文學性視同文學是典型的常識錯誤。鑒于此,將文學的頭銜強行賜予劇作顯得有些牽強和霸道,對此學界早有不滿,“在戲劇、電影、電視劇這種主要以空間和身體的技術訴諸視聽并通過所有觀眾進行選擇觀看的藝術領域,劇作可以是文學,但不必是文學”。⑨
事實上,依據影視生產規律和傳播規律編織而成的劇作,使得原先連貫縝密的故事變成了跳躍性的片段情節、原先抽象性的闡釋變成了形象性的描述、原先立體多元的人物變成了直觀可見的人物、原先細膩的心理變成了可直接讀解的表情,影視畫面對動作性、造型性和展示性的視聽拍攝需要,將人生與人性的復雜性、豐富性做了簡單化和淺俗化的處理,文學作品中富含的語言美和思想美遭到了放逐與稀釋,作為文學重要本質屬性之一的語言美被直白淺陋的說明性文字所取代,沒有了文學語言的媒介載體,其文學本體屬性多半是空心的軀殼。上述變化,不是一種機械簡單的刪繁就簡,而是視聽符號對語言符號的粉碎與再造,這種變化不是形式和表層的變化,而是本質和深層的涅槃,是一種基于解構基礎上的藝術重構活動,其中必定若隱若顯地存在著“文學性”,但媒介符號和媒介載體的雙重轉變通常會帶來媒介形態與藝術審美標準的本質變化,媒介結構的轉變最終引發了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文化形態的巨大變化,所以,此時的影視劇作距離真正的文學作品越來越遠。比如,電影《紅高粱》的劇本主要是以地點場景的變化統領故事情節,不僅將小說中的人物關系進行了簡化,將主要人物的命運軌跡做了大尺度的改動,而且只選取小說的部分精神內涵進行放大和表現,經過“傷筋動骨”后的小說只剩下粗線條的輪廓,以及“顛轎”、“野合”、“抗日”等動人心魄的場景,即便如此,這樣的劇作依然蘊藉著文學性和思想性,但文學的媒介結構與本體符號早已被肢解和置換,造型性和視覺性占據主要地位,運動性和節奏感十分強烈,視聽思維和影像意識主導了一切,再將其等同于小說本身實在難以讓人信服。
再往深處說,部分影視作品倘若被還原成劇本,再以文學的審美眼光去看,會讓文學愛好者乘興而來失望而歸。比如,像《阿凡達》、《第五元素》、《2012》這樣的經典好萊塢影片如果被還原成影視劇本,文學性與思想性的敘說很少,大多是簡單的說明性對白話語,然而,大量驚險刺激的超現實體驗、視聽奇觀的震撼性場面和精妙絕倫的視像創意,讓觀眾在現實與未來的穿越張力中流連忘返。再如,像《速度與激情5》這樣的驚險動作大片,故事情節非常簡單,主要靠極速飆車、警匪追逐、硬漢對決和驚悚槍戰編織而成,其中沒有多少“文學”的精華元素,引人思索和想象的文字少之又少,假如還原成劇本恐怕連三流小說的水準都夠不著。上述兩類影片橫掃全球票房與口碑的確鑿事實給我們帶來許多啟示,與其說此類電影劇作的基礎是文學,不如說是天才般的藝術創意更為準確深刻,這是形式設計和內容表達之間的獨創組合與相得益彰。影視創意簡而言之就是拿什么樣的形式去創造性地表現什么樣的內容,好的影視創意不是模仿克隆,也不是天馬行空般的烏托邦,而是基于現實和理想的視聽化與藝術化表達,背后潛藏著藝術家的深遠想象和新穎追求。具有獨創精神的上述影視作品并非僅僅靠感官刺激取悅觀眾,剪輯流暢的畫面同樣指向哲學和美學,它們同樣具有主題思想,而主題思想正蘊藏于藝術創意的審美觀念中,也就是說,潛伏在影像之下的人生與社會真諦正是它們穿越時空的永恒支撐。在全球影視競爭格局中,得創意者得天下,好的創意根本上講是藝術形式(節奏、風格、技巧等)與生活內容(個體、環境、政經等)之間的科學配方與絕妙隱喻,這是歐美影視多年來笑傲江湖的重要秘籍所在,正如羅伯特·麥基所言,“他們之所以出類拔萃是因為他們選擇了別人沒有選擇的內容,設計了別人沒有設計的形式,并將二者融合為一種不會被誤認的、只能屬于自己的風格”。⑩我們倘不能盡快走出重故事內容、輕藝術創意的審美誤區,難以割舍重“語言文字”、輕“視聽符號”的價值偏好,無法賦予影視媒介合法體面的身份與名分,甚至無視“鳩占鵲巢”的霸道做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中國影視在國際舞臺上恐怕難有大作為和大出息。
落筆至此,影視的崛起勢不可擋,“電視在所有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里已成為主要的公共機構,而且在發展中國家的情形也迅速如此”,(11)與此同時,文學的轉換提升也迫在眉睫。我們不必再糾纏于非此即彼的無休止爭論而內耗不已,跳出影視看影視或者跳出文學看文學,得出的結論可能更加心平氣和與客觀公正。其實,文學天生未必是博大精深藝術的永恒代表,隨著網絡文學和集體寫作的強勢崛起,文學的大眾化和世俗化再所難免,文學不應在自暴自棄中跟著感覺漫無目的地隨意滑行,應在借力影視媒介和網絡媒介中重新找回昔日的自信與威力,媒介的更替越快,越需要文學乃至文學性健步跟進為新媒介提供內容與材質。影視天生未必是淺薄浮泛藝術的特定代表,影視同樣有能力去承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擔當與文化使命,同樣可以表達深刻的精神內涵和文化內容,影視的社會屬性注定了它必須以藝術性的畫面去滿足人的審美需要,不應在過度商業化的操控中放棄了自我的無限潛能和種種可能,任何鄙棄思想性去單純迎合人們快感需求的影視作品在風靡一時之后,很快會被人無情地扔進歷史的垃圾堆而長久遺忘。綜上所述,影視與文學各展其長、有效互補并共存共榮是當代中華文化更加繁榮發展的希望所在。
①參見羅杰·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認識新媒介》,明安香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⑥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陳亮等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26頁,第123頁。
③參見胡經之《文藝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④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⑤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89頁。
⑦參見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⑧理查德·凱勒·西蒙《垃圾文化》,關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頁。
⑨李道新《劇作不必是文學》,載《文藝報》,2010年6月2日。
⑩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周鐵東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版,第10頁。
(11)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電視與社會》,張永喜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