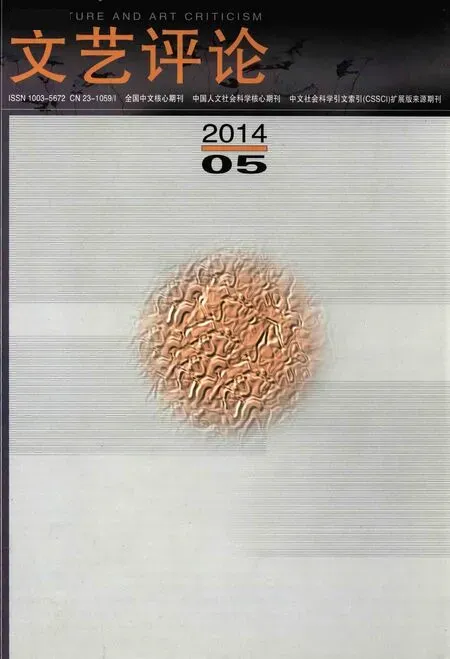跨文化境域中“中國鏡像”的自我塑型
○陶永生
多元化歷史語境下的東西方文化話語形態共生共榮,為我們認知和捕捉不同文化境域、不同闡釋立場之間的“公共文化鏡像”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問題提供了宏闊的認識論背景和廣闊的方法論視域。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對象群中的獨特“公共角色”,“中國鏡像”文化形象不再拘囿于具象化的“中國事實”或“中國事象及事態”,最初定型在“現代性(modernity)”歷史語境中的它跨越了“新舊”時間維度和“東西”空間維度的雙重疆界,實現了對某個特定的地域性文化“自足體”的雙重超越。本文主要運用格林布萊特文化詩學的“厚度描述”手法來“歷史地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它是如何在西方主流社會文化舞臺上長袖善舞、霓裳驚鴻般“才藝展示”和完成“自我構塑”權力運作的。延至轉向為“后現代性(postmodernity)”歷史語境,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交互激蕩,侵染互滲漸成氣候,已成風尚,同時也為“中國鏡像”的重塑注入了更多來自當代中國自身的生態文化群落的“中國元素”。在此理論情勢下,世界文化范圍內催生了形形色色、明滅隱現的文藝思潮和層出不窮、花樣翻新的“文化事件”,當代文化批評的多元化趨勢與整體綜合性指向日益凸顯。
“中國鏡像”文化形象是西方認知主體從“異己”文化形象和“他者”歷史語境中重構、塑形而來的,它既是東西方文化話語形態的“自我力量和自我造型”的“認知闡釋”主體,又是兩話語形態的“異己力量和他者語境”的人化“認知闡釋”客體,其生態構造創生了一種兼容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在、歷時與共時的多種“公共文化鏡像”互動輝映的跨(東西方)文化對話新平臺。誠如王寧在格林布萊特文學批評專著《重劃疆界:英美文學研究的變革》的中譯本《導讀》中所言,“文化研究逐步發展為‘跨(東西方)文化’的研究。它的跨學科、跨文化以及跨疆界等特征使其在全球化的時代又獲得了‘新生’”。①本文擬從格林布萊特“自我塑型”論視域出發,觀照和爬梳“中國鏡像”的“歷時性”塑型流程和“共時性”跨文化意義生成機制。
一、“自我塑型”論的文化觀:闡釋的文化性和文化的闡釋性
斯蒂芬·格林布萊特(Stephen Greenblatt 1943—)“文本闡釋”理論(text interpretation)內在地貫通耦合了格爾茲文化人類學的文化闡釋方法與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將文化對象放置到與社會和歷史過程的某種有趣的關系之中”,運用文化闡釋和歷史敘事的方式來解讀人類“自我塑型”模態的綜合文化行為。作為其核心范疇的“自我塑型”實踐論極大地開拓了根植于“闡釋的文化性”和“文化的闡釋性”雙重特質的文化詩學空間。文學闡釋活動的肇端是從闡釋對象置身于“作為一種共時性文化系統的社會文本結構”和“作為一種歷時性文化系統的歷史文化形態”這兩大文化系統的“某種有趣的關系之中”開啟的,這種“有趣的關系”主要體現為一種彰顯文化性和文學性的“有意味的”藝術形式和審美體驗,它的整個運行軌跡就是經常被解讀者忽視的“一整套文化實踐”,或者稱之為“文化解讀(cultural reading,也可譯為文化閱讀)”。這是格林布萊特文化詩學(Cultural Poetics)的理論原點,也是格氏理論闡發的始基。
如路易·蒙特洛斯(Montrose)所說,“文學的歷史就是聚集的文化語碼,并使文學和社會彼此互動的歷史。我們所重構的歷史,都是我們這些作為歷史的人的批評家所作的文本結構”。②文學史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記錄和述說文學與社會存在互動互融的歷史情況的“文學的文化(literary culture)”書寫系統,它的起訖點都是“作為歷史的人的批評家”的我們所面對的文學文本(literary text)及其聯合體(作品)。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的結晶體和文本的集合體,閱讀理解(understanding)、分析闡釋(explanation)其內在的文化性和文本性這些基因鏈條和文明語碼,才使得文明基因得以薪火相傳、歷久彌新。
在格林布萊特的文學字典里,“文學的文化”一語與政治術語血脈相連,“自我塑型”論的文化觀與它的政治觀一脈相承。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文本闡釋的文化性恰是其政治性或者說意識形態性的外在表征形式。格氏夫子自道,無論是自我力量的構塑,還是自我造型的重塑,“自我塑型”的潛在力量既來自于種種外在的政治權力形式的抑制(suppression)與顛覆(subversion),又來自于內在的文化蘊涵與文本結構的商討與通感,是一種錯綜復雜的、兼容并包眾多“文化力量”和“社會能量”的富有“張力”的塑造過程。伴隨著文化張力的彈性擴張,包羅萬象的非文學文本侵入滲透到文學文本的堅固堡壘之中,碰撞、雜居、同化,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天然“間距”冰消玉殞,最終握手言歡在文本聯合體(con-text)——文化文本這里。文化文本的深度闡釋更是一次“人類文化行為的自我構塑”的復雜理論與實踐旅程。在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的人類文化整體結構中,“自我塑型”模式彰顯了貫通文化筋脈的抑制性(constraint)和流動性(mobility)。在格林布萊特看來,人類的“自我完善、全面發展”是一個社會化構建和“文而化之,化而文之”的代際進程,是在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隱蔽規約下形成的“隱喻性”結構(systematical structure of“metaphor”)。這樣的判語讓人自然聯想起了馬克思那家喻戶曉的論斷,“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③
“西方文化視域中的中國造型”文學形象問題是個特異的文學現象,似乎唯有它成為了能夠共享著東西方文學闡釋對象群公共資源的“這一個”。這一獨特的“混血兒角色”實際是文化哲學視域下多元文化筋脈耦合的概念綜合體。“中國鏡像(Chinese cultural image)”論題至少蘊涵兩大本體元素:其一,無論東西方哪種地域性文學樣態,文學形態本源上是一種“文學的文化”書寫系統,即是一種詩意的人生形式和文化存在,而作為其基元表征形式的文學意象則理應是一種情感世界的對象化和想象空間的審美化呈現。以上特質,作為一種在西方文化遷移中生成的意象集合體,“中國鏡像”文學形象則兼美擅揚。再者,“中國鏡像”命題更屬于一個向異域文化自由敞開的、“不斷構塑著的”文化間性對話和主體間性交流的“商討(negotiation)、流通(circulation)”領域,其間流通著涌流不息的“社會能量(social energy)”和“潛在的力量”,點點滴滴“構塑”著東西方文學話語形態的“自我力量和自我造型”。某種意義上說,追溯“中國鏡像”文學形象的塑造進化史,既交叉著東西方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雙向探究,又積聚著整體性文學批評體系的飽滿顆粒。
觀看、洞燭這一橫跨“古今中外”的“中國鏡像”造型藝術,不僅要探究在西方“現代性”語境下怎樣透視、闡釋“中國造型”的多維度審美特征,而且還要追索西方的“中國造型”作為一種闡釋策略和權力話語,在西方主流文化形態與政治觀念(outlook)中如何被漸進式意識形態化、模式化、體制化的,最終淪為參與構筑“西方中心主義”(west-centered thought)的文化霸權的“馬前卒”。推本溯源,“中國造型”文學意象的本體架構和意義系統的最終“定型”,源自西方文化內在構造和內在規律本身,來自于西方思想原生態的“現代性”社會意識形態與集體無意識。而西方文化文本的闡釋性正是在西方政治模式建構和話語形態塑造的歷程中日益凸顯出來,并得以漸進式強化、夯實。相應地,我們對于這一“奇特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人造物”和獨特的人文景觀,力圖給出眾語喧嘩的“多聲部”復調解讀。文化的豐贍闡釋性從多側面反映了文化樣態的多樣豐富性,以及文化形態的自足性(self-sufficiency)和多元化(multi-element)。
探析西方文化形態里的“中國鏡像”話語架構,作為西方現代文化“自我力量和自我造型”的“托物言志”式投射和隱喻性表達,西方思想觀念中的“中國觀”只有置身在西方自身的社會文本結構和歷史敘事語境中,并行不悖施以條分縷析式闡釋策略,其文化性和社會性內蘊才能夠得到系統深刻的爬梳剔抉和深度闡釋。西方闡釋主體曾在啟蒙運動開放的“前現代性”敘事中褒獎、贊美過中國概念指稱的虛擬社會共同體,又在殖民主義自足的“現代性”敘事中揶揄、批判“中國虛擬體”。在西方“現代性”視域中,西方主流社會始終主導著奠基在一系列二元對立范疇上的文化地理版圖和世界觀念秩序,它們只知一味依據自身的“全知全能”認識論和“唯我獨尊”價值觀來裁量“周圍的社會存在和社會關系”,來評判“異己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力量”。
這種社會與文化的綜合觀是一種知識虛擬秩序(幻象),也是一種價值等級秩序、權力讓渡秩序,代表著某種特定文化樣態的每一個民族群落都被劃撥對號入座。④身處西方后殖民主義歷史時期的“后現代性”敘事語境中,為超越“二元對立”標準答案的思維定勢和闡釋語境,重新厘定“中國鏡像”的文化“他者”和政治“異己”身份,進而解析和闡釋該文化圖像的發生學構造和審美實踐新進向也就成為了可能和必然。同時也賦予了“中國鏡像”文化形象以多義與歧義迭現的多維度(multi-dimension)審美特征和認識論觀照意義。
二、“自我塑型”論的歷史觀: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
格林布萊特的“自我塑型”論在解讀文化現象時,首當其沖的邏輯前提就是倡導一種將其放回到當時特定的“時代與語境”中去的“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歷史觀,他一向主張要通過考察其歷史語境下的社會行為來解讀文學生產和文化權力“互有軒輊”的博弈痕跡。格林布萊特把他的文學詩學批評個案“首秀”毅然決然地投放在文藝復興時期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竭力還原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的風土人情、民俗風情、起居習慣、情感風尚和價值取向等人文風貌,全息照相般透視特定文化歷史語境下的人物事件和社會現實,從而構建了文學與歷史、文化的交互映射機制。在文學的殿堂里,歷史是永遠的座上賓,歷史已遠遠地掙脫了傳統意義上的“交代歷史背景”等配角束縛,它是真正的“在場主角”。“某一特定生活世界中”的文藝作品既是文化世界和社會存在的產物,也是歷史的產物,但它又可以超越這一限定性存在,成為“歷史性客體存在和自由性主體存在和諧共生”的完美的統一體。
文學文本分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再現各種文本碎片蘊涵的“社會能量”流向蹤跡和“復數歷史”合成線索,以求盡可能地還原和挖掘歷史語境下的各種意義內涵和權力運作機制,尤其是備加關注那些被主流文化屏蔽擱置的邊緣化“多聲部”聲音和微量元素。格林布萊特尤其對那些被官方審查體制和欽定宏大歷史(grand histoire)所遺忘和排異的江湖小人物、軼事小事件、逸聞小插曲以至于野史小動作等“小歷史”(petti histoire)情有獨鐘,他固執地認為文學文本的文化意義和“歷史真相”就隱蔽在這些充其量只能被劃撥到正宗歷史的“括號”中去的蛛絲馬跡。格林布萊特格外注重對這些隱蔽之處的“灰色地帶”的發掘與燭照,一向避談主義的他竟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將這種描述方法贊許為“逸聞主義(anecdotalism)”。格林布萊特談道:“通過這種闡釋,我們才會抵達有關文學與社會特征在文化中形成的那種理解。因為對于某個特定的‘我’來說這個我是種特殊的權力形式。”⑤“這個我”的自我力量和自我造型的核心表征形式即在于一種“特殊的權力形式”,它既可以無處不在,也可以無所不包。任何具象化的文本都是特定歷史時代“權力關系”(power relations)戮力而為的產物,同時也是內置于該歷史形態的雜多“權力形式”的集中體現和具體表征(representation)。
文本的歷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既是諸多文本碎片內在融合的黏合劑,又是各種文本特異性與普適性握手言歡的有效載體。正如王岳川指出的,“自我塑型”論的學術創見主要在于“重喚歷史性和意識形態性”。從格林布萊特批評思想的歷史走向和批評視角(critical perspective)的“歷史轉向”來看,主體性的歷史再現和歷史性的主體建構正是重構歷史主義的理論追求和學術旨趣。“自我”(being a self)主體性形象問題,實質上是人的“自我主體力量和自我客體造型”在現實中的歷史性建構問題。在某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下,西方主流社會將“心造的”鏡像化“中國造型”捆綁在對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文化方位”和“歷史定位”上,就為現代殖民主義的全方位擴張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識形態法理。這種定型化或類型化的“中國鏡像”,不僅說明權力結構在創造著文本的歷史性,賡續不斷地延伸了一段接一段“環環相扣”的復數歷史(histories),而且文本構筑的文化造型也在創造著現實這一正在進行時的歷史文本,維持并鞏固著這種虛擬化的歷史認知秩序和文化權力秩序。這是歷史話語模式的權力層面。西方的“中國鏡像”群組是表述西方集體無意識中“文化他者”的話語,業已超越了所謂觀念訴求的客觀認識與真偽之辨。
西方“中國觀”的嬗變,并非該觀照對象——中國事象或事態發生了些微的變化所導致的,更不存在同步的一一對應關系,甚而卻時常出現“錯位”認知現象,歷史形態所固有的真實性竟退避三舍,來自歷史深處的“觸摸真實”(the touch of the real)的遙遠回響近乎噤若寒蟬了。西方認知主體的“中國鏡像”史觀,所反映的恰是西方文化形態自身的變遷與異化,更是通過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關系的雙重介入來“重新評價歷史”和“重構文學史”。諸多歷史形態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既是各種歷史碎片有機膠合的要素顆粒,又是不同歷史分期獨特性與普適性有效整合的基石和平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mainstream ideology)觀念中關于“中國鏡像”變遷史的“歷史觀”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借助于一個又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性文本片段“枝枝相連、葉葉交通”般的串聯、溝通起來,才最終實現了文化釋義、審美觀照、價值評判等復合意義上質的躍升。正如林繼中所言,“文化詩學的貢獻在于揭示了文學問題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和話語形式,必須從多學科角度觀照文學,全面評價文學研究的文化關涉與價值判斷”。⑥
三、“自我塑型”論的價值觀:歷史的主體性和主體的歷史性
格林布萊特在《重劃疆界(Redrawing the Boundaries)》中一再申明,“文學研究的疆界被確定為地理的、政治的、倫理的和宗教的。不同的閱讀和寫作的界限、正統和非正統、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這些界限可以被穿越、拆解,還可以被再更換”。⑦在“自我塑型”論視域觀照下,橫跨東西方文化地理疆界的批評視角(critical perspective)應運而生,它賦予我們會通中西的可然和必然,引領我們進入了理解與闡釋的跨(東西方)文化境域,賦予我們一種“詩意的棲居”在這一境域中所應具有的共通語言和寬廣視野。但文化蘊涵和生態構造的生成是一個作為歷史認知和文化闡釋主體的“精神遠游者的返鄉”,⑧返回到格林布萊特所倡導的那種“歷史的主體性和主體的歷史性”交相輝映的本真原初狀態。
本源意義上來講,跨(東西方)文化視角應該是一種共時性維度的空間地域視野,至少首先應該是這樣。但在西方文化“現代性”視域這個首要歷史邏輯預設前提下,跨文化視角純粹成了一種歷時性維度的時間觀念視野,“西方”一語成了與時高歌猛進、引領時代潮流的現代派“歷史象征物”;“東方”一語成了停滯不前、頹敗幾至于被掃進歷史故紙堆里的落伍者“歷史象征物”。在這一文化視野的固化過程中,雜糅了更多的分析判斷成分,甚而漸次轉換為一種價值判斷和觀念評判。這樣本來是一種純粹的表征東西方地域差別的自然觀,逐步演變成了一種體現了新舊、優劣、高下甚至于尊卑的價值觀(axiology),一種張揚價值主體性和文化主體性的歷史觀。文化主體的“精神遠游”歷程促成了文化的審美視野的極度拓展,“美的歷程”如青草般更行更遠還生。“遠游者”的文化積淀經歷了風吹雨打,大浪淘沙,駐足回望,凝練厚積成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返鄉情結(return complex)”。
其實我們所做的,是希望在跨(東西方)文化的精神遠游中,從理想追求和理論框架上重新建構(theoretical construction)中國“本土”文化的主體價值和主體意識,樹立弘揚中國“自我主體”意識的文化史觀,在當代社會生活現實的精神家園中建構具有本體性和雜多性的中國自身的文化整體價值觀和文化詩學批評話語體系。正如格林布萊特指出的,“在將文學闡釋與社會文化整體聯系的批評過程中,文學文本的形式內涵必須回到文化生產的歷史語境中進行某種‘癥候式’的社會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⑨一般理論情勢下,批評話語的方法論(methodology)主軸擁有三個維度指向:歷史的“善”,邏輯的“真”,審美的“美”,分別一一對應著價值觀、認識論、意義觀。它們在具體的“社會閱讀”行為過程中將達成高度融合,以期希冀抵達文學文本理解闡釋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巔峰境界。
在傳統的跨(東西方)文化話語領域里,關于“遠東”、“近東”以及“中東”等的話題儼然成了通行世界的“通貨(currency)”談資,一時學人言必稱學貫中西,以正宗的東方學學者自居。似乎惟其如此,才算高蹈了“歷史的主體性”,進而持“跨(東西)文化比較研究”之牛耳便水到渠成了。這些指稱界域本已很顯明,而當下人氣走高的“遠西”后現代組合卻界說模糊。殊不知,恰是“遠西”命題不經意間呼應了“歷史性轉向”的后現代理論呼聲,與其說是西方“自我力量”認知主體開始嘗試以迎納他者“異己力量”認知元素的“包容性”眼光來返躬諸己、回望自己,以期實現“主體性的歷史再現與文化反思”,倒不如說它指明了東西方文化話語形態在當下彼此之間的深刻交融的實情狀況罷了,為最終達成“歷史性的主體建構與自我塑型”預留了充足的話語資源和想象空間。能夠意識到歷史的主體性已屬不易,此階段應屬于啟蒙分期,立足于彰顯歷史書寫者的主體性,以實現書寫歷史的自我價值與現實意義。
而更進一步,東西方文化能夠認識到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將“自我力量和自我塑型”自覺地放置到歷史性的大背景中去,還原自我“內宇宙”的本真狀態和本來面目,并開始意識到要關注自身以外的“外宇宙”,尤其是“周圍的社會存在和文化結構”的潮起潮落。更為可貴的是,能夠放低身段,倡導以寬容之心容納“異在”因素和“異己”力量,以平等眼光看取世界,以對話交往方式平和共處。奠基在東西文化文本的“互文本性”之上,“自我塑型”論同步凸顯了主體性和歷史性的交互性:一方面,主體的歷史性維護了“六經注我”的客觀真實性的充盈狀態;另一方面,歷史的主體性又保證了“我注六經”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今日文化藝術的多樣性正是建構在這種互文性雜糅的多重資源和多重闡釋(multi-interpretation)的跨文化境域之上,隨喜張揚了中國文化哲學自身的學術“主體性”。
經典東方學理論的集大成者薩義德(Said)認為,東方學是一種話語形式,其方法論工具是“宏大歷史敘事的策略性定位”,這點與格林布萊特倡導的“小歷史”敘事的“逸聞主義”方法論針鋒相對。在薩義德看來,就一種知識話語(discourse)與批評范式(paradigm)而言,“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批評話語體現的西方“認知闡釋”主體對于東方題材客體的一種特殊的權力形式,是一種歷史敘事方式、一種文學批評文體(style),“東方學是一種支配、重構東方并對之行使權力的西方文體”。⑩這種權力話語形式,首先是一種“歷史的敘述”方式,敘事主體置身于某個歷史分期的社會宏闊背景中,立足于某種特定政治立場和文化姿態,具體采用何種述說手段,來“述往事、思來者”式的“講故事”。其次又是一種批評文體,也可以視為一種公共文化鏡像的喻稱,即一種駕馭闡釋對象的解讀方式,因而分析“東方主義”這樣一種權力話語必須深入到“文化鏡像”經典文本的深層結構和“潛在的語法”,直抵文體風骨的內在肌理。
與格林布萊特力主打通社會、歷史、文化以及政治各文本結構之間的經絡相仿佛,薩義德稱自己的工作是“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是尋找“社會、歷史與文本自身特征之間的關系”。他力主學術、文化與政治之間是一種相互生產、相互撐持的關系,但他又在格外器重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導作用上邁出了更加堅定的步伐,“對東方的興趣是政治性,這一文化景觀與殘酷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原因之間的相互結合才將東方共同塑造成一個復雜多變的地方”。(11)這里的“東方”語詞已突破了語義學窠臼,進入了政治學范疇,獲取了政治性和歷史性“比翼雙飛”的文化圖景。
四、“自我塑型”論的實踐觀: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在的交互塑型
格林布萊特言之鑿鑿一再斷言,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是“一種實踐(practicing),而不是一種學說或教義(aoetrine)”或“全然沒有學說”。(12)(13)他總是以歷史文化和主體闡釋為理論基點,從歷史性和主體性的對話視角整體介入,來重新考察種族、歷史、文化等意識形態問題,在倡揚“現代性”話語的同時,尋找歷史斷裂之處(disruptive outlook of history)的權力蹤跡,恢復被權力遮蔽的“他者”聲音,借以倡導一種以主體建構的歷史性視角重新探究西方歷史碎片中的文化影像的新實踐觀。
與前此的“東西方”之辨相仿佛,“現代性”語詞同樣既顯示一段自然時間,又昭示一種明確對應著該歷史時間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評判。這種觀念首現于文藝復興期,到啟蒙時代已基本形成,其初衷是以自由批判的理性為主導,追求知識與財富,通過教育與民主達成社會和諧,助推歷史的進步。經由爬梳“現代性”一語的來龍去脈,西方闡釋主體如何對待東方話題的話語姿態和模式選擇,以至于定格成“東方幻想”或“東方情結”,這一生成機制和塑造流程就昭然若揭了。恰如羅蘭·巴特爾(Barthes)所說:“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形象是對一種文化現實的描述”。(13)要想真正實現“通過對一種文化現實的描述”,來塑造文化鏡像并凸顯其身處的文化結構、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空間,倘舍棄了——肇端于格爾茲文化人類學的“厚描”(anthropological thick description)手法,后經格林布萊特推陳出新的——“厚度描述”刀筆之功,更其戛戛乎難哉。
落實到“厚度描述”某一具象化的人類文化行為,其關涉點集中體現在如何圈定西方闡釋主體的觀照視野和考察立場,由此出發,走向四面八方,走向天荒地老。立定在西方“現代性”語境這一坐標原點,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觀念中的“中國鏡像”概貌在針鋒相對的正反兩極間回環往復,本源上是作為“文化他者”的中國鏡像,在不同文化語境中自我調適,實現其維護與確認西方“文化本我”宏大敘事的造血功能和免疫系統。這種有意識的“刻意誤讀(misprision)和逆反(antithetic)”在某個歷史分期、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石破天驚的“睜眼看世界”效果,亦即西方主流社會借助“中國鏡像”在宗教觀念、政治導向以及大眾生活諸多領域的鏡像映照和塑型比照中更好地認識和重塑了“自我力量和自我造型”。
籠罩在“現代性”語境下的“中國鏡像”虛擬共同體僅僅是虛無的意象,飄渺的幻象,并非“物自體”本身,也非現場直播的實況,或者干脆說只是“認知闡釋主體”自身的感知綜合體。對應來說,以工筆紀實性描述某種文化鏡像的輪廓和線條,只能是一種精湛的屠龍之術。延至對“現代性”的否定之否定階段——“后現代性”語境下,唯有剔除文學批評話語范疇中積習已久的唯我獨尊、妄自尊大的“自我本位主義”,設身處地來次“換位”思維,倡揚一種包容性、可持續性比翼齊飛的“生態型批評觀(ecocriticism)”,方才有了一窺全斑和堂奧的或然性和可行性。
結語
從西方文化視域出發,粗筆勾勒西方“認知闡釋”主體塑造“中國鏡像”文化形象的全息拍照流程,我們更加強烈地感受到:同樣面臨“如何看待文化史,又如何以史為鑒”的傳統問題和經典命題,東西方解困和突圍的闡釋策略卻迥異其趣。此處的“史”,既可能是本土的歷史,也可能是異域的歷史,但都必須定位在同一“本我”的“認知闡釋”主體上。每一種文化樣態都是平等的,在以其他文化樣態作為相對于自身的多樣性的同時,“自我”也作為其他文化的多樣性,利用“他者”或“異在”文本作為一面鏡子以觀照、認識和提升自己,不同的文化和諧共存、取長補短,才能使“公共文化鏡像”不斷涵養更新并保持創新活力,從而使整體性文化話語形態以至整個人文精神世界異彩紛呈。
但東西方對此的認知程度判若云泥。同樣廁身于“后現代性”語境下,東方認知主體似乎仍未跳出“現代性語境”的漩渦與羈束,依舊頂禮膜拜在西方文化話語形態的威權之下,也無意于發出自己的聲音。而西方“認知闡釋”主體在重估和重構“中國鏡像”的歷史論題時,開始嘗試承認“他者”或“異在”文化形態的存在合法性和蘊涵合理性,不僅為反思自身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再現”架構的意義與價值,亦為自身文化“歷史性的主體”建構的發展和綿延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充沛的邏輯依據。
一言以蔽之,“合目的性、合規律性”的跨(東西方)文化“交往行為”和“流通、商討”應是雙向互動、平等互信的,以跨文化的“文本”間的相互理解、交互構塑為基礎,就是說,特定的歷史語境下的“本土”文化話語形態和“異在”文化話語形態分別承擔著自我身份角色和他者身份角色,在不斷流動的、持續構塑著的跨文化交往、商討中互相轉換了原初的文化身份角色,也為自身的“單聲道(monological approaches)”話語形態楔入了更多的重音符和高聲部。它們各自隨喜升華出兼收并蓄、別開生面的“公共文化鏡像”新闡釋,就會生成某種“交集”共識和“驚嘆”(resonance)共鳴,這是一種內蘊著差異、陌異甚至“異質”的共識和共鳴(wonder),是寓于差異、陌異性和“異質化(heterogenization)”之中的變動不居的詩性本體同源性。“本土”文化和“異在”文化在相互理解、交互構塑中就會超越自身,獲得新知甚至新穎的理路,最終促成整體性文化話語形態的包容趨升及其批評范式的永續革新。
①⑦王寧《重劃疆界:英美文學研究的變革》(Redrawing the Boundarie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1992)的《導讀》,外語教學與以及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
②⑤⑨(12)王進《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格林布萊特批評理論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頁,第13頁,第11頁。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文藝學和新歷史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頁。
④周寧《在西方現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國形象》,《南京大學學報》,2008.03。
⑥曹衛東等《認同話語與文藝學學科反思》,《文藝研究》,2004,05。
⑧許江《中國當代視覺文化的境遇與責任》,《新美術》2009,06。
⑩(11)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頁,第113頁。
(13)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