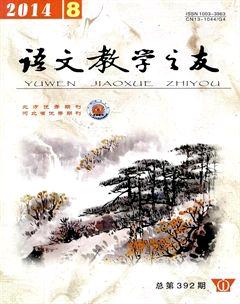《社戲》與世外桃源
鄭秋艷
幾次讀《社戲》,都覺得它太溫情與美好了。它,真的屬于《吶喊》?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出其文章寫作及結集用意的一段對話: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清醒者發出吶喊來喚醒沉睡中的人,使大家能夠一起努力去毀壞困住他們的鐵屋。——這吶喊,恐怕該是聲嘶力竭地直接呼喊出當下悲苦現狀的。從這個角度看,《吶喊》中的文章該都該是像《狂人日記》《墳》等文章,直指社會的黑暗面,剖析黑暗的社會現狀。《社戲》卻仿佛是對童年農村生活的美好回憶,以至于總讓人覺得它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一樣,只是對往昔的回憶,該是來自《朝花夕拾》吧。
然而,它就是小說,就是來自于《吶喊》。那么,它潛藏在溫情與美好之下,到底抱有怎樣的吶喊呢?
《社戲》開篇交代“我”與母親夏季到外祖母家省親,外祖母家的所在地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都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竟覺得這與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很有幾分相似,都是偏僻的所在,桃花源里的人“往來種作”,“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陶淵明借創作出一個偏僻得難以尋覓卻十分美好的小世界——可以短暫逃遁現實的不平和黑暗的桃花源,來表達對東晉戰亂頻繁的黑暗社會的不滿。這兩篇文章都不直言對現世的批評,而改為將心目中所希望的美好世界呈現。用美好的圖景來激發人們對當下黑暗現狀的反抗,顯得格外含蓄低沉,但這何嘗不也是一種吶喊呢?
魯迅《社戲》中創造出的美好小世界又是如何的呢?對于十一二歲及更小年紀的孩子而言,這里是“樂土”——“因為我在這里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得到了哪些優待呢?因為“我”是遠客,許多小朋友都從父母那里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游戲。游戲的內容回歸童真,與大自然親密接觸,如掘蚯蚓、一同去放牛等,且釣到的蝦都歸“我”吃。與《桃花源記》又不謀而合的是,《社戲》中的鄉民們對于外來者也是那么的熱情好客,桃花源人看到外來的漁人后,“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一番交流溝通后,其他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熱情淳樸的民風,讓人流連忘返。平橋村也是這么一個好地方,除了孩子們特別優待“我”之外,孩子們的父母舍得讓自己的孩子不用幫忙家務農活卻來陪“我”玩,自然是好客的,后文六一公公聽到雙喜說摘他家的豆是要來“請客”,立即回答說“這是應該的”,他們的熱情待客可見一斑。
一樣的遠離俗世,一樣的民風淳樸熱情,一樣的怡然自樂,一樣的寫作用意,魯迅的《社戲》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在思想追求上達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一致。那么,是否有區別?區別在哪里?仔細閱讀則不難發現,在接受了西方民主科學等思想之后的魯迅,在字里行間加入自己對于平等自由方面的考量。比如文章一開頭就寫到,伙伴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卻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為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但即使偶爾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當“我”放牛時,黃牛水牛欺生欺侮我,小朋友們便都嘲笑起來了。文章開篇的這些講述,呈現這個小世界里人人平等,沒有那些長幼尊卑等僵化的封建禮法觀念,在這里與年紀相仿的伙伴玩樂起來也是自由自在、暢快淋漓。
不僅如此,彼此之間的情誼回歸到人之根本,是出于彼此之間的關照和愛護。最顯著的是為了能夠讓“我”去看期盼已久的社戲,小伙伴們群策群力,找來了八叔的大白篷船,大家伙兒分工合作,熟練地駕著船,向趙莊飛馳而去。看戲時,小伙伴們也是那么自由自在,淳樸天然:對鐵頭老生、老旦們等表演的評價著實不客氣,吁氣、破口喃喃罵等都是有的,隨時去買豆漿喝也是可以的,不想看了直接走人,也完全沒有什么關系。
回來途中的故事更令人印象深刻:小伙伴們“偷”豆來煮著吃,只是加了點鹽,卻覺著甚是美味。這“偷”,頗值得玩味。首先,阿發主動邀約小伙伴們“偷”自家的豆,因為自家的豆大得多;其次,六一公公家的豆被偷了不少,但第二天發現時,他主要責備的是孩子們“不肯好好的摘,踏壞了不少”,覺得雖然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形下,自家的豆被摘了去請“我”這個遠方來客,也是應該的;而當聽到來自大市鎮讀過書的“我”說他家的豆好吃時,反倒感激起來,不僅夸“我”,還送豆給“我”及母親;再者,他們私用八公公船上的柴和鹽,在他們的思考中,因為去年他們給八公公一枝枯桕樹,所以私用了八公公的一些鹽和柴可以看成等價交換。被“偷”的人(阿發、六一公公)是心甘情愿被偷,“偷”的人因而得以無甚愧疚地享用“偷”來的小羅漢豆,感受伙伴們團結合作帶來的美好滋味。從這個意義上看,借由“偷”羅漢豆這個負面事件,反而更進一步呈現魯迅所要營造出的美好和諧的小世界。
如此看來,魯迅借由《社戲》試圖構建的理想社會,既結合了從孔子的大同社會到陶淵明的桃花源中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美好社會的希冀,更加入了接受西方民主科學思想后對人的平等自由的考量。這個理想社會將來能否實現?魯迅采取了與陶淵明一樣比較保守的處理方式,把它創設在一個偏僻的村落,把主要的理念投射在涉世不深的十一二歲的孩子們身上。也許這樣的純樸自然、自由平等會繼續延續,直到他們長成大人,仍保有這樣的樸實美好。所以,魯迅的《社戲》只寫這一段時間里的美好,低沉的吶喊已發出,將來會如何?留待醒覺的人去創造吧。
(作者單位:深圳市龍崗區龍城初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