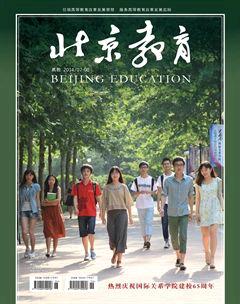大學治理與利益相關者的博弈
陳超群
摘 要:對于大學治理,人們經常談論的是英國的“大學自治、學者治校”或美國的董事會法人治理。進入21世紀以來,很多英美知名大學正經歷著治理危機,有的正在嘗試從多方面改革治理結構。本文回顧胡德在牛津大學、薩默斯在哈佛大學兩次失敗的改革歷程,希望通過比較發掘其中的共性問題,對我國當前的高校治理體系建設有所啟發。
關鍵詞:大學治理 治理危機 教育規律
20世紀90年代,治理理論在國際上大行其道,很多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視角對治理的理論、結構和模式進行了詮釋和界定。而對于大學治理,國內學界津津樂道的經常是英國大學的“大學自治、學者治校”和美國大學的董事會治理模式。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很多英美知名大學在外界刺激、內部紛爭和管理失誤的綜合作用下正經歷著治理危機。本文試圖通過回顧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這兩所高校對治理結構的改革努力,希望能對我國高校治理改革有所啟發。
牛津大學:利益相關者的邊界
牛津大學的治理結構在12世紀~16世紀形成,治理模式表現為主要利益相關者的集體決策、相互制衡,學者參與、分享決策以及組織形式的“松散聯合”。1856年,牛津大學正式確立了教職員全體大會、七日理事會、主政教師大會、校長、副校長等校級治理結構[1]。
1.改革背景。800多年來,牛津大學積累了復雜的管理體制和組織機構。學校擁有40多個院系和研究中心,有39所獨立的私立學院和6所永久性私人學堂。每所學院和私人學堂都是獨立法人,擁有自己的教師、職員、校舍、基金及各種設施。由五花八門的委員會組成的中央機構對全校進行管理,但委員會職責不明、職權重疊、效率低下,以至于哪個委員會對何事負責、甚至是否做過決定都不甚明了[2]。2008年,牛津大學的大學部門管理著5.92億英鎊的捐贈資產,而各學院管理的捐贈資產達26億英鎊。大學經常和各院系發生利益沖突,在其他大學不容置疑的財政預算或資源規劃,在牛津更是無從談起[3]。
2.改革經過。2004年10月,牛津大學突破傳統,聘用具有資深商業背景的前奧克蘭大學校長約翰·胡德擔任校長。胡德上任后,花了18個月時間評估學校現狀,醞釀新一輪改革。2005年3月,經過三輪內部討論,綜合各方意見,胡德主持發布了《牛津治理結構(綠皮書1)》,提出深化治理改革的新方案,但遭到各學院師生的堅決反對。同年9月,牛津大學發布修訂后的《牛津治理結構(綠皮書2)》,部門和學院仍反應激烈。2006年5月,作為《綠皮書2》修訂版的《牛津治理改革白皮書》出臺。為謀求共識,改革派又兩次修訂《白皮書》,組織多次公開辯論和現場投票、郵寄投票,但最終被牛津議會否決,宣告了此次改革的失敗。
3.爭議焦點。在改革派看來,牛津大學校務會統管的事務太多,影響決策效率和決策效果;中央行政機構與學院共同治理決策機制過于復雜,大學與學院之間難以達成共識。英國政府2006年通過《慈善機構法案》,要求大學成立慈善機構,應由以外部人員占多數的校務會管理;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希望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進行類似的治理改革。因此,改革派希望通過學習借鑒美國大學治理模式,改變大學治理結構的組成和規模,在理事會中增加校外理事,對外擴大學校利益相關者范圍,對內加強行政權力、提高管理效率;并設立學術委員會單獨管理學術事務,將學術和行政分開。
在反對派看來,改革使校務委員會由學術主導變為行政主導,既剝奪了學者參與治校的權力,更因為缺乏對行政的監管制衡,容易導致商業化集權,是“管理主義”壓制“學者治校”,動搖了牛津大學“大學自治、學者治校”的根本。反對派認為,對資源的分配使用在學術和非學術事務管理中同等重要,如果沒有資源,特別是經費的分配權,學術事務管理就無從談起,大學的學術和非學術事務不可能完全“分而治之”。雖然政府試圖要求大學都改成外部委員占多數的校務會模式,但這種政策本身缺乏法律依據。據此反對派指出,外部委員占多數的校務會模式并非保障大學學術質量的充要條件,反對為引入更多校外委員將原有校務會一分為二[4]。
4.改革后續。雖然牛津大學的改革者和反對者都認為,需要改變現有治理模式讓大學更好地運行,并不斷提高大學的整體學術質量,但改革終究止于對大學“利益相關者”的理解和引入。經過這次失敗,牛津大學仍和劍橋大學一起,努力“堅守”中世紀形成的大學與學院雙重決策的復雜治理模式。胡德的繼任者安德魯·漢密爾頓上任第一天就宣布:為和世界一流大學競爭,牛津大學將采取美國常青藤大學的獎學金政策,通過向社會募款和提高學費來拓展財源。這意味著,漢密爾頓充分意識到牛津大學的“利益相關者”主要還是在學院、教授和學生;面對競爭壓力,引入外部資源比調整內部格局更容易實現。
哈佛大學:集權效益還是分權自由
美國大學經歷了殖民地時期的董事會主導、南北戰爭后的校長主導,最終在20世紀60年代形成以董事會、校長和教授為核心的治理結構。近20年來,隨著兼職教師的大量聘用,大學終身教職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專職人員主導行政,引發學術權力受侵蝕的討論;而問責制的興盛,促使董事會強化其信托責任。整體上說,美國大學共同治理結構正面臨新的挑戰,董事會和校長權力大有重新加強之勢[5]。
1.改革背景。哈佛大學成立370多年,至今仍在沿用分權管理模式。和絕大多數美國大學統一學費收支不同,哈佛大學各學院院長掌管學費,權力非常大。法學院、醫學院、商學院等熱門專業招生多、學費高,畢業生捐贈也多;而一些冷門專業卻在苦苦掙扎。“各自為政”反映在各學院的校歷不同、教學進度相互沖突、學生很難跨學院選課、學院之間幾乎沒有交流。哈佛大學董事會代表的是美國商業精英的利益,教授們則很容易把科學和學術發現投入市場,成為“獨立的學術企業家”[6],教學反而是“一份煩人的工作任務”。在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除了講課外還得和學生討論;而在哈佛大學,研究生承擔了大部分教學工作。2001年10月《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說,哈佛大學高達91%的學生以優異成績畢業;而耶魯大學只有51%,普林斯頓大學只有44%。文章說,優異成績的背后有個“骯臟的小奧妙”,那就是評定標準的放寬,而這正在腐蝕哈佛大學文憑的含金量[7]。
2.改革過程。2001年10月,曾任克林頓政府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很快著手對哈佛大學的教授結構和治理體系進行改革。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燒向黑人終身教授科爾內爾·韋斯特。薩默斯當面譴責他給學生打分太高、學術水平太低,并通過操控媒體、制造輿論,很快逼走了韋斯特。隨后,他在多個公開場合抨擊教授們的政治偏向,對于他認為不夠格的教授人選毫不猶豫地加以否決,并延攬了一些他認可的學者,并強迫相關院系接受。
隨后,薩默斯開始削減院長職權。上任后第二年,薩默斯與威廉·科比事先“達成共識”,以任命其擔任哈佛大學最大的文理學院院長為條件,要求其在上任后在捐款政策等方面作出讓步。隨后,他又任命了新的教育學院院長、神學院院長、法學院院長。這些院長的任命表面上都走了程序,但薩默斯根本不顧任何反對意見,他們上任后的權力都比前任少。一些院長被迫擯棄先例,允許校長直接過問學院教職人員的聘用問題(哈佛規則,288)。
同時,薩默斯不斷擴大財權。哈佛大學各學院都會印制基金年報,按年級公布捐贈者姓名和捐款額,鼓勵每屆畢業生“創造新的記錄”。過去,如果校友把錢捐給其他部門,名字就不會出現在學院年報中,也不會計入該屆校友的捐資總額。薩默斯說服威廉·科比改變政策,凡是捐25萬美元以上給其他部門的,仍記入該屆校友的捐款總額。名義上,這是為鼓勵校友捐錢給較窮的院系,但實際上,校長可鼓勵校友把錢捐到學校賬戶,再由校長支配,這樣院長就必須去學校申請資金。此外,薩默斯還以審定課程、建新校區為名,發起一系列募捐活動,募得的資金全部(或大部)由校長或校級行政部門掌控。
3.矛盾積累。第一,教授們噤若寒蟬。薩默斯利用其在華盛頓積攢的人脈,操控媒體為其改革鼓吹吶喊、抨擊異議。在媒體面前,教授們要么拒絕采訪,要么避談薩默斯,要么顧左右而言他。唯一一個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說,“無論是從學術訓練還是從個人性格上看,經濟學家往往是學術帝國主義者。他們自認為自己的理性選擇模式能解釋所有的人類行為”(哈佛規則,236)。第二,形式主義的課程改革。在推動課程審定過程中,各委員會由薩默斯一手操控。即便這樣,他有時也要給撰稿者直接打電話。最后出爐的“課程審定報告”只是大體上轉錄了他的辦學理念,提議以分類必修課取代核心課,要求學生在幾個學科大類中選修。輿論一片嘩然,說“它的出籠主要是在薩默斯校長急功近利的政績觀驅動下,花了一年時間閉門造車制造出來的(哈佛規則,344)。”第三,官僚作風激化矛盾。薩默斯的哈佛大學行政班子大多是其在華盛頓的故舊,幾乎毫無高校工作經驗。他還增設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職位,如校長特別助理、個人新聞秘書等,這些人跟著他到處轉,不停地記便條、拍照,幫他拿可樂、披薩和雞翅(哈佛規則,150)。薩默斯的政界作風和“任人唯親”讓師生覺得校園被政府“接管”了,媒體喉舌卻在鼓吹他“坦率直言”,令哈佛人大為惱火。
4.黯然失敗。2005年1月,薩默斯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聲稱,男女之間的先天差別可能是女性在數理領域鮮有建樹的原因,這一言論導致教授們對其不滿全面爆發。同年3月15日,文理學院教授會以218票對185票通過了對他的不信任決議。不過,董事會對此不予理睬,在8月照常給薩默斯加薪3%。為此,董事會成員之一的哈伯,也是唯一的黑人成員憤然辭職抗議。2006年1月,文理學院院長科比在薩默斯壓力下被迫辭職。2006年2月,憤怒的教授們決定進行新的不信任投票,薩默斯只得黯然辭職。
對我國大學改革的啟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現代化的高校治理體系是現代大學制度的重要內容。從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兩所大學失敗的治理改革中不難看到,在建構中國特色的大學治理體系過程中,以下幾個問題似應得到格外關注:
1.要尊重大學民主自治的本質,回歸大學的學術本真。無論從歷史還是從本質看,大學都是教師和學者的民主社團。堅持以教師為本,充分發揮教師的主體作用,是大學治理結構的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簡單運用行政命令推進大學的治理體系改革,必然會遭致師生對“管制主義”“權力政治”的反彈。如果不經過民主程序,在尚未取得價值共識的前提下強行推進改革,甚至通過操控輿論壓制異議,再好的改革愿望、動機和目標也很難得到教師的真心支持,最終必將導致改革陷入僵局,或者走向異化。
2.要尊重核心利益相關者訴求,處理好內外部關系。現代大學是個開放系統,只有主動面向社會開放辦學,積極引入外部監督和問責機制,才能促進大學和外部環境在人員、資源、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不斷激發和釋放大學的活力。然而,師生畢竟是大學直接的利益相關者,只有充分傾聽師生的改革訴求,把握和處理好大學治理和外部機制的關系,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才能激發師生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依靠群眾的力量推進大學治理體系改革。
3.要尊重教育科研的客觀規律,不只用市場評估大學。現代大學承擔了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等多種功能。大學應該追求“卓越”,但“卓越”不能簡單運用經濟學指標來評估,大學治理效率的提高也難以單靠市場機制來激發。正如薩默斯的反對者所說,如果將權力政治和企業治理模式用之于高校,讓權力代替學術、效率代替精神,成為“失去靈魂的卓越”,只會讓哈佛大學成為依附國家和企業的欲望工具,甚至會進一步蛻化為更加純粹的官僚機構。
4.要尊重大學自身的傳統特色,避免治理體系同構化。新制度主義認為,一旦某種制度在某個領域形成并表現出創造力和競爭力,就會對領域內的其他組織產生模仿復制的巨大吸引力,這就是制度同構。胡德和薩默斯的失敗說明,如果不顧大學自身傳統,一味照搬他國大學的治理模式,或者刻意模仿企業甚至政府的治理模式,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習近平總書記說:“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只有消化吸收世界上先進的大學治理經驗,遵循教育規律,尊重大學的傳統特色,才能扎根中國辦好現代大學。總之,只有充分尊重高等教育和大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在改革過程中不斷豐富治理體系改革的價值目標,充分考慮大學的文化傳統以及利益相關者的群體特征,才能最大限度謀求共識、逐步推進大學的治理體系改革。如果簡單運用經濟學指標和市場規律改造大學的治理體系,終會發現在現實面前理論有時會很蒼白,甚至可能把大學推到與歷史相反的方向。
參考文獻:
[1]李維安,王世權. 大學治理[M].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76-77.
[2]蔣馨嵐,徐梅.牛津大學治理改革的行為過程透視 [J].高教探索,2011,(3):61.
[3]趙偉. 保守與變革:徘徊在十字路口的牛津大學[J]. 教育與職業,2007,(4):102.
[4]鐘周.一場對“大學自治、學者治校”的深入反思[J].復旦教育論壇,2010,(8):74.
[5]歐陽光華.董事、校長與教授:美國大學治理結構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8.
[6]莫頓·凱勒,菲利斯·凱勒. 哈佛走向現代[M].史靜寰,鐘周,趙琳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696.
[7]理查德·布萊德利(Richard Bradley).哈佛規則[M]. 梁志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1.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政策研究室)
[責任編輯:李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