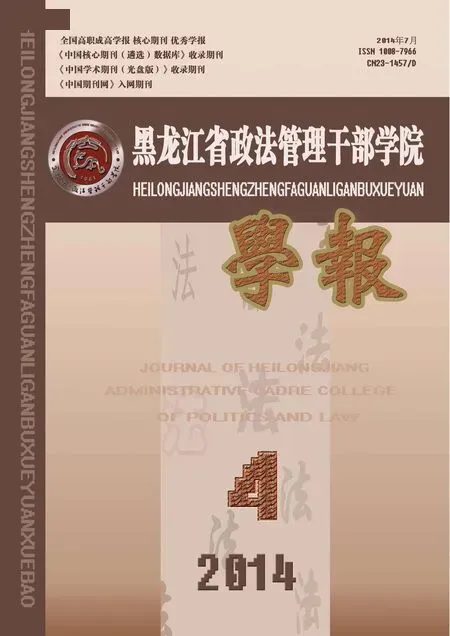唐律之血親規范與現代刑法關系研究
姜鑫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100088)
唐律之血親規范與現代刑法關系研究
姜鑫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100088)
《唐律疏議》是中國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對后代的立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現行刑法與唐律疏議在時間上相差千年之久,但是卻有著濃厚的淵源關系。從血親規范角度比較二者,現行刑法與唐律血親規范一脈相承,唐律血親規范的重要歷史作用和對我國現代刑法的深遠意義。
血親規范;唐律;現代刑法
作為中華法系代表作的唐律,體現出家族法與倫理法的屬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內容就是血親規范。唐律的制度規范,既可以作為中國古代封建法律的范本,也為我們現代法制建設提出眾多的課題。制度如曇花一現,而文化可以千年萬載。唐朝曾經的輝煌已不再,值得我們長久思考學習的是當時先進的文化。這種與宗法倫理緊密相聯的血親規范在現代刑法中也留下了投影。
一、唐律中血親規范在刑事立法中的體現
縱觀唐律,我們發現:唐律共有502條,其中直接以血親關系主體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條文有77條,血親規范凌駕于法律之上,在唐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發揮,典型的有準五服以制罪、親親相隱、權留養親、十惡。
(一)“準五服以制罪”在唐律中的體現
“五服”,即以喪服為標志表示親屬間血緣親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稱“五服”。“準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是:服制愈近,即血緣關系越親,以尊犯卑者,處刑愈輕;相反,處刑愈重。服制愈遠,即血親關系疏遠者,以尊犯卑,處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五服”制度在唐律中親屬相犯方面的具體規定如下:
1.《唐律疏議·斗訟》:“諸毆緦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遞加一等。尊屬者,又各加一等。傷重者,各遞加凡斗傷者一等,死者斬。即毆從父兄姊,準凡斗應流三千里者,絞。”這是關于毆打五服以內近的親屬情形下的刑罰。
2.《唐律疏議·賊盜》:“諸盜緦麻、小功親財物者,減凡人一等;大功,減二等,期親,減三等,殺傷者,各依本殺傷論。”對于親屬之間相盜,唐律采取由疏至親遞減的處罰原則。這是關于親屬之間相盜情形下的刑罰。
3.《唐律疏議·雜律》:“諸奸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異父姊妹者,徒三年,強者,流二千里,折傷者,絞。妾,減一等”,“若奸小功以上親以及父祖之妾,入十惡大罪,為常赦所不原”。對于親屬相奸的處罰原則,可以概括為:服制越近,輩分越尊,處罰越重。這是關于親屬相奸情形下的刑罰①參見《唐律疏議·斗訟》,劉俊文校點,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二)親親相隱制度在唐律中的體現
親親相隱是中國封建刑律的一項原則,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的不論罪,反之要論罪。實行這項原則,是為了維護封建倫常和家族制度,鞏固君主專制統治。《唐律疏議》的各篇中都有親屬相隱制度的規定,具體來說同居相為隱的主要內容為:
1.《名例篇》。“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 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這是關于“同居相為隱”的法律總原則。
2.《斗訟篇》。“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這是關于告發尊親屬的規定。“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這是關于告發卑親屬的規定。
3.《斷獄篇》。“其于律得相容隱,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這是關于不得逼令親屬作證的規定。“自捕送官者,同告法。”這是關于幫助父祖父逃脫囚禁不得復捕送回的規定。
4.《捕亡篇》。“匿得相容隱者之徒侶,假有大功之親,共人行盜,事發被追,俱來藏匿,若糾其徒侶,親罪即彰,恐相連累,故并不與罪。”這是關于“知情藏匿罪人”的規定。
(三)留養制度在唐律中的體現
留養制度指對于犯死刑、流刑等重罪人犯,家中尚有待其頤養天年的直系血親,法律特許死刑犯人“侍親緩刑”、流刑犯人“權留養親”,等到年老的直系血親死后,始令罪犯依律服刑的一種制度,此制肇始于北魏,定型于唐代。《唐律疏議·名例》規定:“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期親成丁者,上請。犯流罪者,權留養親,不在赦例,課調依舊。若家有進丁及親終期年者,則從流。計程會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應侍,合居作者,亦聽親終期年,然后居作。”“諸犯徒,應役而家無親丁者,徒一年,加杖一百二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若徒年限內無親丁者,總計應役日及應杖數,準折決放。”①參見《唐律疏議·斗訟》,劉俊文校點,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唐律對權留養親制度的規定更加具體,體現出唐律注重血親規范立法。
(四)定罪量刑中血親規范的體現
唐律規定,實施同樣的行為,因行為的對象與行為人是否有血親關系,以及血親關系的遠近的程度不同,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就不同。按是否有血親關系,可導致有罪與無罪兩種結果。因此血親關系遠近是區分有罪無罪的標準。另外即使存在血緣關系,血親關系也有遠近之分,所承擔的刑罰也有輕重的差異。
1.《唐律疏議·斗訟》卷二十三。“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意思是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孫本人的行為,子孫不得向官府告發,告者一律處死,不告是子孫的法定義務。告發其他有血親關系的近親屬,即使所告情況屬實,也屬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親等處刑。
2.《唐律疏議·斗訟》卷二十四。“諸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意思是告有重罪,不告無罪。但如果對與自己沒有血親關系的人,或血親關系較遠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為,則必須向官府告發,不告有罪。
3.《唐律疏議·斗訟》卷二十四。“諸強盜及殺人賊發,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單弱,比伍為告。當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意思是血親關系與定罪,還表現為長幼之別,卑幼實告尊長有罪,尊長誣告卑幼無罪,“即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論”。
4.《唐律疏議·賊盜》卷十七。“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沒官,男夫年八十歲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若家人犯罪,不論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參與、是否首從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與家人有血親關系,近親要斬,遠親要流,物財沒收[1]。
(五)唐律“十惡”中血親規范的體現
“十惡”原稱“重罪十條”,設立于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律》中,是將嚴重危害國家利益和倫理道德的行為歸納成十條,放在法典的第一篇,以示為重點鎮壓對象。到隋唐時,定型為“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1.“惡逆”。是指“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此罪的立法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近親尊長的人身及尊嚴的不可侵犯性,從而鞏固封建血親家庭關系和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
2.“不孝”。是指“告言、詛詈祖父母以及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逆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等,子女違背父母意志或者侵犯父母尊嚴的情形。疏議曰:“善事父母曰孝。既有違犯,是名不孝。”封建統治階級認為,在家為孝子,出仕才能為忠臣。用刑法手段來懲治不孝,目的是強調子女要孝順父母,維護血親家庭這一社會基本結構,而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政權[2]。
3.“不睦”與“內亂”。是屬于血親間的互相侵犯的行為。“不睦”是指“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內亂”是指“奸小功以上親、父祖妾與和者”。兩者都是依血親關系規定的重罪,意在維護以家族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并進而鞏固封建統治秩序。
二、唐律的血親規范與我國現行刑法的比較
(一)唐律中的權利等差原則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唐律體現了封建的權利等差原則,皇親國戚和達官貴人犯罪,通過議、請、減、贖等血親特權的規定則可以逃避刑事制裁。如:唐律規定的八議中的議親、議賓就是直接根據血親關系確定的,親指“皇帝袒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賓指先朝王室后裔。袒免以上親指己身以上以下各五代的血親。小功以上親指從己身數起上下四代血親和三代以內的姻親。緦麻以上親指從己身數上下五代以內血親和二代以內姻親。除“十惡”大罪外,這些人犯了罪,法定為流罪以下減等處理;死罪由官員查清案情、犯人身份、相關法律規定和擬定裁判意見,上報皇帝批準。八議者期以上親及孫,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流罪以下法定減等處理;死罪則上報皇帝處理。七品以上官的親屬,流罪以下皆可贖。有上請權者的親屬,流罪可減等處罰。
我國現行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意思是公民的法律地位平等和適用法律的平等,血親關系不再成為司法特權的依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對唐律中司法特權原則的摒棄,現代刑法施行的是民主政治的準則,不應存在特權。較之中國古代刑法的權利等差、同罪異罰原則,我國現行刑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固然是巨大的進步,但是卻流于機械、刻板,因為它忽視了一個關乎中國國情的重要因素——血親倫理。重家庭、重親情,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民情、人情,已內化為中國人的精神和意識,早已成為中國人骨子里的東西。作為國情、民情、人情的倫理學親具有明顯的社會性,是立法必須正視的基礎和依據。當代立法應當充分考慮血親關系的特殊性和中國人重視親情的國情、民情,吸收中國傳統法律中關于倫理血親的合理性因素,用以豐富和完善自身。從法制的發展史看,情入于法,使法與倫理血親相結合,更易于被公眾所接受,且法順人情,可以沖淡法律生硬冷酷的外在形式,更易于法律的推行。
(二)唐律中的親親相隱和現行刑法的偽證罪等
《唐律疏議·名例》卷六:“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外孫,若孫之父,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 語消息亦不坐。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判以上者,不用此律。”意思是凡同財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親屬、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妻、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隱瞞,部曲、奴婢也可以為主人隱瞞犯罪,即使為犯者通報消息,幫助其隱藏逃亡,也不負刑事責任。小功以下親屬相容隱者,減一般人三等處罰。《唐律疏議·斷獄》卷二十九:“其于律得相容隱,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意思是強迫某些血親相證犯罪,是犯罪行為,要承擔刑事責任。分析以上二條,主要的含義如下:第一,在一個家庭內生活的人及其他較近的親屬,幫助犯罪親屬掩蔽證據、贓物、通風報信,隱藏犯罪親屬,不認為有罪,如果有罪,也要依血親關系遠近減輕處罰。第二,強迫血親相證犯罪,是犯罪行為,要承擔刑事責任。唐律的這些規定有其科學依據,法律目的在于以法律的力量將維系倫理親情,鞏固國家統治。血親關系是重要的社會組織,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是社會矛盾的緩壓閥。如果強迫血親相證犯罪,很可能造成該血親組織的瓦解,造成該社會細胞的壞死,唐律實施如此親屬相隱的血親制度,不至于產生法律實施上的得不償失。拋開階級局限性不提,這種規定有一種人性化的東西在里面。
我國現行刑法第三百零五條規定的偽證罪,犯罪主體均為一般主體,并未考慮血親關系的特殊性,在現代刑法的實施中出現諸多的情況。例如:某人涉嫌嚴重的刑事犯罪,其近親屬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終于站在法庭上揭露親人罪行,以彰顯法律神圣,最終戰勝人情、私情。這體現了有的人遵法而行,大義滅親,挺身而出證明涉嫌犯罪的親人有罪或迫其歸案,但現實中此類人數并不算多。還有多數人對涉嫌犯罪的近親屬多方庇護或不愿舉證其有罪,寧愿因此犯了偽證罪、包庇罪,淪為囚犯也在所不惜。因此,這樣的規定并不能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現實中實施起來困難重重。這也是證人出庭率低的一個制度性原因。陳興良教授曾說:“人性乃人之為人的基本品性”[3]。一部良法應該是符合人性的。正如孟德斯鳩說:“為了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而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我國的刑法第三百一十條規定窩藏、包庇罪的構成要件如下:“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根據該規定,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窩藏、包庇行為,不論其與被窩藏、包庇的犯罪分子有何身份關系,都一律予以同樣的定罪量刑。這表明,如果我們的親人犯罪,我們并不能享有拒證權,只能大義滅親。
(三)唐律中血親殺人傷害的規范與現行刑法的故意殺人等
在具體的刑事規范方面,唐律針對親屬間的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設計了不同于普通人之間人身侵犯的規定,充分考慮了當事人之間長幼、親等的區別。《唐律疏議·賊盜》卷十七:“諸謀殺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凡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唐律疏議·斗訟》卷二十二:“諸毆緦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遞加一等。尊屬者,又各加一等”。意義有三:一是殺血親長輩比殺一般人罪重,如謀殺父母,不管情節輕重,既遂未遂,一律斬首;如謀殺非血親,最低刑為三年有期徒刑。二是依親等制刑,如幼殺長,越親罪越重,越疏罪越接近普通殺人。三是依長幼制刑,如有血緣,長殺幼,罪輕于普通人殺人;幼殺長,罪重于普通殺人。唐律制定者認為,血親關系畢竟不同于普通社會關系,長輩對晚輩有養育之恩,晚輩對長輩應有報達之意,且親等不同,行為人與受害人之間情感和利益的親密程度不同,由此決定了行為人主觀惡性的程度。
我國現行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從以上規定看,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此規范沒有考慮到血親之間的犯罪的特殊性,未免過于簡單化。但在現實生活中,血親關系遠近卻真實地影響犯罪者的主觀惡性,影響著人們對此類犯罪的法律評價,刑事司法人員必然陷入法律與現實的矛盾之中。
唐律中關于血親殺人傷害的規范,充分考慮了當事人之間的血親關系及引起血親侵害的具體背景,也很強化對血親非死亡性侵害的刑法保護。筆者認為值得我們吸收和繼承:首先,對于殺死血親長輩的犯人治罪要比殺死一般人罪重,如果是謀殺非血親,那么最低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如果兒女謀殺父母,不管犯罪情節輕重與否,既遂未遂與否,一律死刑。因為血親關系畢竟不同于普通的社會關系。其次,法律依血親等制刑,如果是幼殺長,那么越親罪越重,越疏罪越接近普通殺人。因為隨著血親關系的遠近不同,行為人與受害人之間的情感和利益親密程度即不同,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也不同。再次,法律依長幼制刑,如有血親關系,長殺幼,罪輕于普通殺人,幼殺長,罪則重于普通殺人,因為長有恩于幼在先。因此,刑事立法應當借鑒唐律的相關規定,充分考慮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的當事人之間的血親遠近,區分不同層次和情況,更科學、合理地對血親侵害行為進行懲處。
(四)唐律中親屬間相盜的處罰與現行刑法的盜竊罪
《唐律疏議·賊盜》卷二十:“諸同居卑幼,將人盜己家財物者,以私輒用財物論加二等。”這表明,唐律注意到了家庭內部相盜與一般人之間盜竊行為的區別,一般盜竊十匹布要判一年半徒刑,而盜用自家十匹布只要打十板,處最低刑;家人與外人合謀盜竊自家十匹布,只加二等處罰,即打三十板。同時又規定:“諸盜緦麻、小功親財物者,減凡人一等;大功,減二等;期親,減三等。”即如果盜竊親屬的財物,處罰也低于一般盜竊,并且隨行為人與受害人血親關系的親近而減輕處罰。造成差別的直接依據就是基于血親和家庭關系。因為血親關系越近,其盜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越輕。
我國現行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了盜竊罪,其主體為一般主體,并未考慮親屬間相盜的情況。對于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血親內盜行為,最高人民法院曾出臺過司法解釋,未將一般盜竊自家財物的行為認定為犯罪,且對盜竊親屬財物行為的認定較模糊,操作性不強。
(五)留養制度與現行刑法的緩刑制度
《唐律疏議·名例》卷三:“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期親成丁者,上請。”唐律將盡孝放在特殊位置來考慮,殺人償命是國法,但有的殺人犯卻準許存留養親,以盡孝道,則是法、禮、情的統一,也是為了維系家庭養老和繁育后代的功能,減輕國家、社會的負擔。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這一例外的規定體現了對生命和弱小的人文關懷,合情合理,深入人心。
三、古為今用的啟示
歷史是發展的,現實是全新的。現行刑法與唐律疏議有質的差異性,但也有內在的一致性。血親規范是中華法系一大特色,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是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因為血緣關系永遠是重要的社會關系,人類也永遠不能回避血緣關系。血緣關系是溫情的載體,也是沖突的源泉,中國刑事立法必須面對這一矛盾,也要充分利用這一資源,讓我們看到破解當今立法和法律實施中所面臨困惑、難題的一些線索。既然對人倫精神的關注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點之一,且其作為中華法系優秀的文化遺產,為當今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的法律所吸收和借鑒,那么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刑法是否有必要對以唐律為代表的古代法律進行有選擇地吸收與繼承,進而對血親規則、人倫精神給予適當的包容呢?如果有必要,那么我國新刑法之于血緣精神漠視的原因又在哪里?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強調階級的意識形態影響了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繼承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者的設計,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素質獲得極大提高的社會,因此社會主義社會與一切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具有本質的區別。然而,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科學論斷長期以來卻被我們簡單地理解為:社會主義必須與資本主義“對著干”,與過去任何社會“一刀兩斷”。受這一意識形態所支配,我們一直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視為洪水猛獸,把封建社會的東西視為垃圾糟粕,而徹底予以拋棄,從而造成文化傳統的斷裂。
(二)對刑法功能的認識產生了偏差
按照刑法理論的通說,刑法具有兩大功能:保護功能和保障功能。刑法的保護功能,是指制定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即保護公民和社會不受犯罪的侵害。刑法的保障功能,是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不受刑罰權非法侵害的功能。“自從刑法存在、國家代替受害人施行報復時開始,國家就承擔著雙重責任:正如國家在采取任何行為時,不僅要為社會利益反對犯罪者,也要保護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報復。現代刑法同樣不只反對犯罪人,也保護犯罪人,它的目的不僅在于設立國家刑罰權力,同時也要限制這一權力,它不只是可罰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其表現出悖論性:刑法不僅要面對犯罪人保護國家,也要面對國家保護犯罪人,不單面對犯罪人,也要面對檢察官保護市民,成為公民反對司法專橫和錯誤的大憲章”。然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由于受“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所支配,我們對刑法功能的認識產生了偏差,不適當地強調了刑法的社會保護功能,把刑法視之為“社會尖刀”,而忽視了刑法的人權保障功能。
唐朝血緣關系立法規定中的一些合理性要素,猶如塵土中的珍珠,經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工作,能夠用來彰顯人文關懷,有利于家庭和諧幸福,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更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實為治國之上策,值得我們好好地思考和借鑒。
[1]李偉迪.唐律解讀:血緣立法的經典[J].法學研究,1999,(3).
[2]于朝端.“親親相隱”與現代拒證權[J].江蘇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1,(2).
[3]陳興良.刑法的人性基礎[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李 瑩]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erion of Blood in Laws of Tang Dynasty and Modern Criminal Law
JIANG Xin
The"Tang Code"is a master of law in ancient Chinese winners,which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f legislation.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differs by thousands of years with Tang Code,but they have a deep origin relation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se two blood specification,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with consanguinity specification of Tang Code,which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China’s modern criminal law.
Genetic specification;The laws of Tang dynasty;The modern criminal law
DF01
:A
:1008-7966(2014)04-0014-04
2012-06-11
姜鑫(1978-),女,黑龍江綏化人,博士研究生,哈爾濱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