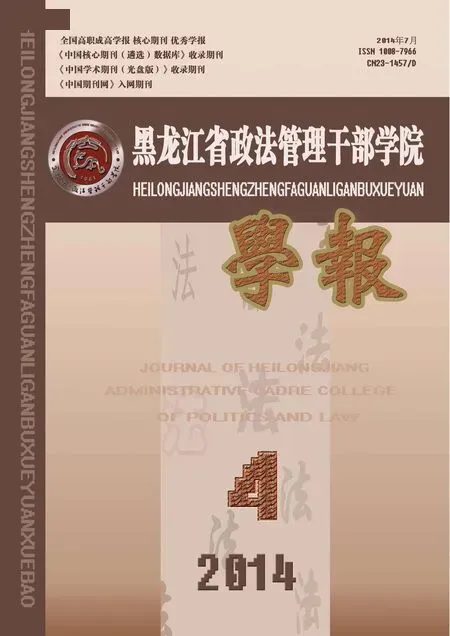司法過程的性質(zhì):卡多佐的心路歷程
劉濤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南京210046)
司法過程的性質(zhì):卡多佐的心路歷程
劉濤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南京210046)
卡多佐對司法過程的理解以邏輯的方法為起點,關注司法中邏輯一致性,特別是普通法中”遵循先例“原則對司法平等與司法信仰的重要作用;歷史與習慣的方法幫助法官解決邏輯思維的僵硬;社會學的司法方法運用客觀的解釋原則,探尋社會福利的現(xiàn)實意涵,賦予法官裁量權的同時也限制裁判者的恣意,最終通過發(fā)現(xiàn)與形塑的方法幫助法律成長。法律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過程。
司法過程;邏輯方法;歷史與習慣;社會學司法方法
本杰明·卡多佐是美國法律發(fā)展史上不容忽視的一位人物。作為一名法官,他長期從事司法工作,撰寫了許多被奉為經(jīng)典的法律判決意見;作為一位法學思想家,卡多佐的學識與智慧啟發(fā)了無數(shù)人的思考。卡多佐一生的著作并不多,而最重要的當屬《司法過程的性質(zhì)》這本由1921年其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所作演講為藍本的小冊子。通過此書,卡多佐向世人展示了其多年對司法乃至對社會的思索。法律不只是一套規(guī)則,它是分配權利與義務、并據(jù)以解決糾紛、創(chuàng)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1]14-15。對于此書的主題:司法過程,卡多佐在開篇就談到了描述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難度。作者認為,司法是一種人類有意識的活動。但是,人類有意識的活動中也有潛意識的成分。法官也是普通人,并不能擺脫這一因素的影響。卡多佐非常坦誠地說明了他對司法過程的思考僅是對那些“難以捉摸”的各種心理傾向與潛意識成分的一種基于自身司法經(jīng)驗的解讀。在筆者看來,卡多佐的解讀無疑將一些前人無法說明或者闡釋得不夠明確的司法過程中的要素以較為清晰的輪廓展示在讀者面前。
一、邏輯方法在司法過程中的首要性
卡多佐認為,當司法中的淵源問題十分清楚的時候,例如面對一定的案件事實,法律規(guī)則由憲法或者法典清晰地提供,法官的工作也就簡明了。在這些情況下,法官法的重要性是讓位于立法者所頒行的法律的。當然,這并不是說在這些情境下,法官的工作就是敷衍和機械的。因為在這些確定的法律條文之間,司法者仍有各種漏洞需要彌補,各種疑惑與模糊之處需要澄清,各種錯誤與困難需要減輕。司法者所有的這些工作在卡多佐看來,都是為了達到這樣一種效果:使得立法者先存的意思得到正確的澄清。此種情況下的司法任務并不十分艱巨,真正困難情形在于:當司法者面臨特定的事實的時候,立法并沒有標明任何特定的意思時,司法者就必須揣摩立法者如果面臨當前的情況所持的意思,也就是實定法的潛在含義。卡多佐認為,這才是司法過程的真正難點所在。
法條存在漏洞與空間的情況隨著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變動。以憲法為例,由于憲法規(guī)范的籠統(tǒng)性,如果要在各種具體的案件中適用,司法者必須對條文予以解釋。
憲法條文的概括性注定了其內(nèi)容與意義隨著時代而變化的特性。而這種解釋,在卡多佐看來,反映了一種“自由裁判”的傾向。法律解釋的意義被擴大了,司法過程超越了僅僅對立法者意志的考察。但是,卡多佐認為,基于立法的司法過程并不是其思考的重心所在。即使當法律解釋出現(xiàn)困難的時候,這些困難并不神秘。真正令其著迷的乃是普通法意義上的司法過程及其性質(zhì)。
遵循先例是普通法司法中的首要與基本規(guī)則,而法官遵循的先例的背后,則是人類的生活習慣與社會組織。而且此兩者之間也存在著互動。在多數(shù)情況下,由此形成的先例判決規(guī)則能夠解決問題,法官的司法工作就可以概括為:搜索與比較。卡多佐認為,如果這樣就能概括普通法意義下的司法工作的性質(zhì),這項工作也未免太無趣和缺乏挑戰(zhàn)。當先例并不能滿足當前案件的審理要求,當兩者存在“色差”時,嚴肅的司法工作才真正開始。司法者在此時必須為當事人以及后人“形塑法律”。而如果我們探究這一司法過程的心理學意義,也就是遵循先例→先例不能適用→形塑新規(guī)則→遵循新規(guī)則的過程心理學意義,在卡多佐看來,這一意義乃是習慣的力量。另外,卡多佐認為,在普通法司法的過程中,我們還應當注意到這一過程的另一種前提:在法律的運行中,并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永恒真理。判例法的法律規(guī)則與原則并沒有被當成一種實定真理,而是被理解為法律場域?qū)嶒炦^程。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此時的規(guī)則變成了彼時的例外,此時的例外演變?yōu)楸藭r的規(guī)則。“一個變動中的社會,所有的規(guī)則是不能不變動的。環(huán)境改變了,相互權利不能不跟著改變。”[2]
在這場變動不息的實驗中,普通法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面臨著兩項工作:首先,他需要將先例中的實質(zhì)規(guī)則部分在紛繁復雜的案件事實與說理內(nèi)容中抽離出來;其次,他需要決定這些法律規(guī)則的走向,也就是適用規(guī)則的過程。第一項工作說起來也并不輕松:先例也是由法官寫成的,而在這些法律意見中,法官自己并不可能按照方便后人的方式去敘述,而且很可能這些法律前輩們在論述案件的核心意見時也是隱晦甚至是錯誤的,而辨明這些規(guī)則則需要法官在法學院學習乃至今后的工作中經(jīng)受大量的訓練。易言之,這是一項技術含量很高的“手藝”。
但是,第一項工作顯然不是卡多佐最為擔心的。當我們發(fā)現(xiàn)了先例中較為確定的法律規(guī)則之后,如何適用才是所謂的“嚴肅工作”。在此,卡多佐對各種不同的適用法律規(guī)則的方法作了重要的分類,他將邏輯的司法進程稱為類比規(guī)則,也可稱為哲學的方法;而歷史的司法進程可稱為進化的方法;傳統(tǒng)的方法則是遵循著統(tǒng)一認同社群的習慣;社會學的方法則是指遵循正義的司法過程,同時也意味著遵循時代道德與社會福利。卡多佐也在其后的論述中闡述了他對各種方法的理解。
卡多佐認為,在司法中注重邏輯的一致性并不是最高階層的善,但是這并不表示在司法中追求邏輯的一致性沒有價值。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在法官適用法律過程中,進行非常嚴密的邏輯推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多數(shù)案件中,保持判決結(jié)果的邏輯一致性仍然十分重要。如果一些具有相同法律爭議的案件,當事人當然期望得到相同的判決。如果情況與當事人的預期恰恰相反,那必然是司法上一種極度的不正義。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的多數(shù)情況下,遵循先例無疑應被當成規(guī)則而不是例外。對于普遍的民眾來說,司法過程中的邏輯規(guī)律是其對司法過程保有信仰與尊敬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我們知道,普通法的發(fā)展是自下而上的,律師階級代表了眾多普通當事人的訴求。在卡多佐看來,這些訴求在特定的時空框架下可能是暫時的和突發(fā)的,但是普通法的發(fā)展延續(xù)性注定了這些訴求終究會成為重要和持久的一種社會訴求。司法中的遵循先例原則幾乎總是將對傳統(tǒng)的熱愛和尊敬與對規(guī)則和合法性的熱愛結(jié)合起來[3]。所以,遵循先例與法律體系的邏輯一致性,在普通法的語境下,絕不僅僅意味著保持法律體系的“好看”與“對稱”等這些所謂的法律美學,其更意味著保有法律對社會民眾深層次的訴求的真實一貫性。質(zhì)言之,哲學的方法運用乃是為了保有法律的普遍信仰。
在司法中使用邏輯的方法會遇到這樣一種問題:沖突的規(guī)則或原則在同一案件中可能都能夠得到適用,我們應當明確司法中選擇的理由。而卡多佐認為,選擇一種規(guī)則而舍棄另一種規(guī)則的理由是由于正義的理念,這種正義也是一種衡平中的正義。在此時,雖然表面上法官仍舊是按照邏輯的一致性作出了司法判決,但是在此種情況下的司法則是由其他的如歷史的、習慣的以及社會福利等方法真正左右了法官的走向,使得司法正義得到體現(xiàn)。
如果說上述問題可以通過使用正義的概念得到解決,另外一種司法定式則是讓人憂慮的:將哲學的方法以及邏輯一致性的目的當成司法的最終和最高的意義。這一司法的思維定式乃是中世紀絕對法律現(xiàn)實主義的殘余,它將實定法及其規(guī)則嚴格地限定在有限的邏輯框架之下,將法律當成一種“信條”,使之無法在變動不居的現(xiàn)實生活中自洽①馬克思·韋伯針對以英國法為源頭的普通法的非邏輯性觀點:在韋伯眼中,英國法更多是在許多地方表現(xiàn)出“非理性”的特征。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英國法盡管具有嚴格的形式主義,但卻缺乏以晚期羅馬法為代表的邏輯意義上的形式理性。英國的判例法,既沒有在法律推理過程中嚴格遵守三段論式的演繹理性,也沒能(或不愿)實現(xiàn)“將所有可以設想到的事實情境都在邏輯上納入無缺陷的規(guī)則系統(tǒng)中”的系統(tǒng)化目標,因此,英國法并沒有實現(xiàn)“邏輯升華”意義上的理性化,只不過仍采用一種羅列式的關聯(lián)方法,一種法律的“決疑術”(legal casuistry)。參見李猛:《除魔的世界與禁欲者的守護神:韋伯社會理論中的“英國法”問題》,http://www.gongfa.com/htm l/gongfazhuanti/chengxulixingzhuanti/2012/0201/1623.html,訪問時間:2013年11月28日。。在筆者看來,這一司法危險在大陸法系中更可能成為現(xiàn)實,但即使是從歷史的角度看,生成規(guī)則和運行機制截然不同的普通法體系,也可能由于司法者的慣常與“偷懶”,使一些案件的判決在邏輯自治的外表下潛藏著“錯判”。總地來說,司法過程中哲學的方法可以被描述為這樣一種形態(tài):以一定的規(guī)則或原則為基準,以與之相應的潛在法律結(jié)果為目的司法適用的過程。不管是在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還是其他法系,這一司法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
司法中歷史的方法著眼于一些法律概念的發(fā)展史。有些法律概念完全來自于歷史的演進,在此種情形中,邏輯必須“讓位”于歷史。“一頁歷史抵得過一整本邏輯。”[4]如果要使得司法的過程“看起來”更有邏輯,在某些法律領域我們必須追根溯源。歷史的方法并不意味著司法過程的因循守舊,在現(xiàn)代司法中,歷史的方法實乃為了法律發(fā)展。在運用歷史方法的司法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卡多佐引用了龐德所舉的一個例子予以說明:贈與動產(chǎn)的合同的效力是否應當以交付為標準?不同的法官會按照不同的法律歷史進行判斷[4]。法官的不同選擇有時候很難說清楚原因。就像法律流派的潮流或者時尚,就像文學與藝術中的潮流與時尚一樣,難以捉摸。
如果哲學的方法或者歷史的方法并不能指明司法的方向,習慣(或習俗,custom)的方法可能會派上用場。卡多佐認為,在普通法發(fā)展的早期,習慣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如今,司法過程中習慣的方法并不是指運用習慣創(chuàng)造新的法律規(guī)則,而是指將其理解為一種司法裁決的習慣(a custom of judicial decision,not a popular action),將習慣作為一種司法檢驗和標準(tests and standards)來決定既成規(guī)則應當如何適用。習慣的方法在現(xiàn)代司法中的意義應當在此處“剎車”,而將更多的工作交給立法去做。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習慣在商業(yè)交往中仍舊具有“發(fā)展規(guī)則”的重要作用,在缺少法律(特別是在當下缺少立法規(guī)則確立的情況下)的情形中,法律的舊有“信條”不能阻止商業(yè)世界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②卡多佐舉了在其生活時代鐵路、電話等新技術所帶來的商業(yè)活動中交易規(guī)則的變化,我們可以以此比照當今世界新技術的發(fā)展所帶來的交易場景與規(guī)范的更新與調(diào)整。。筆者認為,生活發(fā)展的趨勢不僅影響著普通法的發(fā)展,也必然影響以信條學為基礎的大陸法系司法解釋邏輯。例如在大陸刑法中的過失行為能否構成共犯從而對其進行歸責問題,有的學者就指出了信條學的故步自封不可能阻止和抗拒“生活邏輯”,從司法實務來看,這種抗拒也沒有獲得成功。筆者認為,生活發(fā)展的趨勢不僅影響著普通法的發(fā)展,也必然影響以信條學為基礎的大陸法系司法解釋邏輯。任何法律和政令的貫徹,如果沒有習慣的支持,就必然需要使用大量國家強制力[5]。這不僅使得投入到法律執(zhí)行與法律秩序維護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并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尊重習慣并善于在司法過程中利用習慣的力量是在特定情況下明智的選擇。
對于習慣方法在司法中的檢驗作用,卡多佐認為,在一般性的權利義務確立以后,我們應當根據(jù)習慣規(guī)則決定其在司法適用中的取舍。在無數(shù)的司法情形中,規(guī)則應當擇樣適用,我們必須參考特定行業(yè)、特定職業(yè)以及特定交易的習慣規(guī)則予以確認。生活中的活動決定了一定行為的慣常模式,而慣常的行為模式最終可能會成為法律的規(guī)則的一部分,法律的發(fā)展中保留了這些來自生活的慣常。“生活塑造了行為的模子……法律維護的就是這些從生活中獲得其形式和形狀的模子。”[6]38
二、社會學司法方法與普通法精神
在論述了上述司法過程中可能運用的不同方法,卡多佐提出了其想要論述的一個重要司法方法:社會學方法。卡多佐認為,當法官從社會需求的角度認為一種司法解決途徑好于另一種時,我們就必須打破法律的邏輯美學,暫時忽視歷史與慣常(ignorehistory and sacrifice custom)以期追求更重要的司法目的。法律的最終立場是社會福利。如果一項法律規(guī)則不能保證這一目標,其長期存在的正當性就值得懷疑。當法官需要決定既存法律規(guī)則的內(nèi)涵與外延時,社會福利是最終的衡量標準。如前所述,不管是在普通法系還是在大陸法系的司法運行中,無論是法典還是普通法法律規(guī)則體系,我們都會發(fā)現(xiàn)在司法中條文或者規(guī)則之間或者之中都有一定的空隙需要被填補。這些需要填補的漏洞可大可小,重要的是,我們應當以怎樣的原則(或方法)來填補它們。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在司法中填補這些漏洞,我們必須了解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的定義。
卡多佐認為,社會福利這一概念在不同的司法環(huán)境下可能會具有不同的含義。它可以被定義為公共政策,集體的利益;也可以被界定為一個共同體的道德意見。無論如何定義,卡多佐判斷,在現(xiàn)代司法下,規(guī)則的社會價值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重要[4]69。對于社會福利方法的司法運用,卡多佐舉了美國憲法判例對于“正當權利”理解的演變過程。起初,正當權利被理解為對自由的絕對保障,是一種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隨著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與國家治理方式的改變,相關判例與法學理論對于正當權利的理解也慢慢發(fā)生改變。司法的過程也包含著對法律解釋的過程,而這種解釋也是隨著時代及其條件的變化而發(fā)生著變化。所以,卡多佐認為,關于法律的真實概念,在適用于新的事物組合過程中,
不斷地被分門別類、被挑選、被鑄造、被修改。在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判決形成了。在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決定了誰將獲得再生產(chǎn)的權利[6]32。然而,這種改變是漸進式的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某一個時空范圍下,我們也許會發(fā)現(xiàn)兩種存在對立態(tài)度的思潮均對司法產(chǎn)生影響,就如同卡多佐前面論述過的一樣,在較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演變的趨勢使得規(guī)則成為例外,而例外成為一種新的規(guī)則。
卡多佐所描述的這一司法中的“變法”過程顯然是緩慢的,是急不來的。“每一個新案件都是一個實驗。如果人們感到某個規(guī)則產(chǎn)生結(jié)果不公正,就會重新考慮這個規(guī)則。也許不是立即就修改,因為試圖使每個案件都達到絕對的公正就不可能發(fā)展和保持一般規(guī)則;但如果一個規(guī)則不斷造成不公正的結(jié)果,那么它最終將被重新塑造。”[6]10即使是有利于一般社會福利的法律變革,由于法律發(fā)生改變這一事實本身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有害于公共幸福,因此應當慎重。
對于此種司法過程中的方法,卡多佐進一步認為要對其性質(zhì)進行探索。法官并不是在進行完全的“自由裁判”,而是根據(jù)一般人的判斷作為司法裁判的標準,卡多佐將之稱為“客觀標準”。在筆者看來,卡多佐試圖定義的這種運用社會學方法的司法標準,是一種尋找法律及其運行中根據(jù)一定時代特征和一定主體的價值判斷所確立的理想行為狀態(tài)。法官應當通過司法的過程表述對某一規(guī)則或某一法律領域的理想狀態(tài),糾正由于當事人、立法權乃至行政權運行所可能帶來的“錯位”與不正義。社會學的司法方法具有終極意義。所以,社會學的司法方法意味著我們必須探究規(guī)則的目的,而這種探究需要發(fā)揮法官的主觀性,“客觀標準”不是絕對意義上的。規(guī)則的目的探究與規(guī)則的自身發(fā)展息息相關,薩維尼認為,法律在歷史中自發(fā)生長。卡多佐認為這一判斷并不全面。一方面,法律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不以主體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潛在性與無意識屬性;另一方面,法律的成長也摻雜了主體的意識與目的。在有些情況下,只有通過主觀的方式才能實現(xiàn)客觀的司法標準[4]105。
那么,法官應當如何確定在不同的情況下應當采取怎樣的司法方法和標準呢?卡多佐認為,司法過程的材料最終來源于生活。在這種意義上,司法與立法有相似之處。當然,法官在挖掘生活材料方面的限制更多,法官的“立法”只能是在漏洞處進行填補的工作。即使是填補性質(zhì)的工作,我們也無法定義其中可能存在的限制。筆者認為,卡多佐所認為的“自由裁判”也有一重含義在于將司法與立法進行比較:立法者的偏好(優(yōu)勢)帶有“恣意”的性質(zhì),而司法中的“自由”則是針對特殊的個別的案件事實所進行的各種規(guī)范解釋、歷史探究、習俗挖掘以及價值判斷,司法應當保持“自由”,遠離權力。司法是自由的,“是因為在這里它擺脫了實在權威的活動,它又是科學的,因為它能在獨有科學才能揭示的那些客觀因素之中發(fā)現(xiàn)自己的堅實基礎”[6]75。另外,針對“自然法”,卡多佐也不認為其具有“信條”的意義。我們應當在社會功利意義上定義它。自然法規(guī)則不再被認為是永恒的,它并不高于人定法。法律就是人定法,不過當代的法哲學理論尋求的是人定法的完善以及其持久的理念。同樣,卡多佐也批判了實證主義法學派所堅持的法律與道德評價截然分離的理論。
我們應當注意,卡多佐所定義的社會學司法方法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并不是無限的。在個案中,我們發(fā)現(xiàn)按照既有的法律或者先例規(guī)則可能會對一方當事人極為不利。但是,作為司法者,任何一名法官都不可能拋棄已有的規(guī)則、習慣、邏輯乃至社會一般認知,而以“自由心證”去裁判。司法中的絕大部分案件都有較為明確的法律依據(jù)進行裁判,事實問題、證據(jù)問題遠比法律問題來的復雜。所謂將“社會福利”作為裁判的依據(jù),在多數(shù)情況下,依據(jù)現(xiàn)有的規(guī)則進行裁判,探究規(guī)則的目的,我們就可以認為已經(jīng)完成了司法工作的重心。因此,筆者認為,卡多佐的“社會福利”的司法過程意義并不在于我們可以利用這一標準在絕大部分案件中直接進行裁判,這一標準應當是潛在的,是指導司法者的“潛意識”價值觀。從此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認為,任何一次簡單的判決都最終遵循了社會學的司法方法。
三、結(jié)語
縱觀卡多佐的司法觀,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理論并不具有太多的創(chuàng)新之處。不過,在筆者看來,卡多佐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的誠懇以及冷靜的現(xiàn)實分析能力。對于司法過程的各種學說,卡多佐沒有避諱地批判了“理想形態(tài)”的無用性,但他也執(zhí)著地追求著司法的實然屬性與過程;對于實際司法中的各種混亂與不協(xié)調(diào),卡多佐十分清醒地認識到這必然是司法過程的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的常態(tài);對于普通法,卡多佐不吝惜贊美之詞,雖然他的有些判斷可能有失公允。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兼具實務精神與理想信念的思想家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下冷靜的分析筆觸與較為客觀的評說。“細細體會司法過程中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可以發(fā)現(xiàn),無論是法律發(fā)現(xiàn)、法律推理、法律解釋,還是法律論證、漏洞補充、價值衡量,都有一個共同的主語,那就是法官。換言之,法官既是司法過程的靈魂人物,同時也是法律方法的主要實踐者。”[7]
[1][美]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梁治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4-15.
[2]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57.
[3][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曹冬雪,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149.
[4]CARDOZO B N 2012.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M].Dover Publications,2012:51.
[5][英]哈耶克.自由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M].賈湛,等,譯.北京:北京經(jīng)濟學院出版社,1991:23.
[6][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zhì)[M].蘇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7]喻中.法律與現(xiàn)代人的命運:鄉(xiāng)土中國的司法圖景(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11.
[責任編輯:李 瑩]
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Cardozo's Sprit Experience
LIU Tao
For starters,judicial process means logic to Cardozo,formality and“adherence to the precedent”principle are important for the equality and belief establishment in judiciary;the method of history and custom help judge resolve the stiff in logic thinking;the method of sociology is a objective standard in judicial process.Through the discovery the present meaning of social welfare,it restrains the arbitrariness in judge’s decision-making,and eventually,through fashion and discovery,the law has its growth.Law is a process perse.
judicial process;method of logic;history and custom;method of sociology in judiciary
DF0-054
:A
:1008-7966(2014)04-0001-04
2014-03-24
劉濤(1988-),男,安徽巢湖人,2014級刑法學專業(yè)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刑法學與司法制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