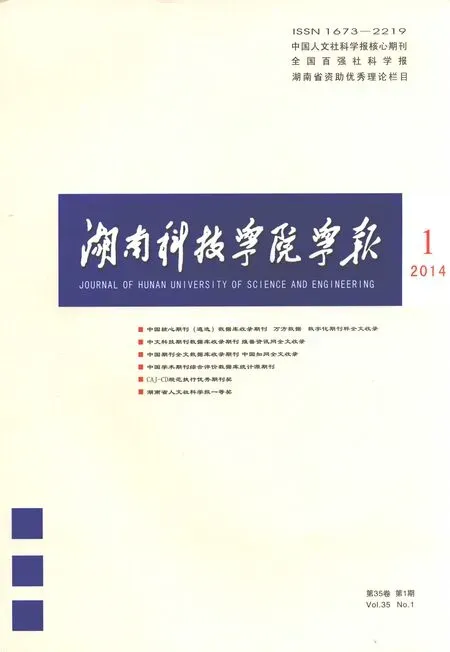敘事中的文學(xué)性生成
藍(lán)建青
(江漢大學(xué) 文理學(xué)院 外語學(xué)部,湖北 武漢 430056)
敘事是人類言語交際的主要形式,即使用語言符號(hào)的方式來講述或記錄不在現(xiàn)場的事件。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敘事傳統(tǒng),但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界所指一般為西方敘事學(xué),因?yàn)椤白鳛橐婚T獨(dú)立學(xué)科的當(dāng)代首先產(chǎn)生于西方,中國敘事學(xué)是在西方敘事學(xué)的影響下發(fā)展起來的。”[1]P1敘事作為文學(xué)文本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敘事手法是文學(xué)文本得以經(jīng)久流傳,成為文學(xué)經(jīng)典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 文學(xué)與文學(xué)性的存在方式
“什么是文學(xué)?”一直是中外文學(xué)理論家們思考的問題。那么是否有特征能夠區(qū)分文學(xué)作品和非文學(xué)作品呢?事實(shí)上,文學(xué)是“特定時(shí)期的特定人群因?yàn)槟撤N特殊的原因形成的建構(gòu)”[2]P11,這導(dǎo)致人們很難對(duì)文學(xué)下精確的定義,也很難找到這種區(qū)別性特征。20世紀(jì)20年代,形式主義學(xué)者雅克布森提出了文學(xué)性的概念,即文學(xué)科學(xué)的主題,并非作為總體的文學(xué),而是文學(xué)性(literariness),也就是說,使一部著作成為文學(xué)作品的東西[2]P2。這一概念嘗試去回答什么是文學(xué)的本質(zhì)。這既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學(xué)理論研究中問題的置換,也為文學(xué)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務(wù)[3]P33。而在卡勒看來,“問題的目的不是尋找文學(xué)的定義,而是描繪文學(xué)的特征,而能夠很好地描繪文學(xué)的特征的那就是文學(xué)性。”[4]P27因此,尋找和描述這些區(qū)別性特征成為文學(xué)理論的重要任務(wù)之一。
在對(duì)文學(xué)性的找尋中,雅克布森認(rèn)為,文學(xué)性的實(shí)現(xiàn)就在于對(duì)日常語言進(jìn)行變形、強(qiáng)化,甚至歪曲,也就是說,“對(duì)普通語言實(shí)施有系統(tǒng)的破壞”[2]P2。什克洛夫斯基認(rèn)為,陌生化(defamiliazation)是文學(xué)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qū)別,即通過陌生化的手法,使得文學(xué)語言產(chǎn)生與日常語言不一樣的效果。“藝術(shù)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復(fù)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shí)延,既然藝術(shù)中的領(lǐng)悟過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它就理應(yīng)延長;藝術(shù)是一種體驗(yàn)事物之創(chuàng)造方式,而被創(chuàng)造物在藝術(shù)中已無足輕重。”[5]P6這一感知過程產(chǎn)生于對(duì)語言形式、敘事方式、情節(jié)安排等形式上與日常語言相異的東西,使得讀者理解變得困難,從而延長人們對(duì)這些形式的審美感知過程。國內(nèi)學(xué)者徐潔瑩等認(rèn)為,文學(xué)語言的變形也即陌生化的程序、手法,正是文學(xué)成其為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之所在[6]。事實(shí)上,文學(xué)語言的陌生化即是對(duì)日常語言的詩意運(yùn)用,使語言產(chǎn)生詩性功能,實(shí)現(xiàn)文學(xué)審美效果。
毫無疑問,文學(xué)性存在于文學(xué)作品中,存在于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層面。但文學(xué)性是以何種形式存在于文學(xué)文本之中。在《文學(xué)理論》中,韋勒克·沃倫認(rèn)為:文學(xué)是一個(gè)交織著多層意義和關(guān)系的極其復(fù)雜的組合體[7]P16。“對(duì)一件藝術(shù)品做較為仔細(xì)的分析表明,最好不要把它看成一個(gè)包含標(biāo)準(zhǔn)的體系,而要把它看成是由幾個(gè)層面構(gòu)成的體系,每一個(gè)層面隱含了它自己所屬的組合。”[7]P158羅曼·英伽登在其《對(duì)文學(xué)的藝術(shù)作品的認(rèn)知》中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是一個(gè)多層次的構(gòu)成”[8]P10。其由四個(gè)異質(zhì)的層次構(gòu)成的整體結(jié)構(gòu),即語音和語音組合、不同等級(jí)的意義單元層次、再現(xiàn)的客體層次、圖式化觀相層次和形而上的特質(zhì)層。可見,在文學(xué)這個(gè)復(fù)雜的組合體中,既層次分明而又相互交織在一起,構(gòu)成一個(gè)立體結(jié)構(gòu)。文學(xué)性作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在文學(xué)文本的各個(gè)層面以語言的形式展現(xiàn)給讀者。
文學(xué)性是文學(xué)存在的理由[9]。文學(xué)性存在于文本的各個(gè)層面,作者的創(chuàng)作手法帶來視覺、聽覺的陌生化,延長審美時(shí)間,取得審美效果,生成文學(xué)性。劉俐俐考察了韋勒克·沃倫、英加登、弗萊和劉勰等關(guān)于文學(xué)作品的層次的論述,認(rèn)為:大致可以表述為文學(xué)作品存在于一個(gè)由語言構(gòu)成的多層次的立體的結(jié)構(gòu)中:各個(gè)層次分別為:1、語辭所具有的語音和語義。2、句子和句子所組成的意群,這是重要的貯存文學(xué)性之所在。3、已經(jīng)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隱喻,其中已經(jīng)具有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意義。4、文學(xué)作品的客觀世界。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統(tǒng)中的詩的特殊“世界”。5、形而上性質(zhì)雖然不是以閱讀可能意識(shí)到的對(duì)象樣式而直接出現(xiàn)的,但是也是生成文學(xué)性的因素[10]P38。可以說,文學(xué)性正是通過語言的變形、扭曲等方式存在文本之中,帶來審美效果和文學(xué)價(jià)值。
經(jīng)典文學(xué)文本對(duì)于一國的語言和文化建構(gòu)的意義重大,不僅在于文學(xué)作品傳遞人類共同的情感,更在于人類對(duì)文學(xué)性的判斷和建構(gòu)。對(duì)文學(xué)而言,文學(xué)性可以理解為文學(xué)成因,成因從原因來說是條件,從作品內(nèi)部的特性來說,是文學(xué)性實(shí)現(xiàn)的結(jié)果[9]。因此,文學(xué)性的發(fā)掘?qū)ξ膶W(xué)本體的建構(gòu)有著深刻的意義。
二 敘事與文學(xué)性
文學(xué)性存在于文本的各個(gè)層面,敘事層面也不例外。但是對(duì)于文學(xué)性在敘事層面的存在方式的探討則顯得比較困難。敘事,顧名思義,就是敘述事情(敘+事),即通過語言或其他媒介來再現(xiàn)發(fā)生在特定時(shí)間和空間里的事件[1]P2。近年來,隨著敘事學(xué)的發(fā)展和拓寬,其對(duì)文學(xué)研究產(chǎn)生了更為深刻的意義。關(guān)注和研究敘事手法對(duì)文學(xué)性的生成和文學(xué)經(jīng)典的形成具有較高的現(xiàn)實(shí)意義。本文以經(jīng)典敘事學(xué)理論為指導(dǎo),探討敘事層面的技巧即對(duì)敘事作品中的視角、引語形式和“不可靠敘述”等對(duì)文學(xué)性生成的機(jī)制和意義。
(一)敘事視角與文學(xué)性的生成
視角是人們觀察事物的角度,敘述視角是作者敘述時(shí)觀察故事的角度,也被稱為聚焦(focalization)或視點(diǎn)(point of view)。近一個(gè)世紀(jì)以來,視角一直是小說敘事研究的一個(gè)中心問題[1]P90。學(xué)者們發(fā)現(xiàn),視角是傳遞主題意義的一個(gè)十分重要的工具[1]P90。視角也是作者和文本的心靈結(jié)合點(diǎn),是作者把他體驗(yàn)到的世界轉(zhuǎn)化為語言敘事世界的基本角度,也是讀者進(jìn)入這個(gè)敘事世界,打開作者心靈窗扉的鑰匙[11]P191。不同的敘述視角或聚焦形式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視覺效果,是作者審美意圖的重要體現(xiàn),是文學(xué)性生成的方式之一。
在視角分類上,弗里德曼、查特曼、熱奈特等意見不一。申丹總結(jié)了前人的論述,認(rèn)為需要區(qū)分4大類視角:無限制型視角(即全知敘述)、內(nèi)視角、第一人稱外視角和第三人稱外視角[12]。在具體文本中,作家往往會(huì)采用某一種視角或者是轉(zhuǎn)換視角來取得特定的文學(xué)審美效果和引導(dǎo)讀者對(duì)生活、人生進(jìn)行思考,實(shí)現(xiàn)文本的價(jià)值。
在《紅樓夢》第四十回中,有這么一段:
那劉姥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里鐵锨還沉,那里犟的過他。”說的眾人都笑起來。
在大觀園里的公子、小姐們看來,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并不稀奇,而從劉姥姥的視角來看,這“叉爬子比俺那里鐵锨還沉”,給大觀園里的公子、小姐們帶來陌生化的效果。從劉姥姥的視角來審視大觀園內(nèi)的生活,帶來的是喜劇的效果,也諷刺了當(dāng)時(shí)富人的奢華,人物的塑造更為豐滿,提高了文本的文學(xué)審美效果,提高了文本的文學(xué)性。
(二)引語形式與文學(xué)性的生成
人物話語是敘事性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敘事學(xué)對(duì)人物話語也有獨(dú)特的興趣,同樣的人物話語采用不同的表達(dá)方式就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效果[1]P144。變換人物話語表達(dá)方式(即引語形式)是小說家控制敘事進(jìn)程,形成敘事風(fēng)格等的有效工具。英國文體學(xué)家Leech和Short根據(jù)敘述者對(duì)人物話語控制程度的差異分為言語行為的敘述體、間接引語、自由間接引語、直接引語和自由直接引語[13]P260等五類,從言語行為的敘述體到自由直接引語,敘述者對(duì)敘述內(nèi)容的控制程度不斷降低。不同的引語形式具有不同的表達(dá)功能和優(yōu)勢。自由直接引語具有直接性、生動(dòng)性和可混合性。直接引語的音響效果、間接引語可以總結(jié)人物話語,具有一定的節(jié)儉性,加快敘述速度,也可使敘述更為順暢的向前發(fā)展。言語行為敘述體具有高度的節(jié)儉和掩蓋作用。自由間接引語具有加強(qiáng)反諷效果、增強(qiáng)同情感、創(chuàng)造出含混的效果、增加語意密度、體現(xiàn)生動(dòng)性等效果[1]P156-166。小說家通常運(yùn)用各種引語形式控制作品的敘事內(nèi)容,從而產(chǎn)生審美效果,即文學(xué)性的生成。
在《傲慢與偏見》的第十四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他們一開頭就談到羅新斯貴賓離開的問題。咖苔琳夫人說:“告訴你,我真十分難受。我相信,誰也不會(huì)象我一樣,為親友的離別而傷心得這么厲害。我特別喜歡這兩個(gè)年輕人,我知道他們也非常喜歡我。他們臨去的時(shí)候真舍不得走。他們一向都是那樣。那位可愛的上校到最后才算打起了精神;達(dá)西看上去最難過,我看他比去年還要難受,他對(duì)羅新斯的感情真是一年比一年來得深。”說到這里,柯林斯先生恭維了一句,又暗示了原因,母女倆聽了,都粲然一笑。
柯林斯先生集傲慢與恭順、自負(fù)與謙卑的雙重性格,是典型的市井小民形象。對(duì)于有錢、權(quán)、勢的人,拍馬溜須、曲意逢迎,為自己謀利益。而對(duì)比他弱勢的群體,則傲慢自負(fù)、盛氣凌人。在與其女恩主的對(duì)話中,作者并未將柯林斯的恭維和原因以直接引語出現(xiàn),自由間接引語加強(qiáng)了諷刺的效果,很好地刻畫了柯林斯馬屁精的嘴臉,體現(xiàn)了奧斯丁刻畫的生動(dòng)性和其諷刺的藝術(shù)。引語的轉(zhuǎn)換和使用體現(xiàn)了作者的寫作風(fēng)格和文學(xué)文本中文學(xué)性的生成。
(三)不可靠敘述與文學(xué)性的生成
小說是敘事交流的藝術(shù),只有在作者與讀者的互動(dòng)中傳遞作者的情和美,并讓讀者感受到。“不可靠敘述”是當(dāng)代西方敘事理論中的“一個(gè)中心話題”。這一概念首先由布思( W.C.Booth)提出,他認(rèn)為,“按照作品規(guī)范( 即隱含作者的規(guī)范) 說話和行動(dòng)的敘述者是可靠的,反之則不可靠。”[14]P159換言之,隱含作者與敘述者的說話與行動(dòng)一致時(shí),敘述是可靠的,反之則不可靠。布思主要研究了兩種類型的不可靠敘述,即事實(shí)/事件軸和價(jià)值/判斷軸。布思的學(xué)生詹姆斯·費(fèi)倫發(fā)展了布思的理論,發(fā)展到三大類,即增加了知識(shí)/感知軸。還區(qū)分了第一人稱敘述中,“我”作為人物的功能和作為敘述者的功能的不同作用。不可靠敘述是一種重要的敘事策略,對(duì)表達(dá)主題意義、產(chǎn)生審美效果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15]。不可靠敘述的魅力在于人物的不可靠和敘述者的可靠之間的張力,以及這種張力產(chǎn)生的反諷效果生成的文學(xué)性。
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余”是狂人兄弟的好友,是正常人,其敘述應(yīng)該是可靠的。其序言中的“撮錄”和“易”卻體現(xiàn)出其敘述的不可靠性,引導(dǎo)讀者去思考狂人的話語。“狂人”對(duì)自身的敘述是可靠的,不會(huì)欺騙他人,但其感知的內(nèi)容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扭曲,是不可靠的。雙重?cái)⑹鲋黧w“余”與“狂人”的不可靠敘述大大增強(qiáng)了敘事的張力,加強(qiáng)了敘事的反諷效果,產(chǎn)生審美效果和對(duì)主題意義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拓寬了文本闡釋的可能性,即對(duì)文本文學(xué)性的生成具有建構(gòu)的作用。
三 結(jié) 語
文學(xué)性抽象的存在于文學(xué)文本的各個(gè)層面,文學(xué)性在敘事層面的生成是可感知的,即通過語言層面的敘事手法或技巧達(dá)到文學(xué)性的感知。通過研究以期為文學(xué)性研究拓寬空間。但是,對(duì)于文學(xué)本質(zhì)的思考和敘事的研究不會(huì)停止,這樣才能更好的拓展文學(xué)理論和加深人類對(duì)生活本質(zhì)的思考。
[1]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xué):經(jīng)典與后經(jīng)典[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2]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3]李龍.文學(xué)性問題研究——以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yàn)閰⒄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Culler,Jonathan.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什克洛夫斯基,等.作為手法的藝術(shù)[A].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C].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9.
[6]徐潔瑩,管勇.陌生化:文學(xué)語言的審美發(fā)生[J].紅河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l2,(1):88-91.
[7]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4.
[8]英伽登.對(duì)文學(xué)的藝術(shù)作品的認(rèn)識(shí)[M].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8.
[9]劉俐俐.民族文學(xué)與文學(xué)性問題[J].民族文學(xué)研究,2005,(2):5-9.
[10]劉俐俐.文學(xué)“如何”:理論與實(shí)踐[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
[11]楊義.中國敘事學(xu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2]申丹.視角[J].外國文學(xué),2004,(3):52-61.
[13] Leech & Short.Style in Fiction[M].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7.
[14] 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15]申丹.何為“不可靠敘述”?[J].外國文學(xué)評(píng)論,2006,(4):13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