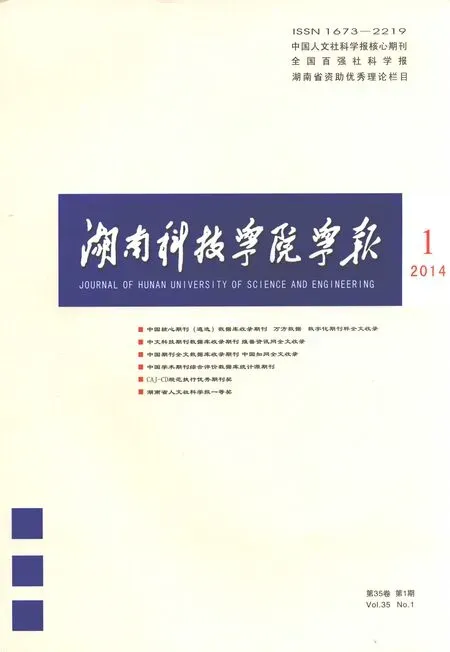漢詩英譯的意象識解與重構——以杜甫《登高》為例
何文斐
(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 基礎部,廣東 廣州510520)
一 引 言
詩歌語言精煉、意境悠遠、韻律和諧,被譽為“文學中的文學”。英詩感情奔放,直抒胸臆,言盡而意亦盡;漢詩重在寫景抒情,以模糊為美,強調意象的運用,言有盡而意無窮。意象即寓“意”之“象”,作為漢詩創作的最重要表現手法,意象指客觀物象經過詩人獨特的情感活動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是外在客觀物象和內在主觀感情的結合體。意象廣泛存在詩歌中,其作用在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所謂“言不盡意,立象盡之”,寄托和凝聚詩人內心情感,從而使情感成為可感可觸的獨特的藝術形象。明代胡應麟于《詩藪》中說:“古詩之美,專求意象。”[1]P1朱光潛也曾在《藝文雜談》中說:“詩的要素有三種:就骨子里說,它要表現一種情趣;就表面說,它有意象,有聲音。詩歌離不開意象。”[2]P46意象以最精煉的語言形式表達最富內涵的感情與意義,是古詩創作與鑒賞的核心,而古詩中豐富的意象所營造的主題多義和朦朧美感則是漢詩英譯的一大難題。因此,再現古詩神韻的關鍵在于意象的傳遞。在意象傳遞過程中,譯者對詩中意象的識解則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譯本的質量與效果。本文運用認知語言學識解理論的內容觀點,對杜甫詩《登高》三個譯本進行對比與分析,剖析在漢詩英譯過程中對意象的意義識解的認知運作,以探討漢詩英譯中的意象重構。
二 識解與識解理論
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表達的意義是作為認知主體的人對客觀世界進行概念化的結果。[3]P39認知能力是人類知識的根本,語言翻譯是譯者認知和再創造的過程,因此認知語言學與語言翻譯密不可分。識解是認知語言學里的一個重要概念,指“人類用不同方式來理解、表達同一現實情景的能力”,是形成概念、語義結構和表達形式的具體方式。[4]人們認知同一事物的角度和識解方式存在著較大差異,從本質上說,語義被賦予了主觀識解性。譯者根據自身的知識背景、審美角度和特定立場,對事物進行分析判斷,突出某一問題,有目的地選詞謀篇。認知語言學者Langacker的識解理論將識解的維度劃分為詳略度、轄域、背景、視角與突顯五個方面。[5]P4著名學者王寅認為五個維度內容重復,把轄域和背景結合在一起,得到了Langacker的認可。[4]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于譯者對這幾個方面作出的不同選擇導致了同一文本意義與譯本的多樣性,因此譯本本身帶有譯者的識解痕跡。運用識解理論作為理論工具對漢詩的意象英譯進行評析,不同譯者在形成不同譯本過程中的主體性一目了然。
三 杜甫詩《登高》三譯本中的評析
《登高》是唐代偉大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律詩名作,整首詩雄渾悲涼,格律工整,情感深厚。明代胡應麟推重此詩 “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1]P95。此詩作于公元767年秋,56歲的杜甫流離到夔州,重陽登高臨眺,面對深秋景色感時傷懷而作。原文:“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詩文前兩聯寫景,后兩聯抒情,實則情景相融。首聯每句三折三景,高天疾風,深谷哀猿,驚心動魄,籠罩在悲涼氛圍中。前句以“風、天、猿”三意象描寫“高”景,后句以“渚、沙、鳥”三意象描寫“低”景,意象紛呈,對仗工整,把六景描繪得淋漓盡致。頷聯平緩而出,通過“蕭蕭”的“落木”、“滾滾”的“長江”的意象描寫,遠近景相結合,感情由孤獨轉向悲壯,表達時光流逝、壯志難酬的感觸。最后通過描寫身邊的瑣事“停酒杯”表達出窮困潦倒、愛國思家的情感。首頷兩聯通過對蕭瑟秋景當中的意象描寫,烘托出作者內心長年飄泊、老病孤愁、憂國思鄉的復雜情感。本文選取的三個譯本分別取自于Witter Bynner,楊憲益、戴乃迭以及許淵沖,兼有來自源語語言國家的譯者及譯入語語言國家的譯者,將三個譯本進行對比分析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對于原文中至關重要的意象,下表給出三個譯本譯文的對比:

原文 Bynner譯文 楊憲益、戴乃迭譯文 許淵沖譯文風急 In a sharp gale Wind blusters The wind so swift天高 from the wide sky in the sky the sky so wide猿嘯 apes are whimpering monkeys wail apes wail and cry渚清 the clear lake Clear the islet Water so clear沙白 white sand with white sand beach so white鳥飛 Birds are flying where birds are wheeling birds wheel and fly落木 Leaves are dropping down the leaves fall leaves長江 the long river the turbulent Yangtze The endless river
(一)詳略度
詳略度指描述和認知某一事物或同一情景時不同精確程度及詳細程度,可濃墨重彩,也可輕描淡寫,從而構成不同的等級、范疇與層次。王寅在《認知語法概論》中指出:“不同識解的形成與對外界觀察的詳略程度密切相關。”[6]P24譯者對原詩詞匯或句子的描述詳略度的不同識解,會形成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從而對譯作的意義及內涵產生影響。
首聯中借風、天、猿、渚、沙、鳥六種景物,并以急、高、哀、清、白、飛等詞修飾,意象入詩,不但形象鮮明,使人讀了如臨其境,雄渾高遠,肅殺凄涼,多種意象組合,構成一幅立體的空間畫面,縈繞著悲涼蕭瑟氣氳,營造出詩人孤獨無依、漂泊痛苦的凄涼意境。其中“猿嘯”、“鳥飛”兩個動態意象使詩人感情的流露更加形象,置于詩句的末尾,創造出感情回響效果。仰望蒼穹,感受著獵獵秋風,耳畔傳來“高猿長嘯”之聲,空谷傳響,哀轉久絕。天高任鳥飛,本該展翅高飛,自由歡快的鳥兒卻在疾風中低回盤桓,無處停息。兩個感情充分流露的動態意象置于靜態意象的背景中,有情有景,情景交融。
從譯文看,Bynner譯和楊譯將“猿嘯”這一意象分別譯為“apes are whimpering”和“monkeys wail”基本能把握意象的意義,而許譯則用并列動詞結構譯為“apes wail and cry”,不僅準備地譯出了原文的意義及內涵,更加深了讀者與詩人間的情感交流,產生情感共鳴,創造出情感回響,使空谷猿鳴更動人心弦,精彩地重構原文意象,與后一詩句交相輝映。“鳥飛”這一意象譯本中,Bynner將之簡譯為“Birds are flying”,fly一詞顯然有所不足,未能再現孤鳥盤桓那種孤獨無依的凄涼之感。楊譯中處理為從句“where birds are wheeling”,意義上雖與原詩基本一致,但從句的再現形式使原詩意象的內涵與情感遭受相當程度的弱化。許譯“birds wheel and fly”成功地構建了鳥兒盤桓往復的孤寂場景,使讀者仿佛目睹鳥兒不停地在高空中盤旋,成功地制造出感情的漩渦,深深的沉浸在那種孤獨無力的氛圍當中,與前一詩句的“apes wail and cry”呼應,營造出孤獨無依的意境。與前兩位譯者相比,許譯顯然更詳盡,對原詩意象的意義與內涵把握地更深入細致。因此詩譯需注重詳略度的重構,簡單的直譯不可取,應該深入把握原詩內涵與作者情感,盡可能與原詩“詳略度”對等。
(二)轄域與背景
轄域指人們理解表述某一事物或情景時需要激活的認知域及相關百科知識。認知語法在描寫詞語意義的時候,主要用轄域,即認知域來替代傳統的意義特征,將意義視為概念化的過程和結果。[6]P25轄域主要包括級階、背景和百科知識三個要素。認知域是人們認知理解事物的背景,具有百科性,包括時間、空間、味覺、顏色等等,有些語義就包括了多個認知域,具有復雜性和層次性。如“紅酒”涉及味覺、嗅覺、顏色等認知域,可見語義與百科知識密切相關。理解一個概念通常需要從其上級及下級概念出發,如“直角三角形”這一概念可借助其下級概念“等邊三角形”以及上級概念“三角形”來理解。除了上下級概念,還需運用到相關概念作為背景,如理解“律師”這一概念,“罪犯”、“法官”、“警察”等概念就起到了背景的作用。譯文的差異正是由于譯者在理解原詩語篇時運用和選擇轄域概念差異所造成的。
《登高》一詩借以各種意象描繪出一幅聲色兼具、動靜結合、情景交融的意象畫。對于“猿”這一意象的理解就需要激活相關的動物域、聲音域和空間域。巫峽猿鳴凄厲。當地民瑤說:“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古代詩詞常以猿嘯來表達情感,如《琵琶行》有“杜鵑啼血猿哀鳴”。猿嘯聲音聽起來凄切,在空谷中回響給人哀傷的感覺,很好地折射出詩人的漂泊多病的悲涼情感。對于這一意象,Bynner譯為“apes are whimpering”,楊譯為“monkeys wail”,而許譯為“apes wail and cry”。其中“猿”除了楊譯運用其上級概念monkeys外,其余兩譯本皆為apes,實現與原詩的轄域對等。巫峽多猿,猿屬于大型靈長類動物,其叫聲與猴子有較大差異,凄涼的猿嘯更能反映出詩人此刻的心境。結合相關百科知識并以猴這一概念為背景,可以看出譯為apes更能重構出原詩這一意象包蘊含的語義及情感。
首聯第二句中“渚清”意象中“渚”指江中小洲,楊譯為“islet”雖既可指大島也可指小島,但基本能與原文語義對等。許譯未將“渚”與其后之“沙”直譯,而是以“water”譯“渚”,以“beach”譯 “沙”,取原詩句中“水清沙白”之深層意義,結合相關百科知識,以背景概念“water”和“beach”來幫助讀者理解與感受詩句中的意象。Bynner譯為“lake”則由于未能激活的相關認知域及百科知識,概念化過程出現誤差,是明顯的誤譯。由此可見,重構古詩中意象需要激活相應的認知域及百科知識,正確運用相關上下級概念及背景概念。
(三)視角
視角是人們觀察和描述事物的立場、方向和角度,涉及事物與觀察者的相對關系。視角的不同,會造成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識解與表達。“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很好地指出了視角不同所造成的差異。視角的選擇和所關注的焦點往往體現出作者最主要的意圖。因此在詩譯中,譯文質量與所選擇的視角與側重點密切相關。王寅劃分了視角的各個組成部分:時間、空間視角,無明顯視角,視覺掃描和心智掃描,主觀觀察與客觀觀察四個部分。[6]P28本文主要從空間視角對譯文進行分析。
詩中首聯中的意象呈現,詩人采用的空間視角是第一句由上至下,先寫風寫天,再寫猿;第二句由下至上,先寫渚寫沙,再寫鳥。試比較三個譯本對首聯第二句的處理:
許譯:Water so clear and beach so white,birds wheel and fly.
楊譯:Clear the islet with white sand where birds are wheeling.
Bynner: Birds are flying homeward over the clear lake and white sand.
對于譯文空間視角的重構,許譯連用了幾個“so”并列結構很好地重構首聯兩句的空間布局,形式極為工整。楊譯中的“渚清”“沙白”意象處理為“Clear the islet with white sand where birds are wheeling”,選用了“with”和“where”來基本闡明詩義,但自下而上的空間概念較模糊。而Bynner譯為“Birds are flying homeward over the clear lake and white sand”,打破了原作中的空間布局,空間視角的選擇未能與原詩保持一致,未能實現空間視角重構。
(四)突顯
確定視角后,人們會選擇事物中的某個部分進行描述和突顯。突顯在詩歌中主要體現在選詞及鋪陳組合中。突顯可通過射體與界標來體現。射體是關系述義中處于最突顯的位置,界標則處于次突顯位置,是定位射體的參照物。射體和界標分別是認知關注的第一焦點與第二焦點。如Mark Twain is a mirror of America.一句中射體是“Mark Twain”,讀者借助界標“mirror of America”來識解射體。根據Langacker的觀點,識解中的突顯與“認知主體的視角和主觀因素密切相關”。[6]P30由于譯者不同的審美情趣、風格傾向,譯者在重構詩中意象時突顯的內容可能存在差異。
詩中意象“鳥飛”與“渚清”“沙白”處于并列地位,其中的“鳥”成為了詩人的化身,鳥飛渚上,如無憑依,風拂翮羽,徘徊難歸,形象地點明詩人由于戰亂不靖而故國難歸,忍貧含苦,羈滯異鄉的困境。許譯選擇并列句的結構將其譯出,與原詩意圖相同。楊譯將“鳥飛”譯為“where birds are wheeling”這一狀語從句,使之成為“islet”和“sand”的界標,這與原詩的意象結構不一致。Bynner譯中“Birds”為射體,使用“over”使“clear lake”和“white sand”成為了“Birds”的界標,這也與原文不符。
頷聯中通過“落木”和“長江”的意象描寫,詩人直抒胸臆,自己憂國憂已,淪落遲暮,自悲身世,難獲團聚的種種哀怨苦愁正如那滾滾撲來的長江之水,無盡無止,兩個意象是并列關系。其中“不盡長江滾滾來”一句中,射體為意象“長江”,界標為“滾滾來”的波濤,使江水般的感情充分流露,傾瀉而出,造就一幅情景交融、動靜兼具的意象圖。許譯與楊譯較明確地譯出詩句中射體與界標的關系。許譯為“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射體意象“The endless river”充當主動語態句子中的主語作為第一焦點得到突顯,而作為次突顯成分的界標“waves”則充當賓語,屬于第二焦點。而Bynner譯為“While I watch the long river always rolling on”,將詩句處理為以“while”引導的一個時間狀語從句,表明了這一意象對于上一意象的從屬地位,不符合原詩的意象群結構。同時,可以看出,“I”成為了譯文的射體,而意象“the long river”成為充當參照物的界標,與詩人意圖不一致。
四 結 語
譯者在進行詩歌意象翻譯與重構時,應從詳略度、轄域與背景、視角和突顯這四個主要維度進行主觀性識解,對原詩深入理解與分析。雖然漢英語言及背景文化存在著較大差異,譯本與原作在意義方面難以達到原詩內涵與讀者理解間的充分一致,但譯者仍需運用認知識解重構詩中意象盡可能地實現與原詩在這幾個維度的識解對等。本文以認知語言學的識解理論為框架,結合具體譯例,探討了不同譯者在漢詩英譯中對同一譯本四種維度的識解操作對意象重構的作用以及對譯本產生的影響,以期為詩歌意象翻譯與重構研究提供認知角度的啟迪與借鑒。
[1]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朱光潛.藝文雜談[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3]肖坤學.識解理論觀照下的損譯現象探析[J].當代外語研究,2011,(4):39.
[4]車明明,田婷.識解理論框架下詩歌翻譯中模糊美磨蝕現象[J].河北聯合大學學報,2012,(6):147.
[5]Langacker, R.W.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M].Berlin: Mouton de Guyter,1991.
[6]王寅.認知語法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7]張保紅.意象與漢詩英譯——以陶淵明詩《歸園田居》(其一)英譯為例[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4).
[8]許淵沖.唐詩三百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9]許淵沖.文學與翻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10]呂叔湘.中詩英譯比錄[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