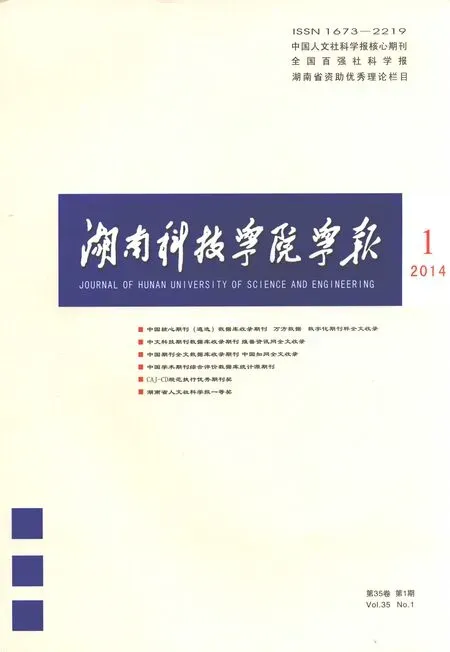論古代抒情詩由情感化向情境化的審美超越
鄧凌云
(湖南科技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系,湖南 永州 425199)
一
東漢末年,中國詩歌樹立起了兩座豐碑,一是樂府民歌中的《孔雀東南飛》,二是《古詩十九首》,它們分別標志中國詩歌敘事詩和抒情詩的成熟。《古詩十九首》發展了《詩經》、楚辭“風雅興寄”的抒情言志傳統,開辟了詩歌抒寫文 人士子個人情懷的抒情化道路,為魏晉六朝文人抒情詩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抒情詩在魏晉時期的發展,由寓情于景的抒情化特征中又增添了一個新的重要因素,即以哲理入詩,這就為抒情詩由情感化向情境化的轉化創造了決定性的條件。
抒情詩在由情感化向情境化的發展歷程中,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在情與景的表現中滲入哲理,在情、景、理的關系中,情和景上升為達理。這以嵇康的詩最為典型,郭璞的《游仙詩》也屬于這種情況;二是詩歌以闡述哲理為主旨。這個階段的詩以東晉的玄言詩為代表。除了“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的直言玄理之外,極少出現的景與情的描寫也成為了闡述玄理的手段;三是陶淵明的田園詩終結了玄言詩言理達性的特質,他把玄學理論中的自然意識由哲學境界發展到了審美境界,他的田園詩以及謝靈運開創的南朝山水詩,將抒情詩從情感化引向了情境化。這三個發展階段正展示出了魏晉文人詩歌發展情、景、理三者關系中理的滲入、異化和復歸的軌跡。從阮籍、嵇康的以玄理入詩到陶淵明田園詩靜穆自然的意境,絕非情、景、理的簡單復歸,而是從感性向更深刻地抒寫理性以及理性到情境的跨越,是詩歌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藝術審美超越。
二
《古詩十九首》是成熟的文人抒情詩。它所蘊含的思想感情,一是以物的永恒與人生有限形成的反差來表達對生命短促的憂慮;二是以離別相思和青春易逝的痛苦感受來表達憂思愁怨;三是以追求榮名或不擇手段地及時行樂來宣泄失意的悲苦。正如葉嘉瑩先生所概括的,其思想感情基本上有三類,即離別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和憂慮人生無常的感情。而這三類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因此它在文人的情感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特征。《古詩十九首》的這些普遍意義的情感,表現出作者對人生真諦的領悟,因此可以說這些作品意蘊深邃。換言之,從《古詩十九首》的游子思婦到陶謝的山水田園,很明顯,詩歌表達的內容是不同的,情感特征似乎也有所不同,但他們所抒發的情感內質卻是貫通的,是基于人生情感最基本的感受而抒發的,這就是生命意識的體現。這種生命意識的感發與超越的軌跡,正是抒情詩的發展軌跡的一個方面;而另一個方面,將這種生命意識的感發與超越形于藝術之象,這正是藝術的審美超越。
《古詩十九首》在表達上述三類情感中,采用了多種多樣的藝術表現手法。詩中的敘述、描寫、議論等基本手法都是抒發上述情感的手段。如《今日良宴會》:“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這是敘述,在宴飲活動的敘述中表達出歡快的情感,并為后面表現纏繞于詩人心中的失意和生命的焦慮情緒進行襯托和比照;而該篇后半部分“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常苦辛”,貌似議論,實為抒發對生命短促、人生瞬息萬變那種悲哀與無奈的感慨。至于描寫,有的是直接描寫情感,如《凜凜歲云暮》中“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豐富細膩,余味無窮;有的是對景物與環境的描寫,也是形象地展示情感。無論如《東城高且長》:“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以景物和氣候的描寫來抒發節序如流的感傷;或者如《西北有高樓》:“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馀哀”,以對音樂的描寫抒發內心的孤寂和凄苦。還是如《迢迢牽牛星》全篇以描寫夜空中的牛女形象書寫男女離別之情。總之,或融情于景,或寓景于情,或情景交融,一切描寫的手法,都是抒情。抒情真切自然,豐富細膩。《古詩十九首》突出的情感化特征達到了一個藝術的高峰。正如《詩品》的評價:“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一字千金。”馬茂元先生在《古詩十九首初探·前言》中所說:“王國維認為‘寫情如此,方為不隔’;‘不隔’,正是詩人全部情感在一剎那間的裸陳。”
《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意識到后來形成了兩條道路,一條是在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中,緊密結合社會與人生,發展為實現人生價值的生命意識,建安詩歌就是走的這條路;另一條是在時代、社會和人生的比較中,發展和超越人生的生命意識,陶淵明走的就是這條路。而這條路經歷了以理入詩的階段,最后實現了情境化的超越。
三
玄言詩以闡述玄理為主旨,以言理達性為主要特征。從抒發真實的情感這一詩歌感發的生命來說,玄言詩“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特質,是對《古詩十九首》和建安風骨的背離。然而,玄言詩在展示和體現強烈的生命意識這一核心的問題上,卻與《古詩十九首》有著共同之處。如果說,《古詩十九首》通過情感化的方式表現出了離別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和憂慮人生無常的這三類人生最基本的感情,從而體現出強烈的生命意識,而玄言詩則以闡述魏晉士人玄學觀念的方式體現出了的那個時代人們特定的生命意識。玄言詩在魏晉之交時就已出現,而到永嘉時期則言理達性特征越來越烈。正如鐘嶸《詩品序》中所說,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但是,玄言詩在詩歌發展中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推進了詩歌的哲理化,由現實和人生中形象的情感向比較抽象和空靈的境界轉化,為實現詩歌由情感化向情境化的審美超越創造了條件。
玄言詩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前期是正始時期的阮籍、嵇康以及西晉的郭璞,他們的詩沒有完全背離情感,而突出地表現出以玄理入詩的特征。相對于《古詩十九首》來說,以理入詩使得詩歌的情感特征弱化了,但這卻在詩歌的“緣情”傳統上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阮籍的《詠懷詩》所塑造的一系列至人、神人、仙人的形象,這些形象表現出他的玄學理念,正如他在《達莊論》中所說的:“至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昆侖之阜,而遺玄珠之根。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嵇康在以《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章為代表的玄言詩中大談玄理,批評流俗執著于生死、物我之分別,高調主張“肆志”、“縱心”,表達了“至人”歸之于自然的詩旨,更是表達出一種無為自然的理念。郭璞的一些表達玄理的游仙詩也是將玄理訴諸情感和形象之中,只是這種情感完全充斥著玄理色彩。他們三人的玄言詩以玄理駕馭情感,詩中突出地表現出了玄學理念,理勝于情。
西晉的孫楚,在詩中大肆談玄,要比郭璞明顯。他的《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是一首地地道道的玄言詩: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于殤子,彭聃猶為夭。吉兇如糾 纆 , 憂喜相紛繞。天地為我爐,萬物一何小。達人乘大觀,誡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堅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除開篇四句寫景和餞行外,全都是闡述老莊思想,言理達性。
東晉時期,玄言詩的發展達到了極致。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詩歌徹底背離了情感而走向了說理。玄言詩表現生命意識的基本特征,是通過玄學生命觀的作用,使生命情緒得到淡釋,玄學家將這一精神過程稱為去除情累。許詢《農里詩》云:“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孫綽《答許詢詩》云:“慍在有身,樂在忘生。”又云:“理茍皆是,何累于情。”支遁《詠懷》云:“亹亹沉情去,彩彩沖懷鮮。”這些都是對除情累過程的形象描寫。除情累心態以及對這一心態的表現,構成了玄言文學與感情的獨特關系。另外,如庾闡的《衡山詩》:“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嶺末。寂坐挹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凌九霄,陸鱗因濡沫。未體江湖悠,安識南溟闊。”這里所表達的玄理正是阮籍《達莊論》中“恬于生而靜于死”的觀點,也就是“無為”的核心思想。其實,這個時候的玄言詩也并非一味地說理,它也有一些寫景甚至抒情。如庾闡的《衡山詩》中,就是“運目”見衡山、南嶺之景而抒發其“四豁”之情的。只不過這樣的情被“寂坐挹虛恬”的理給吞噬了。再來看孫綽的《秋日詩》,這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玄言詩:
蕭瑟仲秋月,飚戾風云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葉悲先落,郁松羨后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這首詩突出地描寫了秋天的景色,并且抒情的特征也很明顯。詩人以山居所見的秋月、秋鳳、秋山、秋林、秋葉、秋露這些濃重的秋天景色特征引發出悲秋的情感。但是,這些寫景以及抒情,其實質是以闡述玄理為旨歸。所謂“濠上”是指逍遙間游之所,也就是玄學中的濠上之風或濠梁之氣。這正如閻采平所說,“玄言詩的主旨,是因循自然的人生觀”。玄言詩人以玄理駕馭景與情,這是與《古詩十九首》的抒情具有根本性的區別。但要指出的是,這種以理馭情的詩,卻具有把情與景抽象到境界的意味,這也是《古詩十九首》的抒情所不具備的。要言之,玄言詩的寫景不是讓人感受景,抒情也不是以情感人,而是將其作為闡述玄理的手段。它雖然把詩理念化,甚至抽象化,但卻具有醞釀詩歌境界化的積極意義。
四
毋庸置疑,玄言詩其闡述玄理把詩理念化的特質,為詩歌由情感化向境界化的發展開辟了道路,而真正實現詩歌境界化的,則是陶淵明和謝靈運。所謂境界化的文學是指通過創作主體的精神活動(當然包括情感活動),在表現客觀世界的同時體現出理性的頓悟。所以,玄言詩雖然不是境界化的文學,但它通過自然山水來表現因循自然的玄理成為了玄言詩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卻將情感化詩歌引向了境界化道路。
陶淵明的田園詩突破了玄言詩的“理過其辭”之弊,表現出了對生命價值的超越,達到了生命與自然和諧的境界。陶淵明的生命意識是追求一種理性的、自覺的人生。這一點,他與玄學思想中超越生命矛盾、淡釋生命情緒的特性是基本一致的,但他與玄言詩人不同的是,他的理性的、自覺的人生與自然達到了和諧與統一;而玄言詩人則高張“理茍皆是,何累于情”的論調,將生命理念、生命情緒與自然割裂開來。盡管陶淵明的“神辨自然”思想是對玄學自然生命觀的繼承和發展。然而他對生命問題的思考和生命行為的實踐卻突破了以往玄學的藩籬。陶淵明的“神辨自然”生命意識突破了莊子憂生之嗟和樂死惡生的虛無主義生命價值觀,也突破了魏晉玄學家放縱任誕的生命價值觀,這種生命意識以超越的思想境界理性地解決了生命在物質形態上的“形”和社會形態上的“影”這樣低層次上產生的種種矛盾與苦悶,使生命形態處于“縱浪大化中”的“神”的境界。這種境界,使生命矛盾達到和諧自然,這是生命的真諦。他實現了生命價值的超越,達到了由對“形”和“影”的生命形態的追求發展到了對“神”的境界的解悟。
“神”的生命境界是陶淵明的理性追求,而這種理性追求使得陶淵明田園詩的平淡自然達到了自我超越的境界。陶淵明歸隱田園,在大自然中將玄理的回歸自然主題由一種哲學境界發展到了審美境界和生命境界。陶淵明的田園詩也從根本上轉變了玄言詩“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的“淡乎寡味”特質,開創了詩歌新的領域和新的風格。
陶淵明將自己的生命與自然融為一體,他的田園詩正是在平淡自然中體現出了他對生命的超越。所以,陶淵明清新自然的田園詩完成了中國古代抒情詩由情感化向境界化的轉變。元好問在《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其四》中說:“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真寫胸中天。天然對雕飾,真膺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紛綠徒爭憐。枯淡自足樂,勿為虛名牽。”這對陶淵明田園詩的平淡自然與人生境界超脫的評價是極為準確并極具代表性的。陶淵明對生命問題的領悟,對生命的超越,達到了和諧的境界,而表現這種境界的詩歌發展方式,形成了一種傾向,這種傾向在謝靈運等山水詩作家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謝靈運的山水詩突出表現的是人與自然的情、景、理的交融,而陶淵明的田園詩則是體現了他在生活中感悟和生命與自然的交融。所以,陶詩的平淡自然是謝靈運所不及的。嚴羽《滄浪詩話》云:“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這在對謝、陶在轉變玄言詩開辟山水田園詩領域的貢獻基礎上,說出了二人詩歌風格和價值的差異。
徐公持先生認為,東晉詩在詩風方面總體上具有清虛恬淡的特色,此與玄學清言特點相表里,亦與玄學本質觀念相一致。這種詩風,是前代所無的,是東晉特定文化環境下所形成,因此具有東晉時代特征。對于中國詩歌而言,它增添了一種全新風格類別,對于后世影響深遠。其影響的直接對象首先就是晉宋之交陶淵明、謝靈運兩位大詩人。陶、謝詩風不同,陶自然真樸,謝自然巧麗,然亦皆有清新平淡一面,此即繼承東晉詩風所致。從玄言詩闡述因循自然的人生觀這一主旨,到陶淵明和謝靈運的田園詩和山水詩,反映出了玄學家和詩人淡釋生命情緒、超越生命矛盾的過程。從詩歌發展的角度來看,以闡述玄理為主旨并把詩理念化了的玄言詩無意是古代抒情詩由情感化向境界化的轉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橋梁。
[1]林庚.中國文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2]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3]徐公持.魏晉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4]饒宗頤.兩晉詩論[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5]王毅.魏晉時期的“自然”說與晉詩之風貌[J].文學遺產,1984,(4).
[6]閻采平.玄學人生觀的藝術體現——論玄言詩的主旨[J].文學遺產,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