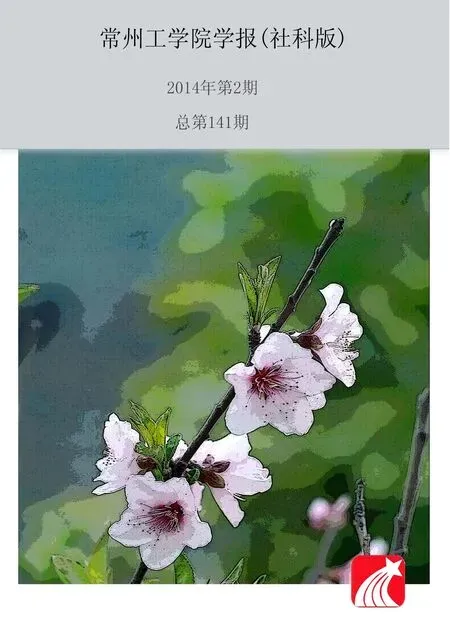反抗與僭越
——論陳雪小說的女同書寫
石松華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徐州221116)
反抗與僭越
——論陳雪小說的女同書寫
石松華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徐州221116)
陳雪是臺灣著名的女性作家,其創作目的主要為同性戀者尤其是女同性戀者立言,在其前期作品中大量描寫了女同性戀者的成長經歷和人生體驗。陳雪的《惡女書》《蝴蝶》《愛情酒店》是典型的女同文本,主要從對傳統性別觀念的顛覆、對異性戀霸權的挑戰、對傳統同性戀觀念的突破等三個方面,展現了其反抗和僭越傳統的書寫姿態及反叛精神。
陳雪;女同書寫;反叛精神
陳雪原名陳雅玲,1970年6月3日生于臺灣臺中,1993年畢業于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是臺灣著名的、極具才華的女作家。其創作題材多樣,風格獨特,其中同性戀題材尤其是女同性戀題材的書寫在其創作歷程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惡女書》《蝴蝶》《鬼手》等,長篇小說《惡魔的女兒》《愛情酒店》《橋上的孩子》《陳春天》《無人知曉的我》《附魔者》,及散文《天使熱愛的生活》等。《惡女書》收錄《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夜的迷宮》《異色之屋》《貓死了之后》四部短篇小說,堪稱其女同書寫的代表之作,于1995年出版后引起巨大反響,被譽為華文女同志小說的經典。《蝴蝶》收錄《蝴蝶的記號》《色情天使》《夢游1994》等三部短篇小說,其中《蝴蝶的記號》由香港導演麥婉欣改編拍攝成電影《蝴蝶》,曾多次獲得國際獎項,同時被選為“2004年香港同志影展”開幕片。陳雪在小說中主要書寫女同志的成長、生活、命運軌跡,表達她對臺灣同志運動社會問題的關注。她的同志題材的創作實踐對傳統觀念進行了挑戰,展現出一種鮮明的反叛與僭越的書寫姿態。
一、對傳統性別觀念的挑戰
在傳統的性別研究中,有三個主要概念: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欲取向,它們主要以兩種對應形式存在:生理性別——男/女、社會性別——陽剛特質/陰柔特質、性欲取向——異性戀/同性戀[1]。在異性戀為主體的社會中,具有陽剛氣質的男性和具有陰柔特質的女性之間產生異性戀才會被認可。這種二元對立的性別/性欲規則長期占據統治地位,被視為社會的常態。而陳雪以其超越常規的書寫姿態徹底打破了這種二元對立的對應關系,顛覆了傳統的性別論。這種顛覆在其女同志題材的小說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主要表現之一即對男女形象的塑造上。
陳雪塑造了一系列俊美的非傳統的女性形象。《愛情酒店》中英俊瀟灑的“阿青”是媽媽酒吧里的酒保,初見阿青時,作者用這樣的文字描述她:“削瘦的臉白皙而透明,憂傷的神情迷離的眼神,單薄的身體在寬大柔軟的白上衣白長褲底下隨著手臂的晃動起伏……俊美得令我幾乎尿濕了褲子”,“嘴角叼著燃燒的香煙,煙霧彌漫了她的臉”,“光是瀟灑帥氣不足以形容,除了俊美斯文還有更多”[2]50-51。通過陳雪的描述,我們似乎很難用傳統意義上溫柔可人的“美女”來形容和概括阿青的俊美,在阿青身上更多體現的是男性的帥氣與魅力,雖然多少缺了些陽剛之氣,卻更符合我們對古代白面書生的想象。在煙霧繚繞之中,我們感受到的是阿青如男子一般的憂郁、冷漠和放蕩不羈。除了那一頭烏黑的長發,從阿青身上我們感受不到任何女性該有的陰柔氣質。
其次,在小說中陳雪也塑造了許多具有女性氣質的男性形象。最典型的莫過于《愛情酒店》中的黑社會組織頭目“黑豹”。黑豹,正如他的名字一樣,有著花崗巖一樣的皮膚,身形高大壯碩,是“用他強壯的肉體去沖撞生命發出火光的人”[2]43,可在這樣強壯的、極具男性特征的外表之下是一顆有著傳統女性氣質的無比柔軟的心靈。他會在寶兒床前哭泣,像小孩子一般,有著如母親一般溫暖的懷抱,他像母親一般容忍和包容著身邊所有人的放肆、撒野和無理取鬧,還會為寶兒一針一線地縫紫色碎花窗簾……這也絕非是傳統意義上有淚不輕彈的男子漢。
此外,八面玲瓏、可男可女的“媽媽”,一心想做變性手術的設計師“橋”,通過愛“我”而愛著黑豹的“小五”,性別上是女人、長相舉止都像社會定義中的男人的“阿貓”……這些行走在性別模糊的灰色地帶的人,無不僭越或顛覆了傳統的性別想象。在陳雪的作品中,我們很難歸納出具體的男女形象,用男性或者女性來定義其人物性別。作品展現的更多的是性別不明,非男非女的形象。在行文之間,陳雪似乎在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也沒有絕對的男性與女性的劃分,也許模糊的性別才是人真正意義上的性別。
二、對異性戀霸權的挑戰
陳雪作為極具反叛精神的女作家,其反叛傳統的精神不僅表現在顛覆傳統性別觀念方面,更重要的表現為對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異性戀霸權的挑戰。在性價值等級制度中,性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和等級,其中“異性戀的、婚內的、一夫一妻的、生殖性的和非商業性的”,“一對伴侶之間、一代人之間、家里”的性實踐才是“美好的”“正常的”“自然的”,它們占據最高層。而那些性行為或者性戀模式超越常規的則處于最底層,被認為是“患有精神疾病的”“非法的”“應懲治的”。在傳統男權異性戀體制中,“男—女—異性戀”被視為唯一合法的性戀模式。異性戀模式占據著性體系的統治地位,然而“性就像性別一樣,也是政治的,他被組織在權力體系之中,這個體系獎賞和鼓勵一些個人及行為,懲罰和壓制另一些個人和行為”[3]68。因此,在異性戀霸權的統治之下,一切不符合常規的性戀方式都將受到壓制、排擠甚至毀滅。人們長期生活在異性戀體制的監控之下,很少質疑這個體制本身是否公平。作為為數不多的對異性戀體制進行反思的作家之一,陳雪用其敏銳的眼光、犀利的筆觸描寫了一系列在異性戀霸權之下喘息甚至遭毀滅的生靈,大膽地質疑和否定異性戀體制的權威性。
首先,陳雪對異性戀是美好的提出質疑。《蝴蝶的記號》中,媽媽和爸爸表面上是一對和諧幸福的令人嫉妒的夫妻,實際上夫妻之間卻充滿著欺騙、虛偽和背叛。爸爸背著媽媽偷偷和“阿姨”們約會,而媽媽在懷疑、猜忌的折磨下幾次曾拉著“我”去投海自盡。而“我”在家庭和社會的重壓之下,被迫離棄同女“真真”,和開店的阿明墮入尋常婚姻。然而,“我”和阿明看似美滿幸福的婚姻背后,只是在用我“難以言喻的痛苦”和行尸走肉般的軀體維持著阿明渴望已久的有一個幸福家庭的夢想。最后,無論爸爸、媽媽,還是“我”和阿明,都不免走向離婚的結局。除此之外,在陳雪其他作品中,一如《色情天使》中“我”和牙科醫生,《愛情酒店》中寶兒和阿豹,《夜的迷宮》中“我”與丈夫阿丁……更把異性戀體制之內的愛欲完全轉變成了發泄肉體欲望的工具。主人公沒有在異性戀婚姻或“愛情”中找到幸福和歸屬感,這至少證明了異性戀不是性實踐唯一的最完美的形式。
其次,陳雪大膽展現異性戀霸權對人以及人性的壓制和毀滅。在《貓死了之后》中,主人公“我”在父權異性戀霸權控制下的家庭、社會、教育之下,被灌輸以同性戀是非正常的、病態的思想。因此,在面對同女阿貓熾熱的感情時“緊張的想逃跑”“總覺得害怕”。“面對阿貓熾熱的情愛和模糊的性別,我簡直束手無策,我甚至無法處理自己對她萌生的熱情和性欲,只覺得好羞恥……”[4]這種“害怕”和羞恥最終導致了“我”對阿貓的逃離。然而同女在逃離同性情誼之后,不但沒有在異性戀的天空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反而變成了折翼的天使,失掉原有的靈魂,只能“踐踏自己、踐踏一切回憶”,“空洞地在世界上飄來蕩去”。而阿貓一類,以扮演男人的方式否定自己身為女人的事實,企圖符合男權異性戀的規范,又何嘗不是父權異性戀霸權壓抑、扭曲人性的一種表現方式?在《蝴蝶的記號》中,異性戀霸權更展示了它不可僭越的權威。高中生心眉和武皓因為“怪怪的”,“好像是同性戀”而被社會、學校、家庭視為“壞孩子”,被同學“指指點點”。終于在“私奔”未遂之后被強制分開,最后導致武皓在被送出國的前一天自殺,心眉精神失常被關在家里的倉庫。本是兩朵嬌艷的花朵,因為純潔的同性情誼而走向毀滅,這無疑是對異性戀霸權的強烈否定和控訴。誠然,千百年來,異性戀模式長期占據著性體系的主體地位,定有其得以存在的合理之處。在此,陳雪也無意否定一切處于異性戀模式之下的婚姻和愛情,只是希冀在異性戀霸權籠罩的天空之下,為現存的其他性戀方式求得一席之地。
陳雪對異性戀霸權挑戰的另一方面則表現在用大膽的筆觸展示同女被壓抑的欲望。在父權異性戀霸權法則之中,女性的情欲遭到壓抑,身體遭到禁閉。女性不能主動要求,只能被給予,擁有欲望是一種罪惡,而女同的欲望則更被視為天地之大忌。千百年來,那些有同女情誼的女人們,只能在教育、家庭、社會的重重包圍、封鎖與壓迫之下“安分”地走進婚姻,“一生都在做違背自己的事”,像小蝶一樣,將自己訓練成行尸走肉般的“什么都似乎感覺不到的人”并以“錯覺”來解釋自己對女人的欲望。然而,同女的欲望卻像蠢蠢欲動的巖漿,壓抑得越久,積攢的爆發的愿望也就越強烈,一旦爆發就是驚天動地的力量。
陳雪的代表作《惡女書》以驚世駭俗的筆觸大膽書寫同女們間的欲望。“灰綠蚊帳頂端冒出一縷黃煙霧向上飛升,屋內充滿甜膩的味道讓蟑螂瘋狂起舞,孩子聽見獸類撕咬的追逐的叫囂,聽見蜻蜓撲撲鼓翅,聽見貓兒痛苦狂喜的呼喊,沿著昏黃夜燈的照射,蚊帳底下兩條人影變得好巨大,彼此糾纏、翻滾、碰撞,在孩子眼中蜷曲交疊幻化……”[5]“她那足以切割人的聲音讓我無法承受,我強忍著不讓自己哭叫出來,滿心盼望著妖獸般的女人快點將我撕扯下腹”[[6]。這近乎野獸般的呼喊,或許如其他評論者所說盡是穢物、垃圾、不堪入目,但那是千萬同女的心,是重壓在火山之下的欲望。惟有這欲望才能讓同女們逃離異性戀的枷鎖,讓“已經死寂的瘋狂因子又重新跳動在我的腸胃心肺里”。陳雪不僅大膽展露女同們的欲望,而且還賦予這欲望以拯救同女們死寂靈魂的力量。通過釋放同女情欲實現同女們的自我救贖,這無疑是對父權異性戀霸權徹底的反抗和顛覆。
三、對傳統同性戀書寫規范的突破
異性戀模式作為一種社會常態,長期占據著社會的主導地位,同性戀文化雖然溢出了異性戀的軌道,卻也不免受到前者的深厚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臺灣的同性戀小說中存在著大量同性戀對異性戀復制的現象,“在挑戰異性戀模式的同時,模擬了異性戀的身份認同”,最主要的表現即“T/婆”含有異性戀角色的劃分。“T的角色常常以異性戀模式中的男性身體再現,婆則復制傳統視野中女性的身體氣質,只不過身體的情欲發生了轉變”,“而被書寫的身體依然為二元對立的性身份認同限制”[7]。如果說同性戀模式是對異性戀模式的反叛與突破,這種潛在的復制異性戀現象卻體現了同性戀對傳統二元對立的性身份認同的限制以及企圖突破性別認同的困境。這種現象在90年代“酷兒理論”登陸臺灣之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相較于紀大偉、洪凌等人的同性戀書寫,陳雪作為“酷兒理論”的實踐者,在其一系列女同題材的文本中,通過對性身份的越界描寫和對情欲的肯定實現了對傳統同性戀書寫規范的突破。
在陳雪女同題材的作品中,她尤其擅長展現身體和欲望的互相穿梭與交織。身體通過情欲的流動呈現出不同的表演形態,因情欲對象的不同而在不同的性身份之間轉換。《愛情酒店》中“我”同時可以在阿豹和阿青之間流轉。和阿豹在一起時“我”是一個猶如天使一樣的女孩,安然接受阿豹如父親一般濃烈的關愛,扮演著“婆”的性身份。而在阿青面前,“我”又是一個主動出擊的“T”的角色,渴望溫暖和治愈阿青受傷而冰冷的心靈。因此,“我”的性身份完全取決于“我”所欲望的對象。“媽媽”更是如此,“她這人忽男忽女,可男可女,從小我也已經習慣她經常是不同性別的打扮……媽媽不是在舞廳就是在酒店上班,上班的時候打扮得妖嬈美麗在那兒跟男人打情罵俏,下了班回家就變成英俊瀟灑的俏公子跟她的女朋友在客廳里摟摟抱抱。”[2]17在此,情欲將身體從傳統的二元對立的性身份中解放出來,使身份具有表演的性質,打破了性和性別身份一一對應的關系。
傳統同性戀書寫對情欲的描寫多指向自我性身份的認同,在辨別自身情欲對象的基礎之上把自身定位到T或者婆的性角色之上。而陳雪卻把情欲書寫成一種個體取得生命認同、證明自我存在的方式。《蝴蝶的記號》中“我”——那具背負著“好女兒”“好妻子”“好老師”等各種身份的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軀體——在真真的愛撫中“好像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身體似的,充滿了驚喜,我也從她身上看見真正的美麗”。情欲的力量使“我”就此得到重生,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異色之屋》中陶陶“喚醒我形容枯槁的靈魂”,《色情天使》中在哥哥死后,“我”放縱情欲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證明自身的存在。《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中“我”通過欲望阿蘇實現對戀母的確認……因此,在陳雪筆下,情欲并不是生理欲望的簡單釋放,也不指向性身份的認同,而是指向個體對自我生命的確認。誠然,陳雪如此大膽地書寫流動多變的情欲,絕不是嘩眾取寵,也不是為了跟上時代的風,而是借由著流動的不可歸類的情欲,反抗已然定型的不可逾越的傳統。
作為才華橫溢、風格獨特的女作家,陳雪用大膽而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女同世界,其僭越傳統的反叛姿態也為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提供一個全新的角度。在其作品中,除了蘊含著上述幾種意蘊之外還包含著許多可以探討的議題,如女同的身份認同、女同身份與母職、家庭問題、精神疾病等等,這些議題都具有多重解讀的意義。筆者從反抗與僭越傳統的角度解讀陳雪的女同書寫,試圖拋磚引玉,為研究陳雪的學者們提供一點借鑒,以期有更多的學者從更多的角度挖掘和解讀陳雪作品中蘊含的豐富意義和獨特價值。
[1]艾尤.變幻與越界:當代臺灣女性小說性別與情欲的多元展演[J].文藝爭鳴,2012(3):138-141.
[2]陳雪.愛情酒店[M].臺北:麥田出版,2002.
[3][美]葛爾·羅賓等.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M].李銀河,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68.
[4]陳雪.貓死了之后[M]//惡女書.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2005:192.
[5]陳雪.異色之屋[M]//惡女書.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2005:67.
[6]陳雪.夜的迷宮[M]//惡女書.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2005:112.
[7]朱云霞.試論臺灣酷兒小說的身體敘事及跨文類實踐:以紀大偉、陳雪、洪凌的酷兒文本為例[J].臺灣研究集刊,2012(2): 78-85.
責任編輯:莊亞華
I106
A
1673-0887(2014)02-0014-04
2014-03-04
石松華(1988—),女,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