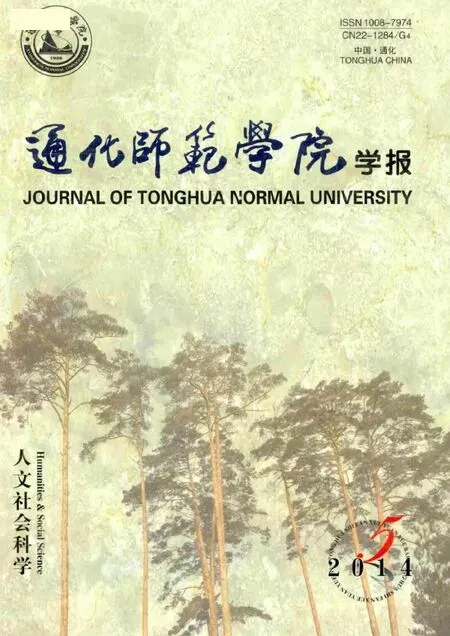鮮卑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
孫 楠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各民族的口傳文學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要素,是研究各民族歷史,尤其是早期歷史不可或缺的資料。鮮卑族作為北方存在時間長,且建立多個政權的少數民族,有豐富的口傳文學。學術界對于這些口傳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學價值和形式方面,對于其史料價值的研究尚顯薄弱,主要有田余慶《〈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國史之獄的史學史考察》,認為《代歌》是拓跋鮮卑的史詩[1];黎虎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論》論及慕容鮮卑的《阿干之歌》,認為《阿干之歌》反映了慕容鮮卑統治集團內部斗爭的歷史[2];逯耀東先生的《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研究鮮卑早期樂歌 《北狄樂》《真人代歌》《國語真歌》《國語御歌》《鮮卑號令》等,論述北魏初期“胡風國俗”雜糅問題。[3]此外,還有一些文學研究涉及到鮮卑族早期歌謠問題,但不是從史料價值角度的研究。本文嘗試從文獻記載的鮮卑族傳說、歌謠等文學資料入手,探討鮮卑各部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以期從一個新的視角對鮮卑族早期歷史進行解讀。
一、鮮卑族口傳文學的淵源及表現形式
口傳是早期人類社會主要聯系方式,在沒有文字或文字使用不普及的時代,人們記錄社會風俗、民族文化與歷史主要是靠口耳相傳,代代延續,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以神話、傳說、歌謠、故事等形式為主的口傳文學。鮮卑族也走過這段文學發展的歷程。鮮卑族作為東胡族系一支,與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一樣能歌善舞,《后漢書·烏桓鮮卑傳》《三國志·烏桓鮮卑傳》均記載:鮮卑族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歌唱成為傳承他們民族文化的主要路徑。在沒有文字時代,“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4]鮮卑族通過“人相傳授”的方式記錄傳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歷史,而“人相傳授”主要是通過歌唱或講故事等形式在代際傳播。
(一)傳世文獻中有關鮮卑口傳文學的記述
有關鮮卑族口傳文學的資料主要見載于《魏書》《晉書》《十六國春秋》《資治通鑒》和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中。從傳世文獻記載看,鮮卑族有大量的樂歌,如《魏書·樂志五》記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北魏《國語真歌》十卷、《國語御歌》十一卷。”已軼。這里的“國語”無疑是鮮卑語,是用鮮卑語吟唱的歌謠。它們與《真人代歌》之間的關系,學術界有所論述,如黎虎先生認為:“這是將鮮卑語言用漢語同音字記錄下來的兩部集鮮卑歌曲大成之作,這也是鮮卑族首次將本民族音樂編撰成書。頗疑《真歌》即包括《真人代歌》等早期鮮卑族歌曲,《御歌》當是鮮卑族建立政權后創作的宮廷《雅》《頌》類歌曲。”[2]可見,當時代北存在大量鮮卑族早期的歌辭,為了宮樂的需要,拓跋魏曾組織人力篩選輯集過代歌,這才出現史歌總集《真人代歌》。《真人代歌》《國語真歌》《國語御歌》《簸邏回歌》《梁鼓角橫吹曲》,其內容應該有不少相似之處,都包含一些鮮卑早期歷史史料,是鮮卑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鮮卑族口傳文學資料在流傳過程中逐步散佚,存世很少,但從傳世文獻的零星記載中也能反映出其存在的價值。
(二)墓志中對鮮卑族口傳文學信息的記載
鮮卑族不僅在沒有文字或文字不發達時期盛行口傳文學,就是在已經漢化之后也依然保留著這種表達形式。有些家族也通過歌謠等形式記錄自己家族歷史傳承。在北魏墓志中有一些關于用歌謠傳唱家族歷史的記載,如正光五年(524年)元子直墓志,說到其家世業績“故已播在民謠,詳之眾口”[5];永熙二年 (533年)元肅墓志,記肅父扶風王怡 “道勛出世,列在歌謠”[5];武定八年(550年)穆子巖墓志贊美先人事跡說:“家圖國史,可得詳言”[5]。 這些墓志是北魏末年和東魏時期作品,在漢字已經普及,漢語已成為官方語言,漢族傳統紀傳體史書十分發達的時期,這種口頭傳唱在鮮卑族中依然盛行,表現出一個游牧民族對自己文化的獨特喜愛。一直到唐代,鮮卑族的這種傳唱形式仍有保存。《舊唐書·音樂志》載:“開元初,以問歌工長孫元忠,云自高祖以來,代傳其業。”“元忠之祖,受業于侯將軍,名貴昌,并州人也,亦世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世相傳如此。”長孫家族出自鮮卑,這種世代傳唱的“北歌”乃鮮卑語歌謠,此時鮮卑族已基本融合于漢族,而這種口傳文學的表達形式進入唐朝宮廷,被當政者接受。目前所見墓志中沒有歌謠的具體內容,但從記述的信息中可以看出,這些具有家族私人性質的歌謠在當時應該有著廣泛的流傳,是記述鮮卑家族和朝代歷史的重要資料來源。
隨著鮮卑族的漢化,文字記載逐步成為他們記述歷史和表達情感的主要手段,口傳文學傳承形式發生改變,逐步文字化,但不能否認早期口傳文學的存在及其價值。
二、鮮卑各部族早期傳說的史料價值
人類最初級的歷史意識是不自覺地、本能的,在沒有文字的時代,就是靠口傳和回憶的形式記錄歷史。這種世代相傳的故事講述,現在我們稱之為傳說,它既屬于文學范疇,也蘊含著豐富的史學內容,其主要功能是傳承文化。“從史學產生的淵源上說,傳說也就成了傳播歷史知識的最原始的形式”,它雖“不是歷史學,但它有歷史故事的內容,反映了一定的歷史觀點,也有自己的表述形式”。[6]每個民族都曾經歷口傳歷史時期,通過口口相傳的形式記憶自己遙遠的祖先。
(一)早期傳說在研究鮮卑族族源、祖先等問題上的價值
鮮卑族因其早期“不為文字 ”,故沒有留下本民族早期歷史的文字記載。較早系統記載鮮卑族歷史的漢籍是王沈《魏書》和范曄《后漢書》的《鮮卑傳》,所記述的鮮卑族已經活動于西拉木倫河流域以北的蒙古草原,此時的鮮卑族已是比較強大的游牧民族,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漠南之地。”[7]在此之前的鮮卑因“未有名通于漢”而不見載于正史,與漢朝政府“始通譯使”確切紀年是東漢建武二十五年(49年)。那么,漢籍記載之前的鮮卑歷史如何?《魏書》作為鮮卑政權官修史書,記載鮮卑族早期歷史的資料從何而來?目前我們無法說明其全部資料來源,但有一個源頭是可以肯定的,即鮮卑族各個部落的傳說。 霍爾姆格蘭在分析 《魏書·序紀》有關拓跋早期史的資料來源時曾寫道:“在這里,魏收所能擁有的,無非是走了樣的口頭傳說和他本人的漢文化的遺產。”[8]口頭傳說是魏收從事史學寫作的素材之一。
鮮卑各部族都有自己的傳說,主要是關于祖先和族源的記載。慕容鮮卑的傳說認為自己是 “有熊氏”的后代,《晉書·慕容廆載記》:“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后與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這段文獻明顯來自于慕容民族的早期傳說,這個傳說為研究慕容鮮卑早期歷史提供了三點信息:祖先是“有熊氏”,族屬是東胡,社會風俗官制與匈奴同。這就為研究慕容鮮卑早期歷史提供了大致的范疇和參考的對象,即以匈奴族為范本,研究慕容鮮卑早期社會風俗史。拓拔鮮卑傳說認為自己是黃帝的后裔,“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為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聰明武略,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4]拓跋鮮卑的祖先是黃帝,鮮卑族名來源于大鮮卑山,一直到毛皇帝才有明確歷史記載,而毛皇帝之前的六十七世的世襲資料應該主要來源于當時存在的傳說。宇文氏傳說認為自己的祖先是神農氏:“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后日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候,為魏舅甥之國。九世至候豆歸,為慕容晃所滅”。[9]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炎帝,并說明族名來源和早期的世襲發展史。
上述傳說是后世史學家根據各部族的口頭傳說和存世文獻整理而形成的,資料有明顯的修飾痕跡,如各部族的祖先“有熊氏”、“黃帝”和“神農氏”明顯是這些部族漢化到一定程度后,統治者為將自己的部族或政權納入漢族所謂“合法”序列而編造的,是出于所謂的“正統”的考慮和政治需要而進行附會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這些傳說的史學價值,有些是根據其民族真正的傳說保留下來的,為研究鮮卑各部族早期發展史提供了線索和資料,后來一些考古資料也證明了其真實性。
(二)早期傳說為鮮卑族名的確定提供佐證
關于鮮卑族名,在其它文獻中也有記載,較早的是《國語·晉語》第八:“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與鮮卑守燎”和《楚辭·大招篇》有“小腰秀頸,若鮮卑只”。《史記·匈奴列傳·索引》引應奉曰:“秦筑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為號”。《翰苑集》注引《漢名臣集》:“鮮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長城,徒亡出塞,鮮,少也;卑,陋也。言其種眾少陋也。今其人皆髡頭,衣赭,手足庸腫,此為徒人狀也。”這些紛繁的傳說,孰是孰非,難以判斷。1980年大興安嶺北部鮮卑人祖先居住的嘎仙洞的發現,里面的碑刻為研究鮮卑祖先提供了新的實證,與《魏書·序紀》中關于鮮卑族早期的傳說基本吻合,即鮮卑族早期主要活動在大興安嶺山脈的中部和北部,居于鮮卑山,因以為名,學術界也因此得出關于鮮卑族名和早期歷史發展普遍接受的結論,證明上述文獻記載的錯誤。從此可以看出,這些傳說中存在著各部族歷史的合理成分,我們不能因為有某些人為修飾或文學性過強而否定其歷史價值。
三、鮮卑各部族歌謠的史料價值
口傳文學除傳說之外,還有歌謠,包括民間歌謠和宮廷歌謠,這里面也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資料,也是各民族歷史的重要傳承路徑。法國語言學家和民間文學者特·拉維勒馬該認為:“這是人民的各種信仰、家庭與民族歷史的儲存處。”[10]鮮卑族歌謠正是鮮卑族文化的“儲存處”,內容涉及了鮮卑族社會生活、思想感情、軍事斗爭等方面,其價值遠遠超出了文學范疇,具有很高的社會學、民俗學和社會史等方面的價值。口傳文學的特質決定其傳承的范圍和時間,環境改變使一些民族的口傳文學喪失存在的土壤而消亡。鮮卑族民歌以口傳形式存世者已經不見,一部分轉變為書面文學而保存下來。
(一)慕容鮮卑的《阿干之歌》為研究鮮卑部族分化與遷徙提供參考
慕容鮮卑的《阿干之歌》見載于《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斗!’吐谷渾曰:‘馬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別甚易,當去汝于萬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又《魏書·吐谷渾傳》云:“(慕容廆)子孫僭號,以此歌為輦后大曲。”曹道衡先生認為此歌謠作于晉武帝太康中后期 (284-289年),“《通鑒》卷90記事于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乃追敘前事,歌則當作于慕容廆繼位之初也。”[11]此歌本是鮮卑語,今已散佚,我們無從知道《阿干之歌》的具體內容,但從《阿干之歌》形成過程看,是出于后悔與兄弟鬩墻之事,懷念兄長的離去而作。黎虎先生認為“他不是一般為懷念而作,而是有著一定的政治目的的。這與慕容氏統治集團內部長期的激烈家族斗爭,特別是嫡庶之爭有關。”[2]為我們了解慕容鮮卑統治集團斗爭歷史和吐谷渾部族歷史提供參考。這首歌謠對后世影響很大,高人雄先生認為,“這首亙古之歌,影響深遠,不僅以地名的形式留在人們口頭,而且與吐谷渾民族文化聯系在一起,甘青寧一帶許多方言中仍稱兄為阿干。”[12]現在,在甘肅蘭州附近的阿干鎮一帶流行一首《阿干之歌》,其歌辭曰:阿干西,我心悲,阿干欲歸馬不歸。 為我謂馬何太苦?我阿干為阿干西。 阿干身苦寒,辭我土棘住白蘭。 我見落日不見阿干,嗟嗟!人生能有幾阿干![13]這首《阿干之歌》不知是否是慕容鮮卑《阿干之歌》直接流傳,但從內容上看,具有慕容鮮卑《阿干之歌》的因素。從流傳的地域看,今本的《阿干之歌》流行于甘肅、青海一代,與歷史上吐谷渾活動地域吻合,這就為研究吐谷渾的族源問題和遷移的路線提供了有力佐證。
(二)被譽為“拓跋史詩”的《真人代歌》史料價值
在鮮卑族歌謠中,最具有史料價值的歌謠是被稱為“拓跋史詩”的《真人代歌》。《魏書·樂志五》謂“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這些歌謠唐以前多已陸續散佚。《舊唐書·音樂志》載:“后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凈王》《太子企喻》也”。田余慶認為《代歌》內容從“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來看,應該就是拓跋史詩。“代歌是經過拓跋君主有意篩選甚或部分改造的燕魏之際鮮卑歌。篩選是按照道武帝個人意志進行的,目的是用口碑資料中的拓跋(也不排除鮮卑它部如慕容等)傳說,編成歌頌先人功烈的歌謠,于代人中廣為傳播,為道武帝的帝業制造輿論。”[1]關于《真人代歌》,學術界研究成果很多,《真人代歌》的名稱、內容、形成時間、后人竄加等問題學術界一直有爭議,在此不再置喙,但有一點是達成共識的,那些歌謠記錄了鮮卑族早期歷史,是《魏書》等正史的重要資料來源,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研究鮮卑族早期歷史研究資料的缺憾。
(三)郭茂倩《樂府詩集》中鮮卑族歌謠為研究鮮卑族生活史、社會史、戰爭史等方面提供鮮活素材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25《橫吹曲詞》中有“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凈王》《太子企喻》”,留存下來的歌辭是由通曉漢語的鮮卑人或通曉鮮卑語的漢人翻譯而來的。留存至今的鮮卑歌辭數量不多,時間跨度大,內容也比較廣泛,主要是反映戰爭、兵役、愛情及百姓生活,為我們從不同層面描繪出鮮卑族生活場景,是研究鮮卑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如《企喻》篇:“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膘。牌子鐵裲襠鸐尾條。前行看后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后頭,齊著鐵。”短短的幾句歌辭,形象地描寫了全副武裝的游牧民族騎兵的氣魄,“鐵裲襠”(護心護背的鎧甲)、“”(頭盔)、“鸐尾條”(頭盔上的裝飾物)為我們展示了鮮卑族騎兵的裝備,這些在史書上很少記載。而其記載的真實性被后來的考古資料所證明,如敦煌285窟西魏壁畫、河南鄧縣北朝畫像磚、咸陽底張灣北周墓愷馬騎俑等南北朝時期的壁畫圖像和北朝貴族墓葬中出土的騎兵、戰馬、武士俑,戰馬和騎兵的裝束與民歌記載基本吻合,足以說明民歌所反映歷史的真實性,完全可以用作研究鮮卑族軍事史料。《慕容垂歌辭》:“慕容攀墻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墻外漢。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愿作墻里燕,高飛出墻外。慕容出墻望,吳軍無邊岸。咄我臣諸佐,此事可惋嘆。”這是一組描寫慕容垂時與東晉之間戰爭的歌辭,形象地描寫了慕容垂在這次戰爭中的不利情景和心態,為研究慕容垂時期與東晉之間戰爭提供了資料。《梁鼓角橫吹曲》中還有一些描寫鮮卑族與其他政權之間戰爭場景的歌辭,這些生動場面的描寫足以彌補正史之不足。
在社會生活方面,歌謠記錄得更生動形象,如《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這是一首熱戀女子歌唱的情歌:“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鷂子,那得云中雀。”歌辭質樸簡潔,表現了鮮卑女子不同于漢族的開朗熱情性格,也內含著漢族文化對鮮卑文化的影響,體現了雙重民族文化的內蘊。樂府詩中的歌謠為研究北方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和鮮卑社會史提供了鮮活的素材。
綜上所述,鮮卑各部族都曾有過自己的口傳文學,它以容易記憶的傳說和傳唱的形式記錄鮮卑各部族的祖先、族源、歷史事件、民風民俗,是研究鮮卑族歷史的重要資料,彌補了研究鮮卑族早期歷史和社會史資料的不足。但我們在運用這些資料的時候,要注意它們在傳承過程中累加的成分,注意剔除后世的有意的附加和刻意的篡改和修飾,最大程度地還原口傳文學的本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