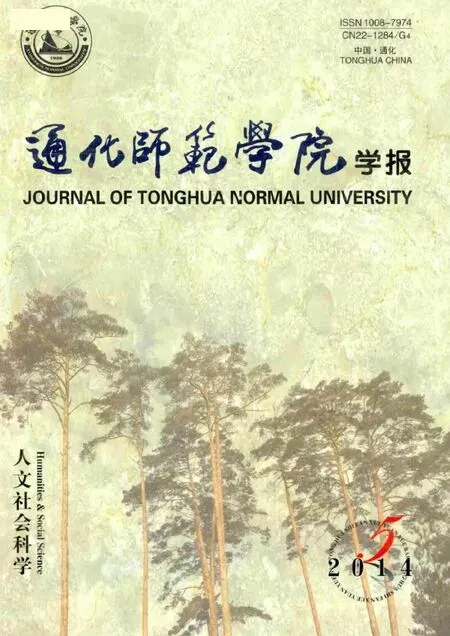移民日本列島和中原地區的渤海人
孫煒冉,董 健
(通化師范學院 高句麗與東北民族研究中心,吉林 通化 134002)
渤海亡國后,其主要遺民被契丹遷往上京道、中京道以及東京道地區;此外,還有據地抗敵者,如定安國和兀惹;再有,便是流入王氏高麗和女真地區者。這些渤海人之流向因有較為詳備的文獻記載而早已被學者所熟知,故而學界對這三方面的渤海人流向問題著眼較早,研究成果頗多。但是相比之下,對于與渤海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島以及陸地上被契丹國境阻亙的中原地區,在當時的自然條件下渤海人很難直接前往、順利到達,所以,這兩個地區流入的渤海人基本是通過二次移民才能完成。因此,少有文獻對渤海人移民兩地有較為詳盡的記述。但是,從相關文獻可以分析出,早在渤海亡國之前,渤海人就開始了移民日本列島的行為,而渤海亡國后經由契丹境內流入中原地區的渤海人遠比明見于文獻的數量龐大得多。
一、移民日本列島的渤海人
中國東北地區之國族與日本的交往和接觸由來已久,早在高句麗時期,日本就與之有著頻繁的外交關系,從公元540年到682年間,就有30余次遣臣出使日本。[1]199而日本與靺鞨之間的交往也比較密切,日本史書往往稱靺鞨人為肅慎人,有記錄表明,靺鞨人曾到達庫頁島、北海道,這些均有考古材料佐證。[2]尤其是到了渤海國時期,以海東盛國的渤海為橋梁,唐文化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日本列島,為日本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變革提供了養分,成就了日本社會文化的形成。而在渤海與日本頻繁的交聘中,又有一定數量的渤海人來到日本定居,尤其是渤海亡國后,一些渤海人通過朝鮮半島為中轉站,來到了日本列島,為日本的發展貢獻了力量。
渤海國與日本的民間交往始于何時無從考證,但國家間的正式通使始于渤海大武藝仁安九年、日本圣武天皇神龜四年(727),武王大武藝派出以寧遠將軍郎將高仁義、高齋德為代表的24人使團出訪日本。然而,使團因海路遭遇風浪,漂流至今日本北部的北海道蝦夷境內,高仁義等16人遇害,高齋德等8人幸免逃脫,輾轉至出羽國地區登陸,完成了此次出訪,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系。[3]由此,開啟了渤海國與日本之間頻繁且友好的國家往來。“至渤海亡國前的公元919年(五代后梁貞明五年),前后192年間,渤海聘日34次,日本聘渤海13次,雙方共交聘47次,平均每四年即有一次往來,比唐和日本之間的交聘往來,既多且密,促進了唐代東北地區與日本的經濟、政治、文化交流,豐富了兩國的社會文化生活,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兩國文明的進程,成為中日友好關系史上動人的一章。”[4]199-200在渤海與日本交聘期間,還形成了專門通往日本的“日本道”,為渤海五道之一,是渤海國經濟、文化輸出的重要道路。
從渤海與日本頻繁的官方交聘中不難看出,雙方間的交往是極為密切的,由此可以推斷,其民間的交往勢必更加頻繁。這其中,一定會有渤海人因商業、政治等原因留居日本,為日本社會的發展貢獻力量。眾所周知,古代的日本是一個吸納外來文化的巨大受體,正是在來自于大陸和半島先進文化的巨大影響下,日本才在極短的時間內擺脫蒙昧,迅速踏入文明社會。而這其中,大量來自大陸和半島的移民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所以,外來人口來到日本是這個時期日本社會的常態事件。唐代以前,即朝鮮半島上的三國時期之前,“渡來人”文化對日本之影響自不用提,單從八世紀初來看,日本政府將移民來者,即“歸化人”有組織地遷移到東日本附籍,并為他們建立村莊,如新羅郡、高麗郡等;亦或采取其他積極的措施予以安置,這樣的事例在《日本書紀》中屢見不鮮。事實上,不唯中原和半島,渤海人也有借機留在日本者。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元年(810)五月,“渤海使首領高多佛脫身留越前,安置越國給食。即令史生羽栗馬長并習語生等,就習渤海語。”[5]后來,日本朝廷還賜高多佛姓“高庭”[6],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920)六月二十六日,“右大臣令元方奏領歸鄉渤海客使大學少允坂上恒蔭等申:遁留不歸客徒四人事。”二十八日,“仰遁留渤海人等,準大同五年例,仰越前國安置云云。”[7]361可見渤海移民在日本定居的事實存在。定居者有的是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如高多佛所扮演的語言教授者,其他能夠定居日本的主要是渤海歌舞伎人、僧人及商人。
渤海文王大興三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十年(739),渤海國的若勿州都督胥要德、云麾將軍已珍蒙在第二次渤海訪日期間,已珍蒙為日本天皇演奏了本國樂,即“渤海樂”,由此產生了很大影響,并引起了日本天皇的關注。渤海樂不僅傳入日本,而且還被列為日本宮廷音樂之一。可以說,“渤海與日本雙方在文化上的交流最顯要的當屬音樂和舞蹈上的結合,堪稱是中日兩國文化相結合的典范。據《續日本紀》卷十三記載:‘天皇御中宮闔門,已珍蒙等奏本國樂,賜帛綿各有差。’這段史料反映了渤海樂已在日本登上朝廷,天皇還對此進行了賞賜。由此,開啟了渤海樂在日本的流傳和推廣,據《舞樂要錄》記載:‘日本塔供養,堂供養。御八講、朝覲行幸、御宴會正,相撲節等活動分別奏《新靺鞨》和《渤海樂》。’可見,在日本寺院內也開始演奏和推廣渤海樂,是日,百官及諸氏人咸會于寺,請僧五千禮佛讀經,作大唐、渤海、美樂、五節田舞、久米舞,這就更加清楚的顯示出渤海樂在日本的上層社會廣為流傳。”[8]相信伴隨著渤海樂傳入日本和在日本的盛行,必然有相當數量的渤海歌舞伎人的對日輸入。
渤海國的佛教僧侶頻繁來往于唐朝中原地區及海外的日本,成為各地區之間文化傳播的使者。著名的有渤海僧人釋貞素,其活躍來往于日本、唐朝中原地區和渤海之間,弘揚佛法,最終葬身海底。如他這樣的僧人定不在少數,許多渤海僧人,懷揣著傳教布道的情懷,遠洋渡海前往日本弘法,這些對于渤海國僧人的記載反映出渤海國內佛教的盛行及渤海國與日本相互交流的盛況。日本保留了大量渤海樣式的佛教建筑和遺跡,這其中的僧人匠人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渤海交聘日本,開辟了新的貿易渠道。“由于渤海地處北溫帶,棉絲較少,換回日本紡織品,滿足渤海貴族的生活需要,這是渤海和日本貿易規模越來越大的社會原因之一。赴日使團大量的隨員是進行貿易的商人,令渤海使團具有濃厚的貿易色彩。頻繁的對日貿易,對渤海一些邊遠地區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最后,發展到民間貿易,由于發展對外貿易的驅使,大量渤海人攀山渡海,舟車織路,歷盡艱險,往來于日本道上。”[9]無論是宮廷貿易、官方貿易還是私人貿易,商賈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私人貿易中,大量商人紛至沓來日本,尋求貿易帶來的巨大利益。在雙方交聘的近兩百年間,有據可查的47次互訪中,渤海就占了34次之多。這些渤海使團每次人員都極其龐大,然而到達日本沿岸后,只有20或40人進京辦理外交事務,還有的甚至全部都不允許進京,他們大多數都停留在安置地,一般在此停留半年之久,這些人如果不是從事貿易活動,為巨大的經濟利益所驅使,又怎么會漂洋過海,冒死犯難,來到日本呢?王承禮研究認為:渤海使團中105人的使團最多,105人使團中有65位大首領,顯然是地方勢力的代表,作為渤海統治者一方面通過讓地方首領出訪,在政治上加以籠絡,同時地方首領多作為地方貿易代表,借此能發展地方貿易,在經濟上得到實惠,滿足地方首領的經濟利益,達到鞏固和加強統治的目的,因此大首領才不斷參與。[4]261-263筆者并不認為這些所謂的大首領就是渤海國基層的部族首領,筆者認為這些大首領其實是以粟特商人為主的商業頭目,是前來貿易的商業代表。無論是地方首領抑或粟特商人頭目,其目的并無差別,即前來從事廣泛的商業貿易。伴隨著貿易的擴大和增長,從事貿易的商人便大量的前來日本,其中定居在日本者當不在少數。
渤海亡國后,文獻記載了很多人駕船投附高麗國,而日本作為距離渤海本土較遠的地方,且遠隔重洋,并不是投附的最佳地區,但一些長期往來于渤海與日本之間的人士,必不乏借道半島或者通過海路奔赴日本的。但因為地理交通的影響,其人數一定比較有限,沒有大規模的投附現象。然而通過前文介紹,從渤海交聘日本到渤海亡國,滯留于日本的外交使臣、伎人、僧人、匠人及商人亦不在少數,他們的到來,加強了中日間的交流,為日本社會的迅速發展貢獻了力量,是中日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筆。
二、流入中原地區的渤海人
渤海亡國后,其民悉數被遷離故土,徙往遼境,東丹國內的渤海人亦先后陸續被移民至遼代地區,其余或南投王氏高麗、或投附女真地區,少數據地割據,如定安國和兀惹等。而中原因契丹阻亙,又遠隔大海,故少有直接逃奔者,但從史料來看,亦有投附中原者。明見于史書者只有三批:第一批為后周顯德元年(954),渤海“酋豪崔烏斯(烏斯羅)等三十人來歸,其后隔絕不能通中國”[10]902、14129;第二批為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以鸞河為渤海都指揮使”[10]14130;第三批為遼統和四年(986年)“渤海小校貫海等叛入于宋”[11]121。除此三批投附中原者,再無明載于文獻者。
從渤海人或南投高麗,或投附女真地區,或占地割據來看,對于契丹的亡國之恨始終貫徹于心,由此可見,被遷徙契丹腹地的渤海人亦懷著強烈的抵觸情緒,《宋史》中便言“渤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10]9124并且,從有遼一代貫徹始終的渤海人的數次起義便可見一斑。因此,除上述明載于文獻的投奔中原事件外,相信還有更多的渤海人通過遼境進入中原王朝。在遼宋戰爭中,遼為了彌補其兵力不足,每與宋戰必帶有大量渤海軍人和其他降服族眾隨同出戰,“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10]10532而這些隨同出征的部族,尤其是渤海人本就對契丹不滿,因此很多人便趁勢倒戈,進入宋境。從宋廷禁軍中設有“歸明渤海”便可證明宋境內之渤海人不為少數。
“歸明”者,乃謂歸服圣明之主之意。唐朝詩人白居易《代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中云:“北虜何為歸明,南蠻何為歸化?”在《舊唐書·僖宗紀》中便有:“賊將李詳下牙隊斬華州守將歸明”的記述。及至宋代,歸明人的處置已有制度,如宋人葉適在《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銘》中言:“歸明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屆時,宋代常稱西南少數民族首領到宋朝廷補官者為“歸明”。宋人趙升在《朝野類要·入仕》中述“歸明:謂元系西南蕃蠻溪峒,久納土,出來本朝補官,或給田養濟。”但從宋禁軍設置來看,除了有“歸明渤海”外,還有“契丹歸明神武”,[10]4577可見“歸明”者非專指西南蕃蠻歸服者,還有北方民族歸服者。宋廷禁軍中設立“歸明渤海”,言“太平興國四年(979),征幽州,以渤海降兵立。”[10]4586可見在宋遼交戰期間,宋朝俘獲了大量遼軍內的渤海兵,能夠充其為禁軍,成以建制,可見人數之眾。僅“雍熙中(984~987),(宋)出師北征,(田)重進……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贇、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千余人”,[10]902所謂契丹驍將大鵬翼者乃遼冀州防御使,[11]120渤海大氏王裔,此戰田重進便俘獲渤海軍三千余人。而渤海人充為契丹帳下乃不得已而為之,在宋仁宗繼位的當年(1022)冬天,“契丹獵燕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高)繼勛曰:‘契丹歲賴漢金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10]9695可見渤海人并不甘心在遼境為其驅使,或逃或叛,更有叛附宋境或“行剽兩界”者,于是便有大量渤海人懷著復國仇遼的心態,充實到宋軍之中。 “歸明渤海”在熙寧以后(1068~1077),便因為渤海人的充實而有所變化,“元豐元年(1078),撥填拱圣一,余撥隸驍騎右四。”[10]4610可見,隨著宋遼對峙,有更多的渤海人叛降到宋,脫離遼的統治。
因此,雖然名載于史料的投入中原的渤海人只有三次,但實際通過宋遼戰爭期間,暗投和臨陣倒戈宋軍的渤海人要遠勝萬余,從雍熙年間,田重進一戰便俘獲渤海兵三千,及宋廷常置禁軍“歸明渤海”,甚至在元豐元年(1078)還擴大其建制可見,其入宋人數雖難統計,但絕非小數。所以,在渤海亡國后,移民中原的渤海人遠比從文獻中看到的要多,隨著這些渤海人與中原人的通婚,他們很快融入漢人隊伍之中,成為最早的一批漢化渤海人。
三、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早在渤海與日本進行互聘和貿易時,就有大批的渤海商人和轄境內政治上不如意者懷著不同的目的投奔歸附日本列島,如高庭氏家族還在日本享有較高的殊遇。在渤海亡國后,盡管直接投奔日本或中原的途徑較為困難,但是通過高麗和遼境輾轉二次遷徙或通過戰俘的形式流入兩地的渤海人并不少見,且流入宋境的渤海人動輒可以千計,還設立了成建制的部隊,足見其人數之眾。這些二次移民來到日本和宋境的渤海人很快便融入到當地民族之中,為當地的發展貢獻了力量,尤其是流入到日本列島的渤海人,不僅為日本帶去了大量的生產力資源,還帶去了大量的生產技術,至今在日本還保留了許多渤海人的印記。渤海人雖然已經湮滅在了歷史長河之中,但其“海東盛國”的文明依然在東亞歷史中璀璨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