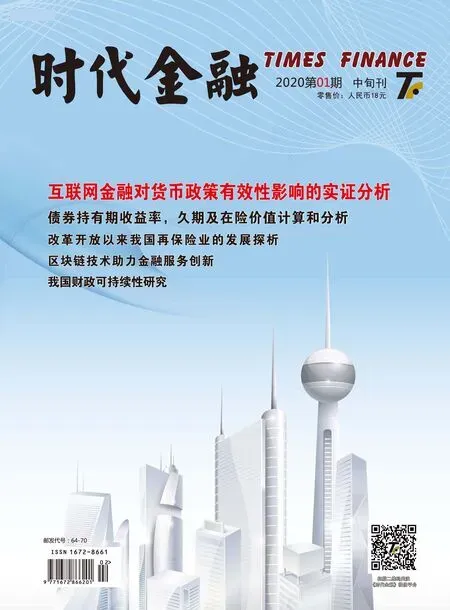文化與公司治理研究綜述
周倩文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亞太經合組織在《公司治理原則》對公司治理的定義如下:“公司治理明確規定了公司的各個參與者的責任和權利分布,諸如董事會、經理層、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并清楚說明了決策公司事務時所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序。”文化是對正式制度和傳統、習俗等等非正式制度的概括,如何精確捕捉文化這一隱形宏觀因素對公司微觀主體的治理有什么樣的影響,似乎困難不小,因為準確量化文化和要控制的變量有很多。那讓我們來看看歷史上的學術人是如何展開這一研究的吧,也許會給未來的研究帶來些許啟示。
盡管每個國家公司治理方式各具特色,但是都有一個相同的公司治理概念。那么這是不是說明存在可能將好的公司治理制度推廣到全球各個國家。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下有不同的公司治理,分析文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對制度改革有啟示,由于特定公司治理的行程離不開一定的文化淵源,在某種文化背景下是好的公司治理在另一種文化下不一定是好的公司治理,因為難以有效和該文化兼容,國與國之間的公司治理的差別是有哪些關鍵文化因素造成的呢?或許我們應該首先關注下有沒有研究支持文化到底會不會對公司治理產生影響,目前有兩篇文獻對此觀點不一。Stulz&Willamson在Culture,Openess,Finance,2001中選取宗教和語言作為文化的代理變量,控制了法律起源以后,發現:宗教在解釋債權人權利保護的國別差異上要比國際貿易、語言、法律起源這些變量的力度強。信仰天主教的國家對債權人的保護沒其他國家好。文化對股東權利的保護幾乎沒影響,對債權人的保護影響很顯著。總的來說,文化和投資者權利保護相關。而最新的一篇文章,Gantenbein&Volonte,2012年Does Culture affect Corporate Governance,以瑞士為研究背景,提出在同一法律和制度下,瑞士法國和瑞士德國的公司治理的是否不同。瑞士公司可以主要分布在兩大文化區域,一個是瑞士說德語的區域,另一個是說法語的區域,瑞士聯邦法對兩個區域同樣適用,因此這為研究除了法律因素,僅考慮文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結論是瑞士法國董事會中說法語的人更多,瑞士德國董事中說德語的人更多。瑞士法國和德國的董事會分別受到附近國家的影響。瑞士法國對股票的轉移限制更為常見。除了這些區別外,幾乎沒什么影響。但是這篇文章研究對象是上市公司,所以看似不大符合我們直覺判斷的結果癥結可能在于此。同時,需要更多的文獻研究來支持我們的直覺判斷。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隨著國際企業的增長,國際企業對在多文化背景下急需知道如何有效管理公司,Hofstede在1980年發表的Culture’s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給了人們很大的啟示,跨文化的管理研究也隨著鋪開。Hofstede在該文章中對文化的結果框架的搭建引發了以該文章為中心的綜述、引用、復制和范式四大類文章。這些文章分別歸納、引申和證實Hofstede的文化結果框架,推動了對跨國文化和管理的研究。值得提出的是,在這些后續文章中,Schwartz在其1999年的A theory of Cultural Values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Work中指出Hofstede的1980的文章作為當時最綜合的一篇研究缺少來自世界重要地區的數據,該文就在這些當時研究不足的地方進行了改進,提出了三個雙極七種價值類型的文化維度:一極是嵌入對智力自治和情感自治,一機是層級對平等,一機是掌控對融洽。
為了探究對公司治理影響關鍵的文化因子,來自Israel的Amir N.Licht,Chanan Glodschmidt,Shalom H.Schwartz出于對LLSV僅僅通過法律淵源的不同來解釋公司治理差異懷疑,作者認為法律的不同更多的是文化的差別,于是在2001年Culture,Law,and Finance:Cultural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aws開始分析國家文化和投資者法律權利之間的關系,指出LLSV按法律法系對國家的分類有失偏頗,無法對公司治理差異給出一個較為精細的解釋。文章的研究發現表示對以前認為英美法系對債權人的保護以及廣義投資者保護更好這一結論有懷疑。同時也發現投票權和債權人的權利與文化維度相關,但補救權利與文化維度不相關。這篇文章對系統研究法律和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有一定的啟示。繼2001年的這篇文章,這三位作者在2005年的Culture,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提出了一個分析法律是如何體現文化這一問題的新的框架。其理論基礎是Schwartz和Hofstede文化維度和LLSV的反應投資者保護的兩個指數ATD(anti-director rights index)和CRD以及LLSV對國家法律法系的劃分:英美法系、大陸法系(進一步分為為法國、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法律)和剩余的法系。首先分別計算Schwartz、Hofstede文化維度和ATD、ATD-vote和CRD之間的相關系數,發現投資者保護程度與和諧、避免不確定性負相關,與個人主義正相關,與權力距離負相關。接著為了檢驗相關系數是否是無誤,即這兩個文化維度作為社會經濟因素的代理變量,不一定全面,因此加入法律規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和宗教(新教徒),分別將ATD、ATD-vote和CRD對和諧、法律規則、人均GDP、新教徒進行回歸,發現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后,和諧可以穩定預測反應公司治理的三個指標。文章列出了每個國家屬于Schwartz和Hofstede文化維度劃分出的文化區域的哪一種和法律法系如何,發現雖然同屬一個文化區域的國家法律法系可能不同,但是通過Goodman-Kruskal lambdma統計量LB 說明,知道一個國家的文化區域可以預測它的法系,盡管這個預測方法很不完美。
在2007年的Culture Rules:The founda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Other Norms of Governance中首先利用兩個經典劃分文化維度的方法作為分解文化的理論基礎,并且用三個基本的治理規則來概括治理:法律規則、腐敗和民主責任,先考察了基本治理維度和Schwartz和Hofstede文化維度的相關系數,接著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將公司治理的三個基本治理規則回歸到Schwartz提出的文化維度和其他影響因素,發現以下結論:(1)法律規則和非腐敗得分越高的國家情感自治、智力自治以及均等程度越高,嵌入和等級程度越低,民主規則與文化之間也表現出相似甚至更高的聯系。(2)加入控制變量英國遺跡、基尼系數、新教徒主義,民族細分、英美法系后,文化嵌入(-)或自治(+)對公司治理的預測依然顯著;等級(-)或均等(+)對法律規則和非腐敗的預測系數下降,對民主責任的預測系數幾乎沒變。新教徒主義與法律規則和非腐敗(+),英國遺跡與英美法系高度重合,在預測法律規則和非腐敗方面,英國遺跡可以涵蓋了英美法系的預測力,在預測民主責任方面,兩者預測力均不高。民族細分的系數不顯著,但是不表明其不重要,民族可以增加人們的族內團結,與Schwartz中的嵌入維度一致,自我主義較低。其中的一個文化維度:嵌入和自治對治理的影響最顯著。最后,考察Schwartz劃分的幾大文化區域分別在治理的三個維度上的得分差異,發現可以劃分為兩大文化區域,一個是English-speaking和West European nations,另一個是 Africa,Far East,Latin America和 Western Europe.文章的貢獻在于利用了來自心理學的跨文化框架和相關數據建立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分析文化對治理的影響。文章的結論對如何進行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啟示,例如在有些國家中將那些受某些文化維度影響大的制度移植到對立文化維度的國家中,會導致惡性循環。
綜上不難發現這三篇文章的可圈可點的地方。其進步之處,借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框架和數據來分析文化中影響公式治理的重要因素,對如何進行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啟示,有些受文化影響大的制度移植到對立文化的背景中,則制度的效率和自我革新會受到很大的阻滯。也提供了一個可以量化分析的一個實證框架。還需改進的方面:S和H的文化框架是否能涵蓋所有的文化或者主要的文化有待商榷,數據的時效性可能不足,新的制度和法律體系反過來也會影響文化,交互影響的過程會使得人們的某些觀念和習慣發生改變。同時,這種交互影響使得在分析公司治理和文化的關系時,很難將文化和制度難以隔開。
A lexW.H.Chan etal.2008年發表Common Cultural Relationship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cross Developed and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的貢獻在于,不同以往對公司治理的定義,通過考慮文化與公司治理利益主體的某些特征的關系來說明影響公司治理好壞的關鍵因子。文中使用Hofstede的PDI,MAS,IDV和UAI四個文化維度來解釋公司治理得分的差異。按公司治理的利益相關人分成9個單個公司治理因素。文章進一步使用了多回歸分析方法將構成公司治理得分的單個公司治理因素得分和總體的公司治理得分分別對四個文化維度和股票市場歷史進行回歸以求發現股票市場歷史和文化維度之間的交互影響是否可以解釋公司治理行為。研究發現股票市場歷史和公司治理得分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文化因素的加入機會涵蓋了股票市場對公司治理行為的解釋預測力。使用向后消除方法,得到只有PDI和UAI這兩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發現在此模型中,PDI和UAI這兩個維度可以解釋公司治理得分的42%。
Buck&Shahrim在2005年的The transl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cross national cultures,the case of Germany,以US風格的ESO(執行董事股票期權)移入德國為例,運用了移植理論和演員網絡理論來分析在一個特定國家文化背景下進行改革后的影響,提出命題:規則性的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在改革過程中方向會被不斷糾正,使得和先前內在的文化價值觀兼容。接著提出四個假設:H1:在德國實行執行董事期權預期相比較在美國和英國實行會更加均等化。H2:德國的執行董事期權計劃下這一期權計劃占公司募集資金的比例相對美國和英國較小。H3:德國的執行董事受到集體控制的影響,權力較低,因此相比較美國和英國,執行董事股票期權計劃相同報酬需要更多的業績是可以被預測的。H4:緊接著H3,相比較美國和英國,德國的業績指標要求業績數量更加嚴格。德國對美國風格的執行董事股票期權的接受,文化背景的不兼容下這一公司治理改革的兼容好像說明了文化與治理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但是存在一些問題,如移植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使我們無法得出肯定結論。總的來說,國家文化和根植于國家文化中的國家制度解釋了當面臨潛在變化挑戰內在商業文化時,公司治理制度表現出慣性、可轉化性和彈性。個人認為這篇文章的局限性在于文章沒有談到US風格的ESO主要受到哪些文化維度的影響,如果這樣的文化維度在德國和美國相似,就難以說明文化對公司治理影響很小。
以上的詳細回顧和點評的文獻基本上是在解決文化是否影響公司治理,影響公司治理的主要文化因素有哪些,文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又有多大。個人對該話題的研究展望是針對不同的經濟環境、文化背景下,可以分析不同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優缺點分別受到哪些文化特征的影響較大,對是否可以將好的公司治理移植到他國,有更加直接的指導意義。同時,可以考慮在一個國家下,從微觀層面分析,比如公司管理層和投資者的文化維度是如何影響公司治理行為的,這樣更有利于思考如何通過制定與文化相關的制度,來更好協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