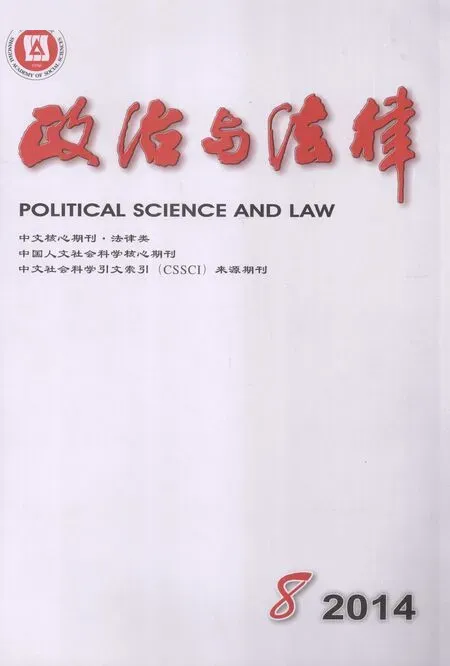裁量基準在行政訴訟中的客觀化功能*
熊樟林
(東南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1189)
裁量基準在行政訴訟中的客觀化功能*
熊樟林
(東南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1189)
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除了越權與程序正義的形式審查之外,亦有走向實質審查的整體要求。實質審查觸及的是行政裁量本身,其始終具有恣意與多變的秉性,因而無論是基于對司法裁量權的擔憂,還是對法官本身的有限智識的懷疑,其都需要一種更為確定的客觀化標準。這一需求在形式審查中能夠通過形式性規范獲致滿足,在實質審查中卻存在政治與技術上的阻隔,因為其往往涉及權力的僭越以及訴訟標的的本質差異。現階段能夠適當緩解這一困境的公法技術是來自于行政機關自身制定的裁量基準。作為一種具有正當性基礎的行政自制規范,裁量基準能夠為實質審查提供直接的、文本式的參照論據,使司法實質審查的客觀化任務獲得質的突破。
裁量基準;行政訴訟;實質審查;客觀化
在我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①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具體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判決維持;(二)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1.主要證據不足的;2.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3.違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職權的;5.濫用職權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四)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可以將行政行為司法審查劃分為形式審查和實質審查兩種類型。②英美法國家一般分為違憲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程序審查(procedural review)以及實質審查(substantive review)三種形式。See Keith Werhan,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Thomson West,2008,pp.308-309.形式審查所要解決的主要是權力僭越的不合法(illegality)問題以及行政程序的失當(procedural impropriety),實質審查的任務則在于巧妙地衡量(delicately balance)訴訟標的的恰當與否。多數學者認為,基于法院需要對行政自治(administrative autonomy)加以尊重,要盡可能地避免用法院的“主觀判斷”取代行政機關的“主觀判斷”。③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心》,《政大法律評論》1999年第62期。因而在行政行為司法審查中最難拿捏妥當的,當屬實質審查。④See Keith Werhan,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Thomson West,2008,p.309.其中的困難,甚至于可以與阻礙違憲審查的“反多數困境”(countermajoritariandiffulty)相提并論。⑤SeeMatthew D.Adler,JudicialRestraintin theAdministrativeState:Beyond the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14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759 (1997);See also Jeffrey Jowell,Of Vires and Vacuums:The Constitutional Context of Judicial Review,August Public Law 448(1999),p.449.法院在實質審查中,往往需要保持類似走鋼絲(walk a tightrope)一樣的謹慎程度。⑥See Keith Werhan,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Thomson West,2008,p.309.實質審查非但是理論研究的中心議題,同時也是橫亙在行政法官面前的棘手之事。⑦有研究者指出,77.2%的受訪法官認為“法律法規不健全,標準不好掌握”是行政審判難的原因。參見林莉紅、宋國濤:《中國行政審判法官的知與行——〈行政訴訟法〉實施狀況調查報告·法官卷》,《行政法學研究》2013年第2期。
本文寫作目的在于從裁量基準在行政訴訟中所能提供的客觀化功能的視角,為上述實質審查的不確定性提供化解思路。筆者認為,無論是大陸法系較為邏輯的比例原則,還是英美法系較為經驗的合理性原則,法官在實質審查中都需要從訴訟技術上借鑒更為客觀化的標準。從現階段來看,裁量基準是一種能夠滿足該需求的新型控權技術。它能夠以簡單、書面的方式,為實質審查提供來自行政機關自身的執法經驗和專業智識,而與此同時,它本身也并不存在正當性瑕疵。
一、行政裁量實質審查的客觀化要求
行政裁量是“行政法的核心問題”。⑧H.W.R.Wade&C.F.Frosyth,Administrativ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35.我們一方面需要警惕其危險性或危害性,另一方面又需要“于法律中授予行政機關一定的活動與決定余地,以滿足個案正義與衡平性的要求”。⑨李建良:《論行政裁量之縮減》,載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編輯委員會:《當代公法新論》(中冊),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0頁注2。因此,立法者的任務并不是要去反對或拒絕行政裁量的廣泛存在,⑩相反,現代統治要求盡可能多且盡可能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參見[英]威廉·韋德:《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而是要剔除那些不必要的裁量。①周佑勇:《行政裁量的治理》,《法學研究》2007年第2期;楊建順:《行政裁量的運作及其監督》,《法學研究》2004年第1期。在邏輯關系上,這是決定行政裁量實質審查之所以會搖擺不定的根源所在。而與此同時,立法者對行政裁量的廣泛承認,會很自然地順延到法院,或者說要求法院也秉承同樣的立場。因此,法院對行政裁量的橫向監督也會在總體上呈現出消極主義姿態。正如學者所言:“盡管在對如何才能最好地執行授權法(enabling act)的理解上,法院的作用至關重要,但其卻永遠是處于從屬(secondary)地位的。”②Keith Werhan,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Thomson West,2008,p.312.因而,在行政行為司法審查中,我們便需盡量避免或者克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從而使司法權僅圍繞在是非問題上或左或右,而不是由法官直接代為履行行政機關的職責(it cannot resolve the matter on its own)。③參見前注①,周佑勇文。
從可行性以及世界各國行政訴訟的發展經驗來看,要使法院對行政機關保持一定程度的尊重(deference),最好的方式,或者說在整體上所表現出來的理念,應該就是為法官提供一系列具有客觀屬性的標準,抑或是“法院自己應努力去尋找客觀化的審查標準”。④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無論是公民基于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擔憂,還是法官本身的有限智識,這種對寓于客觀標準中的確定性奢求始終存在。只不過,它在形式審查和實質審查中所能實現的程度,一直以來都是有所差異的。
(一)形式審查中客觀化標準的達成
在形式審查中,滿足法院對客觀標準的需求的方式,直接涉及行政行為本質上的合法與否問題,因而在界限劃分上便較為簡單,它往往能夠直接從立法機關那里獲致解決,這表現為以下兩種情形。
其一,實體層面的形式不合法。實體層面的形式不合法等同于我國理論界時常提及的行政越權,其是指“行政主體超越其法定行政職權(權限和權能)的違法具體行政行為”。⑤朱新力:《論行政超越職權》,《法學研究》1996第2期。在類型上,其所對應的是管轄權上的事實要件不符、法律要件不符和形式越權。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2項中規定的“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超越職權”便屬于此類情形。與域外尤其是英國的越權行為的寬泛外延有所不同,“就漢語理解和我國行政法理論而言,‘越權’是一個范圍狹窄的概念”,⑥楊偉東:《越權原則在英國的命運》,《政法論壇》2000年第3期;有關英國越權原則的介紹,可參見何海波:《“越權無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嗎?——英國學界一場未息的爭論》,《中外法學》2005年第4期。“行政越權是一種十分嚴重的違法”,⑦同前注⑤,朱新力文。因而法院對形式不合法的判斷并不會出現較大爭議,因為“形式合法性審查是一個確定性的是非評價過程”。⑧同前注①,周佑勇文。無論是對行政機關本身還是對法官而言,他們在行政過程中對形式合法性的遵循,都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客觀化的指引。在源頭上,此類指引一般來源于授權法中的明示條款。這些條款對行政機關而言具有組織法上的意義,但對法官而言,卻具有限制其自由裁量權的客觀化功能。在內容上,它們大多集中于有關執法主體資格的賦予、事務管轄權、地域管轄權以及層級管轄權之間的劃分等方面。而且很明顯,諸如此類內容是不可能在量上發生程度問題的。它們要么是“有或是”,要么是“無或非”,這是質的問題,較少存在斟酌的余地。
其二,程序層面的形式不合法。在確定性上更為表面的另外一種司法審查技術,是被英美國家所青睞的行政正當程序。此時,法院僅需從形式正義上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存有程序瑕疵。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在行政裁量的劃分上,亦有可能會出現程序層面上的選擇裁量問題(程序的裁量),⑨[日]鹽野宏:《行政法總論》,楊建順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頁。但從更為實際的角度來說,這并不會帶來過多的技術難題。“由于司法審查本身就是通過程序來實現的,司法正義也是通過程序來保障實現,法官身臨其境,諳熟程序規則,所以能夠很容易地把法院的這套原則和技術經過適當的修改之后運用到行政機關身上,在程序性審查上也得心用手、收放自如。”⑩參見前注④,余凌云書,第19頁。并且,更為重要的是,程序性審查只是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公正地作出,其并不涉及對行政行為實質內容的評價,不會對行政行為造成實質性的妨礙,不會對分權原則構成威脅。①See Jeffrey Jowell,Of Vires and Vacuums:The Constitutional Context of Judicial Review,August Public Law 448(1999), pp.451-452.因此,“相較于實體性內容的判斷需要專門技術性探討,對法院來說往往是沉重的負擔而言,關于是否采取了正規程序的問題,由法院來判斷則是比較容易的事情”。②楊建順:《論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在大多數情形下,各國的行政程序法本身便是一種客觀化標準。
(二)實質審查中客觀化標準的缺失
法官在上述形式審查中所獲得的確定性依據,在實質審查中卻蕩然無存。立法機關關于規范實質審查的立法是如此的空洞無核,以致于蓋爾霍恩(Ernest Gellhorn)和羅賓遜(Glen O.Robinson)兩位先賢竟諷刺說,其好比“無籽葡萄”(seedless grape)一般。③“The rules governing judicial review have no more substance at the core than a seedless grape”.Ernest Gellhorn&Glen O. Robinson,Perspectives in Administrative Law,75 Columbia Law Review 771(1975),pp.780-781。在總體上,造成實質審查客觀標準缺失的原因在于,此時的訴訟標的已經不是一個確定性事務。寬泛的授權立法將它裝扮成一個裁量空間,“打包”給了行政機關。行政機關從立法機關那里獲得了可以決定擇取何種法律效果的形成權。不過,盡管如此,權力異化的格言卻無處不在。人們并不相信立法機關的贈予就天然具有向善的稟賦,它依然需要接受來自法官的適法性評價。而很顯然,問題便自然轉嫁給了法院。是戒懼還是尊重?法院往往左右為難,④譬如,美國法上有關謝弗林尊重案例的長期討論,就一個典型例證,相關討論可參見鄧栗:《美國行政解釋的司法審查標準》,《行政法學研究》2013年第1期。其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將所有的判斷轉化成一種具有確定性的客觀化標準。
現在看來,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兩大法系之間,業已形成的作為實質審查客觀化標準的司法技術大約有兩種,它們分別是英美法系的合理性審查原則(the priciple of reasonableness)和大陸法系的比例原則(Grundsatz der Verhaltnismassigkeit)。⑤總體來說,合理性和比例原則是現今兩大法系最為典型的兩類實體性審查標準。參見蔣紅珍:《論比例原則——政府規制工具選擇的司法評價》,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頁。對法院而言,這兩項原則的共同特點是,一方面,它們都能夠給實質審查提供框架性的約束,將法院的角色限定在審查而不是替代行政機關作出決策;⑥See Jeffrey Jowell,Of Vires and Vacuums:The Constitutional Context of Judicial Review,August Public Law 448(1999), pp.451-452.另一方面,它們亦通過自身所包含的諸如“不相關考慮”、“目的不適當”、“顯失公正”、“三階段”等具體內容,⑦一般而言,比例原則包括妥當性(Geeignetheit)、必要性(Erforderlichkeit)、法益相稱性(proportionality in the strict sense)三個“層次秩序”(Rangordnung)。同時,合理性原則也包括相關考慮(relevance of considerations)、目的的適當性(propriety of purposes)等。為法院提供更為具體的審查步驟和參考標準,以減少法院在實質審查中的自由裁量空間,避免權力僭越。
不可否認的是,通過這兩項原則及其所包含的涵義,確實讓法官在實質審查中有章可循。也正因如此,在某種程度上將它們說成是實質審查的客觀化標準也并不為過,并且,歐洲法院和歐洲人權法院晚近亦試圖將此兩項原則加以整合,從而提供更為簡捷的判斷方法。⑧參見余凌云:《英國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則》,《比較法研究》2011年第6期。不過,如果據此便斷定實質審查的客觀化任務已經完成,可能依然是武斷的。無論是“吊詭、復雜、難于把握”的合理性原則,還是更進一步客觀化的比例原則,⑨“現有研究已經承認,比例原則比起普通法的合理性原則,仍然客觀性、操作性要強些。”余凌云:《論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法學家》2002年第2期。實際上法院處理裁量問題最終所能憑借的依然是其主觀思維。一方面,由于格林(Lord Greene)和迪普洛克(Lord Diplock)兩位勛爵在Wednesbury和CCSU案中所給出的不夠精確的“不合理”公式,給人們留下了多義的解算,很難鎖定或界定出客觀標準,⑩參見前注⑧,余凌云文。造成了“法官愿意在彼此之間跳躍,避難就易,青睞并轉向那些相對客觀的標準”,①Peter Cane,An introduction to Administrative Law,Clarendon Press,1996,p.210.轉引自前注⑧,余凌云文。限于篇幅,有關案例具體介紹,請參見參見羅明通、林惠瑜:《英國行政法上合理原則之應用與裁量之控制》,羅明通1995年自版,第35-53頁。使得合理性審查變成了一個敷衍了事的(perfunctory)原則;②Ernest Gellhorn&Ronald M.Levin,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另一方面,域外反對比例原則的聲音也認為其只是一種虛置,不能起到所謂“帝王條款”的功用,它存有抽象性缺陷和消極性缺陷。法院通過一系列案例發展了比例原則的諸多內涵,而這可能導致比例原則對法安定性或可預測性的侵害。③參見陳淳文:《比例原則》,載我國臺灣地區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14-115頁。
可見,與形式審查有所不同的是,客觀化任務在實質審查中并沒有被很好地完成,現階段它只是有所邁進而已,司法機關依然面臨著“如何盡可能找出相對客觀的審查標準,盡量避免需要用法院的主觀判斷來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以在兩者之間真正形成一種良好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的權力關系”。④同前注①,周佑勇文。“無論是大陸法系中的比例原則,還是英美法系中的合理性原則,都面臨著審查標準的進一步客觀化問題”,⑤同前注③,蔡宗珍文。同時,“無論是比例原則之中的三階段論,還是合理性原則之中包含的理性精神,還是學者們對二者之間所展開的比較,他們最終追求的都是實質審查的可確定性(identifiable)與可確認性(ascertainable)”。⑥同前注④,余凌云書,第65頁。亦可參見李洪雷:《中國行政訴訟制度發展的新路向》,《行政法學研究》2013年第1期。
二、裁量基準:一種具體化的行政裁量
如上,觸及行政權內核的實質審查,由于需要在行政自治與司法控制之間尋求平衡,其客觀化任務注定無法從法院自身的角度得到滿足。這是因為,它既需要法院充分了解行政內容,也需要獲得憲制層面的正當性,然而很明顯,這是兩項無法同時完成的任務。一方面,法院并不具備行政機關所擅長的專業性資質(institutional competence),⑦See Jeffrey Jowell,Of Vires and Vacuums:The Constitutional Context of Judicial Review,August Public Law 448(1999), p.454.亦可參見Timothy Wu:《行政告誡》,熊樟林譯,《行政法學研究》2012年第4期。另一方面,行政機關本來就享有來自授權法的頗有“自由”色彩的行政裁量權,即使是采取作繭自縛的方式,其也不可能會將自身受制于人,而法院當然也不可能自此獲得憲政上的資質(constitutional competence)。⑧See Jeffrey Jowell,Of Vires and Vacuums:The Constitutional Context of Judicial Review,August Public Law 448(1999), p.454。因此,剩下的也是唯一能夠找到答案的追問,便是行政機關究竟會不會作繭自縛?倘若行政機關自愿為組織法所授予的行政裁量,量身打造一套包括從法律要件到法律效果的客觀化標準,那么,困惑于實質審查中的法院又何樂而不為呢?
恰巧的是,無論是為了標榜人文關懷,還是為了肯定政務,⑨參見熊樟林:《裁量基準的控權邏輯》,載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328頁。也無論是將其解讀為規則主義,⑩參見王錫鋅:《自由裁量權基準:技術創新還是誤用》,《法學研究》2008年第5期。還是行政自制,①崔卓蘭、劉福元:《論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內部控制》,《中國法學》2009年第4期。亦可參見姜明安:《論行政裁量的自我規制》,《行政法學研究》2012年第1期。當下催生于執法實踐中的一種被稱為裁量基準的新型控權技術,正好因應了上述角色。它從起初的萌芽,到最后的茁壯,所吸取的養分大部分都來自于基層公務人員的執法經驗。從形態上來看,裁量基準就是一種具體化的行政裁量,其往往會采用一種直接的、書面的方式,將行政機關的裁量過程予以公布。在邏輯關系上,其等同于行政裁量的具體化或形象化,“是確定如何行使裁量權的行政規則”。②周佑勇:《裁量基準的正當性問題研究》,《中國法學》2007年第6期。一般而言,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予以具體化所采用的技術,會順延授權法中包含的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結構而分為兩種形式,③授權法可以被分為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兩個部分。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6條規定:“旅館業的工作人員對住宿的旅客不按規定登記姓名、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的,或者明知住宿的旅客將危險物質帶入旅館,不予制止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該條文前半段“旅館業……不予制止的”為法律要件,而“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則為法律效果。按照德國法上的理解,行政裁量僅存在于法律效果部分。不過,本文并未做此類區分,全文所指稱的行政裁量具有寬泛的含義。而這大體上便是法院在實質審查中將會遭遇到的問題。其一是法律要件中的行政解釋。對于實質審查而言,法律要件中常常出現的問題是其往往存在過多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盡管這些概念在傳統上應由法院最后定奪,但事實上,它們并不是純粹的法律問題,往往還會涉及科學上的證明與界定,而這同樣是一種法院無法企及的資質(competence),譬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6條中規定的“危險物質”由法院加以判定就不合適。實踐中,裁量基準對法律要件中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確定的方式是行政解釋,或者說是“情節的細化”。④周佑勇:《依法行政與裁量權治理》,《法學論壇》2011年第2期。“對法律規定中充斥的不確定法律概念(undefined legal concept,unbestinm te Rechtsbegriff)進行解釋,是裁量基準制度的一個重要任務。”⑤余凌云:《游走在規范與僵化之間——對金華行政裁量基準實踐的思考》,《清華法學》2008年第3期。譬如,針對上述第56條,浙江省金華市在其《旅館業工作人員違反有關規定違法行為處罰裁量基準》(試行)中便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旅客為一人次的,屬于“情節特別輕微”,可依法不予處罰:(1)不按規定登記住宿旅客信息、不制止住宿旅客帶入危險物質的,但積極配合調查并表示悔改的……”一般而言,上述裁量基準所解釋的內容具有一定的經驗性與技術性,其會結合危害公共秩序的臨界點,區分何種行為應當被涵攝至上位法規定的法律效果之中。當然,需要承認的是,基準所解釋的法律概念也不可避免地會摻雜行政機關的價值判斷,甚至一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偏好。其二是法律效果中的格次劃分。在多數情況下,裁量基準介入法律效果的方式,是被學者稱之為“格次劃分”的設定技術,⑥周佑勇、錢卿:《裁量基準在中國的本土實踐——浙江金華行政處罰裁量基準調查研究》,《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或者說是“效果的格化”。⑦同前注④,周佑勇文。所謂格次劃分,就是指行政機關在上位法授權范圍內(譬如200元至500元的罰款區間),為了更好地實現執法公平與正義,根據過罰相當等原則并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執法范圍等情況,將上述裁量空間細化為若干裁量格次。每個格次規定一定的量罰標準,并根據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和悔過程度,處以相對固定的處罰種類和量罰幅度。在我國,由于現階段的裁量基準僅限于行政處罰領域,因而“格次劃分”最為主要的對象便是罰款數額。譬如,針對上述第56條授權的裁罰空間,浙江省玉環縣便在《違反旅館業治安管理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試行)》第3條中規定:“旅館業的工作人員對住宿的旅客不按規定登記姓名、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的,根據情形分別作如下處理:(1)初次不按規定登記姓名、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的,處二百元罰款;(2)第二次不按規定登記姓名、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的,處三百元罰款;(3)三次以上不按規定登記姓名、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的,處五百元罰款。”很明顯,這一文本就是承載行政裁量的具體形式,其終極目的就在于對原本屬于行政機關自由空間的法律效果予以規則化處理,其在本質上是一種行政裁量。
可見,裁量基準就是一種具體化的行政裁量,其通過對構成要件的行政解釋以及對法律效果的格次劃分,往往能夠將行政機關在裁量過程中所考慮的相關目的、所融入的價值判斷以及所摻雜的專業技術等等這些實質審查所需考量的各項因素,以文本形式公布于眾,進而呈現出客觀化的裁量形態。因此,裁量基準本身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的,而這也決定了其必將會在實質審查的客觀化任務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三、裁量基準客觀化功能之基礎
在整體上,主導裁量基準客觀化功能能夠實現的基礎,大致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一)裁量基準是一種行政規范
盡管現階段對裁量基準的控權邏輯依然存有自律與他律之間的爭議,⑧參見前注⑨,熊樟林文,載同前注⑨,姜明安主編書,第328-330頁。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裁量基準首先是一種行政規范。“在法律屬性上,裁量基準有的屬于規章,但更多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解釋性規則……裁量基準的制定,本質上就是行政立法權的行使,是行政機關對立法意圖、立法目標的進一步解釋和闡明”,因此,其“在制定本質上就是次級立法”。⑨同前注⑩,王錫鋅文。確定裁量基準是行政規范的意義在于,這可以保證法官在實質審查中對基準的援引不會存在“反多數困境”的問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ulty)。因為依據行政機關自己作出的基準對其裁量行為予以制衡,能夠保證監督權力的來源是行政權自身,而非其他,這可以避免易生事端的權力凌駕或權力交叉現象。
同時,更為準確地說,裁量基準還應當是行政規范范疇之中的行政規則,而非法規命令。嚴格而言,德日行政法中的行政命令根據其是否具有授權規范,可以被分為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兩種類別。其中,行政規則有眾多表現形式,而裁量基準只是其一種類型。⑩參見[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93-595頁;[日]鹽野宏:《行政法》,楊建順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8頁。但無論如何,較之于法規命令而言,行政規則的最大特征“是不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并非典型的‘行政立法權’的展現”。①黃舒凡:《行政命令》,臺北三民書局2011年版,第46頁。“其可能僅僅只具有指導作用,原則上對當事人并無法律約束力,行政機關也可以隨時改變其內容。”②William Funk,A Primer on Nonlegislative Rules,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2001,53,p.1322。這一在制度定位上的進一步闡發,是為了說明裁量基準本身“作為一種內部行政措施,不設定公民權利義務……不直接影響公民,對法院裁判國家和公民關系也沒有什么法律意義”。③同前注⑩,哈特穆特·毛雷爾書,第597頁。換言之,在一般情況下,基準所涉及的是裁量行為的妥當與否,而不是合法與非法的問題,其一般只在授權法的內部結構中加以演繹。如果它超出授權法所設定的兩個端點,那么它本身便是非法的,而這便不會涉及其在實質審查中的意義。此種效力范圍的相對保守性,能夠保證裁量基準的制度目標與法院的實質審查目標不會發生沖突。簡而言之,裁量基準的主題是合理性,法院實質審查的主題也是合理性,因而它們是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的,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將基準作為實質審查的客觀標準,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二)裁量基準是一種行政自制規范
豐富上述可能性的第二個理由,是裁量基準異于傳統控權模式的內在邏輯。我們通過對基準的觀察發現,在規則主義之外,“基準所追求的是一種‘行政自治’風格的裁量控制體系”,④同前注⑥,周佑勇、錢卿文。它和傳統行政法蘊含的制定法色彩有所出入。裁量基準的制定初衷只是為裁量權的正當行使提供一種具體化的約束標準,而不構成立法規則或者法律規范。正因如此,筆者在既往研究中反復指出,裁量基準的控權邏輯并不僅僅只有規則主義面向,其同時還有行政自制的內容。⑤參見前注⑨,熊樟林文,載同前注⑨,姜明安主編書,第330-334頁。筆者認為,在行政規范基礎之上,裁量基準應當定位為一種行政自制規范,或者說是一種自制型的行政規范,其具體是指對法定授權范圍內的裁量權予以情節的細化和效果的格化而事先以規則的形式設定的一種具體化的判斷選擇標準,其目的在于對裁量權的正當行使形成一種法定自我約束。作為行政自制規范的裁量基準,一方面可以解決實質審查的客觀化標準無法從其他國家權力中得到提供,而只能依靠行政機關自我約束的悖論;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實質審查的客觀化標準提供了來自行政機關的、出于自律初衷的經驗性結論。很顯然,這無疑可以使實質審查的客觀化任務得到質的突破。
同時,由于作為行政自制規范的裁量基準,“強調的是對裁量權的一種主動、內發的‘自我約束’,而非機械式的‘自我壓制’,也不是一種來自于外部力量的‘被迫’”,寓于裁量基準中的“自我約束”,“主要通過一種‘自我調控’式的‘建構’功能來實現,是一種積極、能動的自我建構”。⑥周佑勇:《裁量基準的制度定位——以行政自制為視角》,《法學家》2011年第4期。因而,此種唯有裁量基準才具有的屬性優勢,可保證其在向實質審查提供客觀化標準的同時,也能恰當地調和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的關系。在邏輯上,這是因為,此時實質審查所依據的裁量基準具有自我約束的品質,其一方面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將裁量過程所涉及的各項因素盡顯無遺,從而為司法監督提供應有的論據;另一方面也可以為自己設定司法規范的最低限度,從而避免“裁量權零收縮”(Ermessensreduzierung auf Null)現象的出現。⑦劉宗德:《行政裁量之司法審查》,載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臺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44頁。因此,如果說規則主義為裁量基準作為客觀化標準提供了可能性基礎,那么作為行政自制規范的裁量基準,便在這一基礎之上添加了更具操作性的現實性基礎。
(三)裁量基準是一種具有正當性基礎的行政自制規范
更為重要的是,裁量基準還是一種具有正當性基礎的行政自制規范。裁量基準盡管在控權邏輯上對自我約束有所側重,但這并不阻礙其獲得規范層面的合法性以及功能層面的有效性身份。這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在合法性上,與德國和美國有所不同,⑧聯邦德國基本法第80條規定:“聯邦政府、聯邦部長或州政府可經法律授權頒布行政法規。”美國憲法第1條第1項規定:“憲法所授予的立法權,均屬于參議院與眾議院所組成的美國國會。”我國并不存在否定行政立法權的憲法條文。《立法法》第8條所設定的法律保留條款,往往只能被認為是規定了裁量基準權力來源的合法性邊界。與此同時,縱使從比較法上的經驗來看,德國“法律保留”原則的晚近發展,也并沒有完全封殺授權立法,而是另外創設了“授權明確性原則”以規定行政命令如何獲得合法性;類似地,美國的禁止授權原則也遭遇了被放棄或另立的命運,歷經變更后所確立的“新的禁止授權原則”逐漸認可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因此,裁量基準在規范層面的合法性爭議實際上已經塵埃落定。⑨參見周佑勇、熊樟林:《對裁量基準的正當性質疑與理論回應》,《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4期。其二,更為重要的是,在有效性上,通過當下行政自制理論的證明,我們同樣可以確證自我約束并不單單只是依靠道德力量實現權力監督,其自身亦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行政自制者認為,自制的實現機能可以從社會學、倫理學、文化學等多重角度獲得認可,其義務來源并不僅僅只是道德層面的。行政自我拘束盡管拒絕司法權的保障,但其本身并未因此而喪失民主精神,也不會出現行政專制,而這當然可以順延至作為行政自制典型實踐形式的裁量基準。因此,盡管是自我拘束,基準在功能主義立場上的有效性獲得也并不存在障礙。⑩囿于篇幅,有關裁量基準正當性基礎的詳細探討,請參見前注⑨,周佑勇、熊樟林文。
對實質審查而言,確認裁量基準是一種具有正當性基礎的行政自制規范的重要意義在于,其能夠保證法院將裁量基準作為客觀化標準,并不會打亂既有的憲制結構中的權力分立格局以及寓于其中的相互制衡的監督體系。有所區別的是,在實質審查中借鑒裁量基準,并不等于說是司法權的妥協,也并不等于說是行政權的專斷。如上所述,裁量基準是具有正當性基礎的,它既具有規范層面的合法性基礎,從而能夠保證法院參照的并不是憲制結構之外的行政專制,亦具有功能主義層面的有效性基礎,從而能夠保證法院所參照的不是一張紙上談兵的政策指南,而是充滿經驗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行政過程的裁量具體化文本。簡而言之,合法性保證了法院對基準的借鑒不會滑向司法無能,有效性則保證了其不會滑向行政專制。因此,如果說規則主義為裁量基準作為客觀化標準提供了可能性基礎、行政自制為裁量基準作為客觀性標準提供了現實性基礎,那么,正當性則為法院參考裁量基準提供了憲制層面的正當性基礎。
四、裁量基準客觀化功能之內容
延續前述論證,接下來的問題是:裁量基準究竟能夠為法院實質審查提供哪些客觀化標準?此即裁量基準客觀化功能的具體內容。對此,筆者擬從法院和理論研究在實質審查中習慣行走的三條路徑,逐一加以展開。它們分別是:其一,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真實目的的限定;其二,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相關考慮因素的列舉;其三,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顯失公正的權衡。①一般而言,實質審查的主要內容就是“不符合法定目的”、“不相關考慮”、“顯失公正”等方面。參見楊偉東:《行政行為司法審查強度研究——行政審判權縱向范圍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3頁。
(一)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真實目的的限定
“遵守授予裁量權法律規范的授權范圍或目的乃是行政機關裁量時應負的義務,如有違背即構成裁量瑕疵而為違法裁量。”②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臺北三民書局2000年版,第317頁。在實質審查中,首當其沖的也是最具有主觀色彩的內容,便是對行政裁量目的的比對。法院在這一過程中不但要確定授權法的原始目的,還要確定行政機關的行為目的,而目的本身是裁量范疇之內的因素,且探求行政決定者的內心意思在舉證上也極為困難,③同前注⑦,劉宗德書,第139頁。因而法院往往會舉棋不定。實踐中,裁量基準限定行政裁量真實目的方式有以下兩種。
其一,在基本文本中對較為宏觀的目的直接予以明確。譬如,《河南省商務行政處罰裁量標準適用規則》第1條規定:“為規范行政處罰裁量權的行使,促進行政處罰行為公平、公正,提高行政執法水平……制定本規則。”又如,《重慶市公安機關治安管理行政處罰裁量基準》第1條規定:“為規范行政處罰行為,保證行政處罰裁量權的正確行使,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制定本裁量基準”。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此類涉及目的的裁量基準并不具有很高的客觀化程度,甚至于說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授權法目的的重復,④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條規定:“為了規范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但有所不同的是,這是出自于行政機關自己的理解,換句話說,這是一種自我限定。這意味著,當我們對某項行政行為的目的存有爭議時,這一敘述宏觀目的的條款便會派上用場。譬如說,由于我國《行政處罰法》第1條對行政處罰權的目的規定,既設定了行政管理,又設定了權利保護,因而當某一行為在這兩者之間難以定奪時,法院便可參照上述條款,將其僅僅限定在權利保護之上。可見,此類基準文本并非毫無用處。
其二,以差異化的法律效果間接表達具體行為目的。相較而言,裁量基準對某項行政行為具體目的的限定,往往需要從法律效果中加以倒推。但是,這一倒推并不意味著它是任意的,因為在基準所設定的法律效果之間往往存有一定的差異,并且這種差異的格局也非常豐富,它一般至少具有三個層次,并配有相應應受行政處罰行為的表現形態,而且它們之間是相互限定的,彼此也具有互為參照的功能。例如,《河南省商務行政處罰裁量標準(試行)》第3規定:“輕微違規行為”所對應的是“進行拍賣公告,但未在指定媒體發布的”,其法律效果是“予以警告,責令改正,記錄違法行為”;“一般違規行為”所對應的是“進行拍賣公告,但未按照《拍賣法》及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日期進行公告的”,其法律效果是“責令改正,延期拍賣或處以5000元以下罰款”;“嚴重違規行為”所對應的是“未進行拍賣公告的”,法律效果是“責令改正,延期拍賣或處以5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依據這一文本,行政機關在選擇某一法律效果時所要達成的目的便非常具體,其要么是為了將拍賣行為“在指定媒體上發表”,要么是為了“要求其進行拍賣公告”等等,而這和上位法的目的是否切合,是一目了然的。
當然,獲知行政行為的具體目的,并不等同于說就一定要否決它。由于行政機關設定裁量基準享有自由形成空間,法院對裁量基準所設定和考量的要素原則上也應予以一定程度尊重(take care to abstain)。⑤See Lord Irvine of Lairg,Judges and decision maker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dnesbury review,Public Law,1996, Spring,p.69.因此,筆者認為,盡管行政機關已經以裁量基準形式事先將其具體行為目的予以了限定,但司法實踐中以目的背離認定之場合,實際上可能也并不多見。在應用上,它可能會更多地結合其他因素予以綜合評價。
(二)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相關考慮因素的列舉
在考量因素上,行政機關往往有三種選擇:什么是必須(must)要考慮的,什么是不必(must not)考慮的,什么是可能(may)要考慮的。⑥See Lord Irvine of Lairg,Judges and decision maker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dnesbury review,Public Law,1996, Spring,p.69.這非但是實質審查中的另外一項主觀內容,也是法院審查相關考慮的主要任務。一般而言,在基準文本中特別是在針對法律效果所制定的格次條款中,都能直接找到每一格次劃分所對應的考量內容,行政機關在格次條款的前半段也都會對此予以提及,這本身也是裁量基準的最大特色。例如,浙江省玉環縣《違反旅館業治安管理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試行)》第3條中的三個格次劃分,相對應的就是“初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不按規定登記姓名、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的行為列舉;又如,《金華市公安機關關于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和處罰裁量基準》對擾亂單位秩序的情節較重情形,也做了六種形態的列舉,且每一種形態所考慮的法益都是有所差別的。因此,在整體上,相較于上述對目的比對而言,查找行政裁量是否存在不相關考慮,是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的。從筆者觀察的結果來看,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相關考慮的限定,主要是在具體的行政處罰方式和程度的選擇上(即量罰)。在裁量基準文本中,涉及較多的是何種行為應該或可以被免予處罰以及何種行為應該或可以從重、加重、從輕、減輕處罰。一般而言,其限定手段主要是例舉各種必須或可以考慮的情形,從而為司法審查提供客觀性的參考。比如說,《金華市公安機關關于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和處罰裁量基準》規定的“主動糾正,社會影響較小的”較輕情節以及“強拿硬要學生財物的”的較重情節。一般而言,這些都是決定行政處罰輕重緩急的相關考慮因素。
(三)裁量基準對行政裁量顯失公正的權衡
應當說,現在大部分裁量基準的基本主題就是為了避免行政執法顯失公正。無論是對授權法法律要件中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還是對法律效果的格次劃分,其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提供一套簡單直接的執法標準,使相同的行為得到同等的處理。實踐中,以裁量基準規范“顯失公正”較常采用的方式是“行為加法律后果”模式。每項行為都能與其法律后果一一對應,非但是“行為加法律后果形式”最為簡單的表述,也是行政機關避免出現顯失公正的最佳選擇。譬如,浙江省玉環縣《違反旅館業治安管理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試行)》第3條將200元到500元的裁罰空間細化為“初次”、“第二次”以及“第三次”不按規定登記姓名、身份證件種類和號碼的行為,相對應的法律后果分別為200元、300元、500元罰款。此時,在裁量基準本身是妥當的情況下,其便可以被法院用以權衡行政行為是否顯失公正。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方式本身是有所局限的,因為諸如裁量基準形式的主觀性規范,是不可能窮盡所有客觀行為的。比如,就上述案例而言,倘若第三次不登記罰款400元,第四次不登記罰款500元,或者說第三次和第四次都罰款500元,法院該如何權衡呢?因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裁量基準對顯失公正的權衡并不僅僅體現在“行為加法律后果”條款上。其實,裁量基準所設定的各種法律效果之間的間距,也可以用以權衡行政行為是否有失比例。譬如,上述基準所設定的100元的間距,便可用來決定在何種情形下采用400元的罰款才是最為妥當的選擇。同時,我們也可以從諸如“從輕”、“減輕”等等一些能夠體現“最小副作用”的相關條款中,衡量行政機關是否選擇了對相對人侵害最小的法律效果,從而達到比例原則所要求的“必要性”精神。
五、作為客觀標準的裁量基準在我國行政訴訟中的適用
必須坦言的是,盡管如上所述,裁量基準在實質審查中的客觀化功能有目共睹,但這并不等于說它在我國一定就能夠發揮功效。“當我們反復敘說一個主題應當如何時,事實上這個應當一般是無法實現的。”⑦“婚姻應該是不可離異的,但我們也只是說‘應該’而已。”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90頁。現階段,有兩方面原因使得我們難以直接將裁量基準作為裁判依據。其一,裁量基準在我國不具有憲政資質(constitutional competence)。我國憲制結構的基本特色是以代議機關為中心的。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只有它們才享有立法權,諸如裁量基準之類的行政立法則不具有此類身份,它們不能被納入法源的序列之中。其二,訴訟法上具有排斥條款。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其第53條也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布的規章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發布的規章……”由于裁量基準既不屬于“依據“范疇,也不屬于“參照”范疇,在我國行政訴訟中對其予以援引,嚴格而言是不具備合法性的,至少在規范層面確實如此。
然而,筆者通過對基層法院15則案例的考察發現,⑧這些案例的名稱或案號分別為:云南省文山縣人民法院作出的周某案(案號不詳,以下簡稱“周某案”,參見陳娟:《駕駛機動車超速,究竟罰多少:云南省公安廳紅頭文件引爭議》,《人民日報》2008年4月2日第15版)。(2011)沈中行終字第174號、(2011)沈中行終字第139號、(2010)廈行終字第9號、(2010)嘉行初字第25號、(2006)一中行終字第668號、(2010)穗中法行終字第584號、(2011)寧行終字第101號、(2000)海中法行初字第11號、(2009)吉行初字第22號、(2010)南行終字第29號、(2011)蘇行初字第7號、(2002)佛中法行終字第49號、(2009)浙甬行終字第116號、(2010)洪行終字第10號。法院實際上并未對上述條文抱殘守缺,裁量基準在實質審查中的客觀化功能,已經通過援引方式進入到裁判文書之中。在15則案例裁判文書的說理部分,直接提及基準并將其作為裁判依據的有8則,⑨案號分別為:(2010)洪行終字第10號、(2011)寧行終字第101號、(2010)廈行終字第9號、(2009)浙甬行終字第116號、(2006)一中行終字第668號、(2000)海中法行初字第11號、周某案、(2011)沈中行終字第174號。占據整個分析對象的一半以上。在援引方式上,盡管此8則案例都是與上位法一起引用的,但實際上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存有單獨援引裁量基準的情形。⑩例如,(2010)遂行初字第6號、(2009)原行初字第28號、(2009)原行初字第22號等案例。筆者認為,這不只是基層法院的一種嘗試,更是裁量基準本身的客觀化功能的彰顯。根據這一數據,完全可以斷定,學界之前所做的“法院可能在符合法律適用規則(如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前提下,直接援引裁量基準進行裁判”的預測,①參見朱新力、唐明良:《尊重與戒懼之間——行政裁量基準在司法審查中的地位》,載《北大法律評論》編輯委員會編:《北大法律評論》(第10卷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已經在基層司法過程中獲得突破。可見,在我國,立法文本與司法實踐之間存在根本性的背離,法院在實質審查中對客觀化標準的奢求,已經并不為靜止的法條所束縛,它實際上已經走在了整個制度的前沿,甚至于從某種程度來說,已經超越了現行制度。
當然,仍然需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盡管筆者在前文中已經確證,裁量基準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憲政資質的(constitutional competence),但作為行政自制規范的裁量基準,畢竟也飽含自制成分,其仍然難以徹底擺脫行政專制的可能,特別是在行政命令日漸增多的現代社會。因此,當我們需要將裁量基準作為審查依據時,可能仍然需要將其與立法機關的立法區分開來。筆者認為,這種區分應當建立在將基準作為“論據”而不是“依據”之上。②參見何海波:《實質法治:尋求行政判決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236頁。此時,基準更像是一種證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和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法律規范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中對其他規范性文件要求予以“參考”的方式十分類似,③參見唐映紅:《裁量基準法律效力之思考》,《時代法學》2011年第5期。也和《若干解釋》第62條第2款規定的“引用”甚是相像。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2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第二,需要予以特別評價的是,同樣是由于裁量基準具有規則主義和行政自制的雙重屬性,難以徹底擺脫行政專制的可能。因而,嚴格來說,我們是不可以在行政訴訟判決文書中單獨援引裁量基準文本的,這與裁量基準的控權邏輯存有沖突。在大多數情況下,裁量基準應當只能單獨作為行政主體的自白,而不能成為司法過程中審查依據的主力軍。⑤在類似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7年發布的《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第14條規定:“司法解釋與有關法律規定一并作為人民法院判決或裁定的依據時,應當在司法文書中援引。援引司法解釋作為判決或者裁定的依據,應當先引用適用的法律條款,再引用適用的司法解釋條款。”這是因為,此時單獨援引的基準文本盡管只是作為“論據”身份出現的,但在沒有任何其他“依據”的情況下,它往往就會被認為是一種“依據”,而很顯然,這和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2條和第53條的規定有所違背。因而,前引三則單獨援引基準文本的判決,其本身并不妥當,實踐中應該謹慎使用這種援引方式。
六、結 語
“眾所周知,行政裁量作為斟酌、評判、選擇的代名詞,其與行使裁量者的主觀意志活動密不可分”,行政裁量的這一意志性特征提示我們,“意欲實現對行政裁量權的控制,就必須將潛藏在行為人內心的主觀考慮,以可以接受審查的、客觀化的途徑加以展現”。⑥鄭春燕:《論“行政裁量理由明顯不當”標準——走出行政裁量主觀性審查的困境》,《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如果審查標準以及亞標準都盡可能地客觀化(就像現在英國、德國以及歐盟的做法),再加上專家出庭作證制度,不具有廣博行政經驗與知識的法官未必就不能勝任相關的審判工作。⑦參見前注④,余凌云書,第82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在1997年的奧爾訴羅賓斯案(Auer v.Robbins)中曾如此說道:“在某些情形下,法院選擇不同的行政解釋,可能與國會意圖或憲法原則存有關聯。不過,其最終準則卻是行政解釋,行政解釋往往是至關重要的。”⑧Auer v.Robbins,519 U.S.452,461(1997).同時,皮爾斯(Richard J.Pierce)近期在《行政法學評論》(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上所發表的一篇長文中更是指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檔案經常包括一些法官并不嫻熟的、結論相互沖突的科學研究成果,這造成法官完全沒有信心處理此類事件。⑨See Richard J.Pierce,What do the Studies of Judical Review of Agency Actions Mean?,63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77 (2011),p.92.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裁量基準一方面可以提高對行政裁量的控制密度,另一方面,除了賦予人民參與裁量基準制定過程的機會之外,并得以依照裁量基準針對具體的行政行為進行行政內部的審查”,也可以“作為審查裁量決定的具體標準”。⑩[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現代行政過程論》,有斐閣2002年版,第341頁。轉引自王志強:《論裁量基準的司法審查》,我國臺灣地區東吳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第41頁。這種客觀化標準功能的實現,非但享有功能主義層面的有效性支持,亦有規范主義層面的合法性支撐。因此,法官將裁量基準作為一種參照或一種論據,非但是行政訴訟從形式審查走向實質審查的理性選擇,亦是行政裁量實質審查客觀化要求的應有之意。
(責任編輯:姚 魏)
D F3
A
1005-9512(2014)08-0063-13
熊樟林,東南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本文受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行政處罰上的有責性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4Y JC820060)和200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行政裁量基準制度研究”(項目編號:08BFX 020)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