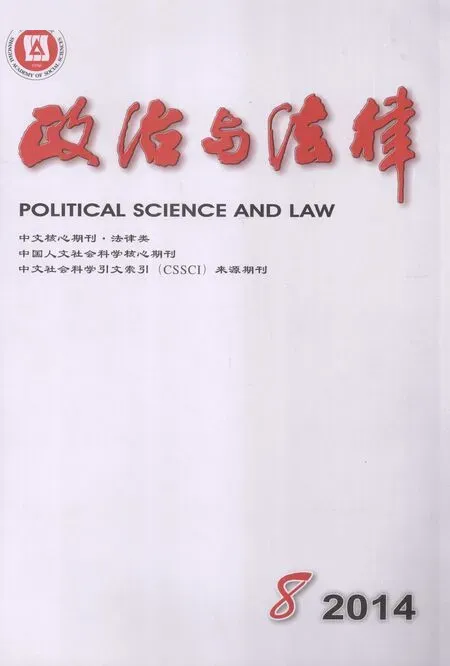論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石油開采設施環境污染的管轄權*
賀 贊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論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石油開采設施環境污染的管轄權*
賀贊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廣東廣州510006)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公約雖然對專屬經濟區內船舶污染的管轄權有規定,但對石油開采設施造成的污染則規定不明。石油開采設施具有特殊的性質,不能套用船舶污染管轄權的規定。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的管轄權宜采取“以沿海國為中心”的規則設計。固定式鉆井平臺和開采(固定)狀態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及鉆探船符合“設施”定義,應由沿海國享有專屬管轄權;航行狀態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及鉆探船應由登記國(船旗國)與沿海國并行管轄。這樣,能恰當平衡登記國航行自由與沿海國環境保護利益;將管轄權有效分配給最有監管動力的沿海國,亦能有效保證污染防治的效果,符合管轄權的聯系和效率原理。
海洋環境污染;石油開采設施;專屬經濟區;管轄權;海洋法公約
石油開采活動中的海洋環境污染問題正日益嚴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雖然對專屬經濟區內船舶污染規定了“登記國(船旗國)、港口國和沿海國相結合”的管轄原則,①高健軍:《中國與國際海洋法》,海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頁。但受其制定時代的限制,其對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則規定不明。傳統海洋大國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在國內立法中將“移動式鉆井平臺”視為“船舶”,極大限制了沿海國對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的管轄權,無法滿足海洋污染防治的需要。“深水地平線”事故的發生暴露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石油開采設施具有特殊的性質,不能適用船舶污染管轄權的規定。石油開采設施污染領域的管轄權問題本質上是石油開采設施登記國與沿海國之間利益的平衡問題。需要對石油開采設施的環境污染管轄權規則的設計問題進行反思。鑒于“預先防范原則”在海洋環境保護領域的重要性,本文將重點探討主權國家在石油開采設施污染領域的立法和執法管轄權。
一、現有海洋環境污染管轄權制度無法滿足海洋環境保護的新訴求
(一)現有國際公約對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規定不明
著名國際法學家奧本海曾指出:“國際法決定國家可以采取各種形式的管轄權的可允許限度,而國內法則規定國家在事實上行使它的管轄權的范圍和方式。”②[英]奧本海著,[英]詹寧斯·瓦茨等修訂:《奧本海國際法》,王鐵崖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頁。國家管轄權主要涉及每一個國家對行為和事件后果加以調整的權利的范圍。在國際領域,每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都享有平等的立法權,并且可以自主地決定其立法的范疇和方式,但行使這種自主權不能侵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其他國家的利益。由于《公約》簽訂時海洋石油開采并未廣泛運用,③Hossein Esmaeili,The Legal Regime of Offshore Oil Rigs in International Law.Ashgate/Dartmouth(2001),p.1.《公約》及直接規制海洋環境污染的公約中均無對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的明確規定。因此,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問題解決的是:國際法在專屬經濟區內石油開采設施的污染問題上對國家與國家之間利益的劃分。具體而言,其涉及的是對于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內發生的石油開采設施污染行為,沿海國是否有權制定法律規章來限制他國石油開采設施的活動,從而防止他國的石油開采設施對本國專屬經濟區的環境產生污染,以及是否有權執行等問題。
(二)適用船舶污染管轄權規則的障礙
《公約》中缺乏對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的明確規定,但對于船舶污染問題則確立了船旗國、沿海國和港口國并行管轄制度,并將沿海國對船舶污染的管轄權擴大到了專屬經濟區。④張湘蘭:《論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船舶污染的立法管轄權》,《當代法學》2013年第3期。《公約》打破了“船舶污染由船旗國獨自管轄”的傳統原則,肯定了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船舶污染的管轄權。《公約》第217條規定:“各國應制定法律和規章,以防止、減少和控制懸掛其旗幟或在其國內登記的船只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據此,沿海國可對其專屬經濟區制定法律和規章,以防止、減少和控制來自船只的污染,但這種法律和規章應符合一般其已接受的國際規則和標準。然而,《公約》仍未動搖船旗國的管轄權在某種程度上優先于沿海國管轄權的地位。⑤同前注①,高健軍書,第154頁。這具體表現在:船旗國對于懸掛其旗幟的船舶的違章行為,“不論違反行為在何處發生,也不論這種違反行為所造成的污染在何處發生或發現”,均應“設法立即進行調查,并在適當情形下對被指控的違反行為提起司法程序”。如果船旗國在任何其他國家就其船只在領海外的違章行為提起司法程序之日起六個月內就同樣控告提出加以處罰的司法程序,則其他國家應即暫停進行司法程序,除非該違章行為使沿海國遭受重大損害,或有關船旗國一再不顧其對本國船只的違章行為有效地執行國際規則和標準的義務。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17條(1)、(4)和第228條(1)。這表明,《公約》在船舶污染的管轄權問題上仍然堅持以船旗國為中心。那么,能否將海洋石油開采設施定位為法律意義上的“船舶”,進而適用有關國際公約中對專屬經濟區內船舶污染管轄權的規定呢?
1.國際公約的定義和分類不一
石油開采設施主要分為鉆探船、移動式鉆井平臺、固定式鉆井平臺等幾類。《公約》對“船舶”和“海洋石油開采設施”并未給出明確的定義。而除《公約》之外的幾個直接規制海洋環境污染的公約,為實現不同的公約目的,對石油開采設施的定位也不一致。如MARPOL 73/78(包括其1997年議定書)《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國際海事公約》第4條對“船舶”作了如下定義:不管是固定式鉆井平臺還是移動式鉆井平臺,都屬于本公約的調整范圍。而《國際油污防備、反應和合作公約》第2條第3款規定:“船舶系指在海洋環境中營運的任何類型的船舶,包括水翼船、氣墊船、潛水器和任何類型的浮動航行器。”其第2條第4款規定:“近岸設施系指從事天然氣或石油勘探、開發或生產活動或油的裝卸的任何固定式或浮動裝置。”該公約明確區分“船舶”與“海上鉆井平臺”。因此,僅依據國際公約的定義和分類,無法主張對專屬經濟區內石油開采設施的污染管轄權問題適用船舶的相關規定。
2.物理特征差異導致不宜對石油開采設施適用船舶污染的管轄權規定
雖然鉆探船和鉆井平臺起源于船舶,但是隨著海洋科技的發展,不管是在外觀、屬性以及主要目的上,其與船舶有諸多不同之處。從功能上看,固定式鉆井平臺不具有航行能力,而鉆探船與移動式鉆井平臺的自航能力極為有限,這與作為運輸工具的船舶存在顯著的差異。船舶應該直接用于航海或為航海服務。⑦潘斌、高捷:《試論建立移動式鉆井平臺法律體系的必要性》,《中國海洋平臺》2003年8月號。船舶之主要功用為航行,因此鉆探船、海上鉆井平臺不屬于海商法之船舶。⑧張新平:《海商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頁。從外形上看,無論是固定式鉆井平臺還是移動式鉆井平臺,都不具備船舶的流線型外形。因此,從物理特征考慮,也很難將石油開采設施歸入船舶,進而主張對專屬經濟區內石油開采設施的污染管轄權問題適用船舶的相關規定。
(三)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規則缺失的實際后果
《公約》中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規則的缺失導致締約國行使管轄權無法可依,出現適用上的混亂。從理論角度而言,各國均能采取防止或減少油污損害的預防措施,將導致各締約國管轄權積極沖突的產生;并且《公約》未對行使管轄權的具體方式、范圍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因此,各國采取預防措施標準不一致,將加劇各締約國管轄權積極沖突。從實踐角度而言,由于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規則的缺失,各國國內法多將石油開采設施視為“船舶”,套用船舶污染管轄權規則。而依據現有的船舶污染管轄權規則,登記國與沿海國并行管轄,且登記國管轄處于優先地位。這樣,沿海國無法完全、專屬地行使管轄權,登記國則往往缺乏管轄動力和實際監管能力,無法實際有效地行使管轄權,進而導致實際上的管轄缺位問題。在《公約》簽訂之后的幾十年間,能源短缺問題日益嚴重,現代新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海洋石油開采日漸普遍。石油開采設施覆蓋面積較大,且結構復雜,一旦發生泄露或爆炸事故,搶險難度較大,所帶來的海洋環境污染的嚴重程度遠遠超出了船舶航行溢油。這就迫使各國重視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規則缺失問題。
二、《公約》中沿海國對“設施”享有專屬管轄權的規定無法全面、準確處理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的管轄權問題
盡管《公約》沒有對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的直接規定,但《公約》中關于沿海國專屬經濟區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的規定以及關于“在其管轄下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所造成的海洋環境污染”等規定為明確該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
《公約》第56條第1款規定了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該條該款a項規定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有以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不論為生物或非生物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以及關于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等其他活動的主權權利。該條該款b項規定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有該公約有關條款規定的對下列事項的管轄權:⑴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和使用;⑵海洋科學研究;⑶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根據這一規定,在專屬經濟區中,沿海國對海床和水體中的設施或結構以及海洋環境保護有管轄權,對其中的自然資源有主權權利。⑨王鐵崖:《國際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頁。
《公約》第208條第1款規定:“沿海國應制定法律和規章,以防止、減少和控制來自受其管轄的海底活動或與此種活動有關的對海洋環境的污染以及來自依據第六十和第八十條在其管轄下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對海洋環境的污染。”這一規定明確賦予了沿海國對“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污染管轄權。⑩此外,《公約》中還概括性地規定了沿海國有權控制自然資源勘探和開發設施所造成的污染。例如,第194條第1款規定一國有權采取符合《公約》規定的一切預防、降低和控制海洋環境污染所必要的措施;第194條第3款第c項規定沿海國應當控制源于海床和底土自然資源勘探和開發設施的污染;第208條第5款建議締約方建立預防、減少和控制海洋環境污染的全球性和區域性的規則、標準,并提出相應的實踐和程序。
《公約》第60條對專屬經濟區內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作了具體規定。其一,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應有專屬權利建造并授權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a)人工島嶼;(b)為《公約》第56條所規定的目的和其他經濟目的的設施和結構;(c)可能干擾沿海國在區內行使權利的設施和結構。其二,沿海國對這種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應有專屬管轄權,包括有關海關、財政、衛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規章方面的管轄權。第60條第1款(b)項和(c)項是對“設施”、“結構”的界定。結合第56條來理解,第60條第1款(b)項中的“設施”、“結構”指的是為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不論為生物或非生物資源),以及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等其他活動為目的和其他經濟目的而建造的設施和結構。
那么,石油開采設施是否符合《公約》對“設施”的定義呢?《公約》沒有直接規定海上石油開采設施,也沒有對“船舶”這一概念進行定義。但是,《公約》第1條規定:“傾倒”是指從船只、飛機、平臺或其他人造海上結構故意處置廢物或其他物質的行為。從該定義可以看出,《公約》對船舶、平臺以及其他人造海上結構進行了區分。這一規定至少可以表明,將平臺歸入“船舶”并無充分的法律依據。在石油開采設施中,固定式鉆井平臺符合“以在專屬經濟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而建造的設施”的定義,且符合“固定于海床之上”的物理特征;鉆探船和移動式鉆井平臺在航行狀態下具船舶的航行能力和特點,在開采狀態下具有設施的特征。因此,開采狀態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也可以歸入“設施”概念中。
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關于條約解釋通則的規定:“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并參照條約的目的與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據此,《公約》第208條第1款所規定的沿海國對“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污染管轄權應結合《公約》第56條第1款、第60條等上下文,并參照條約目的與宗旨進行解釋。《公約》第56條第1款、第60條規定沿海國對“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并授權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有專屬權利,并對這種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應有專屬管轄權,包括有關海關、財政、衛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規章方面的管轄權。其中對“專屬管轄權”的界定采取了列舉方式,并采用了“包括”這一措辭。因此,有充分理由認為此處的“專屬管轄權”也包括了有關海洋環境保護方面的管轄權。《公約》第208條第1款所規定的沿海國對“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污染管轄權是專屬性的。
綜上所述,從《公約》的現有條款可以推導出,固定式鉆井平臺和處于固定(開采)狀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符合“設施或結構”的特征,應適用《公約》中關于“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污染管轄權的規定,由沿海國享有專屬管轄權。而對于處于航行狀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宜將其歸入“船舶”定義中,此時則無法主張沿海國對污染的專屬管轄權,①Hossein Esmaeili,The Legal Regime of Offshore Oil Rigs in International Law.Ashgate/Dartmouth(2001),p.88.而仍應適用《公約》中關于專屬經濟區船舶污染管轄權的規定。
三、以聯系密切程度和實際有效程度作為海洋環境污染的管轄依據
(一)符合與國家的聯系密切程度原則
根據國際法上的管轄權理論,一國對某一事項的管轄權源于該國與該事項的聯系。行使管轄權的權利決定于在有關問題與行使管轄權的國家之間有相當密切的聯系,從而使該國有理由對該問題加以規定,而且也許有理由超越其他國家的競爭性的權利。②同前注②,奧本海書,第328頁。在傳統國際法中,各國行使管轄權一般是依據屬地原則和屬人原則(也就是依據領土和國籍)來行使管轄權。這是國家主權最高性特征所決定的,即國家對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以及領土外的本國人享有屬地優越權和屬人優越權。③楊澤偉:《主權論——國際法上的主權問題及其發展趨勢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對石油開采設施的法律定位,在考慮物理特征的基礎上,還應考察這一聯系是否緊密。
依據移動式平臺和鉆井船分階段的特征,規定其航行狀態下視之為船舶,當為勘探開發海底資源而接觸大陸架的海床時,其由“船舶”轉為“設施”的做法,能夠恰當體現沿海國與登記國聯系的實際狀況。依據《公約》的規定,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對自然資源享有排他性管轄權,對在該區域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有主權權利,未經沿海國同意,非沿海國不得進行開發和勘探。石油開采設施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活動在于海洋石油勘探開發,其活動直接影響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可能造成的海洋環境污染最直接最嚴重的受害者是沿海國。基于沿海國對專屬經濟區內自然資源的專屬性管轄權,它與沿海國的聯系更為密切。因此,由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的固定鉆井平臺以及處于開采狀態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行使專屬管轄權,符合管轄的聯系緊密度要求。
《公約》同時規定,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行使權利和履行其義務時,應適當顧及其他國家的權利和義務,并應以符合《公約》規定的方式行使。《公約》第59條規定,在專屬經濟區內,所有國家,不論為沿海國或內陸國,在《公約》有關規定的限制下,享有航行和飛越自由。分階段區分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的做法認可了處于航行狀態的石油開采設施的航行自由。由登記國對處于航行狀態的石油開采設施行使一定管轄權,而沿海國仍然有有限管轄權,吃水線以上的活動屬于石油開采設施的船旗國(登記國),沿海國對吃水線以下生物和非生物資源擁有主權權利。石油開采設施處于航行狀態的時間較短,在航行狀態下對沿海國海洋環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也較小。因此,航行狀態的石油開采設施與沿海國的實際聯系并不密切。這一做法符合了“航行狀態下的石油開采設施與沿海國聯系相對較遠,與登記國的航行利益聯系較密切”的客觀狀況,較好地平衡了登記國與沿海國利益。
(二)符合管轄權的效率原理
國際法需要決定國家可以采取的各種形式的管轄權的可允許限度。各國國家利益的沖突實際上造成了國際法上很多管轄權問題的模糊,同樣也使管轄權各項原則難以結合成為一個整體。但是,國際社會畢竟有著某種共同的需要,每個國家都需要相對穩定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不同國家之間會有不同程度的共同利益,各個國家都希望在國際社會中實現某種秩序和某種程度上的國家間的利益平衡。④姜琪:《簡論國際法上的管轄權制度》,《當代法學》2001年第5期。在國家之間相對明確國家行使主權的范圍有著現實的基礎,國際法上也已經形成了能夠為大多數國家認可的管轄權制度。究其原因,為實現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各國在一定程度上有協調各自利益的意愿。國內法往往立足于本國的管轄利益,而國際海洋法領域的公約力圖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各國管轄利益的和諧。國際海洋環境污染管轄權規則如果不以國際社會或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的接受為基礎,那么,該制度就不可能有效。因此,評判一項國際海洋環境污染管轄權規則是否是一項真正的法律,取決于該制度是否為實現共同利益而契合了各國的意愿。
1.避免實際管轄缺位問題
如上所述,《公約》對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缺乏明確規定。實踐中,各國國內法多將石油開采設施統一視為“船舶”,這容易發生管轄權缺位問題。發生在美國專屬經濟區墨西哥灣的移動式鉆井平臺“深水地平線”事故的發生即是一個例子。依據美國國內法,移動式鉆井平臺被視為“船舶”。“深水地平線”登記于馬紹爾群島。因此,登記國馬紹爾群島和沿海國美國均對其享有管轄權,且馬紹爾群島的管轄權處于較優地位。通常而言,美國對在本國登記的移動式鉆井享有綜合性的安全和環境監管權,但由于“深水地平線”在美國之外登記,美國無法對其享有勘探開發階段完全的管轄權,進而無法采取全面的、綜合的管理措施以預防海洋環境污染的發生。
目前大多數國家的國內法將移動式鉆井平臺界定為“船舶”。依據現有的《公約》中“以登記國為中心”的船舶污染管轄權規則,登記國享有較充分的管轄權。換言之,移動式鉆井平臺的監管嚴重依賴于登記國。然而,各國附近海域情況各異,往往是沿海國更為熟悉本國專屬經濟區的海床和水體情況,沿海國往往更有能力制定和執行科學、有效的防止污染規則;此外,污染事故的直接受害者是沿海國,其更有制定和實施防止污染規則的動力。“深水地平線”事故的實際情況是:作為登記國,馬紹爾群島政府承擔制定并確保海上開采實施的質量、安全標準實施的主要義務。但是,該鉆井的實際作業地點是在美國專屬經濟區內,美國承擔主要清污工作。⑤See Press Release,Joint Info.Ctr.,U.S.Dep't of Interior,Update:The Ongoing Administration-Wide Response to the DeepwaterBPOilSpill(May27,2010),availableathttp://www.doi.gov/news/doinews/Update-5-27-2010-The-Ongoing-Administration-Wide-Response-to-the-Deepwater-BP-Oil-Spill.cfm;What's the Story on Oil Spills?正是因為這種管轄權分裂問題,沿海國無法完全、專屬地行使管轄權,缺乏對石油開采設施安全、環境標準以及應急管理措施的嚴格規定,以致該鉆井平臺長期處于專業人員配備不足、安全、環境標準松懈的狀況下。在危機風險發生之時,由于管轄權模糊,應急決策主體不明,延誤了避免危機的最好時機,最終導致“深水地平線”的災難發生。⑥Robbie Brown:In Oil Inquiry,Panel Sees No Single Smoking Gun,N.Y.Times,Aug.28,(2010),at A10.
在石油開采活動中,由于移動式鉆井平臺、鉆探船的登記國與沿海國往往不是同一個國家,而海上石油勘探開發作業的危險性大,一旦發生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尤其對海洋環境造成重大危害,嚴重影響沿海國的漁業開采、能源開發、航運等經濟活動。石油開采設施結構、修復技術較復雜,作業危險性大,可產生特殊的風險和責任。從事鉆探、開采、運輸等作業時,不但會遇到通常的海上風險,還可能遭遇鉆井作業特有的井噴、爆炸等危險,從而對人身財產和環境造成重大威脅。在類似“深水地平線”這樣的事故中,災難性的影響往往蔓延全球海域,并不局限于沿海國本身。因此,相對于船舶對海洋環境的污染,石油開采設施對海洋環境的破壞性更大,對此加以適當的法律應對在更大程度上體現了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各國也更具有為達成共同利益而作出協調的意愿。
固定式鉆井平臺和開采(固定)狀態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及鉆探船符合“設施”定義。由沿海國享有專屬管轄權,將對平臺運營的控制權與清污義務集中于同一主體,能有效降低事故風險,同時還滿足了作業階段對安全監管和應急所需要的管轄權統一性,有利于避免安全事故發生。此外,因直接承受損害,沿海國相對于登記國更有實施嚴格監管的動力。將作業階段的管轄權歸于沿海國,尊重了這一規律,有利于實現防治海洋環境污染的目的。在“深水地平線”事故中,如果《公約》中已經有“以沿海國為中心”的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的規定,那么,開采(固定)狀態下的“深水地平線”將被視為“設施”,美國將有權依據《公約》對鉆井污染享有專屬性管轄權。⑦Rebecca K.Richards:Deepwater Mobile Oil Rig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Coastal State Jurisdic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Law,(2011),387.這一做法能解決管轄權不明和分裂問題,避免類似的災難再度發生。
對處于航行狀態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宜由登記國和沿海國并行管轄,保障其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的航行自由,這樣既能確保沿海國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的移動式鉆井平臺污染的監管權力,有效預防海洋環境污染,又能充分尊重和保證登記國對航行狀態中平臺的管轄利益,避免沿海國的過分主張,較好地平衡沿海國與登記國的利益。
2.避免方便旗的弊端
“以沿海國為中心”的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規則還能避免方便旗問題。方便旗船籍最初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的船舶領域,并在二戰后得到迅速發展,成為國際海運業的一種潮流。方便旗國出于擴大外匯收入的需要,通過降低稅率等運營成本和放松法律經營限制的方式吸引船舶登記。方便旗的盛行給航運秩序造成了許多不利影響。石油開采設施也實行登記制度,因此,類似的不利影響在石油開采設施登記中也會存在。例如,方便旗國缺乏成熟的勞動法律體系,無法為開采設施工作人員提供充分的勞動保障;方便旗國家對石油開采設施技術狀態和工作人員管理方面的監管標準寬松,導致在方便旗國家登記的石油開采設施事故率遠高于其他國家;方便旗國家與石油開采設施之間并無“真實聯系”,這也為石油開采設施所有人的違法經營和海上犯罪行為創造了條件。⑧張湘蘭:《論“船旗國中心主義”在國際海事管轄權中的偏移》,《當代法學》2010年第6期。
“以沿海國為中心”的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管轄權規則,區分固定鉆井平臺和移動式鉆井平臺、鉆探船。對于固定式鉆井平臺,適用《公約》第56條第1款、第60條、第208條第1款關于“人工島嶼、設施、構造”專屬管轄權的規定。據此,固定式鉆井平臺不存在方便旗問題。對于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按照其在法律性質上的分階段性,在開采狀態由沿海國享有專屬管轄權,在航行狀態下由登記國和沿海國并行管轄。由于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的航行時間很短,這一規則設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方便旗帶來的弊端。
(三)符合國際海事立法趨勢
從國際法的效力基礎這一角度考慮,“以沿海國為中心”的石油開采設施管轄權規則以承認國際社會共同價值為基礎,相比現有國際海洋法中“以船旗國為中心”的管轄權規則而言,更能實現保護全球范圍內的海洋環境,減少國際海洋爭端,其實際效力也將更強。
在國際法的效力基礎問題上,實證主義者們堅持認為,“同意”是國際法的絕對條件,他們只承認條約和習慣是國際法確定的淵源。⑨[美]西奧多·A·哥倫比斯、杰姆斯·H·沃爾夫:《權力與正義》,白希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14頁。“國際法的根據,一方面基于各國對它的公認,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各國基于事實上的利害關系而對它的需要。因此,國際法是充分反應各國的共同主張及共同利益的法之規范。去尋求實際需要以外的原因,作為國際法拘束力的根源,毫無意義可言”。⑩吳嘉生:《國際法學原理》,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9頁。實證主義觀點確切反映了國際海洋法領域的法律制度的真實形態:它是各國在決定秩序內容的對抗傾向中的一種妥協。目前大多數海洋法律體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體系內強有力的和有影響的國家或利益集團的重要利益。船舶污染管轄權規則的發展即反映了這一規律。傳統的國際法認為,船舶的管轄權由船旗國專有。傳統的船旗國專屬管轄沒有成功消除船舶污染,也未保護沿海國免受快速增長的海上運輸油類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質所帶來的環境威脅。①See Alan E.Boyle,“Marine Pollution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9 (1985),p.348.直到經歷了1967年“托里坎榮號”事件之后,國際社會才簽訂了首部規定沿海國可以在領海以外的區域對他國船舶造成的油污進行干預的公約,即1969年《國際干預公海油污染事件公約》。然而,在海洋大國的強大壓力之下,《公約》雖然肯定了沿海國對船舶污染的管轄權,但仍未承認其主導地位。
“不容置疑,國際法實際效力一個重要的實踐原因是國家自我利益和需要。然為了確保一個穩定和有秩序國際社會,每一個國家利益要受到國際法原則的約束”。②Martin Dixon,International Law(second edition),Blackstone Press Limited,p.8.國際法“越是更一般地承認共同價值,那么國際社會將越是更為堅強,相反,如果不再承認任何共同價值,那么國際社會必然分崩離析。由于共同的人類天性的結果,總是會承認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③[奧]阿·菲德羅斯:《國際法》,李浩培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9頁。國際立法是一種軟法,缺少立法機構以及超國家制約力,所以依然取決于主權國家的基于主觀效益的同意,也就容易導致公約實際受遵從程度低下的問題。有學者指出:“除非國家之間合作制定更嚴格的船舶污染標準,否則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沿海國采取超越《公約》規定的措施來保護其海洋環境,從而違背《海洋法公約》的主要目的——為世界海洋創設一個穩定的制度。”④See Daniel Bodansky,“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Vessel-Source Pollution:UNCLOS III and Beyond”,Ecology Law Quarterly 18(1991),p.721.近年來,沿海國已經采取與《公約》不符的國內措施以應對特殊的環境、安全和經濟威脅。這些措施包括開辟另外的航線以避免專屬經濟區內的敏感區域、要求攜帶有毒有害貨物的船舶在通過專屬經濟區時必須事先通知、對通過敏感水域的船舶征收“環境費”等。⑤See Alan Khee-Jin Tan,Vessel-Source Marine Pol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69-370.這些持續的國家實踐很有可能發展成未來海洋環境污染管轄權規則的重要淵源。因此,即便是在船舶污染管轄問題上,“船旗國中心主義”也已經出現向“沿海國中心”主義偏移的趨勢。那么,對于石油開采設施而言,事關專屬經濟區內自然資源勘探開發的專屬性權利和管轄權,“沿海國中心主義”的原則更應體現于石油開采設施的國際法律制度中。
四、結 語
石油開采設施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發生后,受影響最嚴重的莫過于沿海國。《公約》及現有國際海事公約在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石油開采設施的污染管轄權方面規定不明,與海洋環境保護的訴求相差甚遠。《公約》已經為建立石油開發的國際法律機制提供了依據,國際社會應積極促成新公約或現有公約執行協定的出臺,以補充和細化現有《公約》中的規定。國際法律規則應在尊重石油開采設施的物理特征的基礎上,明確其法律定位,考量管轄聯系密切程度及管轄權規則的效果,決定沿海國與登記國管轄權的可允許程度。對于固定式鉆井平臺和處于開采(固定)狀態下的移動式鉆井平臺、鉆探船,應適用《公約》第56條第1款、第60條、第208條第1款關于“人工島嶼、設施、構造”專屬管轄權的規定。當移動式鉆井平臺和鉆探船處于航行狀態時,應視之為船舶,當為勘探開發海底資源而接觸大陸架的海床時,其應由“船舶”轉為“設施”。這一做法能夠切實體現沿海國與登記國聯系的實際狀況,明確沿海國對其專屬經濟區處于作業狀態的石油開采設施污染的專屬管轄權,有利于海洋環境保護這一國際社會共同目標的實現,同時又顧及了登記國對航行狀態下的石油開采設施的管轄,較好地平衡了登記國與沿海國的利益。這一規則設計還體現了當今國際海事法立法趨勢。我國目前的石油開采多采用中外合作開發的方式,海洋石油開采設施本身具有國籍,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進行實際作業,中國主張對本國專屬經濟區內石油開采設施的污染管轄權將推動中國實現海洋生態文明和海洋強國戰略。
(責任編輯:聞海)
D 997
A
1005-9512(2014)08-0134-09
賀贊,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青年項目“南海油氣資源合作與開發的制度及實踐”(項目編號:11Y JC820145)和華南師范大學青年培育基金項目“近岸石油開采活動中海洋環境污染的國際法律規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