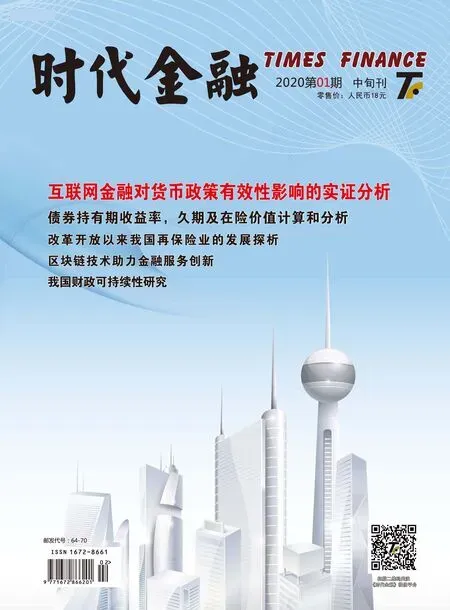論票據惡意抗辯的法律效果
徐 政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63)
一、惡意抗辯的含義
我國《票據法》第13條第1款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法條當中的“除外”,指的是票據債務人在履行票據義務時可以自己與持票人的前手或出票人之間存在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所以惡意抗辯是指票據義務人得對持票人的前手主張對人抗辯的場合,該持票人明知有害于票據義務人而受讓票據時,票據義務人得以對其前手的對人抗辯事由,對該持票人主張抗辯。①
因票據抗辯限制乃是票據法的一項原則,故惡意抗辯是票據法上對人抗辯切斷的例外。對人抗辯切斷的制度具有保護善意持票人的目的,使持票人不因票據本身以外,在受讓票據時無法預見的抗辯事由,阻礙票據權利的行使,以有效的保證票據的流通性。但對于惡意取得者來說,由于其是在受讓票據時已經知道抗辯事由的存在,就喪失了給予其保護的必要,或者說是應該不給予惡意取得者抗辯切斷的利益,制止其對抗辯切斷制度的濫用,否則會因為鼓勵惡意取得而失掉法律上的公平公正。
二、惡意抗辯行使的法律效果
(一)對直接后手的法律效果
一旦票據債務人向持票人主張惡意抗辯,必然會對票據債權人產生一定的影響。以簡單的教學案例來分析,如下圖所示:
A(出票)——B(背書)——C(持票人)
A、B之間為購買貨物的合同,A為出票人,B為第一次背書人,為購買汽車把票據背書轉讓給C,C為持票人。
假設A:按照合同約定的時間了交付票據給B,但B未在合同約定的時間交付貨物或交付的貨物有瑕疵,而B已將票據背書轉讓給C。
假設第一種情況是C在接受票據時,對于A與B存在抗辯事由并不知情,當C向A主張票據權利時,A就不得以其對B的抗辯事由來對抗C,即票據上人的抗辯的切斷。
假設第二種情況,C在接受票據時知道A與B之間存在抗辯事由,此時如果A能證明C的知情,就可對抗C的請求,這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惡意抗辯。
(二)對間接后手的法律效果
在上述案例中,C為支付房租將票據背書轉讓給D,D現為持票人。如下圖所示:
A(出票)——B(背書)——C(背書)——D(持票人)
假設B:轉讓票據給了C時,C是善意的,即C不知道A與 B之間存在抗辯事由,后C又背書轉讓給了D,現在來討論D是善意或惡意情況下,A的抗辯權問題。
第一種情況是D在接受票據時是善意的即不知A與B之間的抗辯事由,毋庸置疑,A對于B的抗辯權肯定不能對抗D,票據法對此有明確的規定。
第二種情況是D在接受票據時是惡意的即已知曉A與B之間的存在抗辯事由,這時如果A能舉證D的知情,A能否對D提出惡意抗辯?也就是說,在票據流通過程中,出現了善意持票人,其以后的持票人是否還可能構成惡意抗辯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學界主要有兩種學說。
1.善意人地位繼承說。這種觀點認為只有在持票人對于票據債務人與其直接前手之間存在抗辯事由知曉的情況下才成立惡意抗辯,而對于間接前手與票據債務人之間的抗辯事由,由于被持票人的直接前手善意的切斷,而不能成立。因為此時的權利已經被洗滌干凈了,干凈的權利是無所謂切斷不切斷的。
2.屬人說。這種觀點認為惡意抗辯帶有強烈的屬人性,它是基于直接當事人之間的人的關系而成立的,而且是對明知會損害債務人仍接受票據的持票人成立的。雖然持票人的前手是善意的,但并不能掩蓋持票人的惡意,應當賦予票據債務人對這樣的持票人以惡意抗辯權。②
3.對以上兩種觀點的分析。第一種觀點的論述是不夠嚴密,從權利本身的屬性看,它是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③是無所謂被污染之說。票據權利根本不存在干凈或污濁的問題,因為根據票據的文義無因性,只要票據債權曾有效成立,即使基于原因關系發生抗辯,票據債權也仍然成立。第二種觀點認為人的抗辯具有屬人性是正確的。因為人的抗辯本來與票據或票據上的權利無關,而是基于票據債務人和持票人的票據外的關系以及持票人取得票據的情形所產生。但惡意抗辯中的屬人性是要有限制的,必須對其進行詳細的分解。
我國《票據法》第13條中的“前手”從制度適用上只能解釋為直接前手,也就是說當持票人明知債務人于其直接前手的前手存有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時,票據債務人不得主張惡意抗辯。
對“前手”做限制性解釋的理由:一是票據流通的基礎品質是信用票據在流通過程中,只有保證其流通的安全性,票據才能真正發揮其信用工具的作用。如果將“前手”做擴張解釋為所有前手,就等于擴張了惡意抗辯權行使的對象。在上例中,如果C為善意的,A不能向C主張惡意抗辯,但當C背書轉讓給D時,D由于知道A與B之間存在抗辯事由,如果惡意抗辯權可對抗所有“惡意”的后手,則D就會拒絕接受這張票據。這樣由于D的知情,使得C因善意取得的人的抗辯切斷的利益就會大打折扣,這張票據無法繼續流通下去,只能由C進行兌現,這顯然阻礙了票據的流通,同時也擴大了票據收受人的注意義務,與票據法的立法目的相悖。
二是根據惡意抗辯構成要件,在認定惡意時,最主要的判斷標準是持票人的行為是否阻卻了票據債務人的抗辯。④在上例中,C因善意已經阻卻了票據債務人A的抗辯,使得構成惡意抗辯的客觀要件已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無論D是否為惡意,A不能主張惡意抗辯。由此可見,惡意抗辯權的屬人性應當限制為直接前手,不能擴大化。
注釋
①趙新華.《票據法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頁。
②董惠江.《票據抗辯制度研究》,http://www.cnki.net/index.htm。
③梁慧星.《民法總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頁。
④虞瑾.《論抗辯制度》,華東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