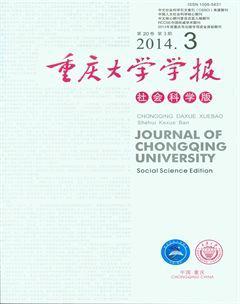中國增長實現邏輯
摘要:區域經濟結構是解密中國增長的邏輯起點,也是尋求公平增長的重要考量,結構與增長的恰合是理解中國高增長奇跡出現的關鍵,而經濟結構扭曲問題的集中爆發則是引導中國進入低增長時代的原因。文章通過對中國特質加以梳理,從中尋求中國區域實踐的特征事實和機理邏輯,強調經濟結構是區域增長的“深層原因”,更進一步明確省市邊界是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研究的適宜空間尺度,要素在區域內和區域間的空間配置是塑形中國梯度發展格局的根源,結構性必須加以強調。其政策含義在于:中國區域經濟應在結構轉變中謀求公平發展。
關鍵詞:區域增長;經濟結構;空間尺度
中圖分類號:F06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14)0300011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國家并于2010年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長期、持續的高速發展被稱為“中國奇跡”,但兩個大局發展構想安排和資源要素在城市和農村的“二元”配置也相應積累了眾多亟待解決的矛盾,實踐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剛性、滯后、地區差序格局固化、二元結構扭曲以及供給與需求失衡等結構性問題,高增長與累積矛盾交錯相連致使區域經濟產生分化,經濟結構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被扭曲,這被一些學者稱之為“結構失衡”[1-2]。合力作用下中國經濟增速漸趨向下調整,從“保八”到7.5%的轉變預言著低增長發展時代的到來。值得注意的是,增長奇跡及增速放緩并不應被看作是簡單的經濟周期現象,而是結構作為“深層因素”引致增長過程和長期積累的經濟結構扭曲問題的集中爆發。為其提供“對癥”的藥方,則需要找到統領全局的結構調整舉措,而這一舉措需從眾多結構失衡之間的關聯入手[3]。區域協調和以人為本的平衡發展是重要的現實問題,若不注重結構與增長的內生邏輯關系將可能制約發展水平的提升[4]。立足現實對中國問題加以審視和研究,增長過程中資源要素在城市和農村的“二元”配置(與要素配置相關)和“兩個大局”發展(既與要素配置相關,更與空間尺度相關)自然地成為揭秘以持續高增長為特征的“中國發展奇跡”的關鍵切入點,需以經濟結構轉變和調整切入闡釋中國區域增長實踐邏輯。
一、在結構轉變中尋求公平發展
新中國60多年是中華民族謀求復興的60多年,在經濟建設層面就表現為對物質文明的追求,而從階段性劃分,可大致將其概括為“前30年”和“后30年”[2]:前30年,以區域平衡甚至平均的發展思路探索計劃經濟體系構建;后3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漸進式改革謀求經濟轉型。但歸根結底是在“效率和公平”這兩大社會發展目標之間權衡,“效率與公平”是糾葛于中國增長過程最為重要的論題,也是區分增長與發展內涵概念的本質,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系,實則體現的是結構與增長的恰合問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非平衡發展選擇在初期解決了階段性發展受阻難題,但時至當下,扭曲的結構積累已使得矛盾凸顯,可持續的題解需要在結構與增長的內生關系中尋求。
強調社會公平,中央政府已將平衡發展納入發展考量,并認為“這些目前已經見到成效” 2013年9月10日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3夏季達沃斯論壇與國際企業界人士交流時稱,中國選擇的策略是突出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市場活力,著力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使之與穩增長結合起來,“這些目前已經見到成效”。,調整經濟結構是其實現途徑。只是在當下,“中國的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中國失衡經濟研究給出了諸多現實證據,諸如投資主導下的消費壓抑、城市與農村的分割與差距、地區的東中西部格局等過度的、扭曲的非平衡表現被認為是“結構失衡”的核心內容得到了關注[2, 5]。中國區域發展的失衡現實是促使我們將研究視角關注于結構的重要誘因,但我們不僅僅關注那些已被稱之為失衡的結構,而是將結構視為引致增長的深層次原因予以在增長解析中加以重視,也更為關注其增長本源性,從結構的轉變中尋求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邏輯:以結構變化尋求高增長的來源,用扭曲的結構現實來解釋放緩的經濟增速。明確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時代的轉換,“增長不等于發展”將有助于對中國經濟的基礎理解,也將有助于失衡問題的深入研究和解決。
我們對結構的強調最為根本的是對公平的追求,“公平之路如何實現”?在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中,因地區偏向和城市偏向的戰略安排導致的要素市場扭曲、城鄉分割、通脹壓力增大和收入分配失衡惡化等經濟結構問題對發展的阻礙和可能的不利引起政府的反思,因而更加重視平衡發展的提法[6]。平均、平等、平衡等概念的內涵逐漸清晰,中國前30年的經濟實踐已證明,想要以“平均”的想法化解區域增長問題,實難如愿,只有在不斷向下分解中理清增長邏輯,才能為“公平”的目標提供理論基礎,保障平等權利的獲得和平衡發展的實現。明確經濟結構增長效應的空間路徑和識別不同地區的結構效應差異是我們的研究主旨所在,并提供區域經濟結構適宜性的評價標準。我們從區域經濟結構解密中國增長實踐邏輯,具有多視角性:從空間看,是主題研究的區域對象邊界和區域內、外的二維度,須納入多層面的經濟內容。從時間看,則強調結構與增長關系的階段性和演化特性,與區域相結合就表現為時空演化過程;增長實現解析更是在理論上提供了供給視角和需求視角的經濟分析框架。基于此,明確了增長主題下的經濟結構概念,認為不同經濟結構可以通過投資、消費和要素流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并影響經濟的空間布局和結構變遷。在經驗實證中強調區域經濟的供給決定性和需求決定性之差異,通過測算和識別經濟結構的增長效應,對經濟結構作用于區域增長的空間路徑和區域異質性給予分析,得知區域“塊塊”平衡增長過程的實現并非孤立的系統,在不損失效率的基礎上實現對公平的帕累托改進是我們對經濟實踐的期望。平衡發展是其目標,結構與增長的協調為其途徑,其中,財政是實現公平的重要手段。
二、區域經濟增長:特征事實與機理解釋
轉型經濟可用于總結中國60年發展歷程,以漸進式改革為路徑的經濟轉型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導向性作用并在探索性實踐中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和適應。農村和城市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提供了區域的增長驅動力,從人口的自由流動到嚴格戶籍制度的形成再到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催生人口流動、二元壁壘出現裂痕,要素的空間分布格局逐漸形成并具有“單向性” 資本和勞動力在宏觀區域間自西向東流動的趨勢早已形成;當然,在近年的人口結構轉變和勞動力工資調整過程中,一些研究者也逐漸開始關注于“回流”問題,要素由城市向農村的延伸得到重視,只是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利弊仍待商榷。。結構變化引致了經濟發展過程,在被動或主動的改革調整中推動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各種問題和矛盾快速顯現,城鄉分割、東中西部差序格局、資本與勞動配置不合理、投資消費失衡、農業發展陷入困境等諸多問題警醒著我們“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一點不比不發展時少” 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0日01版)評論員文章《難走的路是上坡路》。。總體看,人口要素結構變化和土地要素價值重估 1987年4月,土地使用權可有償轉讓,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通過使用年限的方式得以分離,隨后1988年“深圳第一槌”和“土地使用權可依照法律規定轉讓”的憲法修訂案給予了中國土地使用制度根本性變革,這成為土地要素逐漸得以流通的制度基礎。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強調協調發展,結構的適宜性就更為我們所關注,不論是忝列“奇跡”的高增長,還是對未來持續增長的索求,經濟結構成為鏈接中國經濟過去和未來的關鍵。正如陸銘所述,“創造了經濟奇跡的中國人不僅需要知道來時的路,還需要選好未來的路”[7]。結構效應在區域增長中的表現需要得到強調 結構是決定增長的深層次原因,因此也就要求增長需實行結構改革,這是結構主義者從結構分析中得到的重要政策結論。,厘清增長內生邏輯就需要以現實為基礎。
學術問題應從事實而來,那么針對中國區域增長問題,就需要時刻想“世界是什么樣的,對應的中國是什么樣的” 這一認識得益于2012年7月與導師張宗益老師交流過程中,張老師對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刻理解,其關鍵在于拷問“中國是否真的那么特殊”。因為盡管言論都將中國增長喻為奇跡,但投資依賴的增長路徑選擇卻表明中國恰恰是在新古典增長理論指向的道路上前行。那么中國究竟特殊在哪里就需要特別的關注,這也是構建中國式增長理論必要的基礎工作。 ?認識中國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基礎,那么,如何體現中國的特殊性?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必然需要在中國區域增長過程和結構變化中尋求證據支撐。具體的,通過對中國總量經濟和結構變化以及空間分布的描述,中國作為一個經濟主體的一些特征逐漸明晰。
(一)凸顯的階段性
發展過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增長的演化過程需要得到強調,圖1和圖2展示的增長描述無疑為此提供了確鑿證據。從增長速度看,中國發展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區分[2],從大幅波動向高位收斂的過程十分明顯,中國經濟表現出較強的自我適應能力、靈活性和創新性[8],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獨特發展道路,在“效率”追求中實現了高增長軌跡;從地區差異看,增長率的收斂過程亦存在,那么就預示著地區差距的固化或者說絕對指標上的差距擴大過程,后富追趕先富的過程能否達成存在疑問。區域增長加總實現了國家的整體增長,發展戰略選擇、城市化等一系列政策和傾向性選擇伴隨其中,圖1展示的發展描述無疑是對此的概述。值得關注的是,增長率在趨勢上表現出向下調整,政府在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給出了回應,從8%到7.5%,低速增長時代的到來是社會與經濟發展轉型規律所致,中國或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二)強勢政府
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特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仍然存在目標表達的不一致性。中央政府日趨理性,但地方政府從改革開放以來都是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即GDP的攀升,相對中央政府的改變要小得多;地方競爭中的政府短視行為加劇了區域經濟失衡,致使結構矛盾快速積累。中國的層級治理對經濟的影響極大[9],層級制形成的以區域“塊塊”原則為基礎的多層次、多地區的M型組織結構[10],為地方政府“Race to the top”(趨好的競爭)提供了增長的動力源泉[2, 4]。這種影響源于兩方面:中央對地方官員任命的絕對權威和分權體制下的財政約束力。前者實施了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把激勵搞對”[11],中央政府通過掌握地方官員的任免能力提升經濟績效,將政治晉升與地方發展關聯起來從而形成“錦標賽”模式[12-14]和地方保護目的下的經濟割據格局[13, 15-16]。出于合理化集權與分權問題、促進市場建設為目的推行的“分稅制”改革是增長實踐中對政府關系的修正手段,從“財政大包干”管理體制到“財政分權”,通過財政制度安排有效地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重塑了國民經濟分配格局,成為影響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的重要制度變量。當下,分權促進增長的觀點已基本達成共識,但作用機制和路徑的研究還存有分歧 [17],明顯的跨時差異 [18-20]則是需強調的另一關注點。鑒于此,本文在地方分割的假設前提下重點關注財政制度安排下的兩級政府關系,理解中國政治運行模式下的“分塊”經濟增長競爭。
整體上,國家層面的財政收支從平衡向不平衡演化,政府財政壓力逐漸積累。20世紀80年代是財政收支不平衡逐漸凸顯的開始(尤其是1986年之后),財政收支差額的累積擴大成為政府負債的來源 “政府債如何償還”這是在政府治理中需要特別處理的問題之一,但在本文中不再深究 。;從增長速度看,財政收支的增速自1990年之后明顯高于GDP增速,財政在國民經濟收入分配中占比的增加是促進短期高增長的重要力量,但可能加劇結構矛盾而造成更大程度的經濟波動;從收支分配結構看,財政收支比例在兩級政府間的調整過程被稱為“放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的平衡。財政收入和支出在中央和地方間的收支兩條線分配表明,財政壓力正逐漸向地方轉移 當然,隨著中央財政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上升,其宏觀調控能力以及對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均有提升,中央財政支出也逐漸轉向以補助地方為主。。這種收支不平衡性提供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創收”的原始驅動力。以土地為載體,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進一步擴大了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更為關鍵的是,財政結構的轉變伴隨的“事權”下放促進了“地方競爭”進一步加劇,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并競爭中央提供的轉移支付,其手段就是以項目拉投資,而中央政府則通過對地方的財政支持調節區域發展戰略;區域經濟在市場作用與制度力量的結合中,出現了投資驅動性增長,經濟分布的空間差異性也在增長過程中逐漸顯露。此方面,周靖祥和何燕[4]將這一機理總結為通過“差異化的財政支出政策為手段”實現“以中央為起點實施自上而下的政治科層控制”,地方政府的“層層加碼”和“位序爭奪”成為其增幅器。
(三)中國是大國
人口大國和土地大國,嚴重的不平衡問題存在于地區(省市)之間也存在于城鄉之間,此即為空間尺度的差異性問題的根源。世界最大人口規模和通過國家權力以行政邊界分配“土地”通常講,土地要素在增長研究中的資本化處理方式僅考慮了其經濟屬性,而其對經濟空間分布和要素配置方面的作用并未加以強調,一旦剝離出土地的貢獻,代表頂層設計的制度和政策對于中國區域增長的作用就需要重新評估;在本研究中,考慮土地公有制和土地不可流動的大背景,將關注重點放在了大國特征的另一表現形式——空間結構上,通過相關與差異描述增長。 而形成的空間差異成為研究中國增長基本常識,聚焦點必然落在回應大國特質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安排形成的要素配置結構之上 本文以經濟結構為關鍵詞,實際上是對經濟學本質問題“資源如何配置”的回歸,土地和人口(勞動力)作為生產函數中備受關注的投入要素,勞動力和資本積累“何所而來?何所而去?”所構成的結構性增長來源成為本研究的主題所在;實踐過程中,“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性改革開放成為區域結構格局演化的“催化劑”,中國區域增長解密中結構必不可少。,人口及其他要素與空間尺度的糾葛成為探秘中國區域增長動力、發掘內生機理的重要切入口。
我們強調結構性,在大國特質下也更關注要素的空間分布及其伴隨的相關性和異質性。空間尺度成為解讀中國區域增長極為關鍵的視角,這是本研究區別于既有文獻的一個重要特征。進一步的,根源于“中央—地方”層級政府區劃以及形成的“塊塊”狀割據競爭態勢,則指明以“省市”為邊界的空間尺度可稱為研究中國區域增長問題的適宜選擇。根據圖5(依次對應1952、1968、1978、1985、2000和2010年),中國區域發展具有明顯的梯度性,而1978年之后的經濟發展也是從東部沿海地區開始逐漸向內陸蔓延,只是中國區域經濟重心從未離開東部沿海地區,地區梯度格局已經形成且在不斷固化。
人口大國特質則指向中國區域經濟研究需對人口及其結構的作用進行重新審視。在傳統增長理論分析中,采用勞均化方法對供給方程進行處理,將勞動力或者人口的作用掩藏在了單位化的資本等變量背后[21-22]。圖1對人口數量變化進行了展示,其線性表現和增速趨緩的態勢不可避免地預示著總量人口拐點的到來(勞動力供給的拐點先于人口拐點于2011年出現)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1年全國人口年度抽樣數據顯示,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表明結構矛盾已先于總量矛盾出現在中國實踐中,“人口紅利”是否即將耗盡,對結構提出了進一步的改革要求。 ,從依賴“人口紅利”向釋放“制度紅利”轉變的呼聲高漲。在大國特質下,我們關注人口的省域空間分布,更關注人口的結構構成:以城市化為指標的人口城鄉分布結構以及勞動力結構(勞動力占比以及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中的分布結構)。以城市發展帶動區域發展,是中國區域增長的實現途徑選擇,這賦予了城市化人口結構屬性之外的經濟結構屬性。但城市化在消融城鄉隔閡的同時卻也在固化著差序格局和“城與鄉”的劃分,對資本和勞動力的渴求和將“農村轉移勞動力”排斥在城市社會福利之外正在加劇城鄉失衡(圖6中非戶籍人口的集聚地基本都是城市),成為強調“人的城鎮化”的重要根源。倍受關注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舊稱“農民工”)在地域空間上從西部地區向中部和東部地區、從落后地區向富裕地區的單向流動提供了增長空間效應的另一作用機制(圖6) 圖6指出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和廣東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廣西、重慶、四川和貴州為主要的人口輸出省市,而且2010年和2005年的對比更表明這種人口轉移的力量正在強化。,也被認為是勞動力要素流動形成的“人口紅利”。在這一過程中,以農業向服務業轉化為主要特征的產業結構轉變也與農村勞動力跨地區的空間轉移相伴 [6, 23]。先富地區經濟轉型、城市化推進甚至于去工業化等發展戰略的實施必然伴隨著工業的內遷和欠發達地區的產業承接問題,也就為增長和結構具有鮮明的空間相關特性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四)改革貫穿于增長過程
“中國奇跡”的創造離不開經濟改革和制度改革。對適宜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實驗過程,在摸索中尋求中國自己的增長理論軌跡。行至當下,對經濟社會轉型與改革的渴求依舊凸顯,“調結構”被寄望成為可用的改革手段。盡管各界都在傳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被強調、改革浪潮再次來臨,但事實上,從關鍵詞看,中國政府自始至終都是在不斷通過改革和調整結構的方式對中國經濟進行調控和路徑修正(圖7),改革和結構調整對中國經濟的指導從未停止。在此過程中,結構轉變與改革同步,投資與消費需求的重要性也隨著收入的變化而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在重大變革中出現拐點(如1980、1985、1990和2003年) 關鍵詞出現頻次的多寡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問題的“嚴重性”,詞頻降低則可能意味著特定問題已經得以化解或者格局已形成,沒有了討論的必要;變革本身就是對結構的制度性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無疑是在準確地朝著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道路邁進 [24],快速擴大的總量規模掩蓋了諸多結構矛盾的激化,也成為結構矛盾不斷積累的原因之一。投入型增長是對中國增長的描述,投資被作為經濟控制的重要手段影響了中國35年的區域增長,財政轉移支付是這一機制實現的途徑。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和消費的分配趨于失衡并惡化,資本比重不斷累積、消費被抑制,從1978年的36∶62到2011年的48∶49(圖8),兩者的比重發生反轉。這成為擔憂投資依賴型增長的直覺來源:在增長之外,人民開始提出更多要求,消費作為福利實現的必然手段被國民所注重,單純的增長在解決結構矛盾上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區域空間上,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投資消費結構還有所差異,更是與政府的發展戰略安排相關聯,政策或制度安排下的結構引致了區域的增長也隱隱阻礙著長期增長,這需要在實證檢驗中提供經驗證據并予以解答。
可以發現,中國區域增長是在以省份為單位的“塊塊”區域競爭中實現的,不論是大國表現出的空間尺度性質和城鄉差異、發展演變中伴隨的結構演變、改革實踐中以結構為手段的方式選擇還是政府組織架構下形成的諸侯經濟特征,無一不是與“結構”息息相關的經濟內容,因此,與中國特質相應的經濟結構轉變(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可被用于解釋中國“不可能”的增長現象。從經濟學理論講,馬克思的兩部門經濟學可被視為“結構”的起源 馬克思,1885:《資本論》第二卷,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傳統增長理論中描述的增長過程也并“不是單純的邊際增量問題,而是結構變動和全面增長的問題” [25],結構構成在增長過程中表現為“一個經濟和社會系統中相對穩定的關系”[26],增長、波動或發展的實質就是經濟結構演變[6];進一步的,在經濟學思維演化過程中,落后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增長給予了經濟學者諸多靈感,“關心發展中國家那些可觀察到的特征” [26]成為了發展經濟學關注結構分析從而區別于新古典范式的重要來源。承襲這一思路,我們結合中國特質表現出的結構性,從結構失衡與結構變動方面切入對中國經濟發展運行機制進行描述,以展開區域增長邏輯分析。
當我們進一步對“結構效應從何而來”進行思考并承認中國區域經濟過程本身就是要素配置與經濟運行秩序的構建過程之時,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一系列結構性扭曲現象與阻礙要素流動和安排資源配置的制度有關,多層面的結構失衡是制度安排作用于區域增長的途徑和表現,因此制度造設的格局形成對結構解釋增長至關重要。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與之相輔的所有制安排是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起點。勞動力與土地要素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與資本配置結構共同決定經濟增長及波動的方向和質量[27]。財政轉移支付作為資本配置的重要手段要求我們對“分權”加以重視。因此,研究中需闡釋土地制度、人口制度和財政制度在中國空間結構格局形成和要素配置扭曲進而產生經濟結構惡化等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強調制度安排本身即是對增長邏輯關系的描述 [28], Acemoglu等人將中國過去的快速增長歸因于依靠經濟上的包容性制度,因而持續的增長需要在今后實現政治上的包容性制度才可達成;這一分析框架源自Acemoglu和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詳情參見:Acemoglu Daron, Robinson James.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經濟結構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只是在研究主題上,本研究更為強調經濟結構的紐帶作用:結構是制度作用的實現途徑,制度通過結構發揮對增長的效應。因此,在結構視角的增長研究上,對經濟結構的考察應與中國的制度安排對應,強調制度是經濟結構變動發生的來源,制度安排本身描述了區域經濟的增長邏輯,以結構變化解釋增長過程實則是對制度這一根源的強調。那么相應的,在政策含義上,“調結構”不能是對結構的調整,而應是對經濟規則的調整,也就是制度是調結構的關鍵,管理實踐需抓住本質問題。
三、增長實現邏輯:供給、需求、空間
(一)投入決定增長與需求引致增長
此為投入視角和需求視角的兩個不同的經濟增長解析框架,內含的不同要素的配置情況反映經濟結構,是為“結構引致增長”。研究中我們對經濟增長分析方法予以梳理發現,已有經濟增長模型主要是“供給”(生產)面的求證,從供給或者要素投入的角度解釋經濟增長,相關的計量模型也主要是對“生產函數”進行估計[29],生產函數的形式則以CobbDouglas模型為主流,強調資本、勞動力的存量作用。主流增長理論的發展致力于變量的內生化。這一過程中,Solow[30]提出了基于總量C-D生產函數的索洛余值法,并構建了簡明而又優美的增長測度公式(式1),從而開創了經濟增長源泉分析的先河,為眾多學者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其方法論的影響是深遠而帶有根本性的” [31]。供給視角的經濟分析也成為傳統增長分析的主要思路。以此為框架對經濟結構效應加以分析,其形式基本以lny=lnA+λX+αlnk+βlnl最為常見,λX為結構變量,這實則隱含著“經濟結構因素通過影響經濟產出效率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假設,因該分析方法中的計量方程可認為源于Y=(AeλX)KαLβ的人均化和對數化[6]。
生產函數的便捷性無疑導致了供給因素在經濟增長分析中的主流位置,但也因此忽視了總量經濟的另一方面——需求的作用分析。需求是宏觀經濟學中解釋產出的主要因素,隨之而來的思考就在于,經濟增長理論真的能夠較好解釋增長么?秉承需求導向分析方法的經濟學者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32-34]。基本觀點在于,認為需求引致經濟增長的分析可以通過國民經濟核算方程進行微分化展開,其本質在于考慮經濟的總量供給與需求的平衡。相對于投入視角的分析,需求視角的增長分解則對結構作用的強調更為直接,指出需求因素對增長的作用來自兩部分:要素變動比例和占總量的比例,即存在需求結構性影響(式2)。需求核算方程表征的增長構成的流量性則提供了對相應要素的存量指標和流量指標的增長效應差異進行考察的分析基礎,其中尤以投入視角的資本存量和需求視角的投資流量差異最具有經濟含義[35]。換句話說,在理論基礎建構層面,經濟增長分析通常有兩個框架——基于總量生產函數的增長模型和基于需求核算方程的凱恩斯模型。要素作用和結構性在其中被考察,分析框架的選擇則應從研究主題出發。
(二)空間尺度與區域異質性
區域地理空間的信息納入給予了中國區域經濟研究確定空間尺度和考察區域異質性的要求,要素結構與空間分布的糾葛使中國增長邏輯必須對要素在跨區域空間上的分配予以重視。“地方競爭”促成的中國經濟增長 [12, 36]決定了區域經濟的空間相關屬性,區域間競爭/合作、相互模仿學習或者相異的發展戰略選擇形成地區經濟結構空間關聯的來源。然而,受限于計量方法的可實現性,經濟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研究還缺乏確定性的經驗證據,由此產生的方法論層面的要求促使我們引入空間計量方法控制空間鄰近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以及因個體差異而產生的空間異質性 [37-39],明確經濟結構效應的空間路徑與空間異質,是正確識別中國區域增長邏輯的關鍵。
大國特性下的區域差異性則進一步要求分析不能是平均的和大致意義上的,區域的異質性表現需要得到體現。空間與時間的聯接則強調中國區域增長的演化過程,以動態視角探求中國區域增長邏輯,這是對中國階段性特質的回應。時間維度反映經濟增長趨勢問題,而空間維度反映發展戰略、資源流動和區域配置結構(尤其是土地使用和勞動力),中國增長邏輯需同時考慮時間和空間的局部性 [29]。對此研究的阻礙依舊是在方法論層面,因為我們對上述問題的分析需要依賴于局部信息的獲取,而傳統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的回歸模型參數和其他固定系數模型大多只是“平均”或“全域”(Global)估計,并不能反映參數的非平穩性 [40],難以獲得中國區域經濟中的結構性和異質性統計量的考察,全局內部的結構性抵消導致分析結論難以準確描述中國區域經濟實踐的現實情況。因此,對空間的重視和異質性的強調,需要我們引入空間計量分析和異質性估計方法,以此才能提供局部的和更為詳細的經濟關系描述,具體方法涉及地理加權回歸方法(GWR)和地理—時間加權回歸方法(GTWR)[41-42]。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區域的異質性特征顯著,且經濟結構與增長的關系中存在時空演化特征,增長分析應具有針對性。
四、重構發展主義邏輯
前文分析中,我們已明確了“結構引致增長”這一主題,更值得注意的是,結構是增長和發展的“深層因素”,而制度卻是塑形結構的現實基礎。總量問題得不到解決,很大程度是結構問題,但調結構總是不得章法,究其原因卻是因為制度性和系統性的問題。因此,改革改的應是制度而不是結構,調結構也不應是對結構的直接調整,而應該是對制度安排進行調整,這才是調結構正確的途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一個都不能少。基于此認知,我們提出如下政策思路。
第一,強調區域統籌和城鄉融合,中國區域增長過程不能將各個地區(此處強調省市邊界)割裂開來。增長最為關鍵的變量仍舊是人口和土地,在機制設計上則與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相對應,那么考慮經濟增長目標實現的同時,各地區政府應關注就業吸納問題,致力于完善勞動力市場和人口管理工作,做好勞動力安置,引導區域經濟發展中人口集聚和經濟集聚的形成。短期目標應強調非戶籍人口的城市融入,這一目的的實現就要設計戶籍制度中相應的人口自由流動問題,在制度上和機制上維系地區對人口(或勞動力)和資本的吸引力[35];深層次的長期問題則在于農村發展,正如桑德斯[43]所述,“鄉村的命運主要取決于國家如何經營大城市,以及為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樣的權利和資源”。這與我們在《農村發展與稟賦條件一致性甄別:來自村的證據》一文中強調的城市和農村并非簡單且清晰分割的兩部分,而是發展問題站在城市看農村和站在農村看城市的兩個視角的不同卻又相同的思考,單邊行動難以謀求公平發展。
第二,謹慎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切忌忽視小農經營生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作用,并應事先做好失地農民的社會安置工作。土地制度改革被期望成為促進城市化(政府層面強調的“城鎮化”)、扭轉農民收入低的實現手段,似乎轉移農村勞動力成為了農民致富的重要渠道,也是維持人口紅利的重要基礎,但逐漸消逝的農村卻給予了我們更多的思考和需要警醒的地方。通過“走出去”的辦法消除農村的貧困雖然能夠使問題得到緩解,但是卻不能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更為嚴重的糧食、社會保障、公平等問題依然不能得到解決。集中化似乎成為未來幾十年的選擇。2013年《一號文件》業已提出了農村土地集中經營的構想,然而,單純和“粗暴”的集中化可能引來超出我們所預期的更多、更嚴重的問題,實踐中要慎之又慎;另一方面,農民逃離糧食種植活動背后的根源——農業收益過低、農村人口結構(農村老齡化)和新農民訴求變化(年輕農民不再務農),實際上是農村發展更為嚴重的隱患,因此完善農產品價格決定機制、著力于提高“種地”的收益以維系農民與土地的聯系才是關鍵——“讓有錢的農民種地和種地的農民有錢”,根本上就要“順勢而為”,適應當下的農村發展狀況才能使政策有成效。
第三,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推進地方政府改革。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是形成中國諸多結構矛盾的來源,發展過程的兩性分野(政治性和經濟性)及脫節使中國內外經濟失衡不斷加劇[4],從此著手也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而財政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是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的短期內最為有效的工具。財政是政府部門最具有自主控制的管理途徑,更為重要的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是中央對地方、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來源,因此在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除卻人口和土地結構的作用發揮,財政和區域更是管理實踐中需要特別強調的因素。在投資來源上,中國區域投資具有明顯的投資主體性和分配偏向,各地地方政府也是投資的主要提供者。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財政收入回落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巨額的計劃投資金額僅依靠財政收入顯然不可行,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合力推進投資主體結構優化。民間投資作為繁榮城鄉市場、增加財政收入、擴大社會就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力量,其作用在地方實踐中需獲得充分的介入;而對資本投向,同樣需要得到關注,協調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投資比例。
五、結語
總的來講,區域增長是理解中國經濟的邏輯起點,而經濟結構是其深層次原因,結構扭曲的積累要求各地方應將增長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標,促進收入公平分配,以此形成穩定、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區域就是巨大的經濟試驗場。在其中,經濟發展的不同道路得以嘗試,城市化進程可被視為其量化指標。這一過程中,鄉鎮企業的崛起孕育出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蘇南模式” [44-45]以及“戶籍制度”松動條件下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等要素間關系的變化催生的“溫州模式”[46]等,都是以“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方式實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選擇的具體表達。為實現發展與增長的統一,“自上而下”的改革進程逐漸被政府強調,城鎮化大規模推進,試圖通過政府的干預扭轉失衡,實現公平發展,但這未能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也未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中國的未來還在繼續探索中。“穩增長、調結構和促改革”成為當下尋求未來區域發展的訴求點所在。無疑,結構的適宜性是鏈接中國經濟過去和未來的關鍵,尋求有質量的增長需從經濟結構入手,前提則是明晰結構效應的傳導途徑,而這一點則需要以中國現實為基礎,立足本土化經濟實踐建構經濟學理論的現實內涵,以此促成結構視角的中國區域增長分析不斷向下分解。這正是對研究要“頂天立地”的實踐:以問題為導向,問題決定方法,方法解釋現象,在這一過程中尋求“真實的中國經濟”描述。
參考文獻:
[1] 項俊波.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測度與分析[J].管理世界,2008(9):1-11.
[2] 周靖祥.中國內外經濟發展失衡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12.
[3] 陸銘.中國經濟再平衡:改革與危機的賽跑[J].財經,2013(35).
[4] 周靖祥,何燕.財政分權與區域平衡發展:理論邏輯及實踐思路——基于文獻研究的考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3):189-200.
[5] 何帆,張斌.尋找內外平衡的發展戰略:未來10年的中國和全球經濟[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6] 侯新爍,張宗益,周靖祥.中國經濟結構的增長效應及作用路徑研究[J].世界經濟,2013(5):88-111.
[7] 陸銘. 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什么決定中國經濟的未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8] 胡鞍鋼,鄢一龍,呂捷.中國發展奇跡的重要手段——以五年計劃轉型為例(從“六五”到“十一五”)[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1):43-52.
[9] XU C.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49(4):1076-1151.
[10] QIAN Y,XU C.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The Mform hierarch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J].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3(1):135-170.
[11] 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經濟學家在欠發達國家的探險與失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12] 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7):36-50.
[13] 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 LI H,ZHOU L.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743-1762.
[15] 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J].經濟研究,2004(6):33-40.
[16] 王賢彬,徐現祥.地方官員晉升競爭與經濟增長[J].經濟科學,2010(6):42-58.
[17] LIN J Y,LIU Z.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0,49:1-22.
[18] 張晏,龔六堂.分稅制改革、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季刊),2005,5(1):75-108.
[19] 周業安,章泉.財政分權、經濟增長和波動[J].管理世界,2008(3):6-15.
[20] 傅勇.分權治理與地方政府合意性:新政治經濟學能告訴我們什么?[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 (4):13-22.
[21] SOLOW R 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22] RORN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 part II):S71-S102.
[23] 侯新爍.農村發展與稟賦條件一致性甄別:來自村的證據[R].工作論文,2013.
[24] YAO Y.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N].Foreign Affairs,2010-02-13.
[25] SINGER H W.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0,40(2):473-485.
[26] CHENERY H. Structur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27] 周靖祥,何燕.城鎮農村勞動力“吸納”與區域經濟增長實證檢驗——基于1990-2006年省際所有制變革視角探析[J]. 世界經濟文匯,2009(1):33-49.
[28] ACEMOGLU D,ROBINSON J.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M]. 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2.
[29] 侯新爍,周靖祥.需求引致增長:三大結構效應的時空演化[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3,30(5):18-32.
[30] SOLOW R 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312-320.
[31] ROMER P M.Human capital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989,15(1):765-816.
[32] MCCOMBIE J S L,THIRLWALL A P.Economic growth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t [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3.
[33] LIN J Y,LI Y.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A demandoriented analysis[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2003,2:779-794.
[34] MCCOMBIE J S L.Economic growth,the Harrod foreign trade multiplier and the Hicks’ Supermultiplier [J]. Applied Economics,1985,17(1):55-72.
[35] 侯新爍,周靖祥.中國區域投資多寡的空間尺度檢驗——基于省份投資與其增長效應一致性視角[J]. 中國工業經濟,2013(11):31-43.
[36] 張軍,高遠.官員任期,異地交流與經濟增長——來自省級經驗的證據[J].經濟研究,2008,42(11):91-103.
[37] ANSELIN L,GALLO J L,JAYET H.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s[M]// The econometrics of panel data.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2008:625-660.
[38] LESAGE J P,PACE R K.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 [M].Cleveland:Chapman Hall/CRC,2009.
[39] ELHORST J P.Applied spatial econometrics:raising the bar [J].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2010,5(1):9-28.
[40] YU D L.Spatially varying development mechanisms in the Greater Beijing Area: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investigation [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6,40(1):173-190.
[41] TIBSHIRANI R,HASTIE T.Loc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7,82:559-567.
[42] HUANG B,WU B,BARRY M.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for modeling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in house price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2010,24(3):383-401.
[43] 桑德斯.落腳城市[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44] 張敏,顧朝林.農村城市化:“蘇南模式”與“珠江模式”比較研究[J].經濟地理,2002(4):482-486.
[45] 費孝通. 鄉土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46] 史晉川,朱康對. 溫州模式研究:回顧與展望[J].浙江社會科學,2002(3):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