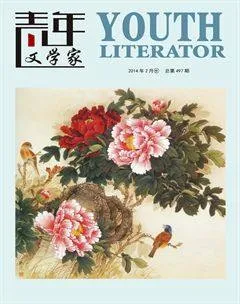解析中國生態文學中的生態倫理困惑
摘 要:本文通過對中國生態文學代表作品以及部分相關的國外作品的解讀,梳理了此類作品在生態倫理方面的思考和表述,并從生態批評理論的角度分析了其哲學內涵,指出了其面臨的矛盾和困惑,繼而針對這一問題,嘗試將生態馬克思主義這一創新理論應用于中國生態文學的解讀與批評,為破解生態倫理的困局和促進生態文學發展探索新的思路。
關鍵詞:自然;生態文學;生態倫理;生態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李臻,天津師范大學在讀博士生,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05-00-02
自上世紀開始,生態主義思想已成為文學創作和批評的重要內容,與生態主題相關的優秀文學作品,以及生態批評學者對作品的解讀,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學作品以其對情感的真切表達和對哲理的生動詮釋,有力地推動了生態倫理觀念的傳播。
如同人際倫理明確了個人對待他人的道德規范,生態倫理指引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看待自然的態度,追求建立規范人類與自然生態之間關系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包括對自然權利的認同、對自然的善與愛意以及人類自身使命的踐行等方面。生存環境惡化的現代人,渴望從詩意盎然或喻意深邃的文學作品中,獲得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正確理解和行為指南。那些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倡導敬畏自然、愛護生態的文學作品所具有的強大感染力,無疑對中國社會上廣泛出現的親近自然環境、倡導綠色生活、保護動物權利等思潮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當人們試圖在現實中踐行這些作品所倡導的精神時,也遇到了諸多的困難和爭議,熱忱的生態環保行動與許多不同社會群體的沖突屢屢見諸媒體就是例證。這種情況因何產生?如果細細回顧那些激勵和召喚了人們的文學作品,可以發現,它們在帶來感動和啟示的同時,其生態倫理也蘊含著困惑與矛盾,仍需要用不斷創新的思維來進行探索。
一、融入自然的“詩意的棲居”恍如夢境遙不可及。
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及散文集《湘行散記》,一直被我國生態批評界推崇為重要代表作品,作品中描寫了湘西水鄉的自然美景,以及在自然懷抱中保持著古老生態和淳樸性情的鄉民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妙情境,人純真的愛與自然寧靜的美相互映襯,令面臨生態危機之苦的現代人無限向往。從這些描寫中,可以看到對《莊子》等中國古代經典所表達的“天人合一”宇宙觀的繼承,對東方傳統文化中和諧審美觀的追求,以及對背離自然的貪婪、污穢的都市文明的批判。中國文學研究者將其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以及王孟山等山水詩人吟詠自然的詩作相提并論,凸顯出了中國歷史文化中一脈相承的自然情結和田園理想。跨文化研究者則將它與19世紀美國作家梭羅的綠色經典《瓦爾登湖》以及《河上一周》相比較,表現出東西方哲人在否定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的奴役、追求人與自然相融合的理想方面存在著相通之處。
沈從文的名作,以及上述與之相似的眾多作品,都為現代人描繪了一個人類詩意地棲居于自然、與各種自然事物結為密友的夢境,但它們大都與社會現實有很大距離。正如陶淵明永遠無法重返桃花源一樣,沈從文也沒有多少時間流連于湘西的偏僻水鄉,他更多地生活在北平這樣的大都市,而現代文明取代原始生活方式是無可替代的趨勢,對此作家似乎無能為力、只能回避。大洋彼岸遙相呼應的梭羅也是如此,他獨自在湖畔林中進行生活實驗,向人們展示出一種原始而簡樸的、全身心與自然溝通的理想生活方式,但美國學者布依爾指出,梭羅作為超驗主義思想家,將自然萬物視為上帝的化身,因而把自己所處的環境刻意美化成了純潔的樂園,而事實上,如果沒有友人愛默生的資助,他是無法在山林中維系閑適生活的[1]。梭羅同樣只能批判現代文明而無法阻止其對自然的改變。這種對原始生態的懷念和對現代文明的無奈,在中國的許多生態文學中都有所體現,作品中人與自然親密無間的關系,似乎只能是一個象征性的寓言,對現代社會生活沒有足夠的參考意義。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源自古代的“天人合一”觀念作為一種思想遺產,雖然對時下消解主客體二元對立的自然觀確有啟發意義,但也有其簡單而偏頗的一面。有學者指出,《莊子》極力強調人與天地同一的自然屬性,而忽視幾乎所有的知識和秩序,其中包含著對文化價值的棄絕和對人類社會屬性的消解,這種極端的理想雖有積極的因素,但永遠不會實現[2]。其實這種觀念甚至也消解了人類的部分自然屬性,對于這一點,掌握了進化論的現代人更加容易理解:自然萬物之間都存在著生存斗爭關系,自古以來人類的生存總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與自然力量的斗爭和對自然資源的開發,這種斗爭關系正是人類文明不斷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所以自然與人之間不可能套用人際倫理中親人或摯友式的始終溫柔體貼的關系,人類也不可能長期固守著原始生活方式而拒絕現代文明。回避人與自然之間的差異和矛盾,認為人只要憑借對性情的陶冶和對需求的簡化就可以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基于這樣的理念當然不易構建起具有實踐意義的全面的生態倫理。
二、回歸自然的“狼的野性”拋棄人道令人不安
當代的一些文學作品吸收了更多的生態科學觀念,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映更加全面,但同時也顯現出某些更加激進的傾向。姜戎的自傳體小說《狼圖騰》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生態文學作品之一,它展示了內蒙草原上生態系統的精妙,以及狼身上體現出的大自然的生態智慧,并對違背自然規律的掠奪性開發行為進行了猛烈抨擊,表達出作者反對人類中心主義,渴望回歸自然的愿望。與前文提到的作品不同,姜戎既描述了自然美麗迷人的一面,也充分表現了自然嚴酷的一面,草原上的一切生命都從屬于自然,它們在相互斗爭和制約中生存,人、狼和其他一切生物都必須學習并服從自然規律,否則就被淘汰,而他們自身的一切訴求都必須服從于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穩定的需要,這種生態中心主義的觀點具有深層生態學特征,贏得了環保愛好者的稱贊。
但作者主張人要具有狼性的觀點也引起了爭議。在主人公陳陣看來,人應該像狼一樣始終接受自然法則的支配,忍耐苦難煎熬和殘酷斗爭,而不改造和開發自然,因為任何改變原始生態的企圖都只會導致災難,他反對一切新的技術進入草原。對于那些不遵守原有法則的外來人口,陳陣認為他們危害了環境,應該被驅逐或淘汰,他對這些人的謀生訴求不屑一顧,卻為他們遭到狼的襲擊而叫好。書中,陳陣以對原始生態的維護效果為標桿,貶低農耕民族,以至于肯定游牧民族和航海民族對其進行的侵略和屠殺,觀點之偏激令人驚愕。天津評論家龍行健的《狼圖騰批判》一書指出,《狼圖騰》以狼的野性踐踏了人道精神,其血腥兇殘使人毛骨悚然。德國漢學家顧彬則在接受采訪時稱《狼圖騰》為法西斯主義,令他想起希特勒時代。這一評語也確有依據,因為納粹德國曾是現代歷史上最先全面貫徹生態保護政策的國家,而它將歷史上外來的吉普賽人、猶太人等視為污染和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劣等種族,加以迫害和屠殺[3]。
當然,為維護生態環境而敵視人類同胞的思想并非這位陳陣所獨有。胡發云的《老海失蹤》和賈平凹的《懷念狼》等許多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致力于生態保護的人所遭遇的矛盾而尷尬的倫理困境。究其根源,這與生態中心主義的偏頗之處有關。美國生態學家和哲學家薩卡爾曾指出,生態中心主義在生態倫理方面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它主張自然生態系統固有的內在價值與人類需求無關,人類只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其他生物權利平等,人類只應遵守自然法則而生存,無權改變自然生態系統中其他部分的運行狀態,但這意味著,人類將按照自然的生存競爭法則,憑借自己的全部能力與其他生物競爭,為自己贏得所需資源,而沒有義務關懷其他生物的狀況,因為任何倫理體系都首先建立在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基礎上,而不是能力與義務對等,即任何人對自己無權干預和享用的事物都不負有道德上的關懷責任,但如此競爭的結果又必然是生態失衡,其他的自然法則將逐漸被破壞[4]。這一邏輯缺陷體現在實踐中,就是人類仍未能明確對自然進行開發和施以監護的正當性及其衡量尺度,多數人無法清楚地看到承擔生態保護義務與從中獲得合理權益的對應關系,因而在處理人的生存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時總是拿不出能被普遍接受的標準,陷于兩難。少數激進的生態主義者不惜違背人道精神而與同類為敵,以致表現出反社會或法西斯的傾向,不可能有出路。所以,姜戎最終未能留住理想的草原,《狼圖騰》以悲憤的嘆息結局。
三、生態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倫理的啟示
不論是理想化的和諧共生,還是更現實的斗爭與保衛,幾乎每個生態文學故事都以無奈結局,似乎映襯著現實社會中生態運動的艱辛,讓讀者感到傷感的同時,也對生態倫理愈加困惑。綜觀上述文學作品,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故事都以原始生態為理想境界,同時以目前生態危機的真實情景為依據,將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直接定義為破壞生態的行為,這樣,只要人類要發展,就必然因改變原始生態而危害環境,而人類又無法停下發展的腳步,于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似乎成了一道無解的題目。
生態馬克思主義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提供了新的視角。馬克思主義堅持以普遍聯系的觀點認識世界,以發展和辨證的觀點分析問題。人具有認知能力和社會屬性,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是必然的,人也具備自然屬性,所以人的發展也是自然生態系統發展的一部分。自然的原始生態不會一成不變,而它的發展不可能也不應該排除人類影響,它隨著人類的發展而產生變化是必然的。人類具有高級認知能力,在受自然規律支配的同時,也必然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和改造自然,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由此可知,人類對自然進行開發利用未必就是罪過,給環境帶來的變化未必就是危害,關鍵在于人類選擇的發展方式是否有利于保持人和自然環境長期共同發展,避免嚴重的失衡和脫節,而發展方式的選擇,則不是僅由人的情感或信念來決定的,而是要依據社會運行的客觀規律,顧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生態馬克思主義正是著眼于社會發展規律,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分析指出:適宜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發展,前提是不能超越自然條件的承受極限,否則將最終起到相反作用。在現代社會,資本的無限擴張和消費異化現象并非是人類健康發展的必要手段,卻推動著人們憑借科學技術不斷加快生產力發展,超出了生產力提升的自然限度,這是生態危機的重要根源,而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并培育相應的文化生活,是解決問題的出路所在[5]。
當今的中國正朝這個方向前進,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正是要改變單純追求生產力的提升與擴張和豐富的物質享受的做法,以人的長期、全面發展為根本訴求,運用先進科技等各種手段,追求建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社會經濟模式,讓現代文明成為生態文明。可以想見,在未來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因現代文明而逐漸享有適度的舒適和便利,但不造成嚴重的污染和損耗,以進步的科技加深對自然的認識,但不追求控制和掠奪。人類以友善、尊重而又包容差異的態度與自然相處,愉快地欣賞自然的美妙,以可再生的方式取用自然資源,并通過適時的干預幫助維護自然界其他生命體的平衡關系,那么此時的人們,應該不會有生態倫理方面的困惑了。
如果以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推論,生態文學的作者們面對生態危機時產生的痛惜和急切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必只將贊美和愛意留給原始的生態,而一味將憤恨和絕望投向現代文明,也應該發現和承認其中含有的正面因素,并對人類自省和創造的能力保持信心。人類在歷史上曾無數次從災難中學習,而后向更加光明的方向前進。對自然的關愛、對自然權利的尊重,完全有可能在現代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實現。而今不論是在湘江水畔、內蒙草原還是在猴群寄居的山嶺之間,人們都努力運用現代的理性重新修復和發展與大自然的關系。在社會經濟和文化模式轉向合理發展方向的客觀基礎上,人類道德與愛的光芒終將照耀社會和自然環境。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可以讀到更加動人的文學作品,它們將繼續帶人們神游于美麗的江邊、湖畔、密林和草原,而在故事的結尾,和諧的歌聲必將取代無奈的嘆息,新的生態倫理也將帶給人無限的希望。
注釋:
[1]Joel Myer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174.
[2]王立、沈傳河、岳慶云:《生態美學視野中的中外文學作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30-35頁。.
[3]張旭春:《生態法西斯主義:生態批評的尷尬》,《外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二期,62-71頁。
[4]Sahotra Sarkar, Bio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57-64.
[5]萬希平:《論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價值和當代意義》,《天津社會科學界第六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集》,2010年,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