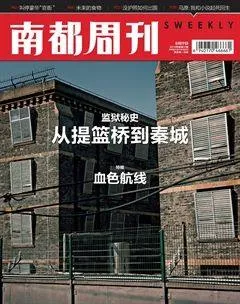外婆的面猴
我滿五歲那年夏天,鄰居玩伴都開始上小學,父母看我落單,決定讓我也上學,不足齡無所謂,我們北投是小地方,規定不像臺北大都市那么嚴,就當沒學籍的寄讀生,先讀一年再說。
我就這樣背起書包上學去,開學當天,老師第一堂課就問,有沒有人不會寫自己的姓名。我老實舉手,環顧四周,把手也抬得高高的,寥寥無幾,看來差不多全班同學都會。
頭一天兆頭就不怎么妙,接下來還更糟。沒過幾天,老師一通電話打到媽媽任職的單位,請她接我回家,因為我坐在課堂上尿尿了。我不只年紀比同學小了快一歲,膽子更小,上課到一半,想上洗手間也不敢講,又實在憋不住……
結果是外婆來接我。事隔多年了,我仍記得祖孫倆從山坡上的校園拾步走下長長石階的情景,我白嫩短胖的小手被外婆細瘦、皺紋滿布的手牽著,她邊走邊心疼地用閩南話說:“免驚,下次跟老師講就好,返來去厝內,我煮面猴給你吃。”外婆手藝好,又像許多傳統的臺灣婦女,往往透過烹調來表達對家人的關愛。
回到鐵道邊的外婆家,她替我洗好澡,換上干凈的衣服,便動手做起面猴。我端把板凳坐在廚房,看外婆先將面粉置入大碗內,加熱水調出一碗稠稠的面糊,放在一旁,接著開始準備菜料:蝦米泡溫水;豬肉切絲,加醬油、淀粉和料酒腌;小白菜切段;蔥切成蔥花,蔥白和蔥綠分開。
然后,刺激的部分來了。外婆起了油鍋,等油一熱,蔥白入鍋,唰的一聲,整間廚房剎時蔥香四溢。泡軟的蝦米跟著下鍋炒拌,廚房里換成另一種香氣,咸咸的帶著點腥,聞來有點像在烈日下曝曬的漁網。
外婆把肉絲也加進鍋里炒了一下,隨即倒進清湯,接著用筷子把面糊一點一點地撥進沸騰的湯中,待小塊的面糊統統浮起,落鹽和味精(是的,那是個味精泛濫的年代),把小白菜扔下鍋,再滾一下即熄火,灑上綠色蔥花,一鍋香噴噴的面猴就大功告成了。
我用調羹攪著我的那一碗,準備等涼一點再吃,一邊問外婆,這道點心為什么叫面猴?
“你看,面猴每一塊都生成不同款,”她答稱:“就像猴仔,沒定性,所以叫面猴。”這到底是身為漢學家之女的外婆隨口編出來哄孫女的,還是果真如此,我始終弄不清楚,如今外婆和媽媽皆已離世,想問也問不到了。
不過,我倒是知道,回到山坡上的自己家,說面猴別人可聽不懂,得講“面疙瘩”才行。我家那一帶的住戶以外省公教人員居多,不管是江蘇人、山東人、湖南人,家家戶戶都會做這種面食,做法跟外婆的大同小異(我覺得她做的最好吃——這當然是我的成見),只是大伙兒稱之為面疙瘩,只有外婆和媽媽叫它面猴。眼下回想起來,面猴和面疙瘩之同異,或是我最早有關族群的記憶。
前一陣子讀清代袁枚的《隨園食單》,看到點心單中記載有一味“面老鼠”,說它是“以熱水和面,俟雞汁滾,以箸夾入,不分小大,加活菜心,別有風味。”我讀著讀著,赫然察覺,杭州人袁枚筆下是的面老鼠,可不就是臺南人外婆口中的面猴。
這一碗家常點心我從小吃到大,如今自己仍時常煮來當午餐,卻渾然不知它居然是起碼可上溯至清朝的老食譜;這熟悉的滋味原來蘊藏著歷史,更顯現常民文化的傳承。我幾乎可以想象,在天曉得多少代以前的一個午后或黃昏,我的祖先也曾煮了一碗香噴噴的面猴或面老鼠,給她不解事的孫兒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