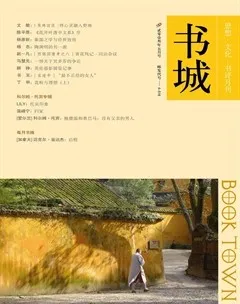歸家
科爾姆·托賓出生在愛爾蘭東南一隅的恩尼斯科西,這是韋克斯福德郡第二大鎮(zhèn)。托賓筆下的許多故事,就發(fā)生在韋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黑水村,威克斯福德鎮(zhèn)……對于熟悉托賓的讀者,這些地名想必不會太陌生。
這些故事有時還會相互串串門。《黑水燈塔船》里海倫的外祖父彼時還年輕,到《石楠花綻放》里亮了個相。而《石楠花綻放》里的基廷家和麥克·瑞德蒙德家,到了《黑水燈塔船》里已成斷壁殘垣。兩部小說中的人物又集體到《布魯克林》里打了個照面—艾麗絲的姐姐去世后,《黑水燈塔船》里海倫的外婆多拉前往拜訪,并且“一直喋喋不休著屋子里其他人沒聽說過的人事”,看來其嘮叨還真是數(shù)十年不改。而《石楠花綻放》里的男主人公埃蒙和他父親也露了一面—“吉姆以前的老師瑞德蒙德先生正頭戴草帽坐在那里,顯然正在度假……他們繼續(xù)往前走,吉姆低聲說,瑞德蒙德先生是他唯一喜歡過的老師,可惜中風(fēng)了。‘他兒子在哪里?’艾麗絲問。‘埃蒙?我想他在讀書吧。他總是在讀書。’”
翻開《石楠花綻放》,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個時間段的埃蒙已見證了祖父和叔叔的逝世,而爸爸也遭遇不測。埃蒙的父親中風(fēng)之后口齒不清,上課的時候經(jīng)常會嘟噥些埃蒙都聽不懂的字詞。后來,埃蒙長大成為法官,繼續(xù)面對人生中的一次次別離與變故。而《布魯克林》中艾麗絲的好朋友南希在收錄于《母與子》的短篇小說《關(guān)鍵所在》中,生下了孩子,因家道中落承擔(dān)起養(yǎng)家的重任。青年埃蒙正在法律界一步步向上爬時,她在苦苦經(jīng)營薯?xiàng)l店,還得想辦法讓兒子打消不上大學(xué)的念頭。
托賓小心地經(jīng)營著這塊土地上發(fā)生的一切。英國大牌文學(xué)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在評論《黑水燈塔船》時就敏銳地指出,托賓的風(fēng)格具有愛爾蘭南部現(xiàn)實(shí)的氣息。這塊土地與這片大海,似乎成了他心頭的一滴血,難以割舍。在散文體短篇小說《空蕩蕩的家》中,他這樣寫下自己的感情—

“家就是這個位于巴里肯尼加的懸崖背面的空蕩蕩的房子,房子里一半裝滿了各種還沒拆包的東西,從灣區(qū)帶來的小幅油畫和素描、威亞·塞爾敏的印版畫、幾幅橋與水的照片、幾張沙發(fā)椅、幾張織毯。家就是裝滿書的后屋,還有兩間臥室和浴室。家就是前屋又高又大的房間、水泥地板、大壁爐、一張沙發(fā)、兩張桌子、倚著墻根放著的幾幅畫,其中有我從都柏林買來的瑪麗·洛汗的畫和其他一些我多年前買來的作品,它們還在等釘子和掛繩。家也是樓頂?shù)倪@間屋子,嵌在屋頂里,一扇玻璃門通往小小陽臺。夜氣清朗時,我站在陽臺上舉頭看星星,望見羅斯萊爾港口的燈火,圖斯卡礁燈塔一閃一滅的光,還有夜幕與暗色大海交融的那條淡淡的線,望之心安。”
按照托賓小說體系中的時間,大概就是在此十幾年前,《黑水燈塔船》中的海倫也看到了圖斯卡礁燈塔那一閃一滅的光。她回想起童年故事,聽媽媽講述對亡夫的想念,對病危的弟弟束手無策,而那原本破碎的親情,卻在這燈光中慢慢重建。最后,她也回家了,重新接納了自己曾一度無比渴望逃離的家庭。
而埃蒙最后也回到了家—摯愛卡繆爾也去世了,往事與死亡都隨風(fēng)而去。他和兒女回到卡什的海邊,重新審視人生在時間的長河中帶來與奪走的一切。在小說的結(jié)尾,他和孫子在海中嬉戲,最后他抱起孫子往岸邊走去,走向家園的隱喻。
對于這幾部小說的人物而言,“家”是一個終將要回歸的地方。它是愛爾蘭東南角的這片土地,也是人生的安定所在。離開的人,無論漂泊何處,走得多么遠(yuǎn),也總還要回到這里,作個了斷,再展開新生。
“家鄉(xiāng)”的背景與“家”的情感相互勾聯(lián),于是我們在這幾部小說中,看到了多層次的“家”的意象。自然,家首先是以情感為紐帶的。而情感,一方面當(dāng)然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的細(xì)節(jié)當(dāng)中。正如《黑水燈塔船》的開頭一章,海倫照顧孩子,布置派對,感受著對丈夫休的溫存。但就在這安穩(wěn)的生活中,卻潛藏著另一股力量,也就是她和媽媽、外婆之間破碎而矛盾的情感。于她而言,這是片“無人居住不可信任的貧瘠土地”。而這種情感,往往借助儀式化的情景展開。
在《石楠花綻放》中,這一場景是死亡。說得武斷些,這部長篇可以看作埃蒙“見識死亡”的歷程。他看著祖父、叔叔、父親和妻子去世,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變得成熟。托賓寫埃蒙第一次見識死亡時的感覺,頗似《百年孤獨(dú)》中“見識冰塊”的場景—一個嶄新的世界從此進(jìn)入了人生。在《黑水燈塔船》中,死亡也是個相當(dāng)重要的場景。海倫父親的去世為三代女性的矛盾埋下伏筆,而海倫弟弟德克蘭的死亡將這三代人重新聚集在一起。兩部小說中,死亡所引出的細(xì)節(jié),其實(shí)多有相似之處。卡繆爾去世之后,埃蒙時常會覺得她還在身邊,恍惚許久才想起她已離開。而海倫的父親去世后,她偷溜回家,用父親的衣物在床上拼湊出一個人形,最后和假想的父親握手、擁抱、親吻。死亡與缺失息息相關(guān),而正是在缺失的提醒之中,感情的濃度才得以展現(xiàn)。
面對死亡,我們更加透徹地明白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布魯克林》中的艾麗絲,也是在姐姐去世后回到恩尼斯科西,才更加清楚離鄉(xiāng)的意義,最后作出了決定。《石南花綻放》里的埃蒙,在妻子去世之后,終于明白自己的人生還剩下什么,在小說的最后,他和兒女一起回到卡什,和孫子盡情地嬉戲。《母與子》與《空蕩蕩的家》中的不少短篇也處理了這樣的主題。如《關(guān)鍵所在》中的南希在失去丈夫后才明白生活的重量與變化無常,《著名的藍(lán)雨衣》中的麗薩在舊唱片中聽到死去多年的姐姐的聲音,發(fā)現(xiàn)“她自己老去了,如同她放在樓上的底片,只有輪廓和陰影,讓她清晰地看到錄制歌曲那些天里姐姐的臉。現(xiàn)在,這張CD走到盡頭,她希望再也不用聽了”。《長冬》中的米蓋爾最終在一場狩獵中意識到母親不在了,他看著父親舉槍對準(zhǔn)禿鷹,“朝后靠在馬諾魯身上,吸取他的溫暖,尋找堅實(shí)的安慰”。《一減一》中“我”的母親下葬后,“次日一早我飛回紐約,回到第九十大街和哥倫布大道交匯處的尚未裝修完畢的公寓,一天后開始教課。我明白這些年來我太過拖延”。
《黑水燈塔船》里的海倫,也是在弟弟德克蘭將死時,才慢慢看清楚自己和媽媽、外婆之間的矛盾,并嘗試去解決。在小說中,托賓為德克蘭的死亡賦予了一種妖嬈的美感。“在廚房的昏暗燈光中,他的面容和骨架都很瘦弱,眼睛下方有陰影,下巴還有沒刮掉的黑而模糊的山羊胡,他似乎有種奇異的美,像畫中的人像一樣。”在托賓對死亡的直接描寫中,這算是濃墨重彩的了。但是他的死卻又暗示著一個家庭新生的可能—一家三代終于化解了積聚了十余年的怨恨。在死亡的陰影中,另一個重要的儀式也得以展現(xiàn)—團(tuán)聚。

愛爾蘭文學(xué)中最為著名的家庭團(tuán)聚,或許是喬伊斯的《死者》。這普通的家庭圣誕節(jié)聚會,背后涌動的卻是關(guān)于愛與死、麻木與懷念的暗流。二○○七年布克獎得主恩萊特的《聚會》,也借助一次家族聚會,展現(xiàn)了一段關(guān)乎三代人的愛與死的故事。在托賓的作品中,聚會并不罕見—盡管這聚會常常也伴隨著爭執(zhí)。在《石楠花綻放》里,埃蒙最終和兒女們團(tuán)聚,但他面對的是人生的缺失和紛繁復(fù)雜的愛爾蘭社會形勢。《黑水燈塔船》中的海倫一家終于團(tuán)聚,但是爭吵和死亡也伴隨而來。《大師》中的亨利·詹姆斯和家人團(tuán)聚后,又要面對形單影只的人生。《布魯克林》中的艾麗絲從美國回到愛爾蘭是因?yàn)榻憬闳ナ馈F(tuán)聚的場景永遠(yuǎn)伴隨著缺失,每一次相聚都并不完滿。或許正是缺席的一切,提醒我們“家”是人生旅程上一場流動的饗宴,家中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也正是人生的殘酷本身,我們也總要與這一切和解,就像我們終將要和死亡和解一樣—人生總得繼續(xù)。
在托賓的小說中,“家”的敘事又常常與“愛爾蘭”的敘事糾纏。《石楠花綻放》這個標(biāo)題來自埃蒙的叔叔湯姆在一次家庭圣誕聚會中唱的民歌《巴拉沃》。巴拉沃位于恩尼斯科西,一七九八年,神父約翰·墨菲帶領(lǐng)教眾投入愛爾蘭起義,之后犧牲。民歌的其中一句歌詞就是“一雙反叛之手放飛綻放的石楠花”。愛爾蘭的歷史與家庭聚會重疊,“家”投射成了一個廣闊的空間。這樣的細(xì)節(jié)還有不少。小說中,埃蒙的父親四處搜集珍寶建立博物館,放在二戰(zhàn)的大背景下,這一行為尤具象征意味—面對分裂的世界,為屬于“愛爾蘭”的東西建立一個家,讓愛爾蘭人回到精神家園中。父親中風(fēng)之后,埃蒙積極承擔(dān)起父輩的期望,在競選活動中發(fā)表演講。此舉是為了自己的家,也是為了自己的國家。而這個時間段,《布魯克林》中的艾麗絲正好到美國去又回來了。當(dāng)她生活在異鄉(xiāng),“家”和“愛爾蘭”往往是糾纏在一起出現(xiàn)的。她不僅在兩個“家”之間搖擺,同時也在“愛爾蘭”與“美國”之間搖擺。她最后也作出了自己的決定。“愛爾蘭”在這些作品中作為“家”的延伸存在。
“愛爾蘭”自身的歷史在托賓的敘事中得以展現(xiàn)。托賓很擅長在細(xì)節(jié)與氛圍中悄無聲息地將“歷史”推到前臺,又讓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沖突在“家”這樣的狹窄空間中顯現(xiàn)。在這些作品中,宗教問題常常成為“歷史-現(xiàn)實(shí)”沖突的表征。《黑水燈塔船》和短篇《家中的神父》、《采珠人》都是很好的例子。伊格爾頓在評論《黑水燈塔船》時,敏銳地指出了其中一幕完全是對愛爾蘭之“道德”的宣泄與反諷。在這一幕中,德克蘭的同性戀朋友保羅和他男朋友弗朗索瓦在一個邋遢神父的主持下結(jié)了婚,神父還請他們吃了一頓大餐。這或許是全書最戲劇化的場景之一,宗教與世俗之間的緊張被以一種略帶詼諧的方式展現(xiàn),當(dāng)然一種和解的可能性也因此被引入。宗教與世俗的對立在書中出現(xiàn)過好幾次—比如海倫的媽媽莉莉年輕時差點(diǎn)成為修女,而海倫的奶奶多拉則在假期放縱莉莉,讓她變成了一個調(diào)皮女生,讓修女們的計劃破滅。在這些小說中,托賓并沒像在長篇散文《壞血》中所做的那樣,直接描述發(fā)生在愛爾蘭邊境線上的“新教-天主教”沖突,而是讓歷史遺留的一切在當(dāng)下鮮活的時間中以諷刺的情節(jié)呈現(xiàn)出來。
在他的兩個短篇中沖突的顯現(xiàn)更為激烈。在《母與子》中的《家中的神父》里,神父兒子弗蘭克在年輕時性侵犯小男孩的故事被揭露,他不敢親自告訴母親莫莉,但她知道之后卻表現(xiàn)出了支持。一方面,她想“他們會不會讓他在監(jiān)獄里做彌撒、穿法衣,拿祈禱書”,另一方面,她對著“神情就像個小男孩”的弗蘭克說,“我們會盡力幫你,弗蘭克……只要我們能做的,都會去做,我們誰都不會離開,我會在這里的。”過往與現(xiàn)實(shí)、宗教與世俗沖突不斷,但人物卻在家中獲得了暫時的安寧。在《空蕩蕩的家》中的《采珠人》里,格蘭妮“在她的周報專欄和廣播上爭論教會的地位、民族的靈魂……認(rèn)定她與其他想法相似的普通教徒比主教、神父更能代表真正的天主教會”,但其實(shí)她年輕時曾和神父派屈克·摩爾豪斯發(fā)生過關(guān)系。更為諷刺的是,小說中格蘭妮的雙性戀丈夫也是當(dāng)年“我”的男朋友。最后,“我”只能獨(dú)自漫步在都柏林的街道上,試圖回到自己的家中,小說最后,“我摸了摸口袋看鑰匙在不在,發(fā)現(xiàn)沒有忘了鑰匙,差點(diǎn)就微笑起來”。這兩個頗具悲傷氣息的短篇,矛頭直指愛爾蘭歷史與當(dāng)下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道德/宗教與世俗感情的矛盾,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矛盾。
這一矛盾在《石楠花綻放》中達(dá)到頂點(diǎn)。已為法官的埃蒙作出了懷孕女孩不能繼續(xù)上學(xué)的判決。諷刺的是,他女兒尼亞姆的兒子邁克爾就沒有父親。在小說的結(jié)尾,他還是和邁克爾一起嬉戲。與道德和歷史的一端相對抗的是現(xiàn)實(shí)的繁復(fù),是更為真實(shí)也更為殘酷的愛爾蘭與人生,在這里,一切都糾纏不清,曖昧而模糊。最后,埃蒙選擇了和家人一起,面對自己的生活。
正因?yàn)榧乙馕吨星椋馕吨鴼v史,所以離鄉(xiāng)背井更為艱難。《布魯克林》中的艾麗絲再度回到美國后發(fā)生的事情我們已經(jīng)不得而知,不過短篇小說《一減一》和《空蕩蕩的家》里身處美國的主人公“我”依然想念著愛爾蘭。《一減一》中托賓寫道:“在離開的那些年里,當(dāng)我看到一絲我想要和需要的熟稔時,愛爾蘭就有好幾回以偽裝的面目突然出現(xiàn)在我面前”。《空蕩蕩的家》中,“我每個星期六都去雷耶斯角,為了想家”。離鄉(xiāng)者就像早期基督教文獻(xiàn)The Epistle to Diognatus所描述的那樣,“對他們而言,異鄉(xiāng)都如同故土,而故土則如同他鄉(xiāng)”。同樣作為離鄉(xiāng)者的托賓,除了在這些散文化的短篇中直抒胸臆,還在《大師》中借客居異鄉(xiāng)的美國人亨利·詹姆斯之口說:“我曾經(jīng)寫過青春、美國,現(xiàn)在我只能寫離鄉(xiāng)背井,人到中年,還有令人失望的故事,無論在大洋哪一邊都不會有很多讀者了。”
但是,家實(shí)在太重要。人們還是想要回到家。不管這家意味著溫暖還是爭執(zhí),圓滿還是殘缺,是某條大街上的一個門牌,是一個人們都相互認(rèn)識的小鎮(zhèn),還是歐洲的一個島國。畢竟,家是個終將要回到的地方。而對于托賓來說,家還是個必須書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