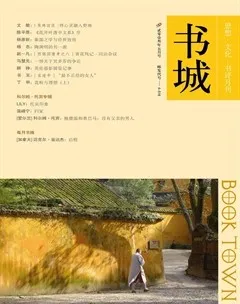舒伯特的“琴之歌”
有詞有曲,撫琴而歌,是為琴歌。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都有傳世名作。樂者口中吟唱,手拂琴弦相伴相和,一人兼唱奏二職,唱為主奏為輔。
歐洲古典音樂中,德語藝術歌曲(Deutsche Kunstlied)是一首或幾首精致的小詩或組詩,經(jīng)作曲家譜寫出音樂,成為歌曲或聲樂套曲。它們不可或缺的部分是鋼琴伴奏,琴音與聲樂聲部合成了完美的音樂形象,因此,藝術歌曲也稱作Klavierlied(鋼琴歌)。
Klavierlied,代表人物是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第一次聽到Klavierlied這個詞,是在維也納巴杜拉-斯柯達(Badura Skoda)大師的鋼琴課上:用手指在琴鍵上吟唱,舒伯特奏鳴曲中美妙的旋律如歌聲一樣從琴鍵中流淌而出,深深沁入心扉,成為我對維也納鋼琴演奏風格和奧地利古典樂派鋼琴音樂的最初印象。此時,我才驚覺好似與生俱來卻又從未意識到的對舒伯特和他的音樂語匯的親近。從那之后,舒伯特的墓地,還有維也納城市公園中舒伯特的雕像,成為清苦的學生生涯中慰藉身心的棲息之地。以至于后來每每在舞臺上演奏舒伯特的音樂時,腦海里浮現(xiàn)的就是和二三友人在舒伯特像前流連或點燃一支紀念蠟燭的情景。Klavierlied,舒伯特,當然還有那些踏著圓舞曲節(jié)拍、拉著游人走在環(huán)城大道上的馬兒們,一起構成了我一生揮之不去的維也納情結。
一九九七年,時值紀念舒伯特誕生二百周年,我在北京舉行了舒伯特鋼琴音樂作品的專場音樂會,這個相當“學院派”的動作在上世紀末的中國,頗有些“曲高和寡”的尷尬,而我仍然固執(zhí)地堅持以我的方式向這位生前并不起眼的天才大師,以及他生長于斯的那座神奇的城市—維也納致敬。值得欣慰的是,這場音樂會得到了文化界、音樂界前輩和同行以及朋友們熱情的鼓勵,舒伯特的音樂當然也贏得了北京聽眾的傾心。
在那以后,我演奏舒伯特的音樂,教授學生們學習舒伯特的音樂,舒伯特藝術歌曲和聲樂套曲中所描繪的場景和情節(jié)不知不覺中融化進他那些并沒有文學標題的鋼琴作品,他的音樂在我和學生們的心中生根發(fā)芽進而枝葉繁茂。這個過程長嗎?十幾年,其實“彈指一揮間”。
舒伯特頭戴“歌曲之王”的桂冠,他的歌曲大多精致雋雅,然而,舒伯特的器樂作品卻更加體現(xiàn)了他的博大與寬厚,其中的深沉與宏偉,需要人們運用領悟詩歌意境的感受力去體驗,同時又斷然拒絕感官的震撼。這對為尋求娛樂而走進音樂廳的蕓蕓眾生未免苛刻,也許這就是他的大部分無詞音樂被敬而遠之的原因。
不論如何,以鋼琴吟唱舒伯特的音樂,在琴鍵上演奏出如歌般動人的旋律,以真摯的情感觸動聽眾的心靈,是鋼琴家們的理想和追求,這也是這張專輯最初的動因,也是專輯名—“琴之歌”的由來。
舒伯特一生作有約千余部作品,其中六百余首是歌曲,其余四百多部作品涉及歌劇、交響樂、室內(nèi)樂、器樂獨奏,而鋼琴作品占了很大的數(shù)量,更有多部鋼琴作品堪稱人類文化史上的頂級藝術瑰寶。一部專輯實在無法展現(xiàn)這位大師的音樂全貌,我僅選錄了三首(組)作品,祈愿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一窺大師風格。
首先是《格拉茨幻想曲》,一九六九年,這部奇妙的作品在奧地利工業(yè)重鎮(zhèn)格拉茨被發(fā)現(xiàn),同年即由騎熊者出版社首次出版,并冠以“格拉茨幻想曲”之名。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文革”的狂熱之中,無暇顧及藝術殿堂上如此驚人的發(fā)現(xiàn)。這部幻想曲背后的故事頗為曲折:在舒伯特最親密的朋友圈子里,可稱為摯友的幾位中有一雙姓胡騰布倫納的兄弟,兄長名為安塞姆,是一位作曲家,長舒伯特三歲,與舒伯特相識于一八一五年,當時他們同為著名作曲家、維也納宮廷樂長安東尼奧·薩列里(Antonio Salieri,就是那位在奧斯卡大獎電影《上帝的寵兒》中被描寫成因妒忌而毒殺莫扎特的當紅宮廷樂長)的學生。兩位作曲家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一件事可資證明:一八一七年,在安塞姆的《E大調(diào)弦樂四重奏》付梓出版之前,舒伯特就以這部四重奏的第三樂章主題創(chuàng)作了一首變奏曲《Anselm Huttenbrenner主題的十三個變奏》(作品編號D.576),值得重視的是,這是舒伯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使用他人的音樂主題創(chuàng)作。此后,舒伯特又結識了安塞姆后來成為律師的弟弟約瑟夫。胡騰布倫納兄弟資助著舒伯特的生活和藝術活動,也很自然地擁有并保存了部分舒伯特作品的抄本甚或手稿。
舒伯特的一些作品手稿,由于某些原因沒能得到很好的保存,比如兩首詼諧曲,而《格拉茨幻想曲》的手稿原稿當時也被遺失,這首作品因而也就不為人知。直到一九六九年,一份手抄本在格拉茨的一位作曲家、教堂合唱隊指揮魯?shù)婪颉ゑT·魏斯-歐斯特博爾恩(Rudolf von WeisOstborn)的舊居老屋中被發(fā)現(xiàn)。手抄本的主人并非魏斯,而是他的親戚約瑟夫·胡騰布倫納。這個手抄本上沒有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標題頁的字跡是約瑟夫的筆跡:“幻想曲/為鋼琴而作/作曲/弗朗茨·舒伯特。”樂譜抄寫的筆跡則是另外一個人的。在標題頁上,還有一位借閱人愛德華·皮爾科特的簽名,這人是胡騰布倫納家社交圈中人。同頁上還有另一鉛筆筆跡寫道:“原稿我借給皮爾科特教授了。”
看一下這個人物鏈:舒伯特→朋友約瑟夫·胡騰布倫納→親戚魏斯。是否還可以假設,約瑟夫(或其他人)曾把幻想曲的原稿借予皮爾科特教授,皮教授不知什么原因還回的卻是手抄本;約瑟夫為手抄本題寫了標題,最后手抄本來到了魏斯家中。這個假設仍然有漏洞,如果皮教授還回的是手抄本,為何皮教授的借閱簽名會在標題頁上?而且也無法證實此中所說的“原稿”即是舒伯特的親筆原稿。
說起來,這部作品屬于舒伯特的直接證據(jù)僅僅是約瑟夫筆跡題寫的標題。所以,它的真實性并非毫無爭議。這部幻想曲近乎推理小說的考古過程固然吸引我,但是作品音樂本身更讓我驚訝:樂曲的引子是一段恬靜優(yōu)美的旋律,左手采用了典型的“夜曲式”伴奏織體,這之后的舞蹈主題更直接標明alla Polacca(波蘭舞曲),我曾為一位極聰明淵博的專業(yè)朋友演奏此曲的引子部分,并開玩笑地請他猜猜作者,他緊鎖眉頭體味再三才猶疑地回答:“非常像肖邦,可是怎么帶著舒伯特的味道?”完整地聆聽過這部幻想曲后,我們確實會驚訝于它和肖邦《安靜的行板與大波蘭舞曲》作品2號有一種同胞兄弟般的相像。這是兩位大師“英雄所見”的巧合,還是肖邦在冥冥中受到這遺失音樂的啟發(fā)?一九九七年,我在中國首演了這部《格拉茨幻想曲》,距它在格拉茨被發(fā)現(xiàn)已過去二十八年。

第二個角度是一組蘭德勒舞曲,共十七首。我鐘愛舒伯特的音樂,還因為他的音樂中體現(xiàn)出濃郁的奧地利民族風情:在樂聲里我能看到奧國山民獨特的民族服裝,看到馬車在街道上穿行—著名的圓舞曲在城市公園里奏響、空氣中飄浮著咖啡的香氣—維也納森林路邊的小酒肆售賣著甘甜的當年釀葡萄酒,也許還有聞名世界的炸豬排和巧克力蛋糕—當然在樂聲里更能聽到奧地利民間歌手唱出的約德爾山歌。畢竟舒伯特是地道的維也納人,維也納的一點一滴都融化在他的血液中,然后隨著他的音樂流淌而來。蘭德勒應該算是最地道的奧地利民間舞蹈形式,選擇這一組舞曲,為的是略微展示舒伯特音樂創(chuàng)作的民族根源。
所謂蘭德勒舞(L?ndler),是一種3/4拍子的民間舞蹈,十八世紀末流行于奧地利、南部德國以及瑞士德語區(qū)的鄉(xiāng)間。這種舞蹈特點鮮明,一對對男女舞伴舞蹈中不時間以跺腳的動作。舞蹈音樂以樂器伴奏,有時也加入人聲,山區(qū)的約德爾山歌調(diào)往往會和蘭德勒音樂融為一體(人們最熟悉的約德爾山歌當屬電影《音樂之聲》中的著名唱段“孤獨的牧羊人”)。十九世紀,人們?nèi)ノ鑿d如同現(xiàn)在年輕人泡吧一樣時尚,蘭德勒舞也開始變得優(yōu)雅,男人們脫去過去跳舞時穿的帶有鞋釘?shù)呐郎狡ぱィ璨揭哺虞p快。今天的音樂學者們通常認同這個觀點,即蘭德勒混合了德國及波希米亞地區(qū)的一干種類的舞蹈,成為圓舞曲的起源。我在維也納學習的女兒更是斷言:“在村里鄉(xiāng)間那叫蘭德勒,進了城,起個宮廷官名就叫圓舞曲。”
十七首蘭德勒舞曲并非舒伯特此種舞曲的全部,只是選自編號D.145(或作品18號),去掉了這組作品中的十二首圓舞曲及九首埃科塞茲舞曲(Ecossaise)。樂譜如同早期的巴赫版本,未標出任何速度和表情記號,這與舒伯特其他作品通常的做法并不相同,但音樂本身卻神奇地引導我自然地選擇了不同的速度和情緒來演奏。這十七首短小的舞曲每首都只有分為兩段的十六小節(jié)音樂,可以無限反復演奏。當年巴杜拉-斯柯達大師甚至為我選擇了兩首組合在一起作為音樂會的加演曲目,并起了個好聽的名字—“云雀圓舞曲”。
專輯最大的篇幅是《降B大調(diào)奏鳴曲D.960》, 全曲共四個樂章,是一部規(guī)模宏大的巨作。一八二八年,舒伯特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這一年他的身體日漸羸弱,而創(chuàng)作力卻格外旺盛,《f小調(diào)幻想曲D.940》、《三首鋼琴曲D.946》、《彌撒D.950,弦樂五重奏D.956》相繼問世,同時結集出版了最后的藝術歌曲集《天鵝之歌》。最不尋常的是他的最后三首鋼琴奏鳴曲《c小調(diào)D.958》、《 A大調(diào)D.959》和《降B大調(diào)D.960》,這三部作品的非比尋常之處除了作品非凡的藝術價值,還有那一胎三胞式的創(chuàng)作方式。通過保存下來的手稿,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三首奏鳴曲是怎樣誕生的,舒伯特的寫作草稿清晰地顯示了這個過程。樂章草稿寫作于一八二八年春夏之際(它們的構思顯然開始得更早),奏鳴曲樂章在草稿上只寫到展開部的開始部分以及結尾。一些分屬不同樂章甚至不同奏鳴曲的樂段有時會出現(xiàn)在同一張草稿紙上,這可以證明這幾部奏鳴曲的寫作是(或者至少部分是)同時平行展開的。還有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草稿顯示,《降B大調(diào)奏鳴曲》的終曲樂章先于第一樂章完成,這不是作曲家通常按順序寫作的習慣做法。一八二八年九月,奏鳴曲完稿,每一部奏鳴曲都具有了完整的套曲形象,它們被分別標示成奏鳴曲I、II、III, 在第三首奏鳴曲末頁底部舒伯特寫下了日期九月二十六日。謄清的完稿與草稿相比較除了整齊清晰得多之外,還有了更準確的表情標記,草稿中空缺的部分也都補充完整了。
一八二八年舒伯特的創(chuàng)作中含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和箴言式的含義,他的藝術歌曲集以寓意絕唱的“天鵝之歌”命名,被巴杜拉-斯柯達大師稱為“具有舒伯特鋼琴音樂的皇冠聲譽的”D.960第二樂章中緩慢的行板,更使人心碎地體味著挽歌的悲傷。《降B大調(diào)奏鳴曲D.960》給世界留下了如此美麗的慢樂章,音響中彌漫著虛幻的畫面,似乎是步履滯澀的葬禮隊伍q344DmldnfQ9B32T/Z5PKA==,小調(diào)的悲哀就像愈合不了的傷口隱隱作痛,樂章中段的A大調(diào)非但沒有帶來明亮的歡樂,哀傷反而更加滲入靈魂深處,使人聯(lián)想起他那首著名的《菩提樹》的詩句,“樹葉輕輕地顫動,好像在呼喚:小伙子,到我這里來,這里有你渴望的寧靜”。也許舒伯特真應該像他仰慕的前輩貝多芬在最后的《鋼琴奏鳴曲作品111》所做的那樣,也在第二樂章作完美的結束,可是不!舒伯特還要和他的桑梓故人作最后的告別,他就像一位偶然進入我們世界的外星過客,短暫的逗留之后,要留下最后的紀念,在終曲樂章里,他在說:
別了,歡樂幸福的城。
別了!馬蹄已經(jīng)愉快地踏響,
我最后一次向你道別。
我的悲傷你從未見過,
告別時我們也不要讓悲傷發(fā)生。
別了,歡樂幸福的城。
“告別”—天鵝之歌(雷爾施塔原詩)
正義倫理與價值秩序:古典實踐哲學的思路
鄧安慶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版
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關涉到其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理想和目的,因而必須在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中落實成為共同遵循的實踐原則,所以它不應該單純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導向,而應該成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動規(guī)范。核心價值的這種約束力不能單靠國家法律的強制性和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來取得,而是源自于國家、社會和公民之間真正的內(nèi)心認同。從何處獲得這種價值認同呢?本書作者從古典實踐哲學的典范分析中,認為只能從對國家政體的認同出發(fā)才是可行的。因為國家政體是一切實際有效規(guī)范的來源。如果我們能認同我們的共和國體,其創(chuàng)始的原則所蘊含的核心價值,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尋求的價值共識的基礎。